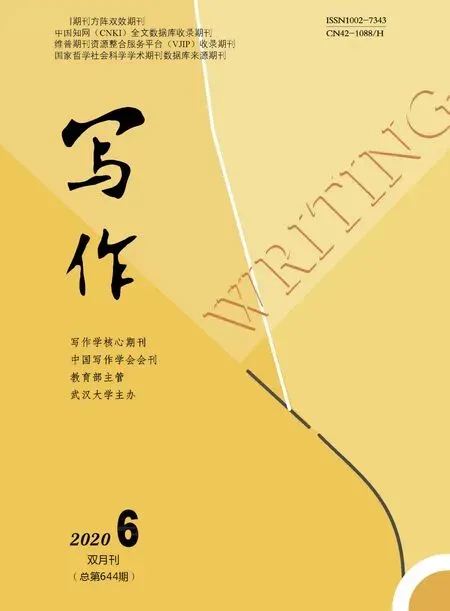山河人間與我
——武漢大學駐校作家啟動儀式上的演講※
李修文
今天跟各位的分享談不上是一場學術演講,只是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的寫作一直困難重重。從20 多歲開始專業創作以來,我幾度擱筆,中斷文學生涯。但是,我如今能夠重新成為一個作家、一名寫作者,其中的確蘊藏了自己的很多困頓和對這些困頓的克服。
一、山河人間使我更加“充實”
先從今年的疫情開始說起。 疫情中,我和文坤斗書記要下社區,為中國作協安排到武漢來的作家們服務。很奇怪,走在寬闊、空寂,過去那么熟悉、如今又判若兩地的場景里,我并沒有產生一種直接書寫疫情的愿望。 但與此同時,我想起自己在中國古典詩詞里所讀到過的許多諸如杜甫、羅隱等大詩人。 這些唐朝中晚期大歷年間的詩人在那個瘟疫頻發、戰亂頻仍的時代所創作的詩歌,也一下子出現在我的腦海。
我一直有個創作規劃,想寫一本關于中國古典詩詞的書。 這當然算不上什么研究。 中國古詩詞在相當程度上是我們每個人的出處和來歷,是我們文化身份的另一種證明。 但很久以來,我覺得詩詞研究更多是從學理、字詞、境界和意境等角度的解讀。 大部分的中國人,無論走到哪里、無論什么時候、無論在怎樣的心境下,總有那么一首詩、一句話在等著我們,來見證我們的困頓、狂喜、卑微與自我和解。特別是在疫情中,當我們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底線開始浮現出來,成為我們日常行為的時候,我覺得許許多多的詩詞在我的身上和記憶里重新復活,于是我開始動手來寫這本書。 這樣的創作念頭其實產生很早,之前我以為自己寫這本書會用非常漫長的時間,但在疫情中我很快就把它寫完了。我總覺得,對于這樣一種強烈的介入、一種見證了我們人生的文學形式,應當有一種相遇般的解讀,把它重點放在人與詩歌的相遇上。所以,這本書的名字叫《詩來見我》,即詩來見證和映照我的人生,說明自己如何與那些詩人和經典的場景相遇。
我本來準備寫中國古代歷史上隱藏在章回體小說里的“有詩為證”,準備研究躲藏在戲曲里的那些中國古典詩歌,也準備去研究禪詩、僧詩。但疫情以來,人生中許許多多的基本詞匯都浮現在我的生命之中:比如,我很久沒有看見母親;比如,朋友寄來口罩,我很想念他;比如,我們在外面奔走的許多時候,都有一個自己說服自己、自己平息自己內心沖突的問題。 這不禁讓我想到唐代詩人里我很推崇的韋應物。 韋應物一生中充滿內心的自我斗爭,但最終找到了一條安妥自己、說服自己的道路。至少,他的詩歌呈現出了這樣一種情境。我還想到與自己終身不能和解、一輩子都沖突劇烈的羅隱。 在我個人的心中,羅隱是一個可以和明朝唐伯虎并稱的詩人。 他們都是當時在整體的語言體系里改造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人。
在中國古典詩歌里,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嘗試白話入詩的“白話高峰”,分別是杜甫和唐伯虎。 在杜甫誕生以前,很多材料無法寫進詩歌。 杜甫之所以如此偉大,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以詩歌給萬物重新命名。我們許多無法歸納、總結的一些基本感受,在杜甫之后才真正進入詩歌。比如在他之后的羅隱,寫出“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自遣》)等等。這些如今看來的大白話實際在唐朝就已經入詩。他的命運和遭際把他送往那里,類似地還包括唐伯虎。 他們絕對不是無心插柳,而是真正地有意為之。 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詩歌的奇跡,也不禁讓我想起這兩個人的命運。 羅隱十次科舉不第,長期流落江湖,長期需要說服自己,也需要說服自己與這個世界和平相處。 唐伯虎更是如此。 他很年輕的時候介入“徐經科考案”(徐經之孫是著名的徐霞客),并受此牽連,就此墮入一個他根本無法想象的境地。 除此之外,他的妻子、女兒、父母和帶他長大的人在五年之間全部死亡。在極短的時間內,死亡以一種非常密集的方式改正、改造和改變了他的人生。 我們通常認為唐伯虎的詩歌明心見性、淺白如溪,但我覺得在當時的寫作倫理中,能夠建立起這樣一座高峰是非常罕見的。 之所以講到他們,是因為我在疫情中的遭際促使一些最關鍵和最基本的詞匯重新進入我的記憶和想要描摹的對象。 所以,我很快地寫完了這本書。它也在某種程度上部分觸及了我今天與大家交流的題目,即《山河人間與我》。
我的寫作就是被山河人間所改造過的;我的寫作就是廣闊無邊的山河人間。它幫我在每一次寫作充滿困難的時刻重新選擇了字詞。 從某種程度上講,我今天能夠重新寫作,依靠的正是如朱熹所說的“充實”,“充”就是擴大生活的邊界;“實”就是盡可能把自己要寫下的所有字詞落實為自己的命運。 所以我特別希望,凡是我所寫下的,都盡可能映照出自身命運的一部分。 但這個東西它淵源何在? 而我又何以至此呢?
二、捍衛有“我”的寫作與傳統
20 多歲,我在《收獲》上連發兩部長篇小說。 那是一種完全依靠某種想象力和審美力來推動的寫作。 從寫作以來,我就處理著一個非常艱難的問題,即我和古典傳統之間的關系。 所以,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實際上是創作了一大批中國古典的戲仿、小說和戲曲等一些所謂“互文性”的文本。 它們出自某種莫名其妙的憤怒以及某種零度敘事的誘惑,但我很快就覺得不太滿足。
我從小受戲曲影響巨大,在愛上文學以前就愛上了戲曲。這樣的一種文化出身使我經由戲曲的引導一步一步地走向文學本身。 在這樣一種影響和20 世紀90 年代初期中國先鋒派文學甚囂塵上的背景之下,我寫了一堆在那個年代看起來充滿了憤怒、充滿了不平靜的作品。 但它們其實無根無基、其來無自。所以,我當時就想自己能不能盡可能通過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中國小說的某種話本、傳奇和說書人的傳統。 事實上我也這么做了,就連寫了兩部長篇小說。 但我很快就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身處那樣一個年代,我所依靠的古典價值和古典美學在快速行進的幾十年里,不斷分崩離析、遭受粉碎。而我在自說自話,妄圖用一套我從中國古典傳統里所得到的美學浸染,強行地歸納我眼前看見的事實。所以,我很快就產生了某種身與心的背離。與此同時,我用第一人稱以一個垂死者的口吻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捆綁上天堂》。寫作者的悲劇往往在此,一個寫作者內心里的驚濤駭浪往往不足為外人道。
在寫作《捆綁上天堂》時,我常年以第一人稱模擬自己是一個垂死者。 半年過后,我覺得自己的創作和生命力都受到了巨大摧殘,感覺自己因為入戲太深,已經寫不下去。后來我選擇去做影視,除了因為我的創作一開始就和戲曲密切相關, 還因為我的寫作里一直有這樣一個自始至終都在影響我的淵源。于是,我經過了心如死灰、浪跡江湖、形跡可疑的十年時間。因為要活下去,一個專業作家的身份認知使我無日不感到羞愧,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寫不出作品的專業作家。 在相當程度上,我已經完全不相信自己還能成為作家。 其后,有的批評家講《山河袈裟》有一些抒情過度,我承認這一批評。因為在寫《山河袈裟》的時候,我有一種對自己巨大的、熱烈的歡迎,即我能夠重新成為一個作家了。別人可能會覺得我在大驚小怪,但對我而言,這宛如一次“借尸還魂”。我感覺自己活在一種巨大的幸運之中。
可我重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演講的題目《山河人間與我》。 它換個稍微學術或者理論一點的名字叫作《我們一定要有勇氣和能力捍衛一個正當的文學生活》,或者《相對純正的文學生活》。如今人們都不太討論這樣的一個話題。實際上,經過這么多年的創作歷程,我覺得,無時無刻地捍衛某種有可能使自己恢復活力和創造力的文學生活,是作家終生都要打的一場仗。在寫不出作品的這十年里,我流蕩在中國的一個又一個小劇組里。 在十八大以前的十年里,幾乎每一個劇組都是草臺班子。好不容易投入一個項目去做,不是老板被抓,就是項目沒了。但因為我比較擅長去寫作或參與一些歷史劇、軍事劇和民國劇,所以我這十年幾乎每天都游蕩在祖國的各處窮鄉僻壤。那么毫無疑問,“山河人間”經過我這一己之身,得到了落實。我生活的邊界通過我的遭際,變得越來越寬闊。寬闊在何處?主要有兩點。第一點,我重新確立了一個新的自我;第二點,我和廣大人間那么多名目、那么多風暴、那么多無名無姓的人的一種遭遇和相逢。 在和他們的相逢中,在那種不如和他們滴血認親的愿望以及行徑中,我覺得一個新的自我可能得以產生。 比如,他們都極大地啟發了我的寫作。
我經常跟同道們分享一個我自己的真實遭遇。有一年,在陜西榆林,我遇見過一個盲人。這個盲人跟我一起趕路的時候,我發現他非常快樂,而我非常苦楚。 頭上暴風暴雨,我寸步難行,但這個盲人引吭高歌。我問他為什么,他說自己現在并不是跟我走在一起;我問他走在哪里,他說自己現在走在北京長安街。 通過他的描述,我意識到,中國或者全世界有很多盲人為了對付這一生一世的不堪和苦楚,早就已經在頭腦中給自己虛擬了一個世界。也就是說,他既活在與我們同在的世界里,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其實有很多盲人最后死于精神分裂,死于兩個世界對他的拉扯。 在相當程度上來講,我們的世界是假的,他為了度過他的一生所給自己創造的世界才是真實的。所以,我后來寫了《三過榆林》。 這篇文章是我個人寫作歷程的一個分水嶺,對我十分重要。 其后,很多文章都受它影響,比如《致江東父老》中的《白楊樹下》。 《三過榆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給了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即決心徹底拋棄既有的“散文”概念,重新恢復到在中國有很深淵源的、橫亙了上千年的文章傳統。 在文章傳統里,沒有新聞意義的真實,沒有今天“散文”概念所給出來的那些答案。 它虛實不分,上天入地。 只有躲藏其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我”,才能為這個世界提供出一個作家所能提供出的最大真實,即美學的真實。
如今,非虛構寫作是一門顯學,也是創意寫作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年,為了給缺乏現實關照的中國當代文學,填補一些非常堅硬的東西,倡導一種直面現實的態度,我們發明了“非虛構”的概念。 但是,我個人從頭到尾都認為“非虛構”的邊界實際上非常可疑,比如“非虛構”所要求的真實。對于剛才談到的盲人,怎么去歸納他身上的真實呢? 在人們看起來,他頭腦中虛擬的世界一定不真實,但對他而言,難道不是他觀照自己人生并見證自己人生的一個最大的真實嗎? 當然,蒙田也早就有名言,叫作“強勁的想象產生事實”(蒙田《論想象的力量》)。 我是在這樣一個人身上,在一個真正的同心者、同路者身上,發現了強勁的想象產生的事實。 這種事實竟然就成為映照他一生、扶持他一生的一座圣殿。他日日要叩拜,但又是他的日常生活,所以他帶給我非常大的震撼。進而,我想起我們生活的這片荊楚大地,尤其是從小生活的江漢平原。 這里過去常常巫風大作,我小時候沒怎么住院,只要一生病,基本就是靠做法事。 我覺得我無數次看見過一個歸來的亡者。 我小時候上學路過一個老太太家的時候,老太太總是非常認真地跟我講,昨天他的兒子回來給她的水缸里挑滿了多少水,又給她買了多少米,早上吃完飯已經愉快地走了……但實際上人人都知道,她的兒子已死去多年。
同樣的境況,在蒲松齡的小說里有《王六郎》的故事,在唐宋傳奇里也可以讀到大量這樣的故事。這就不得不使我自己重新思考一個問題,即這么多年以來,固然社會不斷獲得巨大進步,但當來分析我們的文學,或者分析一些具體的文本時,我們是不是往往更加地從社會學意義側重將文學視為整個社會進程的一面鏡子或一個證據。 可是在中國人的美學里,無論是在四大名著,還是在傳統的中國古典價值里,躲藏的那一聲中國文學最深重的嘆息,或者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我們的抒情傳統,它就不存在了嗎?它在今天這樣一種日新月異的社會進程中,是不是在做著最后的搏斗?或者說中國人之所以身為中國人的那些東西,是不是在進行著最后的申訴? 要知道,我們中國的小說傳統有個非常重大的淵源,即司馬遷的《史記》。正所謂“異人異事”,“異”表達的就是生命力的象征。某種程度上中國的小說自從其誕生,就一直在為中國人的生命力作證。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走這樣一條道路,即經由魯迅先生的改造,我們中國人的精神行進在一個通往現代性的歷程之中。 有一個歐洲哲學家講“可能美國會有一個完成了的現代性, 歐洲出于歷史的負擔一直有一個正在行進的現代性,而中國的現代性,可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維度里,處于一個持續行進的進程中”。
我說一點閑話:為什么我和寧浩導演合作《瘋狂的外星人》? 其實合作的時候,我們的創作實例一直都是魯迅先生的作品,沒有其他電影作品。 可能有點狂妄地說,我們一直在魯迅先生改造民族性的進程中,并以這樣的維度來觀照、指導我們的作品。也就是說,在全球充滿了一種地球英雄對抗外星災難的敘事中,我們中國人對抗的武器和方式到底是什么?是那種直接地像古希臘英雄式的或者西西弗斯式的斗爭嗎?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想要征服地球而來的外星人迷失在中國人的同化里?迷失在中國無邊無際的酒局中?有沒有可能我們在地球上作為人所遭遇的日常生活障礙,對它而言也是如此? 正是基于此,我們開始創作《瘋狂的外星人》。 但在創作作品中,我們又遇到一個難題,即某種所謂的“作者性”很難在現代化的電影工業展開之時得到維護,日常工作進程很難準確地落實創作者的抱負。 跟我合作的導演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無法捍衛他的抱負。 這和我今天講的主題也有關系。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在這樣一套進程中,我如何捍衛自己作為一個有“我”的寫作者?和以前的時代不同,我們每個人過去都可以完整地參與一場勞作,并且在一整場的勞作里產生某種神圣感和崇高感,但如今這個世界成為一個碎片化的社會:我們每個人卻被限制在一個格子間、限制在自己的領域,每個人都懷揣著各種各樣的個性靠近彼此,但最終又成為一個蒼白的集體。所以在我看來,如何建立一個今天的“新我”,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說,不管在寫作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捍衛有“我”的寫作,要重新確立一個新的自我。
李敬澤老師是對我啟發很大的一位作家。 他前年出版了一本我逢人就會推薦的書, 叫《會飲記》。從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人,雖然身處同一場域,卻時而要在會場致辭,時而要狼狽地尋找廁所,時而思考書記員在想什么,時而想著德里達等思想家;他一會兒在咸陽機場吃牛肉面,一會兒又在一個北京郊外的山頂上“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如此分裂的一個“我”竟又如此緊密地凝聚在一具肉身之上。這就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即我們的身體和心理當此之際其實成為今天生活中的一座客廳,一臺處理器,乃至一個戰場。我們每天吞吐著那么巨大的信息量,又靜悄悄地潛伏,潛伏了那么多這時代里新的無奈和苦難。 但這一幕我又覺得并不新鮮,因為它同時回應著我們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即有“我”的傳統。
在我個人看來,很多時候其實不像文學史經常總結出來的,認為某個年代出了多少個代表性作家,比如中國古典文學里的“建安七子”或“大歷十才子”這樣的命名。實際上,我經常感動的是:中國古代文人在面向虛空或不存在事物之時往往都有一種對自己的確認, 在大部分時候靠一己之力完成了他自己。 換言之,一個時代的變化并不明顯、普遍,不是井噴式的,那么多文人或大師其實是在靠一己之力、靠自身的遭際,在巨大的孤絕當中完成了他自己。前面提到的羅隱和唐伯虎就是如此。在最近剛剛寫完的《詩來見我》中,我梳理了一批詩詞,覺得這么多詩人所接受的這些經歷,不斷地安慰我,不斷地說服我,也帶給了我今時今日的力量。
三、“我”要發出中國人的聲音
所以,我想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寫作者? 我覺得要勇敢地講今天的中國,有勇氣成為一個可以提出中國問題,處理中國問題,描摹中國式的面孔、情感和倫理的作家。今時今日,當一個新的、巨大的主體性誕生后,我們置身于一個偉大傳統之中。但就像艾略特曾經講過的那樣:“傳統從來就不在我們的過去,是因為我們的加入,傳統又悄悄往前挪動了一步。”所以我們一直在這樣的一種情感和遭際中。還是以我個人的遭際舉例。在影視界,我曾簽約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公司,叫“小馬奔騰”。這個公司過去是中國前幾名的、非常有創造力的公司。但隨著老板去世,這個公司已經風流云散。公司垮了后,我無數次路過當年云集那么多座上賓的會所,又眼睜睜地看著它成為別人的新會所。 當我路過它的時候, 我經常會想起一些中國文學里最深刻的一聲聲嘆息:“樹倒猢猻散”“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可是當它跟我的生命、我的朝氣結合在一起,我就想,在前幾十年整個中國所紛繁、復雜、快速、凌厲邁入的一種進程中,其實一直存在和流淌著中國文學里最深重的一聲嘆息。我們今天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重新呼應這偉大的傳統的寫作者?寫出一部發出那樣一聲嘆息,并讓活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人們感同身受的作品?
事實上,日本作家中島敦的《山月記》是處理中國古典題材的一個好例子。這本小說涉及唐宋傳奇里一個非常有名的傳奇,即一個進京趕考的書生和朋友兩個人如何在山路上斗野獸的故事。但在中島敦的筆下,這個故事改造成了這樣:有兩個好友進京趕考,一個高中、一個落第。 高中的人也沒做多大的官兒,去一個小地方上任,宦海沉浮十年后并沒有多大的長進。 有一天,他經過一條山路,遇到一只要吃他的猛虎。 他躲避猛虎時,猛虎突然開口,說自己其實就是當年和他一起進京趕考的同伴。 同伴如愿高中,而自己則被自己內心巨大的憤懣、怨恨和怒氣所改造。 有一天晚上,當自己住在一個小旅館的時候,狂風暴雨中聽見遙遠的山崗上有一頭猛虎在呼喚,于是自己再也控制不住內心里的猛虎,狂奔出去。 在風雨里不斷地攀援時,毛發和器官都發生改變,最終成了一只猛虎。 這個小說非常動人,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日本版或中國版的“少年派”。 我最近剛開始寫的小說受此啟發。我之所以舉小說的例子,是因為我希望在未來的工作中,跟有志于搞創作的朋友,可以就分享類似的實例,講出我的創作因何而起、何以至此,這樣可能更加有效和具體。
雖然我現在的主要精力在創作小說,但明年也會在幾個雜志上開散文專欄。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想把它作為我這一階段散文創作的終結。 在《山河袈裟》里,我講了一個人和一個世界的重新相遇;在《致江東父老》里,我講了那些不置可否、那些贊美的對面、那些人的復雜性。 我想重新在散文形式上,真正地做一些個人意義上的掘進。 比如,把小說、戲曲、詩歌,甚至電影、書信和說書人的傳統引進到今天的散文中,并以此來表達更加復雜的際遇以及生長在這種復雜際遇里的一些心靈。
這么多年“落魄江湖載酒行”的生涯,讓我遭遇到了大量的中國式面貌,所以現在我又想重新給自己一個目標,就是把這些典型的中國人寫出來。 這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但是如果我要通過寫作坐實自己一生的命運,那么我認為自己和他們之間有盟約,畢竟我曾經歷過這樣的時刻。 比如在甘肅雅丹地貌的一個戈壁灘里,我碰到很多鋪路工。他們常年看不到植物。在被風蝕過的、可以避風的地方,這些鋪路工給自己種了一棵小樹,然后每天要帶我去看那棵小樹。 與此相似的是我們去內蒙古草原的經歷。我們一去就看到花花綠綠的、很殘缺的畫報。一兩張紙被他們剪貼在一起,成為一個畫報冊子,然后他會把這個破爛的小冊子丟給我。一開始我不理解,后來才明白,這就相當于我們去別人家,別人沒有什么招待我的,只能請我看電視。實際上,他覺得把從草原上撿起來的很多碎屑集合在一起,相當于給我提供了某種外來世界的信息。
除此之外,我還碰見過許多其他活在苦楚、不堪之中的人們。 實際上,只要走進他們,就會覺得人人的體內都有暴風、暴雪,有真正的、最純粹的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一種聲音。我要通過自己的寫作不斷地靠近、觸摸和追尋這種聲音。雖然我今天是個充滿困惑的作家,但我在相當漫長的時間里,會堅決地追尋這種無論處在任何時代,只有中國人自己能夠發出的聲音!
附:李修文答學生問
提問1:老師您好,我是文學院的一名本科新生。 剛剛在您的演講當中,我能感受到,您有一個非常浩瀚的內心世界,我想請問您,您是如何理解一位法國女作家杜拉斯說過的一句話:只有天才才會真正照亮自己的內心世界,只有瘋子才會徹底地寫作。
李修文:某種程度上我肯定是個瘋子,所以我剛才一開始就在講,自我和解以及對自我沖突的某種克服,可能是很多作家一生當中最重要的東西。但是你說的“瘋子”,我覺得有兩個概念,不瘋魔不成活,我剛才講我是一個入戲甚深的人,如果我入戲不那么深,我不會寫完這樣一個小說之后,每天都懷疑自己。 當時我還不了解什么叫抑郁癥,今天我深信我當時肯定是有病,并且莫名其妙的就把它給克服了。 所以,一個作家肯定有極其瘋狂的時刻,這與我們的熱愛以及對于熱愛要履行的責任有關系。但是,我們也不能拿一個日常生活當中的瘋子,來衡量我們寫作時候的瘋狂。至于一個作家一生當中能不能做天才,能不能被天才照亮,那個是其次的。不過,如果我們一生當中缺乏這種瘋狂的時刻,我覺得還蠻可疑的。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要捍衛我們創作當中的一些瘋狂時刻,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幸福。
提問2:修文老師您好,我也是2020 級的新生。 剛才您說到,寫作的時候,我們要回歸中國的散文或者小說傳統,我想問一下能不能具體地展開,中國的小說和散文有什么樣的傳統? 我們在自己平時的練習或者構思上面,要怎么樣去做到能夠更加的接近中國的小說和散文傳統?
李修文:我覺得很難用一兩句話把中國小說、散文傳統進行歸納和總結,就像我剛才講,《史記》所開啟的小說傳統,它是為人的存在、為生命力作證的,這個可能非常重要,它講述了生命力的蓬勃,也講述了生命力的被限制。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的小說要為我們如何地存在于世來作證。中國的散文,如你所知,“散文”這個概念很晚才進入到中國,具體的我說不清楚,到現在大概有90 多年了。周作人是第一個把散文的概念引進到中國來的,但某種程度上“散文”也是我們中國偉大的文章傳統當中的一個部分。有可能是學科分得太細了,現在“散文”好像漸漸的代替了中國的“文章”這樣一個稱謂。 至于如何去繼承,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繼承中國文學傳統里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它的冒犯、破壞和重新建構,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充滿了冒犯的世界,有很多現在被我們視為傳統的東西都是過去產生了最強勁的冒犯的一個產物。 我就拿戲曲做個例子,像《天女散花》這樣的大夢一場,完全不同于西方分幕敘述的戲劇的路徑,這種表現形式,西方現代戲劇簡直無法想象。很多的時候,我們的戲曲創作依靠著文學當中的那種情境,所以中國的戲劇和文學的距離特別的親近,我感覺這似乎是我們可以通向的一個結論。 比如,我們今天來看,梅蘭芳的《天女散花》是如此偉大的一個作品,但是當它被改造之前,從來沒有誕生過這樣的戲曲,實際上在那個年代,經由他的改造,經由他對于當時戲曲制定方式的冒犯,才變成了我們今天的膜拜這樣一個傳統。我覺得還是要活在人間,寫有我的文學,勇敢地對于一切既定的形式進行冒犯,以此重新確立一個新的自我。
提問3:修文老師,您好。 我是文學院的一名畢業生,也是一個寫作者,我剛聽到您提到非虛構,您對非虛構寫作這個概念表示懷疑,但是同時您的作品里又有一種我認為恰到好處的、非常難得的現實感,首先我想問您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關于非虛構還有一個問題,這兩年被廣泛討論的《家鄉在溫州》,作者是人類學學者項飆,他在一些訪談里經常談到,他希望我們年輕一代的人會繞過一些已經漸漸在后疫情時代失效的理論框架, 直接地去把握我們身邊可能越來越尖銳的一些現實的問題。 那么我就想請問您,您認為新一代的年輕寫作者該如何處理個人和時代的關系? 站在什么樣的距離去書寫或者說去思考這個時代是最合適的?
李修文:我最近參加了一個年輕的女作家淡豹的一本小說集的分享會,可能很多年輕的作家認為我的評價過譽了,但實際上我覺得她的作品帶給我很多啟發。 在她的作品中,我似乎看到了新世紀的孤兒、苦兒的流浪記,他們平時過著看起來很光鮮的生活,今天在紐約,明天在北京,今天探討的是me too 的問題,后面又陷入各種各樣的自身焦慮當中。他們在物質上確實是比前幾代要充裕、幸福得多,但實際上,信息量的不斷擴張繁殖,已經變成了今天這個時代年輕人要面臨的一場巨大的災難。 我們每一個人都拿著自己的各種人設,我們在不斷地靠近彼此,但實際上這個靠近的最后也并沒有形成一個有什么穩固價值的集體。 所以,這一代的年輕人確實很苦,但是我又很羨慕淡豹這樣的作家,或者是今天才開始寫作的作家。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她具備了一種嶄新的創新能力,她正在處理一個和前一個時代完全不同的問題,這就是這個時代賜給她的一個最大的機會。因為她處理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我們這一代作家,或者說比我們更上面的這些作家要處理的問題,她將重新變成一個命名者,一個處理問題的人,我覺得還蠻幸福的。 所以,你說今天年輕一代作家和時代的關系,這個就是泥流入海,將心比心,然后在這個過程當中產生貨真價實的個人遭遇,我覺得沒有什么東西比這個更重要。老實說自從先鋒文學誕生在中國以來,為什么除了一個福貴從來沒有誕生過驗證中國人文學,驗證中國人生活的典型人物? 我覺得問題在于,我們的審美經驗從來沒有內化為我們的整體的生命經驗,而我們的作家確實割裂得太狠。 我這不是在做老調重談,為什么我再三提醒自己,一定要在今時今日當中產生自己的遭遇和命運,這在根本上是我對自己要如何去做一個寫作者的提醒,舍此還有其他的道路嗎? 我覺得也沒有。 我兩個問題合在一起了,謝謝。
提問4:李老師您好,您的兩本散文集我都有幸讀過,也非常感動。 我想請教您兩個問題,第一,《山河袈裟》和《致江東父老》兩者之間有沒有內在聯系,或者換句話說,您在《致江東父老》當中對《山河袈裟》有哪些突破?在我看來,它們描寫的對象、描寫的手法都是比較接近的,《山河袈裟》出版在前,我覺得您是不是先挑了一個精華的集子,后來把剩下的又挑出了一批,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其實這兩部作品各有各的感動。您今天演講的題目突出“山河人間”,是不是您自己對《山河袈裟》這本書更看重一點? 您還說到“今時今日,山河人間”,讓人想起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山河歲月”,跟這個有沒有一定的內在的關聯,這是我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作為一位年輕的作協主席,在寫作的環境和傳播的途徑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下,怎么樣引領培養年青作家?
李修文:第一個問題是這樣的,《山河袈裟》都是我的急就章,要知道《山河袈裟》中的大部分文章,其實都沒有發表過,就像我剛才講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還能夠重新成為一個作家,所以某種程度上它實際上是我自己做的一場功課,這場功課不問來去,實際上完全就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需要,需要安頓自己的寫作。我個人覺得《致江東父老》是一本比《山河袈裟》要復雜的作品,《山河袈裟》里面充滿了“信”,“相信”的“信”,但是《致江東父老》里面是有“不信”的。 《山河袈裟》里面自我的和他人是鐵板一塊,《致江東父老》自我和他人有分裂。 從某種文學實驗的意義上來講,我覺得它對我來講可能更加重要,更加重要在哪里呢? 我不斷地在這個里頭進行著某種實驗,比如說在這些文本去引進說書人的聲音,對我來講,每一次嘗試最難的是敘述的方式,就是找到一種合適的美學上的建構。 比如說像《我亦逢場作戲人》《何似在人間》這樣的作品,我重寫了無數遍,比《山河袈裟》重寫的次數多得多,它其實就是在尋找一個最合適的聲音。 有的文章我是下定決心要擠干所有的形容詞,有的文章我決心以一個傾訴者,沒有對象來展開敘述,有的文章打算用一個不置可否的“他”,看起來是“我”,但其實又不是“我”。這就是我要產生的那種效果,就是說,他既是我,他也不是我。在更多的程度上,《致江東父老》寄托了我對寫作更多的思考。 通過它的寫作,我又順利地重新邁上了虛構文學創作的道路,所以我非常感念它。 至于你說第二個問題,如何培養年青作家,這個話題太大了。但是我想將心比心跟所有年青作家分享一句話,就是:你就不問后果的好好寫,作協一定會注意到你,會過來找你,會來問你,我能為你做一點什么?就好像2018 年我當選作協主席的時候,記者采訪我,我講了這樣一句話,我說:好的文學創作環境當然離不開作協,但作協絕對不是文學創作環境本身,本質上還是要依靠個人的修為。個人對自己命運的堅信,以及執行自己的命運的能力,我覺得更加重要。 但是也請大家相信,今天我們這些人,我相信是有能力的,也有胸懷,有能力看見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也能發自內心地和他們一起來共同成長。 就像我剛才致謝辭中講的,我覺得文學活動的唯一的意義就在于擊鼓傳花,把文學的火苗、文學的能量傳遞給另外一個人。我在作協討論的時候,也經常講,作家協會,作家自古有之,行會自古有之,只有這個“協”字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協”?就是在個人妥協基礎之上展開的協同。
提問5:修文主席,您好。我是文學院19 級的博士。我讀過一些您的作品,發現您的作品當中人物的命運往往是幽暗、詩意或者神秘的,帶著一些不可言說的意味。想問一下,您如何去理解這種人生的詩意? 然后在寫作中,如何去寫出命運的不可言說?
李修文:我覺得這不是我有意為之,某種程度上這是我受到的文化影響,就是我剛才沒有展開講的,我們的荊楚文化。 荊楚遺風對我個人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荊州博物館的楚墓里頭有西漢的男尸,在他的棺材里頭放著一封“告地書”,“告地書”是什么?就是一個人死去了,陽間的人有責任要給他即將要去的世界寫一封“告地書”,既是通關文牒,也是身份證明,也是對他最美好的祝愿。這樣一種面向虛空的實在,這種于不幸處產生的相信,這樣一種強烈的想象產生的事實,這樣一種從美學上呈現出來的陰陽不分、虛實不辨,都給我造成了一種下意識的文化影響。我生于斯長于斯,我有一篇文章叫《白楊樹下》,發表在《長江文藝》,在我的生命當中,我的姑媽去世以后,我有兩次就貨真價實地看見過她。 如果說拿一個今天的散文的概念,拿“真實”去衡量,你當然就會覺得在胡扯,但是,這種幽暗,這種詩意,這種莫可名狀,這種吸引力,這種所謂的飄逸,恰恰是楚文明、楚文化的一些最關鍵的詞匯,我覺得我本質上是受到了楚文化的影響。
提問6:修文老師好,您剛才的演講提到了很多您本人在創作過程中發生的改變,以及山河人間對您的影響。 同時,我也注意到您的演講中反復提到了很多詞匯,如荊楚大地、中國以及西方文論或者日本作品,也提到了傳統性、現代性這樣的詞匯。 所以,所謂“山河人間”實際蘊含著非常多元的觀念和價值,包括地域、民族和全球,也包括傳統、現代和后現代。 它們雖然多元,但其實彼此之間也發生著沖突和混亂。 基于“山河人間”對您的影響,您在小說創作中也要創造出一個“山河人間”,那么您如何在這種多元乃至沖突、混亂的觀念和價值中,篩選、平衡或塑造出一個您小說中的“山河人間”?
李修文:我暫時還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我是誠實的。 是這樣的,中斷了好多年以后,我剛剛才重新邁上了小說寫作的道路。 從疫情結束之后,我開始寫小說,就和我當時重新寫散文的狀態差不多,每天充滿了難以置信,我想以我對小說這么深重的怨念,我應該會經歷很多的不能克服的時刻,但似乎也還好。你問前面的兩部散文集,我還有一些心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但小說這件事情我確實是今年才剛剛開始。 我想給我一段時間,我在寫一本小說集,我現在需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捍衛自己,把它寫完,這個念頭永遠不要被熄滅,我能夠把它寫完了,我再來跟你分享,好不好? 不好意思。 有的時候不敢說,有時候每天都在懷疑自己有沒有能力,那種特別艱難的自我克服,那種時不時會冒出來的無意義感,所以我不太敢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