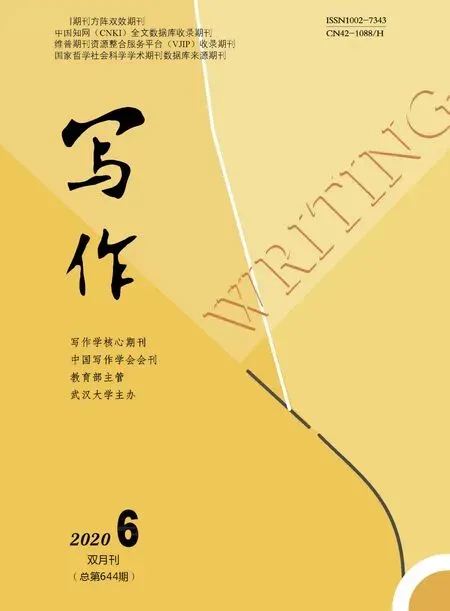小說家的小說課
——以近年來幾種“小說課”講稿為中心
戰玉冰
近年來,一批以小說家授課、講座為依托的“小說課”講稿先后出版或再版,形成了一股由作家進行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的風潮,這其中包括王安憶的《小說課堂》(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再版)《心靈世界》(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再版),畢飛宇的《小說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閻連科的《閻連科的文學講堂:十九世紀》和《閻連科的文學講堂:二十世紀》(香港中華書局2017 年版),以及張大春的《小說稗類》(天地出版社2019 年再版)等等。 在這些“小說課”講稿中,小說家們往往結合其創作實踐經驗與感受,形成了對經典小說文本的獨特理解,同時兼及對小說虛構與現實的關系、小說與影視不同藝術媒介之間的區別等議題的討論與闡發。此外,這些“小說課”講稿的出現,既是源于國內高校創意寫作專業與作家駐校制度的發展, 也為文學研究和批評日益學院化的現狀提供了一些新的話語方式和表達可能。
一、小說家讀小說:文本內部與細部的新發掘
與學者和評論家不同的是,小說家的“小說課”講稿往往很少借助西方理論的抓手和框架,也不拘泥于文學史的經典化定位,而是多選擇從文本內部入手,采取一種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式來品讀作品的內部邏輯、 細節魅力, 甚至是遣詞用字的必然性。 如果按照雷·韋勒克(René Wellek)和奧·沃倫(Austin Warren)“在文學‘本體’的研究范圍內”的分類——即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文學理論、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三分法——這些小說家的“小說課”講稿大體上可以歸入到“文學批評”的范疇之中①[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版,第31 頁。。 這并不是說這些“小說課”講稿是完全剝離于文學史脈絡和理論認識框架之外的文學批評性文字——事實上,它們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畢竟基本的文學史定位與理論框架已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認識某些經典性作品的前提與“共識”——而是想要強調這些“小說課”講稿在文本內部和細部所給予的更大氣力的分析與獨具慧眼的洞見。
比如在王安憶的《小說課堂》與《心靈世界》中,面對《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百年孤獨》這樣體量巨大且情節復雜的小說文本,王安憶也會非常耐心,甚至可以說是不厭其煩地“重述”小說的故事情節與重要枝節。 有時候,這種情節的“重述”可以占到一篇講稿的大半篇幅。 這里一方面需要考慮到講稿產生的現場語境,即王安憶是在面對學生或更多聽眾講述和分析這些小說,因而必要的情節介紹是授課或講座過程中完成最大效度的信息傳遞的前提和基礎; 另一方面,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于小說情節的“重述”并非簡單的故事梗概,而是王安憶根據自己對小說的理解做出的有所側重的情節主干選取,同時她還經常采取“評述”的方式,在“重述”小說情節的過程中融入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進而將對小說故事情節的介紹與自己的文學思考和創作理念熔于一爐。
對于文本細部邏輯的重視與詞句的品讀,是這些“小說課”講稿非常突出的特點之一,甚至有時候會讓人感覺這些被講述的小說不僅僅是“無一字無意義”,還在每句話之間、每個詞之間都存在著某種不可取代的必然性。比如畢飛宇在《“走”與“走”——小說內部的邏輯與反邏輯》一文中分析《水滸傳》“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這個故事里“最常見的動態”——“走”——“在小說的內部是如何被描述的,它是如何被用來塑造人物并呈現小說邏輯的”②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28、36、42、8-10、11-12 頁。時所說,在小說這一回中,“從一個技術干部變成一個土匪骨干,他一路是怎么‘走’的?施耐庵又是如何去描寫他的這個‘走’的?我想告訴你們的是,施耐庵在林沖的身上體現出了一位一流小說家強大的邏輯能力。這個邏輯能力就是生活的必然性。如果說,在林沖的落草之路上有一樣東西是偶然的,那么,我們馬上就可以宣布,林沖這個人被寫壞了。 ”③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28、36、42、8-10、11-12 頁。在接下來的分析中,畢飛宇對小說里的“風”“雪”,以及擋住廟門的一塊“石頭”在情節功能方面的必然性進行了極為細致且透徹的條分縷析,并進一步得出更具普遍性意義的結論:“由白虎堂、野豬林、牢城營、草料場、雪、風、石頭、逃亡的失敗、再到柴進指路,林沖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說的內部邏輯、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這才叫‘莎士比亞化’。在‘莎士比亞化’的進程當中,作家有時候都說不上話。”“但寫作就是這樣,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權力就越大,反過來,他的能力越強,他的權力就越小。 ”④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28、36、42、8-10、11-12 頁。
類似的小說細讀在畢飛宇的《小說課》中隨處可見。同樣是在《“走”與“走”——小說內部的邏輯與反邏輯》一文中,畢飛宇通過對《紅樓夢》第十一回中鳳姐在探望秦可卿的病情后,“正自看院中的景致,一步步行來贊賞”這一處細節的“反邏輯”,窺視出賈府中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與鳳姐幽暗的內心世界:“這個世界上最起碼有兩個王熙鳳,一個是面對著秦可卿的王熙鳳,一個是背對著秦可卿的王熙鳳。”⑤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28、36、42、8-10、11-12 頁。而在《看蒼山綿延,聽波濤洶涌——讀蒲松齡〈促織〉》一文中,畢飛宇認為小說中“此物故非西產”一句看似可有可無的閑筆,既意味著“悲劇就不該發生在這個地方”,同時還因為這一句話,“小說一下子具備了荒誕的色彩,具備了魔幻現實的色彩”⑥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28、36、42、8-10、11-12 頁。。 此外,小說主人公成名的“為人迂訥”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性格介紹,當和“里胥猾黠”四個字放在一起時也會產生出某種情節發展上的必然性,即“當‘迂訥’遇見了‘猾黠’,性格就必須是命運”⑦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28、36、42、8-10、11-12 頁。。這種對于小說文本中個別字詞深入且精彩的分析在畢飛宇的《小說課》中還有很多,比如畢飛宇認為“那么,蒲松齡的藝術才華到底體現在什么地方? 是這8 個字:‘夫妻向隅,茅舍無煙。 ’這是標準的白描,沒有杰出的小說才華你還真的寫不出這8 個字來。隅是什么?墻角。夫妻兩個,一人對著一個墻角,麻袋一樣發呆;房子是什么質地?茅舍,貧;無煙,爐膛里根本就沒火,寒。 貧賤夫妻百事哀。 這8 個字的內部是絕望的,冰冷的。 死一般的寂靜,寒氣逼人。是等死的人生,一丁點煙火氣都沒有了,一丁點的人氣都沒有。這是讓人欲哭無淚的景象。”“這8 個字有效地啟發了我們有關生活經驗的具體想象,角落是怎樣的,煙囪是怎樣的,我們都知道。 悲劇的氣氛一下子就營造出來了,宛若眼前,栩栩如死。 你可以說這是寫人,也可以說是寫景;你可以說是描寫,也可以說是敘事。 在這里,人與物、情與景是高度合一的,撕都撕不開。 ”①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5、21 頁。似乎在畢飛宇看來,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中沒有一處是閑筆和廢筆,所有的細節與詞句都有著其無可取代的意義和功能。 這里,我們可以回過來借用王安憶在講稿中的觀點,來作為畢飛宇對林沖“走”的命運必然性解讀的某種互文性印證,即如王安憶所說:“小說的情節應當是一種什么情節?我稱之為‘邏輯性的情節’,它是來自后天制作的,帶有人工的痕跡,它可能也會使用經驗,但它必是將經驗加以嚴格地整理,使它具有著一種邏輯的推理性,可把一個很小的因,推至一個很大的果。 ”②王安憶:《心靈世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3、234、236-237 頁。
和畢飛宇相類似,張大春在分析《水滸傳》“魯智深倒拔垂楊柳”這個故事時也流露出對于細節乃至字詞的格外重視, 并最終認為小說中的一些字詞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意義。 比如他在分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著;卻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一句話時指出:“這一組連續八個動作的敘述之中,用了四個‘把’字、一個‘用’字、一個‘將’字;除開‘相了一相,走到樹前’之外,每一個動作之前都(因口語之習、之便)添加了補強動感的助動詞。”原文好像不夠精煉,但如果“去掉四個‘把’字、一個‘用’字,敘述似乎簡潔起來,可是,‘智深’這個主詞的負擔卻顯得無比沉重,沉重到恐怕拔不起垂楊樹了。 此外,如此修改并無助于改善書寫文字在一切動作面前拖泥帶水、夾枝纏葉的蹣跚景況。 ”③張大春:《小說稗類》,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1 頁。在對于小說細部的關注中,動詞似乎是很多小說家都普遍更加重視的對象,王安憶在講稿中就曾坦陳“張煒說過一句話,我以為非常對,他說,動詞是語言的骨頭”④王安憶:《心靈世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3、234、236-237 頁。“動詞是語言中最沒有個性特征,最沒有感情色彩,最沒有表情的,而正是這樣,它才可能被最大限度地使用”⑤王安憶:《心靈世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3、234、236-237 頁。。而在張大春看來,“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原文中看似啰嗦的動詞用法,其實已經達到了某種相當完滿的藝術表達境地。
我們不必去爭論《水滸傳》這兩個故事中的“風”“雪”與動詞是否真的在邏輯上嚴絲合縫且在修辭上無可取代,而是要看到這種對文本的認識態度與分析方法背后所折射出的畢飛宇與張大春自身的文學創作觀念和態度。 正如畢飛宇自己所說:“我經常和人聊小說,有人說,寫小說要天然,不要用太多的心思,否則就有人為的痕跡了。 我從來都不相信這樣的鬼話。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你寫的時候用心了,小說是天然的,你寫的時候浮皮潦草,小說反而會失去它的自然性。 你想想看,短篇小說就這么一點容量,你不刻意去安排,用‘法自然’的方式去寫短篇,你又能寫什么? 寫小說一定得有‘匠心’,所謂‘匠心獨運’就是這個意思。我們需要注意的也許只有一點,別讓‘匠心’散發出‘匠氣’。”⑥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5、21 頁。而正是出于這種“寫小說”時的字斟句酌與錙銖必較,才會使得這些小說家在分析小說時,也同樣格外注重文本局部甚至是細部,并且可以更加感同身受地體會到其他小說作者(比如施耐庵)寫作時的匠心獨運,并為其中的精彩之處而擊掌喝彩。 在這一點上,劉艷對畢飛宇《小說課》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他所做的是‘文本分析’,但他的文本分析,不是印象式批評和讀后感式批評,他是從作家寫作實踐的角度,來分析其他作家是如何寫出‘好小說’的。 ”①劉艷:《做有溫度和體貼的文學批評——析畢飛宇的〈小說課〉》,《中國文學批評》2018 年第3 期。因此,我們與其說畢飛宇和張大春在分析施耐庵的小說,不如說他們在試圖想象和還原施耐庵是如何在構思和完成小說的每一處局部。甚至我們可以認為畢飛宇和張大春是在“小說課”講稿中進行著一個有趣的文學實驗:如果我是施耐庵,我會怎么寫“林教頭風雪山神廟”和“魯智深倒拔垂楊柳”中的每一處細節,乃至安排每一個字詞。
二、小說的本體論:真實與虛構的再思辨
在這些“小說課”講稿中,作為講者的小說家們除了在文本細部展現自己的別具慧眼之外,他們所必須面對的另一個相當重要且繞不開的問題就是關于小說自身本體論與合法性的討論, 而在這個大問題之下,小說真實與虛構的關系經常為他們所提及。
對于這一問題最為敏感的可能要首推王安憶,她在《小說課堂》與《心靈世界》中多次試圖對此作出自己的回答。一方面,王安憶認為小說不同于真實生活,而這種藝術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差別,正是小說這一藝術形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性條件:“當我們看到一個東西,完全和我們真實的生活一模一樣,何苦再要去制作這樣一個生活翻版呢? 我們就不得不懷疑它的藝術性質了。 ”②王安憶:《心靈世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3 頁。具體到小說中的人物塑造與表現,王安憶認為:“小說有機會在現實常態中表現異質人物,也就是這些異質性才使得小說所以是小說,而不是生活。 ”③王安憶:《小說課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7、275、158、274、294 頁。而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我覺得,非虛構是告訴我們生活是怎么樣的,而虛構是告訴我們生活應該是怎么樣的。 ”④王安憶:《小說課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7、275、158、274、294 頁。同時王安憶還指出:“我以為虛構是偏離,甚至獨立于生活常態之外而存在,它比現實生活更有可能自圓其說、自成一體,構筑為獨立王國。生活難免是殘缺的,或者說在有限的范圍內是殘缺的,它需要在較大、較長的周期內起承轉合,完成結局。所以,當我們處在局部,面臨的生活往往是平淡,乏味,沒頭沒尾,而虛構卻是自由和自主的,它能夠重建生活的完整性。”⑤王安憶:《小說課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7、275、158、274、294 頁。從上述羅列的這些觀點來看,王安憶對于真實與虛構關系的看法大概可以歸屬于現實主義一派,其上述表達基本不脫“文學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學要注重典型性等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觀念。
另一方面,王安憶又多次從材料、邏輯與秩序的角度,強調小說虛構與現實真實之間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是血肉相連的關系。 “小說是什么? 小說不是現實,它是個人的心靈世界,這個世界有著另一種規律、原則、起源和歸宿。但是筑造心靈世界的材料卻是我們所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⑥王安憶:《心靈世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3 頁。甚至王安憶提出自然和歷史本身才是最偉大的“虛構者”,它們在某種程度上被上升到了虛構神格的意義和地位:“我們想象我們的故事,我們去虛構,絕不是憑空而起的,我們必須找到虛構的秩序、虛構的邏輯。 這個邏輯一定是可能實現的,當然我們最后要達到的是一個不可能的東西。 我們非常尊重自然,這是虛構者對于自然的尊重,為什么尊重自然? 因為自然是一個最大的虛構者。 ”⑦王安憶:《小說課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7、275、158、274、294 頁。“你虛構得再好也虛構不過歷史,它的那種合理性,你很難推翻它,顛撲不破。 因此,我們寫小說的人往往企圖找到一個現實的核。這個核里面包含著極強的、沒商量的一個合理性,由什么來決定,我可能永遠不知道,但是我信賴它。”⑧王安憶:《小說課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7、275、158、274、294 頁。在王安憶的上述理解中,小說虛構與現實真實被賦予了某種“同構性”,即小說的材料、邏輯與秩序要源于現實,而現實在某種程度上又只不過是一種更大意義上的“虛構”,她由此擺脫了現實主義“鏡子說”與機械反映論的窠臼,而把握住了真實與虛構之間更為復雜且互動的辯證關系。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安憶才會在不同的課堂或講座中多次提及美國小說家安妮·普魯克斯在創作小說《斷背山》時,對20 世紀60 年代早期的美國是否有一對白人牧童看護牧群這件事做了仔細的調查和考證的故事, 可見王安憶本人對這個故事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創作理念的深切認同與記憶猶新:“當我們去虛構我們的小說時,我們有一個原則——還是要從我們的現實出發,因為現實它實在是出于一個太偉大的創造的力量。這種創造力超過我們。我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認識和模仿大自然的創造力。 我在想,這個問題,其實很多寫小說的都在思考,否則你怎么解釋安妮·普魯克斯那么較真白人放羊的事情。 ”①王安憶:《小說課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295 頁。
和王安憶相類似,畢飛宇也談到了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問題:“長大以后,我已經是一個職業作家了。 我依然會經常碰到這樣的問題,我的工作就是虛構,但是,有一個東西我必須面對,那就是基本事實。這個基本的事實可以分兩頭來說:一個是現實的基本真實;一個是邏輯上的基本真實。就虛構而言,邏輯的基本真實是可以突破現實的基本真實的,但是,依然有它的邊界。”②畢飛宇、張莉:《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16 頁。“文學需要想象,想象需要勇氣。想象和勇氣自有它的遙遠,但無論遙遠有多遙遠,遙遠也有遙遠的邊界。無邊的是作家所面對的問題和源源不斷的現實。 ”③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4 頁。而閻連科則進一步將現實真實區分為宏觀的“歷史背景”與微觀的“世俗世相”等更為復雜且細膩的層面,來展開自己關于真實與虛構的理解和闡述:“讓時代或歷史背景成為小說的本身,而不僅是舞臺和舞臺之幕布的存在,這是所有關心歷史、現實和時代的寫作的難度和考驗。十九世紀偉大的作家,無不是在此做出努力并取得成功的人。” “當我們談論人類的世俗世相, 是文學中精神萬物生長的根本土壤時, 我們發現了這世俗世相另外一個層面的意義——它若不是惟一的一份證明文學‘真實’的證書,那么,在文學‘求真’的法庭上,它也是最為有力的證據。尤其當文學面對浪漫、傳奇和戲劇性的到來時,惟一可以讓讀者認同這種浪漫、傳奇與戲劇性是‘真的’,而非‘假定’‘虛構’‘編造’的,那就只能有‘世俗世相’出面作為證據和證詞。蘇珊·桑塔格說:‘文學惟一的責任是真實。’在這兒,無論她說的是面對生活本質的真實,還是寫作者面對讀者,必須完成的來自于虛構和想像的文學性真實,但有一點,無論作家或讀者,所要求的真實,是一個共同的追求和目的。真實倘若不是所有作家的最高目標,那它一定也是所有文學作品不可突破的最低的底線。”④閻連科:《閻連科的文學講堂:十九世紀》,香港:中華書局2017 年版,第106、117 頁。閻連科甚至于還曾嘗試獨辟出一套理論,用“零因果”“全因果”“半因果”與“內因果”的角度來重新解釋現實主義、現代主義與魔幻現實主義在虛構與現實層面上的差異⑤具體參見閻連科:《發現小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相比于王安憶、畢飛宇、閻連科都比較認同現實主義的某些基本理念(這里并不是說他們都是現實主義作家, 而是說他們在理解虛構與真實的關系問題上表現出了和現實主義相關理念的部分一致性),張大春則更加強調小說虛構與現實真實的差異性的一面,他提出小說應該是某種“另類知識”,而這種“另類知識”需要具備一定的“冒犯性”:“是的,在冒犯了正確知識、正統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同時以及之后,小說還可能冒犯道德、人倫、風俗、禮教、正義、政治、法律……冒犯一切盧梭為愛彌兒設下的藩籬和秩序。 冒犯它們固然不足以表示小說的價值盡在于斯,但是小說在人類文明發展上注定產生的影響就在這一股冒犯的力量; 它不時會找到一個新的對象,一個尚未被人類意識到的人類自己的界限。 ”⑥張大春:《小說稗類》,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年版,第38 頁。他甚至認為小說得以存在的根本性意義和價值就在于這種“冒犯性”和“另類知識”:“當小說被寫得中規中矩的時候,當小說應該反映現實生活的時候,當小說只能闡揚人性世情的時候,當小說必須吻合理論規范的時候,當小說不再發明另類知識、冒犯公設禁忌的時候,當小說有序而不亂的時候,小說愛好者或許連那輕盈的迷惑也失去了,小說也就死了。 ”①張大春:《小說稗類》,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年版,第38、99、100 頁。
三、講稿與論文:文學研究的另一種表達可能
在幾種“小說課”講稿中,作為講者的小說家經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一些關于現實問題的關注和焦慮,比如關于小說與影視不同藝術媒介之間的區別。張大春一方面坦陳影像媒介在某些表達方面的優勢:“宣稱‘小說已死’的先進之士的確可以振振有辭地夸夸其談。 連環圖、電影、電視以及任何我們可以接觸得到的影像媒介早已騁其臨即感、 逼真性和普及力提供了閱聽受眾所能想象的滿足——對于動作的滿足。”同時又對小說在虛構想象領域的合法性地位是否會被影像所取代而感到擔憂:“高度發展的音畫科技難道真的迫使小說‘讓位’給劇情片或電視影集了嗎? 影視工業所導致的感官刺激難道真的‘霸占’住人類對虛構文本的想象空間了嗎?”②張大春:《小說稗類》,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年版,第38、99、100 頁。相比之下,王安憶對于小說作為文字媒介的藝術表達形式則充滿了自信:“影像的表達會非常方便而且很有效率, 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它會把生活的表象表達得非常之直接,而小說的閱讀是一個需要想象力的勞動,它給你空間很大,你是需要想象力去完成你最后的接受。 ”③王安憶:《小說課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236-237、116 頁。“電影更針對感官的享用,而小說是要用頭腦的,它所傳達的信息要豐富得多,也需要有更多接受的準備。”④王安憶:《小說課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236-237、116 頁。“我現在就要開始講《巴黎圣母院》。大家一定看過這本書,至少是看過它的電影。 我覺得電影是非常糟糕的東西,電影給我們造成了最淺薄的印象。 很多名著被拍成了電影,使我們對這些名著的認識被電影留下來的印象所替代,而電影告訴我們的通常是一個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 ”⑤王安憶:《心靈世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版,第85 頁。
此外,小說家們在格外注重對小說局部與細部進行文本細讀的同時,有時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跳出文本之外, 甚至直接回到當下社會, 來表達他們對現實問題的關懷與思考。 比如在《兩條項鏈——小說內部的制衡和反制衡》一文中,畢飛宇表示,“在莫泊桑的《項鏈》里,我首先讀到的是忠誠,是一個人、一個公民、一個家庭,對社會的基礎性價值——也就是契約精神的無限忠誠。 無論莫泊桑對資本主義抱有怎樣的失望與憤激, 也無論當時的法國暗藏著怎樣的社會弊端, 我想說,在1884 年的法國,契約的精神是在的,它的根基絲毫也沒有動搖的跡象。 《項鏈》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⑥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59、60 頁。他進一步指出,“契約精神是全體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在路瓦賽夫婦的身上,這種集體無意識在延續,最關鍵的是,它在踐行。 正因為他們的‘踐行’,《項鏈》的悲劇才得以發生,《項鏈》的悲劇才成為可能,《項鏈》的悲劇才能夠合理。 ”⑦畢飛宇:《小說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59、60 頁。通過對于《項鏈》這篇小說的分析,畢飛宇更多地表達出他對于當下社會生活的現實性關切。 或者如張定浩所說:“這里面可以看到畢飛宇作為‘優秀讀者’的敏感,這敏感不單是針對文本,也針對生活和時代。 ”⑧張定浩:《文學的千分之一——讀畢飛宇的〈小說課〉》,《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6 期。
最后,我們也必須回到當下,回到這些“小說課”產生的第一現場與社會環境,尤其是高校文學教育改革的背景之中來重新審視這些講稿。 一方面,我們需要注意,這些講稿最初都有一個現場講述、事后整理成文的演變過程。比如畢飛宇《小說課》里的大部分篇章來自畢飛宇在南京大學授課和講座時的講稿;王安憶“《心靈世界》一書,來源于1994 年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的講稿。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正式上講臺,不是講座,而是一整個課程”①王安憶:《心靈世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年版,第1 頁。,其《小說課堂》里的文字也是王安憶不同時段講稿的整理與集結;閻連科的《閻連科的文學講堂:十九世紀》與《閻連科的文學講堂:二十世紀》則是其“為了應對”到香港科技大學“教一學期的寫作課”而寫的講稿②閻連科:《閻連科的文學講堂:十九世紀》,香港:中華書局2017 年版,第3-4 頁。。即如裴亮所指出:“和傳統的‘從觀念到文字’的創作談與文學筆記相比,‘文學課堂’式的批評因其增加一個‘有聲’的‘講授’環節,故而往往呈現出因‘課’而‘作’,‘講’后成‘文’的新形態。 ”③裴亮:《從創作“談”到小說“課”——駐校作家制與作家批評的復興和塑形》,《天津社會科學》2019 年第1 期。而作為講者的小說家們也都相應有意識地在最后整理成文的“講稿”中保留了一些口語化元素,進而使得這些“小說課”講稿呈現出更具親切感與現場感的特點,從而不同于一般評論性文字或學術性文章。 另一方面,這些“小說課”講稿產生的更大的社會背景與制度根源在于,國內創意寫作專業在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高校的引領下紛紛建立,“作家駐校制度”更是在中國海洋大學等國內多所高校試點展開。再次借助裴亮的精辟分析:“這種以作家為中介的駐校制度,連接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以及大學校園的文學教育,實現了課堂內外的聯合、批評與實踐的溝通。 當代作家借助駐校制度而展開的一系列批評實踐活動,豐富而立體地整合了當前的批評資源與批評話語,為復興文學批評的文化建設與價值傳播功能提供了新經驗與新路徑。 ”④裴亮:《從創作“談”到小說“課”——駐校作家制與作家批評的復興和塑形》,《天津社會科學》2019 年第1 期。的確,近年來“小說課”講稿的集中出版或再版,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內文學研究和批評日益學院化的現狀提供了一些新的話語方式和表達可能。 同時也在另一個層面上印證了“在文學領域,理論與實踐從來都不是互為水火,而是相互激蕩。 ”⑤張定浩:《文學的千分之一——讀畢飛宇的〈小說課〉》,《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