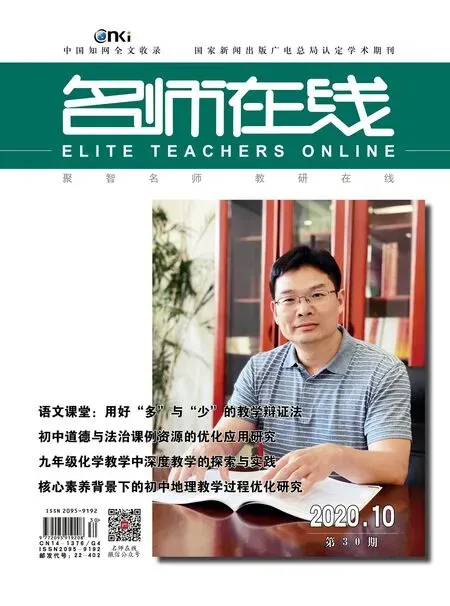語文課堂:用好“多”與“少”的教學辯證法
教學環節、教學內容、教學提問是語文課堂教學的“三駕馬車”,科學駕馭好這“三駕馬車”,關系著語文課堂的有效性、增值性。而駕馭好這“三駕馬車”的關鍵在于,教師要協調好它們之間的“多”與“少”。只有處理好教學環節、教學內容、教學提問三者之間“多”與“少”的辯證關系,語文課堂教學才能自由、高效地“馳騁”。
一、教學環節的“多”與“少”
王榮生教授認為:“語文課堂其實就兩個點,一個是起點,一個是終點。”起點就是學生對文本的基礎理解,終點就是教師希冀他們對教學內容的理解,甚至是超出教師的預設,形成讓人喜出望外的更深刻的理解。在從起點到達終點的攀登過程中,教師要給學生鋪好臺階,這里的臺階是指教學環節或教學活動。
一節語文課應該設計多少教學環節?是不是多多益善?顯然不是。一節優秀的語文課通常有兩到三個核心教學環節,一個教學環節安排10~20 分鐘的教學時間。目前,很多語文教師認為,語文課要設計五六個教學環節,甚至更多。一些教師設計的環節、臺階、活動多,寫在教案里看似連貫、邏輯性強,但到了課堂上具體實施時往往是散亂零碎的。
究其原因,一方面,環節多了,到處是重點,也就沒有了重點。一節有效的語文課,常常以一個主任務,也就是課堂終點為目標,圍繞一個主問題展開,鋪設幾個教學重點來實現。而教學環節的隨意增加,容易使教師困住手腳,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聚焦真正的核心教學環節,教學重點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突破。這樣,從起點到終點的臺階就容易失去應有的梯度,變得雜亂無章、支離破碎。另一方面,環節多了,容易旁逸斜出、喧賓奪主。教學環節過多,教師容易“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如字詞的寫法讀音、句子的手法含義、段落的表達作用等,教師興之所至,隨意拓展知識,等回過神來,發現偏離了教學中心,而教學時間又不夠了。
所以,一節合理的語文課,其教學環節的設計、教學活動的安排應摒棄“多”,聚焦重點,去粗存精,精心安排兩三個環節即可。
二、教學內容的“多”與“少”
《道德經》云:“少則得,多則惑。”這同樣適用于語文課堂教學,如果教師選擇的教學內容過多、過繁,讓學生“撐得慌”,那么這些內容就很難作用于學生的學習,也必將隨著學生有效學習的缺失而失效。產生這種問題的原因如下。
其一,部分教師對語文課程改革中資源開發的理解比較片面。特別是一些公開課、比賽課上,常常出現課外資源超過教材本身的喧賓奪主的現象。學生還未讀懂文本,教師就鏈接了一大堆與文本或近或遠、或密或疏的文章,要么是同一作者的其他文章,要么是不同作者的同類文章,導致學生無法真正掌握教學內容。
其二,部分教師過分強調融合,導致語文課堂變成“四不像”,失去語文的韻味。一是學科之間牽強跨界,把語文課上得像思政課、歷史課、音樂課、美術課,表面熱鬧,實則偏離了教學重點。二是文體之間混淆不清,一些教師將一種體裁的文本從幾種體裁的角度解讀,導致學生暈頭轉向。
其三,部分教師不會取舍,抓不住課堂主任務。備教時,這些教師總覺得這個內容是重點,那個內容不能丟,只知道做加法,不懂得做減法,以致抓不住課堂的主任務,過多地糾結不必要的細節。
其四,部分教師應試色彩濃,將“教材試題化”。新課程改革提倡從“教教材”轉變為“用教材教”,但一些教師受應試教育的影響,踐行“教材試題化”的教學理念,常常把每個知識點都翻個遍,把新授課上成復習課,忽略了學生的語文思維發展。例如,一節文言文課,教師只顧對語言的講解歸納,有幾個實詞、虛詞、活用詞、古今詞等,對文章的其他解讀一帶而過,導致課堂支離破碎,教學質量低。
由此可見,教得過多,不僅不能使學生獲得更多的知識,還會降低甚至湮滅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動力。
三、教學提問的“多”與“少”
語文課堂提問多不得。王榮生教授認為,教師在一堂課上提出太多問題,內容的確定性就弱了。學生在這種零碎的、連珠炮似的提問或追問下,很難形成連貫的、整體的認識,教師容易被課堂的碎問和多問碾壓得忘記了初心,失去了方向。究其原因,部分教師缺乏對教材文本的取舍,以致課堂上對文本的“刷屏”之問泛濫。一些教師抱著應試的心態來解剖文本,以命題者的思維來設計課堂提問,將閱讀教學課上成了試卷講評課,拋棄了文本本身的情感溫度。還有一些教師缺乏語文學科素養及整體架構課堂的能力,導致課堂提問四面出擊又四面碰壁,廢問、假問、碎問、雜問批量產生。其結果是教師提出的問題不深刻,學生的思維也無法走向深刻且容易產生“惰性知識”,高階思維能力得不到提高。
語文課堂提問也少不得。一是課堂的“大”問少不得,這里的“大”問是指著眼于教材文本大處的提問,是架構課堂的框架性問題、主問題。這樣的問題數量不多,但極為重要,直指課堂的核心、靈魂、主任務,往往與上文論述的教學環節相照應。教師抓住了“大”問,語文課堂就不會散,教學內容的確定性就有了保障,教學環節就變得清晰,教學重點和教學任務就能夠落實。比如,在教學一篇回憶性的敘事散文時,文章敘述了哪些事,塑造了怎樣的人物形象,表達了作者怎樣的情感,諸如此類常見的“大”問不能缺失。當然,提問的形式可以靈活多變。
二是課堂的“巧”問少不得。“大”問著眼于大處,架構課堂;“巧”問著眼于細節,促進“大”問的有效達成。錢夢龍先生認為,在教學中,教師應鍛煉和掌握“善問、巧問、妙問”的技巧,讓自己的提問給學生的思維指明前進的方向,為學生的成長建立一座燈塔。錢夢龍先生給教師留下了眾多經典的教學案例。比如,在教學《愚公移山》時,對于“且”“孀妻”“遺男”等文言詞的教學,錢先生沒有采用常見的直接灌輸或自問自答的教學方法,而是通過巧妙的設問、追問,讓學生通過思考加深對這些文言詞的理解,從而使其輕松記住這些文言詞。語文課堂“妙”問的“妙”應該體現在提問要問到點子上,在恰當的時機提問,從而緊抓文章的關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因此,語文課堂可適度多一些“妙”問,杜絕假問、廢問、碎問、雜問。
教師應在語文課堂教學的設計上,聚焦澄清的教學環節、澄澈的教學內容、澄明的教學提問。當然,教學環節、教學內容、教學提問之間也是密切關聯、相互影響的,一方的增減一定會導致另一方的增減。總之,教師應尊重課堂教學規律,尊重語文學科規律,尊重學生的認知規律,合理設計教學環節、教學內容、教學提問,用好“多”與“少”的教學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