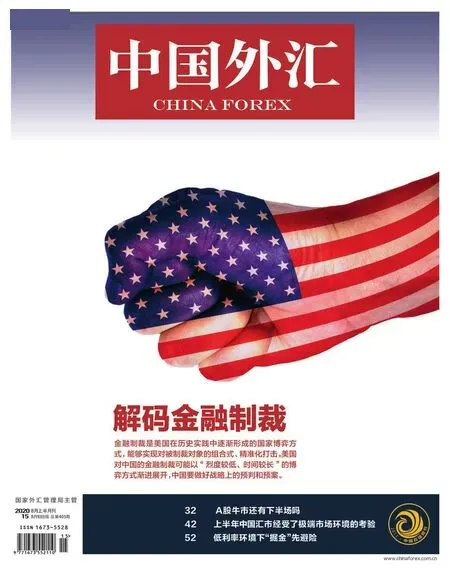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資本流動的影響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全球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受到明顯沖擊,新興市場和發達市場均出現證券資金流出,但不同市場匯率走勢出現分化;同時,由于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普遍采取了流動性紓困措施,因而也暫時緩解了各自的資本外流趨勢。本文將就此輪資本流動的特征、驅動原因以及各國采取的應對措施展開分析。
市場表現分化
第一,不同國家匯率表現各異,新興市場貨幣大幅貶值后出現分化,發達市場貨幣普遍走強。2020年年初,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及油價暴跌,不少新興市場貨幣受到影響。從對籃子貨幣走勢來看,2020年2月末至3月中下旬,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土耳其里拉、俄羅斯盧布、印尼盾等貶值明顯,其中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貶值超過20%。此外,智利比索、韓元和印度盧比出現小幅貶值,而人民幣和阿根廷比索幾乎沒有貶值。4月份以來,隨著各國廣泛開展流動性紓困以及歐佩克+(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達成協議,部分新興市場貨幣開始反彈。其中,印尼盾、哥倫比亞比索和俄羅斯盧布反彈明顯,南非蘭特和墨西哥比索趨于穩定,但土耳其里拉和巴西雷亞爾仍處于持續下跌中。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包括美元、日元、歐元和瑞士法郎在內的發達經濟體貨幣,一直普遍走強;英鎊和澳元在3月上半月下跌后亦反彈接近年初水平。
第二,全球證券投資流入停滯,新興市場和發達市場證券出現被同步拋售的現象,但規模和速度有所不同。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資本流入停頓主要發生在銀行業不同,此次受疫情影響的資本流入停頓,主要在證券市場。全球新興市場證券投資基金研究公司(EPFR)的數據顯示,疫情發生后,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債券類共同基金比較少見地遭到同步拋售,新興市場和發達市場債券類共同基金資金流出分別占總市場價值比重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96,而在全球金融危機時,只有0.33。國際收支初步數表明,新興市場證券投資2、3月流出大增,尤其是巴西。發達市場中意大利債券資金2、3月份大幅流出,日本和美國債券資金3月份也出現大幅流出。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以往,新興市場證券資金流出的規模更大、速度更快。根據EPFR的數據,疫情爆發的最初9周,新興市場債券類基金投資資金流出270億美元,達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6倍,是2013年“縮表恐慌”時期的3倍。受債券資金流出的影響,3月上半月,5年期新興市場政府債券利息平均上升了100個基點,與全球金融危機和縮表恐慌時期的升幅差不多,但利息高點出現得更早、更快。
近期,資本流出已有所緩解,債券市場較股票市場恢復更快,發達市場好于新興市場。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數據,新興市場債券資金在4、5月份已經呈現流入,股票資金雖然持續外流,但速度也已遠低于3月。EPFR的數據顯示,發達市場債券類共同基金資金4月底以來流入明顯,美國和日本的股票類共同基金3月份就已經出現了流入。不過,歐洲則呈北歐流入、南歐流出的分化態勢。
資本外流的主要因素
全球性外部沖擊和內部脆弱性疊加,構成此輪資本外流的主要驅動力。
一是美元流動性收緊和融資成本上升。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以“外匯掉期基準”(貨幣市場美元利率與外匯掉期市場美元的隱含利率之間的差值)衡量的美元融資成本大幅增加。4月以來,由于美聯儲擴展貨幣互換安排、其他外國央行顯著壓縮回購國債安排,新興市場資本流動的外部約束條件由緊轉松。
二是貨幣錯配風險依然較高。近年新興市場越來越多地發行本幣債券,外幣債券發行占比已顯著下降。但這次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和資本外逃仍聯動發生,主要原因是外國投資者份額較高:本幣發債雖減少了國內發債人的貨幣錯配,但增加了外國投資者的貨幣錯配風險。國際清算銀行(BIS)發現,此次疫情初期,本幣債券市場中外國投資者占比越高,本幣債券息差越高。
三是非居民撤資影響顯著。本土偏好、貨幣錯配和風險敏感,使得非居民在全球風險上升時撤資意愿更強,特別是全球配置資產的非居民投資者。如外國投資者在俄羅斯政府和企業債券市場上的凈賣出,主導了俄羅斯的資金流出。但發達市場往往受益于這部分居民撤資回流,一定程度上對沖了本國的非居民資金流出。如日本居民海外投資較多,外部沖擊下日本居民往往大量撤資回國,使得日元升值;2020年3月,智利、法國、美國等也出現了明顯的居民境外證券投資撤資趨勢。全球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居民對外投資雖有所增長,且在疫情中亦撤資回國,但尚難以形成明顯的對沖力量。
四是內部脆弱性存在差異。各國外債融資工具(貸款或債券)、外匯債權人(居民或非居民)、債務資金來源(外匯存款或國外借款)、外國投資者在融資工具中的占比、負債部門(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或企業)不同,導致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也不同。如土耳其外匯債務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業,且外匯貸款來源為國內銀行的國外借款;而印尼主要依靠居民美元存款來為外匯貸款融資。這導致土耳其在疫情下貨幣貶值的恢復較印尼更慢。
各國采取流動性紓困政策應對資本外流
根據以往的經驗,外部流動性問題對一國市場造成的資本流動沖擊甚至比內部脆弱性更大。鑒此,各國紛紛出臺各項政策措施來進行流動性紓困。總體來看,這些政策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政策出臺力度大、速度快。基于歷次應對危機的經驗,新興經濟體普遍加大了外匯儲備積累、豐富了外匯風險緩沖工具。因此,新興市場債券息差達到高點雖然比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縮表恐慌時期更快,但息差回縮的速度也更快。這是流動性紓困收效的結果。
二是政府外匯干預發揮了重要作用。外匯市場干預達到2008年規模,一些國家(如挪威)20多年來首次干預外匯市場。干預資金來源除外匯儲備外,一些國家還通過國家間貨幣互換安排提供資金支持。
三是基于居民的外匯管制較少,各國主要依靠宏觀審慎(MPMs)和基于貨幣政策(CBMs)應對沖擊。經過多次危機應對實踐,新興市場已逐步認識到直接采取資本流出管制措施效果不佳(如1997年泰國、2008年烏克蘭、2013年印度的案例并不成功),只能作為危機應對的最后防線。這次危機應對中逆周期調節政策使用顯著上升,主要集中在提升金融系統應對金融沖擊能力的宏觀審慎政策,以及緩解銀行系統貨幣錯配風險的基于貨幣政策的兩個方面。
四是外匯管理政策以放松為主。不少國家放寬了外匯流入,旨在釋放銀行外匯流動性,或吸引外資流入;個別國家如阿根廷,放寬了外匯流出政策,主要是為了滿足居民境外用匯需求;也有少數國家收緊了外匯流出,主要是為了防范銀行過度依賴境外衍生市場等加大本幣貶值條件下的資金外流壓力。
當前,新興市場針對外匯流動性采取的紓困措施,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流動性問題向深層次的償付危機演進。長遠來看,新興市場應促進資金流出和流入均衡,拓展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通過發展衍生品市場提供更多的風險對沖工具和流動性支持工具,加強對國內機構投資者的培育、減少對外部投資者的依賴,提升證券主權信用度,強化國際合作,加強資金儲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