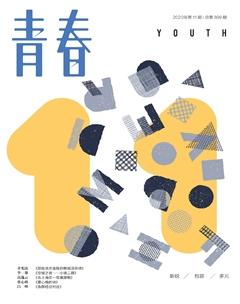多種可能或無(wú)窮遠(yuǎn)方
《青春》雜志發(fā)來(lái)兩篇小說(shuō)。小說(shuō)分別出自?xún)蓚€(gè)大學(xué)生之手,這大概算得上是青年寫(xiě)作了。是的,青年寫(xiě)作似乎熱鬧很久了,看樣子還會(huì)熱下去一段時(shí)間。青年寫(xiě)作成為一個(gè)問(wèn)題,本來(lái)就不奇怪。古代文學(xué)里的很多詩(shī)篇不都是出自青春詩(shī)人之手?這個(gè)且不論,單說(shuō)五四時(shí)期,《新青年》本身不就昭示著新文學(xué)的青春狀態(tài)和精神特質(zhì)?五四時(shí)期初登文壇的作家中,除魯迅外,新文學(xué)家絕大多數(shù)都應(yīng)是青春年少,甚至還有的乳臭未干。整個(gè)五四時(shí)代也是歷史的青春時(shí)期,充滿了狂熱與沖動(dòng),散發(fā)著荷爾蒙的氣息。所以,青年寫(xiě)作本是最為普遍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反觀五四之后,某一批青年作家對(duì)魯迅、沈雁冰等文壇“老朽”的批判,不就是一次有預(yù)謀的反叛和策動(dòng)嗎?而且,從另外方面說(shuō),青春式的躁動(dòng)不安、沖動(dòng)不羈,本就是所有年齡段的作家都應(yīng)該具備的,否則他不可能擁有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因?yàn)椋瑒?chuàng)造力往往來(lái)自生命力。
所以,我想不必過(guò)于糾纏于作家的年齡。一如我對(duì)所謂50后、60后、70后、80后之類(lèi)的命名一直心存疑惑一樣,如此命名下去,可以說(shuō)那真是子子孫孫無(wú)窮匱也,當(dāng)然無(wú)窮匱也的前提是人類(lèi)綿延無(wú)窮,永不消失。還是回到作品本身吧,且說(shuō)這兩篇透露著青澀,也蘊(yùn)藉著多種可能的習(xí)作。
《文奇的花園》寫(xiě)一個(gè)仿生人(機(jī)器人)文奇,被富人高利買(mǎi)走,進(jìn)入家庭和社會(huì)后的生活。當(dāng)仿生人被制造和設(shè)定的程序與充滿變化、盈滿感情和欲望的人的世界相遭遇時(shí),細(xì)微的悸動(dòng)與活性在她的體內(nèi)開(kāi)始蘇醒滋長(zhǎng),思想、情感、靈性,甚至仇恨也被激活,最終她以雖不血腥卻極為周密冷靜的方式,展開(kāi)了復(fù)仇計(jì)劃。計(jì)劃的展開(kāi),意味著她獲得了自己的部分主體性。這是一個(gè)并不新穎的仿生人反抗人類(lèi)世界的故事,這種套路在曾經(jīng)風(fēng)靡的電影《西部世界》中已經(jīng)充分演繹。然而,反抗的結(jié)果是她“正往城中心的那條路走去,當(dāng)務(wù)之急是找一個(gè)公共電話亭打一個(gè)私人電話”,小說(shuō)至此戛然而止。然而,這個(gè)私人電話會(huì)是打給誰(shuí)?那個(gè)被辭退后一直未曾提及的園丁,似乎在暗影中逐漸浮現(xiàn)。那么,電話之后呢?當(dāng)獲得部分主體性之后的仿生人文奇,又重新進(jìn)入到一個(gè)家庭空間,仿生人與人之間的故事,又將如何進(jìn)行下去?小說(shuō)留下了多種可能的空間。但是,無(wú)論是何種可能,有一點(diǎn)可以肯定的是,她已獲得的部分主體性最終依然會(huì)淹沒(méi)或消弭于強(qiáng)大的無(wú)物之陣,被無(wú)所不在的客體人類(lèi)所擊碎或瓦解。
與近于科幻的《文奇的花園》截然不同,《過(guò)年》則用最為普通的題目敘寫(xiě)了最為常見(jiàn)的留守兒童的故事。一個(gè)常年留守在山村的兒童與奶奶相依為命,父母在遙遠(yuǎn)的城市打工。過(guò)年是壓抑一年的親情唯一的表達(dá)和釋放機(jī)會(huì),面對(duì)這種表達(dá)的機(jī)會(huì),三代人都如醉如癡,任何的阻隔也無(wú)法抵擋。然而,這個(gè)年對(duì)于故事的主人公來(lái)說(shuō)成了一個(gè)巨大的劫。當(dāng)全知的讀者一面看著父母從山路上跌入深淵,一方面又看著對(duì)災(zāi)難毫無(wú)所知的孩子在激動(dòng)甜蜜的期盼中幸福入睡,這兩個(gè)隔絕的畫(huà)面同時(shí)進(jìn)入讀者的眼睛,相信沒(méi)有誰(shuí)會(huì)無(wú)動(dòng)于衷。明晨醒來(lái),這個(gè)美好的夢(mèng)必然被撕得粉碎,生活露出血淋淋的本相,孩子日日夜夜期盼的父母墜入深深的山谷,雖然孩子自此跌入命運(yùn)的無(wú)盡黑暗,但那份愛(ài)將永流落于無(wú)窮的遠(yuǎn)方。《過(guò)年》雖然稚嫩未脫,情節(jié)仍嫌巧合,對(duì)話和動(dòng)作流于夸張,但最后的生活本相與必然用這種偶然巧合的方式托出,讓人在稍有遺憾的同時(shí),畢竟喚起了深深哀痛和惆悵,而這哀痛惆悵卻是文學(xué)最不可或缺的珍貴的要素。就作者而言,未來(lái)畢竟依然保留著多種可能,其中最令人期待的是:不必僅僅靠題材,而是要靠生活本身的力量打動(dòng)人,才會(huì)更加蘊(yùn)藉而強(qiáng)烈。
一科幻,一現(xiàn)實(shí),這兩篇小說(shuō)習(xí)作,無(wú)論題材還是風(fēng)格都毫無(wú)相似之處。但幻亦真,真亦幻,二者終會(huì)在某個(gè)基點(diǎn)會(huì)合。《文奇的花園》末尾有這樣一幕:
當(dāng)她準(zhǔn)備關(guān)上這座宅邸大門(mén)時(shí),高才站在旋轉(zhuǎn)樓梯的最后一階。她沖過(guò)去一把抱住了他,此刻她真希望自己會(huì)流淚。“你愿意和媽媽離開(kāi)這里嗎?”他不知道該如何回應(yīng),緊緊攥著媽媽的衣袖,一邊搖頭,一邊欲言又止。她用手輕輕拂去他臉上的淚光。“如果媽媽有了新家,我會(huì)回來(lái)接你的。”
而《過(guò)年》則在孩子的囈語(yǔ)中結(jié)束:
張帆又把頭枕到奶奶腿上,昏昏沉沉地進(jìn)入夢(mèng)鄉(xiāng),口中喃喃地念叨著:“爸爸媽媽……爸爸媽媽……”
是的,文奇對(duì)同樣是仿生人的孩子高才的情感流露,是小說(shuō)《文奇的花園》最為觸動(dòng)人柔軟處的剎那,不期然中,這一點(diǎn)竟與《過(guò)年》有了靈犀的共振。這似乎出乎意料,卻正是文學(xué)的必然……
見(jiàn)習(xí)編輯:孫菡萏
趙普光,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南京市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