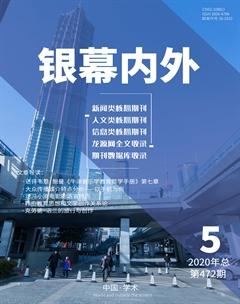對立是為了更好地統一
摘要:本文只解決一個中心問題,即康德晚年為什么極度贊揚理性,同時又批判理性 看似自相矛盾,實則并未違背自身邏輯,康德此舉是為了引導人們在合理運用理性的同時不至于拋棄本能、漠視本能,實現大自然賜予人類的自然秉賦的充分發展。
關鍵詞:對立;統一;康德;理性;矛盾
《歷史理性批判文集》是著名歷史哲學家何兆武老先生的譯作,收集了康德晚年所寫的關于歷史、哲學、國家、社會制度等方面的論文,被何先生稱之為“第四批判”。這本書算是康德對自己畢生所研究的哲學領域的一個總結與反思。我在通讀這本論文集之后,心中產生了一個巨大的疑惑,即康德為什么屢屢提到“理性”在人類思想解放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多次對“理性”進行至高無上的贊揚,給予“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后又自相矛盾似的大力批判“理性”,指出“理性”在人類社會生活以及國家層面上的種種弊端和障礙。難道哲學家都是喜歡自相矛盾嗎 我想也許正是因為哲學家看到了事物的復雜性,所以才不會隨意妄下定論,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去看,從而能夠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本文就著重分析貫穿康德晚年思想中的這種對“理性”的矛盾性。
一、為什么高舉“理性”的旗幟
在中世紀的歐洲,神學占據統治地位,信仰成為理性的前提,“天啟真理”至高無上,領悟上帝的旨意成為社會認識的主導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人類智慧和人的自主意識。 像黑格爾說的那樣,“教會體制的根本錯誤在于否認精神能具備各種能力,特別是否認理性。當理性受到教會的否定,教會體制就成了非人的體制。”伊曼努爾·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東普魯士的首府柯尼斯堡,康德的父親是一個馬鞍匠,父母都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Pietismus)教徒,虔信派強調宗教的精神,重視虔誠的信仰感情,康德小時候的精神世界受到很深的虔信派影響。八歲時,康德開始上學,學校提倡的是人文主義教育,反對宗教帶給人的思想上的僵化。學校的教育改變了康德的宗教態度,他從此開始一生都對宗教祈禱和教堂唱詩感到反感。因此,他試圖以理性去對抗神性,希望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的權威地位,進一步說,也就是試圖彰顯人性——雖然它并不像神性那般完美無瑕和崇高無比——爭奪被神權壓抑的人權——這一點可能是受到了盧梭的“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可以看出康德對“人”本身的重視。
在代表著人類思維的最高級的形式的理性被提出之后,“人類終于登上了所有哲學的巔峰,讓他感到眼花繚亂。但是,為何人類時至今日才想到重視自己的尊嚴,才認識到人類有同一切神靈平起平坐的能力呢 我認為,這個時代最好的標志,就是人類自身受到了如此的尊重。它證明壓迫者和諸神頭頂上的光輪已經散去。哲學家正力圖證明這一尊嚴,人們將會習慣于這一尊嚴,不再低三下四地祈求被肆意踐踏的權利,而是自己去爭取,并將其占為己有。宗教和政治同流合污,宗教的教條正是專制制度夢寐以求的……”
受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的影響,康德在《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中說道:“大自然決不做勞而無功的事,并且決不會浪費自己的手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她把理性和以理性為基礎的意志自由賦給了人類,這就已經是對她所布置的目標最明顯不過的宣示了”。康德的歷史哲學開宗明義的大經大法就是:大自然決不做徒勞無功的事。這一命題當然是純屬目的論的命題,于是它那必然的結論就只能是:大自然既然賦給了人類以理性,所以理性就必然要在全人類身上充分地發展并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人類可以憑借著大自然賦給自己的理性和意志自由去完成大自然設定的目標。“人類并不是由本能所引導著的,或者是由天生的知識所哺育、所教誨著的人;人類倒不如說是要由自己本身來創造一切的。生產出自己的食物、建造自己的蔽護所、自己對外的安全與防御(在這方面大自然所賦予他的,既沒有公牛的角,又沒有獅子的爪,也沒有惡狗的牙,而僅只有一雙手)、一切能使生活感到悅意的歡樂、還有他的見識和睿智乃至他那意志的善良,——這一切完完全全都是他自身的產品。”人類憑借自己可以創造一切,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東西,大自然下達任務之后,就盡可能地隱藏自己,交由人類自己去完成一切。康德在這里給予人類在認識和改造世界方面的高度肯定和自信。
有了理性,并學會了對理性的合理運用,人就能夠能動地認識和改造世界,就能夠認識自我,從而不被神學和宗教盲目控制。這是康德贊揚理性的根本目的。
二、為什么批判理性
人文科學隨著人類文明發展而逐漸形成,它以廣泛的人文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以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學為主干學科,目的在于幫助人類理解和把握自身,也就是幫助人類認識自我。而從地心說,再到日心說,再到銀河系學說,星云學說,隨著理性的深入發展,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越來越模糊不定了,這會導致人類越來越迷茫,認不清自己,也就沒辦法認清他人,更別說認識社會、認識歷史了,一切都變得游移而再無準繩。
“正是由于人類不滿足于原始狀態,所以他們就不會使自己停留在這種狀態,更不會傾向于再返回到這種狀態;從而他們就得把目前這種艱難困苦的狀態終究要歸之于他們自身以及他們自己的選擇。……并且當他們自己能很好地意識到,他們在同樣的情況之下也會恰好是那樣地行動,并且在第一次使用理性時就要(盡管是違法大自然的指示)誤用理性;他們就完全有理由要把以往所發生的的這些事情認為就是他們自己親身所做的事情,并且把由于誤用自己的理性而產生的災難全部歸咎于他們自身。”(《人類歷史起源臆測》)。
這段話中的“原始狀態”指的是可以滿足人類純粹天然的需要、可以實現人類徹底的平等、可以達到人類之間永恒的和平、人類可以“無憂無慮地只在閑情逸致之中優游或是在天真無邪的嬉戲里面卒歲的純粹的享樂”的“純樸無辜的時代”;相對的,“目前的這種艱難困苦的時代”指的就是文明時代。康德一次又一次地表示自己的惋惜:那種人人徹底平等、純樸天然的原始狀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類已經步入文明社會,并在文明社會中苦苦掙扎了許久,未來還會受其攪擾,終究會不堪重負。康德還進一步指出,人類第一次使用理性時就開始誤用理性了,這種誤用理性的做法會導致他們在面臨艱難困苦的局面時過多苛責自身、歸咎自身,近幾年,社會上的自殺率越來越高,背后的原因,是否也包含“誤用理性”這一個呢
理性是好東西,但是它對人的發展是有利有弊的。人類不能沒有理性,但是不能拋棄本能,完全按照理性的指導去生活,那樣就是違背大自然的命令,違背天意,必然不會有好下場,人類可能會因此走向滅亡。正如自然界有“左”和“右”的區分,而這種區分又是建立在有“中”這個標準作為前提一樣,贊揚理性之于左,批判理性之于右,兩者得以對立的潛在標準是:對理性的合理運用。縱觀從古至今的戰爭——先秦時期,每場戰爭死亡人數達到10人的時候,雙方就會停止戰爭,以免造成兩敗俱傷的場面;到了戰國時期,例如長平之戰,就活埋了40萬人;再到唐宋元明清幾個鼎盛時期,戰爭中尸橫遍野的現象就屢見不鮮了,更遑論一戰、二戰了,死傷人數更是不可勝數了——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隨著社會歷史的演變發展,人類的理性越來越發達,人類的生命卻越來越貶值了。
對于戰爭,康德的所秉持的態度和立場也是矛盾的,既批判又贊揚。例如康德曾在《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一文中批判過戰爭:“野蠻人的無目的的狀態所做的事情,就是它扼制了我們物種的全部自然秉賦;然而它卻終于通過把人類置諸災難之中而迫使他們脫離這種狀態,并走入一種可以使他們全部的那些萌芽都將得到發展的公民憲法。而這也正是已經創立的各個國家之間的野蠻式的自由所做的事情,那就是:由于相互抗衡的武裝耗盡了共同體多大的一切力量,由于戰爭所造成的破壞,而尤其是由于經常維持戰備的需要,人類的自然秉賦在其前進過程中的充分發展確實是受到了阻礙;”又比如,在《人類歷史起源臆測》一文中,他又對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戰爭即戰略防備進行了一番批判:“我們必須承認:文明民族所承擔的最大災難就是被卷入戰爭,并且的確與其說是由于現實的或已有的戰爭,倒不如說是由于對未來戰爭的永不松懈的、甚而是不斷增長著的準備。國家全部力量、它那文化的全部成果,本來是可以用之于促進一個更高的文化的,卻都被轉移到這上面去了;自由在那么多的地方都遭到了更大的損害,國家對于每一個成員那種慈母般的關懷竟變成了殘酷暴虐的誅求,而這種誅求卻由于有外來危險的威脅,竟被認為是正當的。”毫無疑問,他認為戰爭以及戰略防備都會阻礙人類自然秉賦的進一步發展,“戰爭只不過是自然狀態之下的一種可悲的,以武力來肯定自己的權利的必需手段”。但是,戰爭又是社會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是自然而然會發生的現象,并不受到人的意志力的控制。同樣在上面所提到的文章中,他又無奈地權宜地說“在人類目前所處的文化階段里,戰爭乃是帶動文化繼續前進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唯有到達一個完美化了的文化之后——上帝知道是在什么時候——永恒的和平才對我們是有益的,并且也唯有通過它永恒的和平才是可能的。”
黑格爾也曾對戰爭的合理性作出過生動形象的論斷:“戰爭會使各民族保持倫理上的健康,就像刮風會使海洋不至于腐敗發臭一樣,長期的靜止是會使海洋腐敗發臭的,長期的乃至‘永久的和平也會使各民族腐敗發臭。”(《法哲學原理》)
人類有了理性,才有了戰爭,在無意識的狀態下,人只想著維持生存,根本不會想著擴張領土、資本剝削。因此,從康德對戰爭的矛盾態度中,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理解他對“理性”的矛盾態度了。
三、在對立完成統一
康德早已說過,如果思維想深究事物的本質問題,矛盾永遠是不可避免的思維結果。人類社會本來就充滿矛盾,社會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社會矛盾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內部以及各個領域之間都存在矛盾。社會矛盾貫穿于社會發展的全過程,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就沒有人類社會。社會矛盾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真理并不等于對立的力量同一或者不同一,而是兩者的統一。在康德的論述體系中,我們明顯可以看出,他是將贊揚理性和批判理性這兩個相對立的做法統一起來的。他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就是希望人類看待萬事萬物都能避免片面性,充分認識到理性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利弊。人類不能沒有理性,但是有了理性之后,就得學著合理運用它,不能過度使用理性,過度使用理性會釀成一系列惡果,不利于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哲學所探討的一部人類最古老的結論便是這樣:應該滿足于天意,應該滿足于人間事物全體的總進程,這個進程并不是由善開始而走向惡,而是從壞逐步地發展到好;對于這一進步,每一個人都受到大自然本身的召喚來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人類歷史起源臆測》)我們可以把這看成是一份康德理想主義的宣言,“受到大自然本身的召喚”即順從本能。康德希望人類能夠順應自然,并返回到自然狀態中去。因為一切出自自然的事物都是美好的,但一經人手就壞了。“萬物一經過人手,即使是目的良好,其終結也都是愚蠢
參考文獻:
[1] 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2] 黑格爾.《黑格爾書信集》第1卷[M].漢堡:梅納出版社,1952.
[3]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作者簡介:李蕓(1996—),女,安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