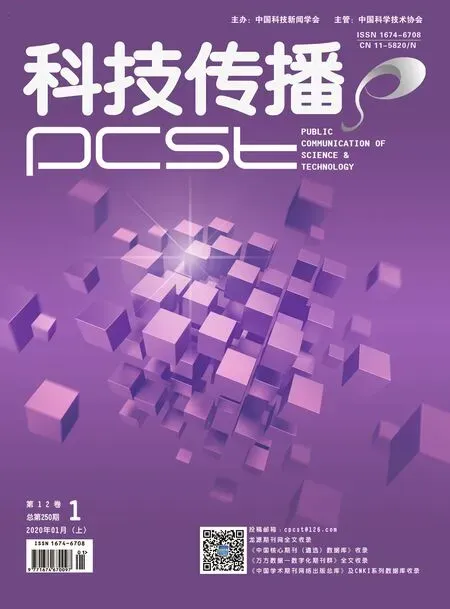媒體參與消費者維權行為的思考
杜藝帆
2019 年4 月9 日:西安一女車主情緒激動地坐在利之星4S 店奔馳車引擎蓋上,訴說自己的委屈與無奈,此視頻在網絡一夜爆紅。事件情況是女車主購買的新奔馳車剛開出門店就發生發動機漏油故障。車主請求換車,但請求被拒。最終女車主選擇坐在4S 店內的奔馳車引擎蓋上哭訴,進行維權。網傳視頻中,這位女車主稱自己是碩士研究生,辯論過程邏輯清晰,據理力爭,關乎千萬百姓和汽車行業命運的“金融服務費”也浮出水面,引起各界廣泛關注。女車主扛起維權的大旗,誓求為大家討公道,決不妥協。直到4 月19 日,網曝女車主“拖欠他人錢款”“詐騙近千萬”等新聞。女車主緊接著回應傳聞:“漏洞百出,已委托律師代理名譽侵權案”。自此此事才慢慢淡出人們的視線。
無獨有偶,據河南電視臺民生頻道報道,鄭州的王女士也遇到類似的情況,新車出現方向盤助力系統突然失效的問題。王女士要求退換車,但屢次遭到推諉。她求助媒體時說:“我是不是非得像西安的那位女車主一樣坐在引擎蓋上哭才能解決啊!”
“奔馳女車主維權”事件調查結果為:西安利之星存在兩項違法行為,罰款100 萬元,為車主更換新車,補過生日,十年VIP。
這是媒體參與消費者維權事件的典型案例,近年來此類事件并不少,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勢頭。檢視這類事件,從中發現一些共性,比如:經營者確實存在過錯,但是過錯不一定和維權事件直接相關;經營者一般為聲譽較大的公司、企業;維權者都為個人;處理結果全部是維權成功,而且其中存在“維權過度”的傾向。
1 消費者維權行為中媒體的角色與作用
1.1 媒體維護消費者,不再客觀中立
新聞媒體的基本職責[1]是集散信息、傳播新聞。在我國,媒介系統還要求媒體必須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判斷,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忠實反映社情民意,用主流價值觀引導社會輿論走向,通過客觀、真實的報道,促成社會的和諧發展。與外國媒體相比,我國的新聞媒體更加注重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一些涉及社會民生的新聞記者常以“知心人”甚至“保護人”的角色出現,真正做到了“人民的記者”。然而,在客觀公正方面我國媒體卻存在問題,尤其是在涉及人民群眾利益時。新聞報道首先應該保證真實,只有這樣新聞報道才可以減少主觀偏見進而探知事件真相。如果一旦記者對當事一方帶有同情或者偏見,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在消費者維權事件中,媒體是站在消費者一方的,譴責經營者的侵權行為。
1.2 媒體輿論單一,形成“沉默的螺旋”[2]
在我國這類消費者維權的新聞報道的輿論導向非常單一,輿論一致倒向“弱者”既維權者。究其原因是對群眾立場的維護、迫于群體壓力等等。“西安奔馳女司機維權”的視頻一經爆出,就獲得大量網友的同情和支持,各大新聞媒體也一致支持女司機,譴責4S 店“店大欺客”。在輿論譴責聲甚囂塵上之時少數理智的網友和媒體迫于群體壓力,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噤聲”,形成“沉默的螺旋”。直到10 天之后,一些理性的思考才被提出,人們這時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反思。
1.3 媒體促成消費者維權成功
在大眾傳播領域,媒體掌握著大量的信息資源并且擁有話語權,它控制著主流傳播渠道,其影響之大、范圍之廣,令諸多企業聞風喪膽。企業,尤其是聲譽較大的名牌企業,其名聲是具有很大附加價值的,出于對品牌的保護他們不惜花重金平息紛爭,一部分是對侵權實質的賠付,另一部分是為輿論買單。拋開糾紛內容不談,個人向企業維權,這種“個人對企業”“弱者對強者”的對立姿態自然會博得大眾的同情,而這種情感上的同情會干擾對糾紛判決唯一重要的因素——證據的考量。由此可見,媒體促成的維權成功是帶有輿論干擾的結果。
2 媒體參與消費者維權行為的社會影響
2.1 大眾對媒體角色的誤解
新聞首先要保證真實性,然后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做出價值判斷和價值引導。在我國,新聞媒體是為最廣大人們群眾服務的,這是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決定的。但是在新聞報道中政治立場不能凌駕于真實性之上,因為不以客觀事實報道為前提的媒體是不具有公信力的。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線。如果要保證報道的真實性,首先要樹立正確的職業理念既真實報道。然后打造理性、中立的職業形象,而中立的媒體角色會反作用于新聞報道的真實性;最后媒體還必須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出發,辯證地報道事件。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受眾是主體,應該鼓勵自由意志,獨立判斷。與此不同,媒體承擔的角色任務主要是曝光事件,多角度還原,啟發大眾獨立思考等,而不是參與事件、急于擺明立場。
2.2 從眾心理導致“沉默的螺旋”
矛盾沖突越尖銳,持相同觀點的群體內部的“黏性”越強,內部對個人的群體壓力越大。過大的輿論壓力抑制群成員的理性思考,其中能夠獨立清醒思考并提出質疑的少數群成員也迫于壓力無法發聲。消費者維權事件處于社會矛盾很尖銳的區域,再加之媒體強大的輿論引導,最終導致受眾對當前輿論氣壓狀況的進一步偏高估計,這使得“沉默的螺旋”加速發展。此時,再要想規避“沉默的螺旋”從而理性地提出不同的看法就變得非常困難。
寬松的輿論環境是“沉默的螺旋”的對立面,只有營造具有包容力的媒介氛圍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自由與民主。
2.3 形成“有困難——找媒體——成功”的慣性思維
由于媒體介入消費者維權事件,經營者出于對輿論的顧慮不得不做出退讓,糾紛的處理結果往往是讓利給消費者。在維權的過程中,媒體的作用被放大而維權的正常渠道——訴諸法律卻相應被忽視。這種“有困難找媒體”的做法,會干擾到社會正常的維權秩序,不利于法律權威的建立和司法公正,導致經營者被“過度維權”,而且縱容了大眾“聲高有理”的任性想法。
3 媒體參與消費者維權行為的反思
3.1 對經營者形成了震懾,向大眾普及了維權知識
毋庸置疑,媒體對消費者維權事件的全程關注、跟蹤報道確實是起到了監督作用。跟蹤報道使維權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公開化、透明化,這種公開化、透明化是民主社會的內在要求。媒體監督[3]不止是對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關注,還是對社會亂象,法律漏洞的揭示并形成震懾。對經營者的震懾不止局限在當前的維權案件中,更重要的是通過大眾傳播對全社會的經營亂象敲響了警鐘,起到防范于未然的作用。
在跟蹤報道期間,受眾在知曉事件進展的同時也獲悉了消費維權的程序,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相應的解決辦法。這些維權知識依托著大眾對“維權事件”的關注而最終得以廣泛傳播,以實例來呈現的維權知識比抽象的法律條文更加生動。
3.2 消費者優先求助媒體說明工商管理投訴渠道存在問題
根據經濟學原理,消費者首先求助于媒體而不是訴諸工商管理部門,這說明訴諸媒體的成本要比訴諸工商管理部門的成本小,而獲益大。每年的“3·15”晚會以及媒體頻頻曝光的經營亂象并不是個例問題,這種普遍的侵權行為如果都需要媒體曝光后工商管理部門才派人調查,那么是不是說明工商管理部門的門檻也有點兒高了呢?消費者維權合理的順序應該是先和經營者協商,如果協商無果則訴諸工商管理部門,請求法律公正裁決。在整個維權的過程中,媒體的作用應該只是輔助監督,但是在現實中,消費者維權難,轉而紛紛優先投向媒體,這個現象說明工商管理部門訴訟渠道不暢。應該引起有關部門重視。
3.3 媒體報道應當聚焦實證性思考而不是偏向性思考
中國是法治社會,法治優于人治就在于用事實說話,重視證據,不以個人好惡為評判標準,公平、公正、公開地處理事務。在中國,新聞媒體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但是新聞媒體首先還是要用事實說話。媒體的新聞報道應該是客觀、理性的,不能只從一個角度偏向性地報道事件,要致力于提出問題、啟發大眾進行理性地多角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