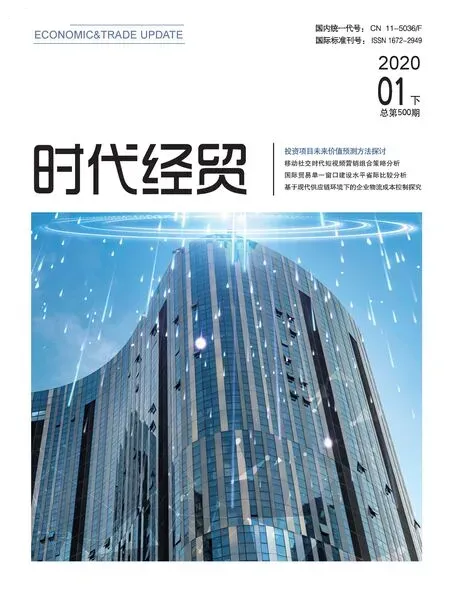從《清明上河圖》看北宋的經濟危機
邸卉雅
北宋年間,先進的生產工具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坊市解體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瓷器、紡織、造紙、醫藥、采礦冶煉、漕運造船、印刷等行業空前發展,以致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清明上河圖》中,車水馬龍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流,鱗次櫛比的商鋪,形態各異的市民鉤成了北宋汴梁城鮮活的城市生活和繁榮的經濟形態,是北宋城市經濟情態的真實寫照。宋朝被認為是中國封建王朝最富有的朝代,有著繁華的市井生活、開放的社會環境和繁榮的經濟發展。然而成畫于北宋的《清明上河圖》卻是以一株斷樹開篇,這已暗示此圖絕不是一副簡單描繪清明盛世的畫卷,在《清》圖這幅宋朝繁華浮世繪的背后,畫家張擇端以巧妙的手法和獨特的氣魄表現了北宋末期的種種經濟危機。
一、財政赤字
史學家多認為《清明上河圖》繪成于北宋徽宗年間,大約在公元1102年至1110年。此時宋徽宗即位,徽宗不是位暴君,卻是個實實在在的昏君,他奢侈無度,大興土木,宮廷用度十分奢華,宮苑中亭臺樓殿、奇石珍鳥數不勝數,必然需要龐大的財政開支支撐徽宗奢靡的生活。徽宗崇尚道教,大肆修建道觀,大封道士在朝為官。北宋官員數量更是十分龐大,一職五官的現象比比皆是。從哲宗到徽宗,不過十余年時間,官吏總數竟是擴張了十倍。而官員的薪酬更是豐厚,除了基本俸祿以外,還有各種津貼、良田、米錢、酒錢、衣錢、鹽錢等等。北宋統治集團也是大肆揮霍,連綿不斷的大小戰爭和龐大的軍隊,導致國家軍費開支巨大。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在北宋末期達到頂峰,待靖康之役,金國的鐵蹄南下侵宋,這個曾經富庶的帝國國庫已然空無一物。
二、通貨膨脹
在《清明上河圖》中,有三位運輸貨幣的車夫,從他們的身高比例和銅錢的大小看,這些銅錢比普通錢幣大得多,這是典型的大錢。大錢是當時財源不足的北宋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大肆鑄造發行的,時為“當十錢”。這些大錢虛幣的流通,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其次,交子的誕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北宋交子的出現也是中國貨幣史的一大進步,然而在北宋末年,統治者為了籌集軍費開支,不備本錢地大肆印刷交子,致使交子大幅貶值,造成了紙幣膨脹,統治者為了遏制通貨膨脹,發行新交子以一換四置換舊交子,這一措施又嚴重損害了持有大量舊交子的普通民眾,使經濟更加混亂。
三、物價飛漲
貨幣市場的混亂在徽宗時期達到高峰,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速上漲。宋人愛食羊肉,在《清明上河圖》中,有家羊肉店叫“孫羊店”,店外掛著每斤六十足的牌價,這個價格應該是店家掛在外用于招攬顧客的最低價,據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輝先生推測,該店一斤凈羊肉價格應該在一百二十文以上,而北宋英宗年間的羊肉不過才三十余文,到了北宋末年,羊肉價格已漲到每斤三百八十五文。短短幾十年,物價飛漲了幾十倍。在絹布市場,哲宗時絹布每匹大約一千余錢,三十余年后的徽宗退位時每匹已近五千錢。北宋末期,物價的瘋漲是經濟危機的典型表現,盡管政府也在極力平抑物價,卻是無能為力。
四、稅務危機
北宋政府的年財政收入大概在6000余萬兩左右,但是財政支出遠超收入,政府竭力提高稅收收入,以維持國家運轉。北宋中后期,商稅漸漸加重,稅務明目繁多,酒稅、鹽稅、茶稅等等名目層出不窮,在《清明上河圖》中就有一處臨街稅務廳,在稅務廳門前,一位稅務官正在核對稅單,對面堆著幾包貨物,貨物邊圍著三個貨主,一位貨主嘴大張,表情扭曲,似與稅官激烈爭吵;一位貨主手指貨物、背向畫面、面向稅官,也似在辯解什么,第三位貨主則表情嚴肅地面向稅官。他們幾人的爭執聲應是很大,以致引得稅務廳內的官吏和城樓上的守衛紛紛側目。這個簡單的小畫面表達了北宋末期的嚴重的稅務危機,封建社會層級分明,普通民眾少與官吏爭斗,此情此景,不得說北宋末期官民矛盾已是十分激烈。
徽宗時期實行鹽鈔法,商人需先付錢買鹽鈔,然而宋庭統治者朝令夕改,鹽未拿到,鹽鈔已換,鹽商不得花錢買新鈔,如此一番,上萬的就鹽鈔變廢紙,以致鹽商傾家蕩產。北宋中期以后,鹽稅大增,鹽商需要擔負沉重的鹽稅,使得官鹽價格昂貴,以至于無人問津,這也導致私鹽市場壯大起來,黑市交易猖獗。政府收不到足夠的鹽稅,便逐漸加稅,形成惡性循環。在《清明上河圖》中,就有一個鹽鋪,店里堆積著大量鹽塊,店家在一一稱重,然而這家店卻是無一顧客。北宋的食鹽制度和稅務措施,壓抑了鹽業的發展,在食鹽這個暴利的專營行業,在北宋時卻沒有出現一位巨富鹽商。
五、糧食危機
徽宗奢靡,喜愛花石綱,甚至調用大批運糧官船來運輸花石綱,這直接導致了國家無法控制糧食,大量私家運糧漕船囤糧入汴。在《清明上河圖》中,有大量篇幅描畫汴河上繁忙的漕運,這些繁忙的運輸景象和高超的造船技術后,卻是一條條沒有任何的守衛兵卒的運糧船,顯然這不是運糧官船,而是私家糧船。在皇權社會,糧食是國之根本,由統治者絕對控制,然而宋廷統治者的愚蠢讓他們直接放棄了對百價之源的控制,數年以后,糧食危機,米價較宋初上漲了五倍,官倉空虛,政府已無力平價糧食,物價瘋漲,社會最終動亂。
六、失業上升和貧富差距
在《清明上河圖》中,有很多挑著行李鋪蓋游走在大街小巷尋找工作機會的人,他們都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在城門外有幾個在向路人乞討的乞丐,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許多辛苦勞作的手工匠人、衣不蔽體的貧苦勞動者、奔波勞碌的小商小販,當然還有流跡于市井的小偷盜賊,他們游走在社會的底層,與同在畫中那些騎馬乘轎的官宦貴族、仆人成群的商賈巨富、閑坐飲酒的富足人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明時節這個天氣依然寒涼的初春,上層人士穿著厚厚的衣裝,下層貧苦百姓卻穿著簡單的夏裝賣起了力氣活。在這個繁華城市生活的背后,有著一個龐大的貧困階層,而在北宋末期,這個階層飛速發展壯大。北宋這個在中國封建時代堪稱最富裕的王朝,有著最高的官員俸祿,一個九品小官的工資可以拿到月薪8兩加將近60公斤米,外加綾羅布匹,這個俸祿是六百年后清朝官員的5倍。然而在這些繁華背后,卻是極大的貧富差距和嚴重的社會矛盾。
七、生產能力下降
北宋末期,奸臣當道,蔡京、王黼、楊戩等人為非作歹,當權者采取各種名目征錢斂財、苛捐雜稅繁多,免夫錢、和買、支移各種名目斂錢層出不窮。徽宗時重新實行方田均稅法,但是這個腐朽王朝的官吏們徇私舞弊現象太嚴重,丈量不均、均稅不等,對肥沃而土地雖然征稅多,卻相對稅輕,對貧瘠的土地雖然征稅少,卻已是重稅了。這導致底層農戶的賦稅負擔加重,大量貧農棄地而逃,農業生產力大大下降。官僚地主趁機兼并土地,大批民田變公田,隱田漏稅現象嚴重,最終繁重的稅負轉嫁到了貧農身上。方田均稅法這個本是積極意義的措施最終沒有給這個沒落王朝的經濟收入帶來任何轉機。
北宋末期,水利設施不修、河道不整,從《清明上河圖》可看出,汴河兩岸竟無一堤壩,無一筑堤防水設施。宋朝統治者借興修水利之名,大肆斂財貪腐,在徽宗統治的二十余年,特大水災就發生了14起,使農業生產活動大大衰退。嚴苛的統治、繁重的賦稅、連綿的戰爭加上頻繁的天災,讓北宋末年的百姓奮身起義反抗,光有規模的有記載起義就四十余起,最終上百萬的起義群眾被殺,勞動力大量流失、農田無人而種,生產力大大萎縮。
《清明上河圖》為我們展現了北宋繁華的城市生活,對繁華的表面細細解讀,卻是盛世之下的種種危機,清明盛世不過是統治者的一廂情愿,北宋王朝已是岌岌可危。《清明上河圖》成畫十余年后,北宋王朝便倒在了金人的鐵蹄之下。畫家張擇端以他赤誠的筆畫向世人警示繁華背后的種種經濟社會危機,然而這個千瘡百孔的政權已經漸漸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