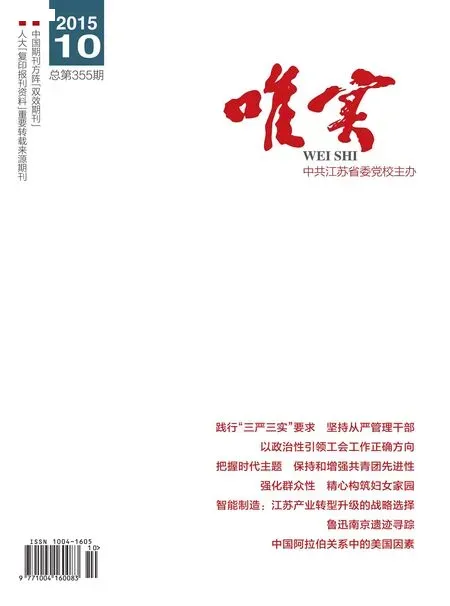瞿秋白與黨報黨刊編輯
劉維榮
瞿秋白(1899—1935),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lǐng)袖之一,祖籍江蘇宜興,生于江蘇常州青果巷(今常州青果巷82號),本名雙,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
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1919年,他投身五四運動,后又加入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xué)說研究會。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采訪。他懷著“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的抱負,從1920年10月18日到1923年1月25日,寫下了《餓鄉(xiāng)紀(jì)程》和《赤都心史》兩本通訊集。“餓鄉(xiāng)”是當(dāng)時舊式知識分子(即所謂“士的階級”)對俄國的譏稱。瞿秋白在《餓鄉(xiāng)紀(jì)程·緒言》中明白無誤地指出:所謂“餓鄉(xiāng)”,更應(yīng)是“紅艷艷光明鮮麗的所在”,“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強烈地表達了自己對社會主義熱烈而堅定的信仰。
1921年6月22日,共產(chǎn)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遠難忘的日子,他第一次見到了自己深深敬仰的革命導(dǎo)師列寧,并在會間進行了簡短的交談。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電力勞工工廠參加工人的紀(jì)念集會,又一次見到了列寧,并聆聽了他的演講。1921年秋,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chǎn)主義大學(xué)開辦中國班,瞿秋白進入該校任翻譯和助教,中國班單獨編一班,該班學(xué)生有劉少奇、羅亦農(nóng)、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蕭勁光等。1921年5月瞿秋白由張?zhí)捉榻B加入共產(chǎn)黨,當(dāng)時還屬于俄共黨組織。1922年2月,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瞿秋白一生與黨報黨刊結(jié)緣,先后主編了《向?qū)А贰缎虑嗄辍贰肚颁h》《熱血日報》《布爾塞維克》《紅色中華》,并積極為這些報刊撰稿。
主編《向?qū)А分軋蟆?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創(chuàng)辦第一份機關(guān)報《向?qū)А分軋蟆?月13日,《向?qū)А穭?chuàng)刊于上海,先后由蔡和森、彭述之和瞿秋白任主編。
西湖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由共產(chǎn)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提議召開,馬林認(rèn)為當(dāng)時中共辦日報有困難,特別是人力不足,于是提出辦一份周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guān)報,這就是其后創(chuàng)刊的、在中國歷史上起著重要作用的中共中央第一份機關(guān)報《向?qū)А分軋蟮木壠稹?/p>
1922年9月13日,《向?qū)А分軋笥谏虾柺馈!断驅(qū)А分軋笠粏柺溃鸵灾泄蝉r明的政治主張出現(xiàn)于全國人民面前。當(dāng)時“打倒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很新鮮的口號。《向?qū)А穼1佟巴饣既罩尽睂冢鹑战衣兜蹏髁x侵華罪行,喚起國人警醒。經(jīng)過《向?qū)А返男麄鳎按虻沟蹏髁x”的口號逐步深入民心,成為中國反帝運動的與論先導(dǎo)。
《向?qū)А分軋笤跇O力宣傳反帝的同時,還突出反對封建軍閥的宣傳。《向?qū)А芬砸幌盗泄P力千鈞的政論回擊了所謂“聯(lián)省自治說”“法統(tǒng)說”“武力統(tǒng)一說”等為軍閥制度張目的謬論。
《向?qū)А分軋笤O(shè)有編輯委員會,除蔡和森主編外,編委尚有陳獨秀、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他們同時又都是主要撰稿人。另外,毛澤東、周恩來、趙世炎、張?zhí)住垏鵂c、羅章龍等亦常為《向?qū)А纷濉?/p>
《向?qū)А肥且耘u時事、解釋時事為重心且充分宣傳中共政治主張的政論性報紙,黨對時局發(fā)展的政治主張,黨的理論與政策指導(dǎo),就通過《向?qū)А愤_于黨員、群眾之中。《向?qū)А吩谥袊鴪罂飞系谝淮误w現(xiàn)了列寧的報刊原則: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
《向?qū)А分軋笊钍苋罕姎g迎,讀者盛贊其為四萬萬同胞的救命符,中華民族的福音,是劃破黑夜的曙光,是中國“兩千年來歷史上破天荒的榮譽作業(yè)”。這些評價充分說明了《向?qū)А吩谧x者心目中的位置。由于《向?qū)А菲鞄悯r明地反帝反封建,因而多次遭到反動當(dāng)局的迫害,禁郵查封之事時有發(fā)生。然而《向?qū)А吩诟锩邼q的年代,其發(fā)行量竟高達十萬余份。
主編《新青年》。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三大后,決定改組休刊的《新青年》,積極為刊物撰稿,使之成為中共中央的理論性機關(guān)刊物,瞿秋白主編,前后僅出了4期,1924年12月休刊。
主編《前鋒》。192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廣州創(chuàng)辦了另一份機關(guān)刊物《前鋒》,由瞿秋白主編,1924年2月1日出第3期后即停刊。
主編《熱血日報》。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fā)生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面對突發(fā)事件,中共中央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劉少奇等人組成行動委員會,領(lǐng)導(dǎo)罷工、罷課、罷市斗爭,同時為及時傳達黨指導(dǎo)“五卅運動”的方針政策,決定創(chuàng)辦一份大型日報——《熱血日報》,以及時引導(dǎo)這場斗爭。《熱血日報》是建黨以來中共第一份日報。1925年6月4日創(chuàng)刊。
《熱血日報》由瞿秋白任主編,同時從中宣部、上海《民國日報》編輯部抽調(diào)鄭超麟、沈澤民、何味辛等人組成編委會。瞿秋白在創(chuàng)刊詞中說:“創(chuàng)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xiàn)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nèi)跽咧挥袩岬难欢覀冃闹泄挥袩岬难怀顚硎种袥]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的末運。本報特揭此旨,敢告國人!”《熱血日報》就是以熱的血來代表中國共產(chǎn)黨人為追求真理而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
《熱血日報》設(shè)有社論、本埠要聞、國內(nèi)要聞、國際要聞、緊要消息、輿論之批評、輿論之裁判等專欄。同時針對當(dāng)時的實際情況提出“六不主義”,即:不賣白菜給外國人,不當(dāng)外國人的西崽,不當(dāng)外國人的奶媽,不在洋行辦事,不用外國鈔票,不吸外國香煙。《熱血日報》指導(dǎo)了當(dāng)時的“五卅運動”,為擴大“五卅運動”的影響、掀起大革命高潮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讀者中產(chǎn)生了強烈的影響。
《熱血日報》從它創(chuàng)刊之日起,就受到租界當(dāng)局的多方刁難,主編瞿秋白曾被英租界工部局下令通緝。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瞿秋白仍堅持戰(zhàn)斗。他勇敢地挑起重任,《熱血日報》的編輯部設(shè)在上海閘北華興路56號狹小的房間,瞿秋白在這里寫社論、看大樣。因為報紙有著特殊的宣傳功能,故而瞿秋白自己稱:“這樣的工作比在大學(xué)講臺上講課要有效得多。”
6月23日,《熱血日報》被無理禁售,29日被迫停刊。《熱血日報》雖然只出版了24期,但它對激發(fā)民眾的民族自尊心,指導(dǎo)人民群眾不屈不撓地反抗帝國主義,起著巨大作用。
擔(dān)任《布爾塞維克》周刊編委會主任。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機關(guān)刊物《布爾塞維克》。10月24日,《布爾塞維克》在上海創(chuàng)刊,先為周刊,從第20期起改為半月刊或十日刊,從第29期起改為月刊,后來逐漸演變?yōu)辄h中央的理論性刊物。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被迫停刊,歷時近5年,出版52期。初期編委會主任為瞿秋白。
主編《紅色中華》。1931年12月11日,《紅色中華》在江西瑞金創(chuàng)刊,《紅色中華》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第五份機關(guān)報,每周出版一期,初期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guān)報。周以栗、王觀瀾、楊尚昆、李一氓、沙可夫、謝然之、瞿秋白、任質(zhì)斌等先后任主編。
1933年2月4日,《紅色中華》在第49期第4版刊登的《特別通知——關(guān)于紅色中華的通訊員問題》中稱:“我們認(rèn)為健全我們的機關(guān)報——紅色中華——是極端必要的,我們決定:改紅色中華為黨團、政府與工會合辦的中央機關(guān)報。”從1933年2月7日第50期開始,《紅色中華》改為中共中央、中央工農(nóng)民主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聯(lián)合機關(guān)報。此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guān)報《紅旗周報》仍在刊行。《紅色中華》鉛印,每周出版兩期。1933年6月17日,《紅色中華》第86期又改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guān)報”。從1933年10月12日第118期開始改為雙日刊,星期日休刊,每周出版三期。1934年2月16日(第150期)《紅色中華》改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guān)報”。《紅色中華》在瞿秋白擔(dān)任報社社長兼主編期間,大力宣傳紅軍戰(zhàn)績和擴大紅軍運動,報道群眾踴躍參軍和節(jié)約糧食經(jīng)費支援紅軍的模范事跡等,有力支持和配合了反“圍剿”斗爭。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瞿秋白留在國民黨重兵圍攻下日漸縮小的蘇區(qū)堅持斗爭,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1935年6月18日就義,時年36歲。瞿秋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遺書中坦白: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對他予以高度贊揚:“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作者系江蘇省檔案館研究館員)
責(zé)任編輯: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