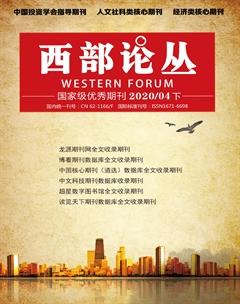《活了一百萬次的貓》中兩個可能的倫理轉變
仝語蒙
在過去,佛教和儒學思想建立了這個基準。然而它們已經失去了力量,徒留虛無與空白于我們的靈魂之上。
——西谷啟治 《虛無主義的自我克服》
摘 要:《活了一百萬次的貓》,這大概是佐野洋子最著名的繪本,它在1977年出版。凡是閱讀的人,幾乎都會贊成這個輪回與貓的故事可以被劃為兩節:在前半部分中,貓度過了一百萬次的輪回——它被不同的主人占有;而在最后的一生中,它離開了文明,在牧歌的氛圍中切斷了輪回,實現了本真的愛與歸屬。這涇渭分明的二分結構——還有它空前的成功與流行——揭示了將這篇兒童故事作為日本社會倫理轉型哀嘆的主題。然而,這篇論文將采用一個把這個故事一分為三的解讀方法。在第一部分中,它呈現了一個從儒家家庭倫理脫離,擁抱新自由主義的倫理轉變。而在第二和第三部分,通過和三島由紀夫《豐饒之海》的對比,它將暗示佐野洋子的貓如何克服自我,并且達到宗教一般的虛無實現。
關鍵詞:兒童文學;繪本;佐野洋子;三島由紀夫;豐饒之海;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魯思·本尼迪克特被派遣調研日本的文化。她在那篇著名的報告中就指出戰后的日本仍然是一個角色主導的社會。盡管她在某一處似乎想要區分日本的家族制和中國的宗族制(Benedict, 1989: 49);然而,在其余章節中,特別是當她談到“德之兩難”的時候,那多種多樣的義務的要求似乎與儒家倫理中的社會角色義務相重合[1];而孟子著名的“四端”說也證實了這種角色倫理的生物政治學基礎:人們應該去提升自己的教養來成為一個正人君子,并且通過和他人的交往互動來達到“仁”的境地。因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的本質并非為他/她作為個體的我;而是通過他/她扮演的各個角色所呈示的,整體的我。
這種角色倫理在這個社會結構中自然而然是不平等的。處于被劣勢階級的個體不得不對年長者,有權力的人表現出他/她的孝順和忠誠。而且,這種表現不能是虛偽的;它是一種真正的,情感的本性認同。因而,在這種本性認同的驅使下,日本的社會(包括近代中國社會)的劣勢個體不得不面對各種各樣的角色沖突。因此,涂爾干所言的利他自殺(Durkheim, 1897)悲劇就變成了一個重復的主題。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在芝加哥的興起;日本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迅速達到了經濟發展和倫理西化 (Harvey, 2005)。這股自由開化的浪潮,在全球化的推動下逐漸取代了原有的儒家倫理結構,東京和紐約結成了“姊妹城市”,右派的掙扎隨著三島由紀夫的自殺而告一段落 (Seidensticker, 2010: 575)。
因此,個體自由不可避免地被鼓吹。在佐野洋子發表她繪本的那一年,福柯也發表了他里程碑式的作品《規訓與懲罰》。在這本對資本主義生物政治的批判中,福柯把現代的各式機構比喻成環形監獄,而在一個又一個機構中往返,生存,掙扎的馴順的肉體就如同漂流在一個“監獄群島”(Foucault, 2009: 297)上。那擁有權力的群體設計了不公正的規則;在它的規訓下,劣勢群體和囚犯別無二致。
這監獄的群島是文明的產物。作為回應,如同浪漫主義者反抗啟蒙運動那樣,佐野洋子將她的解藥埋藏在自然中。當她的貓離開人類社會之后,那第一個倫理轉變就開始了:再也沒有不公平的主人-奴隸契約,就像擁抱了新自由主義的公民一樣,那只貓變成了自己的主人。
因此,這個繪本中前后兩部分的對比暗示了從文明社會的機構中解放的過程。在主人的權力下活著,貓的生命即使流經各種輪回但是卻沒有個體的自由。在這個故事的第一部分里,作者在代表它一次生命的每一頁中都解釋了一個在貓主人控制下不平等的,哀傷的生活,因此,葬禮就成為了一個不變的主題。在這種重復之下,這只貓就如同一個徘徊于監獄群島的囚徒:它沒有權利去言說自己,只能在每一節的開始用“討厭”這類詞匯暗示自己的反感。不管它的主人如何愛它,這種建立在不對等關系下的感情從未改變。病因很清楚:它不是自己的主人,它被他者掌控。因而,那種基于情感認同的儒家角色倫理學,在這種不對等的關系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在文明社會的角色扮演中,那只貓從未流淚。那種主人-奴隸的愛只是給予者上演的空洞的獨角戲;它的接受者從來沒有真情地投入進去——它只是逢場作戲罷了。
在故事的第二部分,貓回歸了自然。之前機械式的行文結構變得松散了。它開始言說自己的愿望和欲求,它開始將它的力比多導向它心愛的母貓。在這一階段,貓的自由仍然是自我中心的。它完成了主人-奴隸的辯證法,因而從未忘記自己,并沉浸在了一種主人式的自戀中(Yoko, 1977: 12)。在這種精神狀態中,母貓喪失了主體性,變成了他者,淪落為了公貓意識中投影的工具。
這功利主義與物化女性的主題在不同的貓給母貓禮物時變得愈發明顯。其他貓的贈禮行為回應著虎皮貓主角的自戀表演,有著一種被阿多諾[2]所批判的“扭曲的人際關系”的特征。在這一階段,真誠的感情被交換價值取代。通過表演,贈禮,吹噓,在“自然”中的貓就像在新自由主義的人一般:盡管沒有外部的意識形態控制他們,他們被自己自戀的欲望控制。因此,新的主人-奴隸枷鎖形成了:在故事的第二階段,公貓通過求愛想要占有那淪為物化意識對象的母貓。
因此,這是一種雙重的諷刺:對女性物化的諷刺以及對新自由主義辯證法的諷刺。這些被“清新”的自我權力空氣所迷惑的貓盲目地追求欲望,囚禁在自負的工具-目的理性中,然后迷失了自身。換句話說,他們同時是主人和奴隸(Han, 2017:11),懷著對自由虛幻期許完成了諷刺的自我異化。隨著日本邁進70年代,江戶的風華逝去了。三島由紀夫的自殺揭示著這意識形態的分水嶺。正如謝登施威克所感嘆的那樣:他的自殺只是對自己堅定意識的表現。然而這意識并非單純為政治的,武士道的,它還蘊含著美學純潔性的宣告。在他的《豐饒之海》中,這種美學的空無性便得到了體現。在這4本蜿蜒的大河小說中,所有主人公的掙扎終究枉然。于是在《天人五衰》的最后,當本多與聰子再度相遇時,后者質疑了前者所觀存在的真實性。這種絕對的虛無主義并非悲觀;恰恰相反,這是對空無美學所含的純潔性的揭示[3]。這種“真實”的純潔反諷地揭露了現實存在的衰落,因而,真實與虛無顛倒了。本多在40歲之后身體變得丑陋,而《豐饒之海》的后兩個主人公則喪失了純潔的精神:月光公主華而不實;而透則自戀頑固。作為新世紀下男女精神墮落的縮影,松枝清顯曾經的美不可被尋回。
三島無疑是右派分子。他對過去武士道的訴求和他對純潔性的幻想遁入對空虛揭示。正如西谷啟治(1990)在數十年后述說的那樣,對于虛無主義的克服蘊于佛教的“空”。這種“空”,正如他在另一本書所強調的那樣:是一種宗教超驗的體現(1983: 4)。在這種體驗中,所有的必然性和工具性喪失了;在虛無中,人停止詢問自己的存在和意識,宗教和美便浮現了。
佐野洋子的貓最后似乎就進入了這種宗教實現狀態。對于自己輪回過往的吹捧不僅是一種目的-工具思維的體現;還是一種自負與“有我”的象征。在虛無的意識下,貓最后停止炫耀自己的前世,因此,它體驗的世界就變成了自我意識中的純粹經驗。于是在對于工具性的遺忘中,它收獲了純愛的體驗。在這時,它的自我并為前述非等級式的,而是平等的分散在了周圍的意識中,于此同時,功利的世界消失了;交感共鳴的主體間性因此而出現。
這種領悟是深深的根植在禪宗之中的。正如鈴木大拙(2010)所言,禪宗強調通過靈魂的本真和純粹的直覺把握真實。通過這種直接的把握,世界的美就會“反射在人靈魂的鏡子上”(354);生命就變成了一個不可分的整體(355)。故事中的貓最后仿佛就變成了一個禪悟者,通過它對自然的直接把握,它拋棄了功利世界,因而切斷了輪回的束縛。這條佛教的道路,正如西谷啟治所暗示的那樣,是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一種浪漫主義牧歌式的解藥。可是不幸的是,即便保有童真的作家強調它,京都學派的哲學家認可它,他們所言終究成為被尼采所唾棄的麻醉劑。不過反諷的是,這種幻景式的麻醉成為了這篇故事經久不衰的原因;也成為了它現在仍舊能打動許多成年讀者的理由。
參考文獻
[1] 例如在《孟子》的《滕文公上》中,當他談論角色關系和人道關懷時他說:“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2006)。
[2] 見《最低限度的道德》(Adorno, 2005: 43)
[3] 見(Wagenaar and Iwamoto, 1975: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