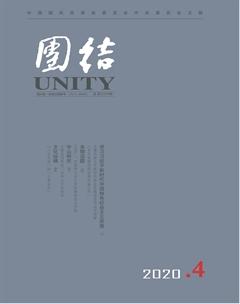王宏廣:吃飽和吃好之間的糧食安全問題
張棟
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chǔ)。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發(fā)展糧食生產(chǎn)、保障糧食安全,提出了“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nèi)、確保產(chǎn)能、適度進(jìn)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zhàn)略。
經(jīng)過持續(xù)不斷的努力,我國在口糧上絕對安全,已經(jīng)成為基本共識。但我國的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還存在著嚴(yán)峻的結(jié)構(gòu)性對外依賴。這一問題在當(dāng)前的國際局勢下,顯得日漸突出。為此,我們采訪了王宏廣教授,請他分析闡述,以饗讀者。
記者:從口糧安全,到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安全,價格穩(wěn)定,糧食安全在不同層次上擁有不同意涵,您如何理解闡釋?
王宏廣: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小糧食安全和大糧食安全,通俗講就是吃飽和吃好的問題。國際糧食安全基準(zhǔn)線是年人均占有糧食400公斤,我們依靠自產(chǎn),2019年就能達(dá)到人均470公斤。不出現(xiàn)極端情況,吃飽不是太大問題。我們每年還得進(jìn)口1億多噸糧食,人均七八十公斤。發(fā)達(dá)國家一般來說人均糧食消耗600公斤以上,我們的人均糧食消耗在540公斤左右,離發(fā)達(dá)國家吃好的拐點還有距離,那在此之前,我們的糧食消耗就還會繼續(xù)增長。所以就吃好而言,我們的糧食安全還有問題。
把糧食換算成耕地,這個問題就更好理解,我們國家養(yǎng)活14億人口,讓人民吃飽吃好,需要30億畝耕地,我們自己大概有20億畝出頭,剩下的10億畝缺口,要靠進(jìn)口。
記者:糧食進(jìn)口對我國來說,基本是不可避免的,就平時而言,國際糧價低,進(jìn)口糧食也是經(jīng)濟的,如何理解進(jìn)口安全問題?
王宏廣:糧食進(jìn)口大頭是大豆。2019年,我國進(jìn)口糧食1.06億噸,其中大豆8851萬噸,自產(chǎn)只有1810萬噸,這還是在相比2018年播種面積增加11%,產(chǎn)量增加13%之后的情況。糧食的進(jìn)口安全焦點就是大豆。大豆的問題歸結(jié)起來,差不多是兩個80%的問題,第一是我們的大豆對外依存度超過80%,第二是我們的進(jìn)口大豆超過80%來自美洲,主要是美國、巴西。南美大豆的定價權(quán)和貿(mào)易也主要掌握在美國手中。
這個格局下,風(fēng)險在兩邊是極不對等的。對美國來說,這是個純經(jīng)濟問題,其對我國一年130、140億美元的大豆出口,在它將近20萬億美元的經(jīng)濟總盤子中,算不上多大的問題。但對我們來說,這就遠(yuǎn)不止是經(jīng)濟問題,而是食用油、飼料和肉類供應(yīng)問題,是民生問題,是糧食安全和社會安定的問題。如果大豆供給出問題,那肉禽蛋奶價格就大漲,老百姓的生活就會受到很大沖擊,就沒法吃好。中美關(guān)系好,這個問題就不突出,中美關(guān)系不好,這就是很大的風(fēng)險。
大豆的缺口,來自不同作物的比較優(yōu)勢,也來自我國的政策導(dǎo)向。首先,大豆是低產(chǎn)作物,一般地廣人稀的國家和地區(qū)種植才有比較優(yōu)勢。其次,我們國家耕地總量相對于人民的生活需求,必然是不足的。總書記說,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那我們就必須通過政策引導(dǎo)把有限的耕地先用在主糧生產(chǎn)上,先確保吃飽的問題。大豆的生產(chǎn)和進(jìn)口主要還是吃好的問題,是第二步的問題。實際上,在吃飽的問題上,在我國現(xiàn)有產(chǎn)能和儲備水平下,安全是沒有問題的。大豆對外依存度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國糧食安全輕重權(quán)衡之下必要的代價。
記者:大豆主要轉(zhuǎn)化為食用油脂和蛋白飼料。食用油脂的來源較廣泛,進(jìn)口來源也相對分散,潛在替代品較多,但豆粕的缺口似乎更難有替代品?
王宏廣:大豆的問題,第一,是要把單產(chǎn)提上來,現(xiàn)在我們的大豆單產(chǎn)大概每畝270斤,美國的單產(chǎn)是430多斤,我們還有將近翻一番的潛力。單產(chǎn)差距主要是技術(shù),進(jìn)一步說主要是轉(zhuǎn)基因的問題。關(guān)于轉(zhuǎn)基因,專家都說沒問題,疑慮的是老百姓。實際上所有的育種技術(shù),都是轉(zhuǎn)基因,優(yōu)良性狀怎么來的,都是基因表達(dá)出來的,不同的只是性狀篩選、基因重組用什么手段,是靠雜交一代一代的嘗試和選擇,還是靠基因技術(shù)精準(zhǔn)控制。
第二,在播種面積上,大豆和玉米經(jīng)常是相互替代的關(guān)系,大豆種植面積為什么減少,主要是轉(zhuǎn)種玉米了,玉米是高產(chǎn)作物單產(chǎn)經(jīng)常1200斤,我們講糧食產(chǎn)量十六連增的同時,也不要忘記我們的糧食進(jìn)口也是十二連增,其中原因很大一部分是高產(chǎn)作物把低產(chǎn)作物擠掉了,能不能把大豆的單產(chǎn)水平提高一些,把經(jīng)濟效益提高一些,讓大豆的種植面積少被擠掉一點,或者還回來一些?
第三,是發(fā)展替代品。大豆的需求實際是兩個方面,豆油和豆粕。食用油脂的來源比較廣泛,進(jìn)口渠道也相對多元,問題相對小一些。有風(fēng)險的主要是豆粕,也就是蛋白飼料,替代品也有一些,首先是豆科牧草,比如苜蓿,蛋白含量18%左右,比大豆低,但單產(chǎn)高,畝均干草產(chǎn)量能到千斤左右,單算蛋白產(chǎn)量還高于大豆,更重要的是苜蓿耐瘠薄、鹽堿、干旱,種植不擠占耕地。與之相似的還有藜麥,也是蛋白含量較高,耐鹽堿高寒,不擠占耕地存量。其次,還有飼用昆蟲,也可以使用農(nóng)產(chǎn)品廢棄物生產(chǎn)蛋白飼料。再次,還有雜粕,但它們也都是其他油料作物的副產(chǎn)品,但很難稱為增量供給。
現(xiàn)在我國大豆對外依存度超過80%,就我們的測算,降低到40%左右是有可能的。
記者:耕地相對需求的不足是短期內(nèi)無法改變的,那么我們能否依靠投資海外農(nóng)業(yè)緩解這個問題?
王宏廣:通過各種方式,或租或購,在外國建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基地,彌補我們自己的耕地缺口,提升我們在國際糧食貿(mào)易、生產(chǎn)中的參與深度和掌控力度肯定是有必要的。雖然在極端情況下,比如戰(zhàn)爭條件下,海外農(nóng)業(yè)也不可靠。但在戰(zhàn)爭條件下,我們對糧食安全問題的需求也會退到吃飽的層面上。我們對于糧食安全的基本需求是,平時吃好,戰(zhàn)時吃飽。而我們所面對的主要糧食安全問題,還是在平時,確保供給安全,價格穩(wěn)定。所以,農(nóng)業(yè)出海,增加我國在國際糧食生產(chǎn)貿(mào)易中的話語權(quán)很有必要。
投資海外農(nóng)業(yè),實際上我們國家也一直在開展,已經(jīng)完成投資的已經(jīng)超過了3億畝,離我們的10億畝缺口還有距離,但也是可觀的規(guī)模。站在他國的立場上看,耕地的出租出讓給外國,還是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很多外國對我國,尤其國有資本存在相當(dāng)?shù)慕湫摹T谵r(nóng)業(yè)出海問題上,我國還是應(yīng)該大力支持,幫助民營企業(yè)去開展。
記者:糧食儲備是糧食安全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但糧食儲備也是一項龐大的經(jīng)濟負(fù)擔(dān),您怎樣看待糧食儲備的合理規(guī)模?
王宏廣:如果算經(jīng)濟賬,糧食儲備永遠(yuǎn)都是虧錢的。首先是龐大的資金沉淀造成的利息損失;其次是糧食本身的耗損和陳化,糧食也是活的生物,每年呼吸作用就會消耗掉2% ̄3%,再加上陳化、霉變風(fēng)險;第三,糧儲系統(tǒng)本身設(shè)備折舊、運營開支、人員開支也是一個很大的數(shù)字。雖然儲備糧有時高拋低吸,平抑市場波動也可能帶來收益,但遠(yuǎn)不足以平衡虧損。
既然存糧經(jīng)濟上不劃算,那能不能少存糧,多存錢?糧食儲備肯定不是越多越好,但一旦出現(xiàn)危機,很可能也就是有錢也買不到糧的時候,糧食儲備即使虧損,也必須達(dá)到保證糧食供給的安全線。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提出糧食儲備安全線是年消費量的17%~18%,我國的儲備水平肯定遠(yuǎn)遠(yuǎn)高于這條線。我國糧食安全水平和其他國家橫向比較,一直處于比較高的水平上,這得益于黨中央一以貫之的高度重視。
如果把國家比作一個公司,那么肯定不是每一個部門都是用來創(chuàng)造效益的,糧食儲備也是這樣,它虧損是為了國家整體安全,是其他部門創(chuàng)造效益的保障,這個錢必須要花,花得也是有價值的。
記者:儲備的作用在于應(yīng)急,是國家在面對短時沖擊能夠平滑市場,挺到情況好轉(zhuǎn)或者產(chǎn)能釋放。在您的觀察中,我國的糧食生產(chǎn)還有多少產(chǎn)能潛力?
王宏廣:我們的糧食產(chǎn)能潛力還有很大。
比如復(fù)種指數(shù)問題。耕地一年不只可以種一季,在不同地方,隨著農(nóng)作物不同而不同,有的地方可以一年兩季、三季,有的只能一年一季。整體上我們國家復(fù)種指數(shù)至少可以達(dá)到150%,但現(xiàn)實中只有123%,中間至少還有27個百分點的潛力。這個數(shù)據(jù)在不同口徑下有不同數(shù)值,但還有很大潛力這個判斷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種地不掙錢,老百姓種糧積極性不高。但在必要條件下,國家加以一定的經(jīng)濟刺激,復(fù)種指數(shù)還能提上去。
再就是糧食單產(chǎn)。以前,小麥單產(chǎn)到700斤、800斤,我們都覺得差不多到頂了,后來,小麥單產(chǎn)到1400斤,一開始大家都還不敢信,2019年,我國小麥單產(chǎn)記錄已經(jīng)到了1680斤。像水稻,1997年,當(dāng)時“誰來養(yǎng)活中國”的問題,全世界都關(guān)注,當(dāng)時袁隆平院士的超級稻畝產(chǎn)才1400斤,現(xiàn)在已經(jīng)達(dá)到2200斤,增加了50%不止。同等土地和氣候條件下,科學(xué)家能種出來,老百姓也能慢慢跟上來,但技術(shù)的擴散是有梯度的,袁院士今天做到的,老百姓可能要七八年后才能做到。橫向比較,按產(chǎn)量除以播種面積,玉米單產(chǎn),中國800斤出頭,美國1500斤;水稻,中國900斤出頭,美國1100多斤,差距也很大,美國土地資源條件比我們好,但主要還是技術(shù)差距。總的來說,我們的單產(chǎn)潛力還有很大。
記者:提升種糧積極性,就需要提高種糧效益;提高單產(chǎn),就需要強化技術(shù)推廣,這兩者都存在一定困難,您怎樣看?
王宏廣:提高種糧效益,要么是提高糧食價格,要么是降低種糧成本,要么是提高單產(chǎn)。糧食是最基礎(chǔ)的民生物資,提高價格需要慎之又慎,不是能夠輕易為之的;降低種糧成本,主要還是靠補貼,我們現(xiàn)在的補貼水平已經(jīng)不低,繼續(xù)提高也有難度。主要的還是應(yīng)該提高生產(chǎn)水平。
提高生產(chǎn)水平,規(guī)模化經(jīng)營是必由之路。小地塊經(jīng)營,收益很少,但勞力投入并不少,相對于進(jìn)城打工,農(nóng)民機會成本太高,種糧積極性低是必然的。同樣技術(shù)推廣,面對規(guī)模化經(jīng)營者和小農(nóng)戶,難度和成本也相差極大,不在一個數(shù)量級上。但是我國的土地格局,就是小地塊、小農(nóng)戶經(jīng)營的底子,對此,我們也有很多嘗試,鼓勵土地流轉(zhuǎn)、龍頭企業(yè)、合作社、家庭農(nóng)場的發(fā)展等等。成效很大,問題也很多。土地流轉(zhuǎn),經(jīng)營者和分散的小農(nóng)戶交易,交易成本太高,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預(yù)期也不穩(wěn)定,經(jīng)營風(fēng)險缺少有效合理的分?jǐn)倷C制。我比較看好的模式是在農(nóng)民自愿基礎(chǔ)上的土地股份化,兼顧規(guī)模化經(jīng)營、為農(nóng)民創(chuàng)造財產(chǎn)性收入、經(jīng)營風(fēng)險合理分?jǐn)偟男枨蟆5r(nóng)民的土地股份化能不能搞好,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基層治理問題。如果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基層組織和經(jīng)營者之間,不能相互信任,乃至矛盾糾紛頻發(fā),那也是巨大的問題。實際上,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不論采取怎樣的路徑,都離不開基層治理的探索和進(jìn)步。
記者:很多關(guān)于糧食安全問題的論述,也會涉及種質(zhì)資源問題和農(nóng)資化肥供給問題,您怎樣看?
王宏廣:關(guān)于種子問題,我覺得大家的擔(dān)心可能有點過。我們的主糧種植用的基本都是自己的種子,外國種子沒有明顯優(yōu)勢。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的糧食單產(chǎn)水平已經(jīng)翻了好幾番,靠的都是我們自己的種子,這是我們農(nóng)業(yè)科學(xué)家的功勞,相對于其他領(lǐng)域,我們在農(nóng)業(yè)技術(shù)上自給率是比較高的。不如人的主要是大豆,但也不必過于擔(dān)心。
在肥料上,氮肥和鉀肥我們自給無虞,可能有問題的主要是磷肥,我們主要是從澳大利亞進(jìn)口,但分散供給也不難,所以也不用太擔(dān)心。
(責(zé)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