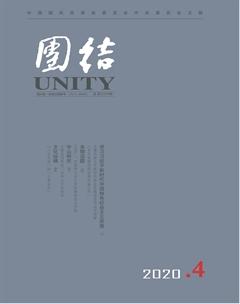儒家的傳承(中)
吳克峰 董穎波
在南北兩宋300多年間,人才輩出,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xué)家成群結(jié)隊(duì)而來,他們使得兩宋的天空,群星閃爍。
被譽(yù)為“宋初三先生”的孫復(fù)、石介和胡瑗,賡續(xù)韓愈的傳統(tǒng),并承接范仲淹,以儒學(xué)排斥佛、道。但面對(duì)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他們的批評(píng)卻顯得力不從心。宋代的儒家知識(shí)分子亟需構(gòu)建一個(gè)足以和佛教相抗衡的完整的思想體系。于是,周敦頤、張載、邵雍和程頤、程顥兄弟應(yīng)運(yùn)而生,而由朱熹集其大成而成理學(xué)。他們?cè)诳酌现螅讶寮宜枷朕D(zhuǎn)進(jìn)為一個(gè)嚴(yán)密精深的體系,開創(chuàng)出理學(xué)的新天地,并從元朝開始,歷經(jīng)明清,成為一千年中一以貫之的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成為主導(dǎo)此間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私意以為,宋朝理學(xué)家們的最動(dòng)人處,在于對(duì)“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三個(gè)哲學(xué)的大哉問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使得認(rèn)同他們的文人士大夫,以“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篇》)為其終極關(guān)懷。
周敦頤在其《太極圖說》中建構(gòu)出儒家的宇宙觀,回答了宇宙萬物從何處來,人“從哪里來”的問題。他認(rèn)為“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dòng)一靜,產(chǎn)生陰陽萬物,“萬物生生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在《通書》中,周敦頤認(rèn)為圣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認(rèn)為“誠”由“太極”所派生,“純粹至善”。因而以“誠”為內(nèi)容的人類本然之性亦是完善的,它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并進(jìn)而提出“主靜”、“無欲”的道德修養(yǎng)論。所謂“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后至”。在周敦頤的論域中,無極、太極與人極同源,人們只要通過學(xué)習(xí)和修行,就能夠“自易其惡,恢復(fù)善性”,達(dá)到不僅超越現(xiàn)實(shí)生活,也超越個(gè)人生命限制的“誠”的境界。這種境界,在漢唐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而張載則莊嚴(yán)宣告儒家讀書人的抱負(fù)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他這四句話回答的是“我是誰”且“往哪里去”的問題。
《康熙字典》說,“果核中實(shí)有生氣者亦曰仁”。程明道說,“心如谷種。生之性,便是仁”。如果把天地當(dāng)做一個(gè)果實(shí)的話,那它的核心是什么?張載說,只能是人,只能是人的仁。因此,“為天地立心”的含義,就是要求士大夫識(shí)仁求仁,好仁惡不仁,把仁這種價(jià)值樹立于天地之間。
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張載的“為生民立命”是說,士大夫的使命在于通過教育而使得民眾都能保持自己的性體全德,無愧于天,不怍于人,活出人的體面與尊嚴(yán)來;“為往圣繼絕學(xué)”是說要把孔孟之道繼承下來,傳播開去。而為萬世開太平”則是前面三個(gè)命題的結(jié)果。張載自信已經(jīng)找到“為萬世開太平”的鑰匙。
在哲學(xué)層面,周敦頤、張載和后起的邵雍、二程、朱熹,認(rèn)為理、氣是宇宙萬物的本源,萬物一理。這個(gè)理,乃是天理。它是事物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而氣是構(gòu)成一切事物的材料。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理、氣相依而不能相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又?jǐn)嘌浴袄碓谙龋瑲庠诤蟆保坝惺抢肀阌惺菤猓硎潜尽保选耙焕砗腿f理”看作“理一分殊”的關(guān)系。提出“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事物“只是一分為二,節(jié)節(jié)如此,以至于無窮,皆是一生兩爾”。(朱熹,《朱子語類》)這一思想,對(duì)于君王來說,就是他們的統(tǒng)治必須建立在對(duì)理的遵從上。理高于君王。君王受命于天,需要得天理、行天道。而對(duì)于理的解釋和闡發(fā),則在儒家士大夫。對(duì)于儒家士大夫來說,所謂理想的生活就是理直氣壯的生活、心安理得的生活。據(jù)此,思想家們認(rèn)為他們找到了通往萬世太平的道路,這就是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齊治平,內(nèi)圣外王。他們強(qiáng)調(diào)通過道德的修養(yǎng)和錘煉,成賢成圣,達(dá)到人格的圓滿,天下的太平。這一路徑,強(qiáng)化了文人士大夫自漢朝以來重視內(nèi)在修為、強(qiáng)調(diào)氣節(jié)與德操,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勇于承擔(dān)歷史使命的凜然風(fēng)骨與文化性格。它也使得浸潤其間的兩宋文人,活出了中國歷史上最自由最自在的面相。
我們且通過范仲淹和蘇東坡二人來領(lǐng)略一下宋朝士大夫的風(fēng)貌。
范仲淹(989—1052年)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xué)家,也被認(rèn)為是理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他27歲經(jīng)科舉步入仕途,因直言敢為,在1029~1036年間曾三次被貶。但每被貶一次,他的聲望就提升一次。在他看來,降級(jí)、降職乃至罷免、流放是你朝廷的權(quán)力,但據(jù)理力爭(zhēng)卻是我的操守。在世俗生活之上,一定還有一種道義的生活需要追求,所謂“瓢思顏?zhàn)有倪€樂,琴遇鍾君恨即銷”。(范仲淹,《睢陽學(xué)舍書懷》)
晏殊曾經(jīng)向朝廷舉薦過范仲淹,對(duì)范仲淹有知遇之恩。但當(dāng)范仲淹直言進(jìn)諫之時(shí),晏殊十分擔(dān)心,責(zé)備他沽名釣譽(yù)并且可能會(huì)連累到自己。范仲淹回答說:“我正是因?yàn)槊棵繐?dān)心配不上您的推薦而令您蒙羞,才直言進(jìn)諫。沒想到今天您卻因?yàn)槲业闹艺\正直而責(zé)備我。”(樓鑰,《范文正公年譜》)隨后,范仲淹又寫信給晏殊說:“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范仲淹,《上資政晏侍郎書》)。
梅堯臣也曾作《靈烏賦》勸范仲淹:“結(jié)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喙兮爾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要他閉嘴,別自尋煩惱,別像烏鴉那樣報(bào)兇訊而“招唾罵于里閭”。范仲淹回復(fù)說,“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zhì)兮,處天地之覆露”,我的言論“思報(bào)之意,厥聲或異。警于未形,恐于未熾”,所以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靈烏賦》)其凜凜風(fēng)神,千年以下,如在目前。
1045年,47歲的范仲淹因慶歷新政受挫而自請(qǐng)出京,由參知政事出任邠州,繼而改任鄧州、杭州。在鄧州,謫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寫信來告訴他重修了岳陽樓,要求他“作文以記之”,范仲淹寫下了傳誦至今的《岳陽樓記》。他說: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yuǎn)則憂其君。是進(jìn)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shí)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才是儒家士大夫應(yīng)該選擇的生活。范仲淹最后“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深沉感慨回應(yīng)的正是1500年前孔子那句:“十步之內(nèi),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回應(yīng)的正是孔子那句:“德不孤,必有鄰!”
《宋史》說,“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shí)士大夫矯厲尚風(fēng)節(jié),自仲淹倡之”。這篇充滿了入世精神、憂患意識(shí)的《岳陽樓記》,一經(jīng)寫出,即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并傳誦至今,成為哺育中國知識(shí)分子心智結(jié)構(gòu)的重要精神食糧。范仲淹影響的又豈止是一時(shí)一世?!
蘇東坡(1037—1101年)是天才、全才,宋仁宗贊譽(yù)他有宰相之才,但他的仕途卻并不順暢。
1057年,20歲的蘇軾進(jìn)士及第后,先后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1080年,43歲的他因“烏臺(tái)詩案”被貶為黃州團(tuán)練副使。正是在黃州,生活困頓的蘇軾因衣食不充受地于東坡而自號(hào)“東坡居士”,為后世留下了“前后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帖》等一批不朽之作。而《定風(fēng)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所表現(xiàn)出來的作者的曠達(dá)超脫,如果不是悟透了人生三問,又如何能夠“一蓑煙雨任平生”?如何能夠“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
1094年,蘇東坡再次被貶至充滿瘴癘之氣的惠州,他卻寫詩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zhǎng)作嶺南人”。1098年,朝廷三貶已是62歲的蘇東坡至蠻荒之地的儋州,但蘇東坡“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把他鄉(xiāng)做故鄉(xiāng)。在儋州,花甲之年的蘇東坡不僅帶領(lǐng)民眾修路、筑橋、挖井、制衣,將中原地區(qū)先進(jìn)的生活觀念、生活方式傳授給當(dāng)?shù)孛癖姡⑶医▽W(xué)校,興講堂,講授儒家文化,踐行儒家君子士大夫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從而成為儋州文化的拓荒者和播種人。流傳至今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都無一例外地表達(dá)了人們對(duì)蘇東坡的緬懷之情。不錯(cuò),蘇東坡是遠(yuǎn)離了政治中心的東京汴梁,也遠(yuǎn)離了儒家文明浸潤千余年的中原,但誰又能說,蘇東坡的這些作為遠(yuǎn)離了政治?
在蘇東坡43年的仕宦生涯中,除去他為父母守喪的6年,37年中,他輾轉(zhuǎn)于京師與16個(gè)州府之間,平均每2年多就換一個(gè)地方,最后客死常州。在如此的顛沛流離中,蘇東坡可曾意氣消沉過?可曾失望過?可曾后悔過?
脫脫說,蘇軾“器識(shí)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dá)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于禍患之來,節(jié)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雖然曾經(jīng)被仁宗、神宗所賞識(shí),但終于不得大用。有人說,只要“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dāng)免禍”。(《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蘇軾列傳》)但如果是這樣,蘇軾還是蘇軾嗎?
而蘇軾之所以是蘇軾,借用陸游的話來說,是“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借用他本人的一句詞來說,在困頓流離中,蘇東坡堅(jiān)信“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
(吳克峰,南開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副教授;董穎波,瑚璉簠簋(天津)科技有限責(zé)任公司職員/責(zé)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