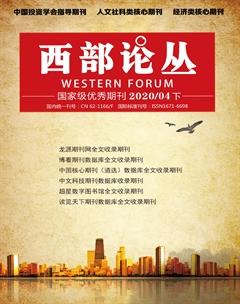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研究
摘 要:詐騙行為是詐騙罪構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詐騙行為的實質在于行為人的欺詐行為使得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產。行為人的欺詐行為要想構成詐騙行為,必須達到足以使可能受騙的同類一般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的程度。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詐騙行為可以分為事實詐騙與價值詐騙,作為詐騙與不作為詐騙。
關鍵詞:詐騙行為;實質;程度;價值詐騙;不作為詐騙
我國現行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立法者采用簡單罪狀的方式規定詐騙罪,并未對詐騙罪的犯罪構成特征作詳細描述,根據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的普遍認識來看,要構成詐騙罪,必須同時滿足五個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要素,即:“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對方陷入或者繼續維持錯誤認識——對方基于錯誤認識處分(或交付)財產——行為人取得或者第三者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1]而行為人實施的詐騙行為是詐騙罪構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對于詐騙罪的成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對詐騙行為進行深入研究。
一、詐騙行為的概念
從詞源上來看,《漢語大詞典》中“詐”是指“欺騙;作假、假裝;用語言或手段騙人,誘使對方透露真情”。“詐騙”是指“訛詐騙取。”[2]《辭海》中“詐騙”一詞是指“以假冒身份、偽造證明、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欺詐手段來騙取公私財物以及其他招搖撞騙的行為。”[3]可見,“詐騙”一詞在詞源意義上具有兩層含義,即“騙”與“取”。“詐”是指欺騙、欺詐,包含行為人虛構、隱瞞等欺騙行為;“騙”是指通過騙人的手段以取得對方的財物。其中“詐”是行為手段,“騙”是行為目的,行為人通過欺騙、欺詐行為以最終實現取財的目的。但是,作為詐騙罪客觀方面構成要素之一的詐騙行為,其重點應在于“詐”而不在于“騙”,因此詐騙行為應僅包括行為人為實現取得他人財物的目的而實施的欺騙、欺詐行為,不包括后續的取財行為。綜上,筆者認為,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應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為使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產而實施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行為。
二、詐騙行為的實質
行為人所實施的欺詐行為并非都屬于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要構成詐騙行為,必須滿足“行為人實施欺詐行為——欺詐行為足以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被害人因行為人的欺詐行為而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并‘自愿處分財產”的行為模式。行為人所實施的欺詐行為與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之間必須具有因果關系,即被害人是因為行為人的欺詐行為而陷入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的,如果沒有行為人的詐騙行為,被害人就不會處分自己的財產。但是,若行為人確實實施了欺詐行為,而被害人卻沒有因此陷入錯誤認識,則該欺詐行為就不是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例如,甲使用偽造的演唱會門票,被檢票人員識破未放行,隨后其又趁檢票人員不注意偷溜進演唱會現場的,不屬于詐騙行為。但是,如果甲將偽造的門票交給檢票人員查驗,檢票人員誤以為該票為真實門票,從而放甲通行的,則屬于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
綜上可見,詐騙行為的實質在于行為人所實施的欺詐行為使得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產。行為人的詐騙行為開啟了詐騙罪的大門,如果被害人沒有陷入錯誤認識,或者雖陷入錯誤認識但處分行為并不是基于該錯誤認識而作出的,被害人就不會跨進詐騙罪的大門,不成立詐騙罪。
三、詐騙行為的程度
社會生活中的欺詐行為無處不在,特別是在商業活動中,例如某服裝店在商店門口掛著“清倉大甩賣,最后五天!”的廣告牌,但事實上該商店并未真正進行虧本甩賣活動,掛廣告牌只是他的一種營銷手段。這些欺詐行為實際上都屬于行為人對某一事實的吹噓或夸大,但卻不屬于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因為在社會生活中,行為人對某一事實進行一定程度的吹噓或夸大往往是能夠被人們所容忍的,人們通常也能夠根據日常生活經驗辨別該行為的真偽,一般情況下行為人的行為并不具有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的可能性。此外,如果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就能認定其構成詐騙罪,刑法就會有過多干預人們日常生活之嫌,刑法的過分規制也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并非所有的欺詐行為都能構成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只有當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傳達虛假信息的行為具有使人陷入或維持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的可能性時,該行為才達到構成詐騙行為的程度,才有可能成立詐騙罪。
那么究竟應以何種標準來認定行為人的欺詐行為具有足以使人陷入或維持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的可能性?目前刑法理論界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主觀標準說認為,判斷欺詐行為是否能夠達到足以使他人陷入或維持錯誤認識的程度,應當根據具體的、特定的受害人的情況來確定,綜合考量被害人的年齡、性格、對詐騙行為的謹慎程度、辨別能力、生活經驗等要素來認定。而客觀標準說則認為欺詐行為能否達到足以使他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的程度,應以社會一般人的判斷能力為標準。筆者認為,若堅持主觀標準說,則需要根據欺詐行為所指向的特定對象的具體特征進行綜合分析,若被害人受教育水平低、認知能力較一般人弱,即使是對于其他人而言十分荒唐的騙局他也可能深信不疑;若被害人社會經驗豐富、警惕性高,即使行為人的詐騙手段十分高超,他也不會因此上當受騙。這樣一來,對于詐騙行為的認定就會失去統一標準,使得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喪失定型性,不利于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因此主觀標準說并不可取。對于客觀標準說,筆者亦不完全贊同,因為社會生活中的詐騙行為無處不在、各式各樣,而行為對象的認識水平、認知能力、社會經驗、警惕性等主觀因素確實也各不相同,若僅以具有普通認識水平、認知能力的一般人的判斷為標準來認定詐騙行為,則會使得某些欺詐行為得不到合理定性,不利于對社會上的弱者及缺乏社會經驗的人給予刑法保護。[4]因此,筆者認為在認定詐騙行為的程度時,應以客觀標準為主,同時適當考慮主觀標準,即認可客觀標準說中以一般人的判斷能力為標準認定詐騙行為,但應通過主觀標準對“一般人”進行限定,這里的“一般人”應指在特定情形下與被害人情況相似的可能受騙的一般人,而不是具有普通認識能力、辨別能力的所有社會一般人。應考察他們在相同的情況下是否也具有被騙的可能性,若答案是肯定的,則應肯定行為人的欺騙行為已經達到構成詐騙行為的程度,成立詐騙罪。
綜上,行為人對外傳遞虛假信息的行為要想構成詐騙行為,必須達到足以使可能受騙的同類一般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產的程度。以此作為詐騙行為的統一認定標準,既能最大限度地給予弱者刑法上的保護,又能更好地實現詐騙罪的規制效果。
四、詐騙行為的表現形式
(一)事實詐騙與價值詐騙
根據行為人在實施詐騙行為時所使用的依據是事實還是價值判斷,可以將詐騙行為分為事實詐騙與價值詐騙。
1. 事實詐騙
行為人以“事實”為依據向被害人傳遞錯誤信息的行為是詐騙罪中最常見的詐騙行為之一。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所使用的“事實”既可以是外在的事實,如自然事實,行為人的身份、能力,行為人或他人已經實施的行為,法律規則,也可以是內在的事實,如心理意思、支付能力。無論是什么類型的“事實”,只要行為人虛構或隱瞞的該事實在客觀上足以使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并因為該錯誤認識處分財產即可。具體來看:詐騙行為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能力進行詐騙是指行為人為實現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對自己的身份、能力進行偽裝,通過偽造假證明、假文件,制造開設公司的假象等方式把自己搖身變成一個有身份地位的人,并通過該虛假的外表騙取被害人的信任,以便于更好地實施后續的詐騙行為。就規則進行詐騙,是指行為人通過對法律、法令以及其他規則的虛假陳述,使對方陷入錯誤。[5]即法律或有關規定明確將某一行為規定為有效/無效行為,但行為人利用被害人對他的信任,歪曲法律規定,使被害人認為其行為是符合/不符合法律規定的,進而實施違背其真實意愿的處分財產行為。利用心理意思實施詐騙,是指行為人對自己或他人的心理活動內容進行虛假表示,致使對方陷入或維持錯誤認識。心理意思屬于個人的心理活動內容,他人不易察覺或對其加以證實,但行為人往往是利用心理意思的該特點來欺騙他人。
2. 價值詐騙
價值判斷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于各種事物、現象所作出的好與壞、正確與否的判斷。價值是由人來判斷的,因此會不可避免地帶有較強的主觀性,不同的人由于知識結構、認知能力、生活經歷及價值觀等不同,在對同一事物進行評判時難免會得出不同的價值判斷。因此,對于行為人是否能就價值判斷實施詐騙行為這一問題,理論上也存在不同的主張。持否定說的學者認為,只有事實才有真假之分,意見或價值判斷屬于一個人的主觀評價,其不是事實,也無真假之分,因此虛構事實中的“事實”不包括價值判斷的內容。持肯定說的學者認為,就價值判斷進行虛構也能構成詐騙行為,如日本學者平野龍一指出:欺騙行為,是指使人陷入錯誤的行為,除此之外沒有特別限定,因此,不僅可以是有關事實的欺騙,而且可以是有關評價的欺騙。[6]
筆者贊同肯定說的觀點,首先,詐騙行為的實質在于行為人的詐騙行為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產,因此行為人無論是對客觀存在的事實進行虛構,還是對價值判斷進行虛構,只要行為人所虛構的內容足以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并基于該錯誤認識處分財產,即可構成詐騙行為。其次,雖然價值判斷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在社會生活中對于某一事物、現象的價值判斷往往存在著能為大眾所認可并接受的公認標準。通常情況下,一般人對某一事物、現象的評價結果相較于公認標準而言并不會存在太大的偏差,一旦出現偏差過大或與公認標準截然相反的情況,就可以認定該評價與事實不符,若行為人在進行價值判斷時主觀上還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該行為最終也導致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的,即可認定行為人成立詐騙罪。
(二)作為詐騙與不作為詐騙
根據詐騙行為所違反的規范類型的不同,可以將詐騙行為分為作為詐騙和不作為詐騙。對于作為的詐騙行為,理論和實踐中都不存在爭議,但是對于詐騙行為能否表現為不作為這一問題,理論上則存在著不同的觀點。
1. 作為詐騙
在刑法中,“作為是指行為人以身體活動實施的違反禁止性規范的危害行為。”[7]從表現形式上看,作為是積極的身體活動;從違反法律規范的性質上看,作為直接違反了禁止性的規范。即積極地違反法律規定,不應為而為一定的行為。我國刑法中規定的絕大多數犯罪都可以以作為的形式實施,詐騙罪亦如此。作為詐騙既可以以明示的方式實施,也可以以默示的方式實施,其中明示的作為更為常見,包括利用自己的身體實施的詐騙行為、利用工具或動物實施的詐騙行為及利用他人實施的詐騙行為。而默示的作為則表現為行為人通過可推知的舉動進行虛假表示。
2. 不作為詐騙
不作為是與作為相對應的另一種危害行為的表現形式。不作為,就是指行為人負有實施某種行為的特定法律義務,能夠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為。[8]即消極地不履行法律義務,應為而不為一定的行為。對于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能否表現為不作為,國內外理論中都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全面否定說認為,行為人的不作為不能構成詐騙行為,因為刑法并未明確規定詐騙罪可以由不作為的方式實施,若將不作為認為是詐騙行為的表現形式之一,則存在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嫌。部分否定說認為,詐騙行為可以表現為不作為的形式,但是需要對其進行嚴格的限制,不作為只有與作為具有等價性時,才能構成詐騙行為。肯定說是目前刑法理論上的通說,其認為詐騙行為既可以表現為作為的形式,也可以表現為不作為的形式。
筆者贊同肯定說的觀點。首先,詐騙行為的實質在于行為人的詐騙行為使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產,而刑法并沒有對詐騙行為的方式進行限制,因此只要是能夠使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的行為,無論是以作為還是不作為的形式表現出來,都屬于對“不得詐騙他人財物”的禁止性規范的違反,當然構成詐騙行為。其次,當行為人負有向被害人告知真相的義務以防止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時,被害人相對于行為人而言處于弱勢地位,此時被害人對事實的判斷依賴于行為人所傳遞的信息,若行為人不向其告知應說明的事實,極易使被害人陷入或繼續維持錯誤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是由于行為人的不作為掌控了被害人財產遭受損失這一危害結果發生的因果進程,行為人應對被害人的財產損失承擔責任。可見,以不作為方式實施的詐騙行為與以作為方式實施的詐騙行為具有同等的社會危害性,可以構成詐騙行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不作為都能構成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正如張明楷教授所說“不作為的欺騙要達到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就必須與作為具有等價性。[9]不真正不作為犯的成立,要求行為人存在基于保證人地位的作為義務。只有處于保證人地位的人的不作為引起侵害結果,才能與作為引起的侵害結果同等看待,才能肯定這種不作為符合構成要件。[10]即只有當行為人處于保證人的地位,具有法律所賦予的告知義務,能向被害人說明真實情況但不說明,致使被害人陷入或者繼續維持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產的,行為人的不作為才構成詐騙行為。如果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并不是由于行為人的行為引起的,而且行為人也不負有向被害人說明真實情況的義務,其只是單純地利用他人的錯誤認識取得財物的,此時行為人單純的沉默不構成詐騙行為,不宜認定為詐騙罪。參照一般不純正不作為犯的義務來源的判斷,不作為詐騙中的保證人的作為義務主要來源于以下幾方面內容: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職務或業務上要求的義務、法律行為引起的義務,以及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
注 釋
[1] 張明楷著:《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 《漢語大詞典》(第11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版
[3] 《辭海》(上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
[4] [德]克勞斯·羅克辛著:《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 張明楷:《論詐騙罪的欺騙行為》,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第3期
[6] [日]平野龍一著:《刑法概說》,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版
[7]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六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8]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六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9] 張明楷:《論詐騙罪的欺騙行為》,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第3期
[10] [日]山口厚:《刑法總論》,東京有斐閣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信息:楊璟(1995-),女,云南普洱人,上海大學法學院2014級刑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