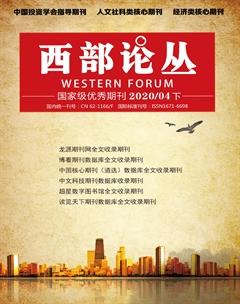“興中會”性質簡評
摘 要:“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這句耳熟能詳的口號。興中會作為革命團體,已經根深蒂固印于我們思想之中。但是,從興中會成立的背景,組織的人員及其成分,并且就興中會的章程來看,似乎很難說明興中會是革命團體。種種的證據和推論表明,把興中會定性為革命團體,似乎有相當的成見在里面,我們有必要撥開成見,用新的視野去看待興中會。
關鍵詞:興中會;孫文;誓詞;檀香山
引 言
“凡公認為顯而易見和‘當然的,很少真如此。……因為傳統成見往往不是從無懈可擊的推理中得出來的,而是從幾個世紀的混沌頭腦中涌現出來的。現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阿蘭·德波頓之言。興中會的性質為我們所公認,而它正是從混沌的腦中涌現出來的,不是建立在合理的推證之下。
(一) 成見迷惑
唐德剛《從晚清到民國》中說:“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只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多愈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每股‘收回本利百元。”咋看之下,我們所認為作為革命團體的興中會,卻成了“銀會”。不得不說,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檢校孫文原文,唐氏所說也是人云亦云的一種無推證的結論。首先,1894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宣言幾無有如唐氏所說。檢1895年《香港興中會章程》第八款“款項宜籌也:……每股科銀十元,認一股至萬股,皆隨各便。……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至于“每人出底銀五元”則是在1894檀香山興中會章程第一款。唐氏混同了檀香山和香港的興中會章程,其沒有去認真檢校兩章程的原文,就堂而皇之的推論,無疑是受了流俗影響。但把興中會說成是“銀會”,并非空穴來風,香港興中會章程第八款確實有此嫌疑。
楊天石曾說:“1894,孫中山在興中會章程中提出‘創立合眾政府,所謂‘合眾,就包含了‘國民國家的意思。”話出大家之口,可以正確無疑了?檢校《孫中山全集》不論是1894年還是1895年的兩興中會宣言,沒有“創立合眾政府”的句子,甚至是連創立新政府的意思也沒有。那此話從何而來?檢孫中山全集第三卷:檀香山興中會盟書“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話出于盟書而非章程,但是楊氏卻說是出于興中會章程,豈非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章程無一處有這句話,卻沒有檢校原文,想當然的認為有,這難道不是成見作祟的結果嗎?
以上兩例,作為近代史研究專家是如此,那么一般人呢?可想而知了。
(二)興中會誓詞問題
1894“檀香山興中會盟書”:“聯盟人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查。”興中會是否作為革命團體在于這句誓詞。此話出處大有可疑。首先,此話出自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卻引自鄧想《中國國民黨茂宜支部史略》。作為元老的馮自由,1895年是最年輕的興中會員,親身經歷,居然不知此誓詞,需參看他人著述,豈不怪哉!且《孫中山評傳》引馮自由寫1895年入會場景:“宣誓時‘由李昌宣讀,各以左手置于耶教圣經上,高舉右手,向天次第讀之,如儀而散。”現在考察兩個問題。第一,此話出自馮自由《革命逸史》。話中連帶頭宣誓人,及其宣誓的各種舉動都記得清清楚楚,卻為何不知道這么重要的誓詞,還要去參看鄧想的書?作為具有革命傾向的組織,此話不僅為宣誓詞而已,更是作為奮斗目標理應要銘記于心,怎能忘記!第二,馮氏寫革命史自1928起,續篇在1946年出版。為何初編時不把誓詞這么重要的事寫進去,要等到四十年代才加到里面,是忘記了嗎?合理的推測當然不是。因誓詞是判斷興中會性質的關鍵,及東北異旗,國民黨實現了名義上的全國統一。馮自由為國民黨及孫文形象,有必要做歷史性的推重,那么興中會是孫文最早建立的組織,其革命性與否自然就是國民黨形象和國父形象塑造最合理的事件。這自然是推測,卻是合理推測的一種。
其次,這句誓詞于史無據。林增平指出:“孫中山在1898年著《倫敦蒙難記》和隨后的各類著述及談話里,均不曾提到;參與1895年乙未廣州之役被捕的陸皓東等的‘供詞里,也沒有透露有若何誓詞存在;宮崎寅藏在1902年發表的《三十三年之夢》里,謝纘泰在1924年發表的《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里,陳少白在1929年發表的《興中會革命史要》里,也沒涉及誓詞片言只字……”林氏所說的都是老一輩親歷的革命家,盡無一人提出過此誓詞,那鄧想是從何得知?如有此誓詞,馮自由大可以找這些人或是他們遺孤,何至于參看沒有什么依據的鄧想之書。鑒于上所言,有必要懷疑,此誓詞的存在或說其產生時間。此誓詞即便是真實存在,那出現的時間恐怕要往后挪。
(三)興中會章程與孫文行跡
章程也叫宣言有1894年檀香山和1895香港兩章程,兩章程在格式都是一致的,內容也頗多相似之處。首先,兩序言都表達了中國政府腐敗及社會民眾的愚昧“上則因循守舊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但是,1895年章程有更激烈的政府抨擊“政治不修,綱紀敗壞”“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其次,則表達了列國侵凌,民族危亡的現狀。“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最后,呼吁智識拯救危亡的愛國之心。“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可以知道,兩章程序言中表達的是對現實政權的不滿,還不到要革命推翻的意思,而在所列各實施項目中就更沒有了。如1894章程第一項“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國體”一詞自然不會是維護滿清政府,但是也不會是民主共和,國體只是說維護一個國家應有的機體,因為原文緊接著說“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所以,維護國體,自然就是整個中國完整的有機體。反而是1895章程第八項“每股科銀十元······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這明顯具有誘導投資的商業性質,無怪唐德剛先生說興中會是“銀會”。總觀章程,最多表明該團體是愛國團體。
再看興中會的成員,《孫中山評傳》指出:“綜合起來看,商界13人,銀行家1人,農業家1人,公務員3人,報界1人,工人5人。”參加興中會大部分都是較有成就且家資深厚之人,似乎這也符合章程中引資的傾向。再說,這些人有多少革命情懷很難相信。這些人大都生活殷實,在外打拼多年,有必要冒險從事革命,拿自己身家性命做賭注嗎?復次,孫文組織興中會在一個月之間,與這些人大部分都未有深交,雙方之間能做出革命這樣的重大決定嗎?最后,如張灝指出:1899年梁啟超到檀香山得到當地僑民的歡迎,而且梁還加入了當地的三合會,使得許多三合會會眾加到保皇黨,這還引怒孫文。會黨長期都是孫文專注且利用的對象,到1899年尚且沒有真心依附孫文,何況是1894年的興中會會員呢?綜上,也能知道興中會會員大部分都無革命傾向,充其量最多是愛國而已。
最后考察孫文本人在興中會成立前后的行跡。1889年孫文寫了《致鄭藻如書》要求改變時政,利用西藝,尤其關注農業方面。1894年1月草擬《上李鴻章書》,6月定稿上達李鴻章,因李氏正忙于中日甲午之戰,沒有禮遇孫文,投書失敗。10月初啟程去檀香山,11月24日成立興中會。上李書從內容上看主要還是上鄭書的發展,改良思想濃重。把興中會看成革命團體,則孫文在一個月之間思想大變且建立組織,從改良到革命何其速?
綜上所述,不管是從誓詞本身而言,或是從誓詞有無而言,或是從興中會章程及會眾而言,或是孫文本身而言,把興中會當成是革命團體都難以成立。
作者簡介:張文杰,男,福建建甌人,馬克思主義學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國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