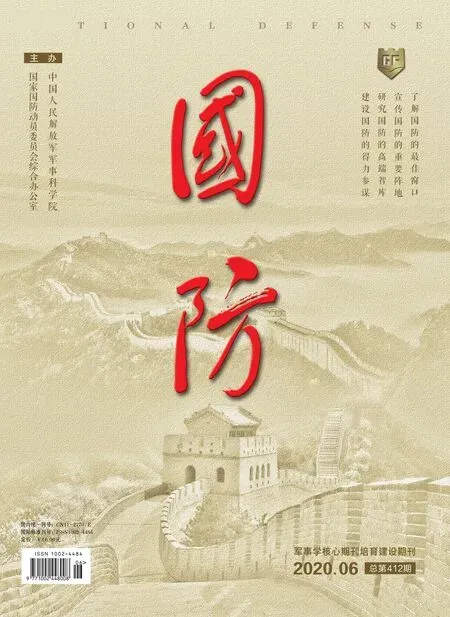武裝沖突法領域的中國實踐探研
胡世洪
內容提要:新時代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武裝沖突法是一個重要領域。作為絕大多數規約的締約國,武裝沖突法領域的中國實踐,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包括:依法使用武力,捍衛國家主權、統一和安全;自覺規制行為,樹立大國軍隊作戰典范;堅持“結伴不結盟”,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懲治戰爭犯罪,維護國家利益和人類正義。
新時代的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重大問題解決和重要規則制定不斷貢獻中國方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應當是全方位的,涵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律等,規制武力使用、作戰行為和戰爭犯罪懲治的武裝沖突法便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作為絕大多數規約的締約國,武裝沖突法領域的中國實踐,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一、依法使用武力,捍衛國家主權、統一和安全
人口數量第一、經濟總量第二、國土面積第三的中國,自身的主權、統一和安全,對整個人類的安全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石的武裝沖突法,賦予會員國為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而使用武力進行自衛的權利。依法使用武力,捍衛國家主權、統一和安全,是中國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最大貢獻,也是武裝沖突法領域最重要的中國實踐。
(一)捍衛國家安全的自衛作戰
根據武力自衛權相關規則,結合國際國內形勢,中國未來為反對侵略、捍衛國家安全進行自衛作戰應當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嚴格遵守時間要件,不搞預先自衛。中國一貫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衛原則,經濟和國防實力不強時如此,現在作為國力強盛的新時代大國,也應繼續堅持,不搞先發制人的預先自衛。二是嚴格遵守對象要件,不搞連帶打擊。自衛只針對正在實施侵略的國家,而非任何別的國家,即使該國對中國也深懷敵意或是曾經的“敵國”,又恰好與侵略國地理鄰近。三是嚴守自主決定權,不受他方左右。如中國遭受別國侵略,應根據具體情勢自主決定是否行使自衛權,不受他方左右,防止別有用心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挑撥離間,坐收漁利。四是恪守定義精神,應對新型侵略。在新軍事革命日新月異的新時代,對電磁和網絡攻擊等新型侵略行為,應在恪守有關侵略定義和立法精神的同時,采取有效手段應對。五是堅持相稱性原則,防止自衛過當。歷次自衛作戰中都遵守相稱性原則的中國,如今雖由大向強,也不會恃強凌弱,在可能的自衛作戰中亦將繼續堅持這一原則。
(二)維護國家統一的反分裂作戰
武力使用規則明確,任何部分或全面分裂一個國家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與聯合國憲章目的和原則相違背。主權國家在其領域內使用武力鎮壓暴動、平定分裂,并不違背禁止使用武力原則。1959年,中國中央政府為平息西藏地方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武裝叛亂進行了反分裂作戰,有力維護了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當前,反分裂斗爭形勢更加嚴峻。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實現國家統一的大國,臺灣問題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一大掣肘。如果“臺獨”勢力冒天下之大不韙,置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福祉和大義于不顧,“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①參見《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中央政府使用武力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完全符合武裝沖突法(當然還有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等國內法)的正當行為。
(三)捍衛主權獨立的反干涉作戰
“不干涉內政”和“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是武力使用的一項基本準則,但在實踐中這一準則不斷遭到惡意破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武力干涉他國內部事務的現象層出不窮。新時代的中國,為捍衛主權獨立可能進行的反干涉作戰主要有三種情形。第一種,自衛作戰中反對外國軍事干涉。例如,中國在爭議海域對構成侵略的國家進行自衛作戰,區外國家以同盟條約規定的“協防義務”為借口武力介入的可能性比較大。對這種于理無由、于法無據的武力介入,中國完全可以依法使用武力手段還擊。第二種,反分裂作戰中反對外國軍事干涉。當中國出現以武力方式制止國家分裂的法定情形時,某些大國極有可能以其國內法為“法律依據”進行武力干涉。他國所謂“依法保護”行為,明顯屬于違反武力使用規則的行為,中國完全有權依法予以武力反擊。從安全形勢看,這種情況最有可能出現在反“臺獨”作戰中。第三種,反“人道主義”軍事干涉。在反分裂作戰或自衛作戰中,中國都有可能面臨他國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他國以“人權”或“人道主義”為由對中國進行的軍事干涉,屬于嚴重踐踏武力使用規則的行為,中國軍隊有權依法進行軍事反擊。
二、自覺規制行為,樹立大國軍隊作戰典范
關于作戰行為,武裝沖突法從作戰方法和手段到人道保護進行了大量而具體的規制。對中國來說,依法規制作戰行為,不但是應盡的法律責任和義務,而且是負責任大國的應有風范。同樣重要的是,通過依法規制己方作戰行為,還能對敵方施加約束性影響,促成交戰各方更好地遵守作戰行為規則,最大限度減輕戰爭帶來的傷害和痛苦。
(一)實事求是的常規武器政策
常規武器是戰爭中運用最為廣泛的武器,接受有關法律規制,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切不可信口承諾“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束縛自己手腳。在有關常規武器的武裝沖突立法中,中國應當根據本國國情、軍情和世界形勢,充分表達中國關切,提出中國方案。同時,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立場,維護共同利益。如果通過各種方式都達不成意圖,可以選擇不簽署有關條約,或以保留條款的方式有條件加入。中國未參加《集束彈藥公約》《限制使用集束彈藥的議定書》《渥太華地雷公約》等常規武器公約,正是實事求是政策的具體體現。
(二)義薄云天的核武器政策
基于核武器在軍事上的超常威力和政治上的巨大效益,國際社會(特別是核武器國家)多年以來都未能對全面禁核達成共識,迄今也沒有一部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全面禁止核武器條約。①2017年7月聯合國大會以122票贊成的結果通過了《禁止核武器條約》,但中、美、俄、英、法、日、澳、印等國未參加投票。可見,該條約并未獲得有核國家支持,不具有“全面禁核”的實際效力和普遍意義。也就是說,中國并無單方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責任和義務。即便如此,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當天,中國政府就向世界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②《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載《人民日報》(號外),1964-10-16。,并堅持至今,即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2019年7月)。,充分體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義薄云天的國際胸懷和高尚道德。反觀美國等核大國,非但沒有做出類似承諾,反而把核作戰納入戰略、戰役和戰術作戰行動之中,明確主張使用核武器打擊敵作戰人員和軍事目標不構成違法作戰,并將其寫進各種軍事法規和作戰手冊。
(三)光明磊落的作戰行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九十多年的歷史中,都堅持光明磊落地以合法手段和方法打擊敵人,實施人道保護,有些甚至是在“不知有法”的情況下一種樸素的“人道”自覺。武裝沖突法關于依法作戰的一項基本規則,就是禁止背信棄義行為,即誘取敵人相信其在武裝沖突法上有權享受保護或有義務給予保護,并利用敵人的這一信任而危害敵人的行為。武裝沖突法有關條約列舉了大量背信棄義的典型行為,在中國軍隊中均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只有一條例外,即禁止在攻擊時“使用敵方的旗幟或軍用標志、徽章或制服”④《日內瓦四公約關于保護國際性武裝沖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第三十九條。。中國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對將此條列為“背信棄義”持有異議,認為在作戰中使用敵方有關標識物偽裝成敵方戰斗員以迷惑對手,并不會誘使敵方基于武裝沖突法的規定而產生信任并給予保護,不應歸于被禁止的背信棄義行為。⑤參見宋新平:《武裝沖突法》,79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6。
(四)優待戰俘的世界典范
中國軍隊素有優待戰俘的傳統,有關政策、法規及做法,甚至還優于武裝沖突法有關戰俘待遇的規定。從建軍之初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到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規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虐待戰俘罪”寫入刑法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工作規定》專門立法,從抗美援朝戰爭到對越自衛還擊戰,都體現出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優待戰俘的優良傳統,并堪稱世界典范。例如,抗美援朝戰爭中,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碧潼戰俘營,美軍戰俘在衣、食、住、醫等方面的待遇,比管理者中國軍官的待遇還要優厚,甚至有中國軍人為保護戰俘獻出生命。志愿軍的模范戰俘營引起了美國媒體、國際組織和戰俘家屬的高度關注,通過實地考察,他們稱贊中國軍隊的優俘政策“正如母親的心一樣”“具有真正的人道主義精神”,一致認為“沒有發現中國軍隊有任何違反日內瓦公約的地方”。⑥叢文勝:《法律戰經典案例評析》,81~84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三、堅持“結伴不結盟”,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一貫“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堅持“結伴而不結盟”“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旨在維護國家利益與世界和平、地區安寧,因而必然也必須是有底線的,絕不是更不能無所作為。當事態的發展對國家利益與世界和平、地區安寧構成威脅的特定情勢下,以適當方式、規模和程度介入國際安全事務,則是作為世界大國應該履行的國際義務,也是達成“結伴不結盟”宗旨必不可少的手段。對此,新中國早有抗美援朝等成功實踐。習主席指出:“我們捍衛和平、維護安全、懾止戰爭的手段和選擇有多種多樣,但軍事手段始終是保底手段。”①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7-08-01。在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致使國家利益緊密交融、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新時代,更應該根據實際情勢靈活實施“結伴不結盟”戰略,包括使用“保底手段”維護人類共同利益與世界和平。
(一)他國間(內)利益爭端引發戰爭時
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歷來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地區熱點問題,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對國家之間或一個國家內部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利益爭端引發武裝沖突或戰爭時,中國應本著“不結盟”的宗旨,或通過發表立場聲明等外交方式表示,反對使用武力,呼吁有關各方和平解決爭端;在聯合國安理會審議有關決議時投棄權票,表示不偏袒任何一方。幾十年來,對于兩伊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爭等多場國家間(內)利益之爭引發的國際性或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國都堅持這種態度和做法。
(二)聯合國采取或授權軍事行動時
聯合國采取或授權的軍事行動,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合法使用武力的情形之一,在國際安全事務中也有過幾次實踐。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當支持或參加聯合國采取或授權的軍事行動。如果將來因國際形勢需要,聯合國根據憲章行使武力使用權,依照合法程序通過決議,對某一國家或國家集團采取或授權會員國進行軍事行動,中國政府原則上應積極參與其中,或予以物力財力支持,或以“維和”等方式直接參加,為維護全人類利益與世界和平、地區安寧貢獻中國力量。2015年9月28日,習主席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對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莊嚴承諾:中國將出資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發展基金,加入聯合國維和待命機制,建立8000人的維和待命部隊。2017年這支部隊組建成軍并完成在聯合國的注冊工作,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所有出兵國中組建維和待命部隊數量最多、分隊種類最全的國家,展示了中國堅決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和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三)局部戰爭嚴重威脅地區穩定和安全時
當局部戰爭嚴重威脅地區穩定和安全時,中國可以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做出決策,動用軍事力量援助戰爭中的正義方,以維護人類共同利益與地區和平。這種援助,新中國成立之后有過較多實踐。其形式可根據戰爭規模、戰場形勢、自身實力、地理位置、正義方的需求等具體情勢靈活處置。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種,以國家名義派出軍事顧問、提供武器裝備、幫助培訓軍官、修建軍事設施等,如援越抗法。第二種,以國家名義直接參戰,派出軍隊協助正義方作戰,如援越抗美。第三種,不以國家名義而是以國民名義介入,組建“志愿軍”性質的武裝力量幫助正義方作戰,如抗美援朝。
(四)大規模戰爭嚴重危及世界和平時
當殃及廣泛地區和龐大人口的大規模戰爭嚴重危及世界和平時,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大國都會基于對本國和全人類共同利益負責的目的,或以人力、物力、財力支援正義集團,或直接出兵參加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都經歷了從中立到參戰的戰略轉變,大大提升了正義集團的戰爭能力。如果將來再發生類似大規模戰爭,中國應責無旁貸支援或加入正義集團,為維護人類共同利益與世界和平、地區安寧而戰。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加入戰爭時機的選擇將更為主動、及時,支援或參加的方式將更多樣、力度將更大。國富兵強的新時代中國,早已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國力羸弱的中國。那時的中國,弱國無外交,對危及世界和平的戰爭,無論是抗議、中立還是宣戰,甚至作為戰勝國的利益維護,主動權都始終掌握在帝國主義列強手中。今天和未來的中國,絕不會再受任何國家的影響、慫恿或脅迫,對支援維護人類共同利益與世界和平的大規模戰爭,完全擁有獨立自主的決定權和強大的行動力。
四、懲治戰爭犯罪,維護國家利益和人類正義
戰爭結束后對戰爭犯罪的懲治,根據有關武裝沖突法規定和實踐,包括國內懲治和國際懲治,二者相輔相成,共同完成對戰爭罪行的追究。未來可能的戰爭之后,中國應依法懲治敵方所犯戰爭罪行,以鞏固軍事勝利成果,達成維護國家利益和人類正義的最終政治目的。
(一)獨立自主進行戰爭犯罪國內懲治
國內懲治,指有關主權國家通過國家司法機關,依據有關國際法和該國刑事法律規范,對犯有戰爭罪行的人實施懲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國內實踐,主要是對侵華日軍戰犯進行的懲治,如沈陽審判和太原審判,共判決戰犯545人,其中處死刑145人。①參見李甫山:《我參與偵訊日本戰犯始末》,載《黨史博覽》,2008(5)。
未來可能的戰爭結束后,中國可根據具體情況,在國內特設軍事法庭或在一地或數地普通法院下設立特別刑事法庭,依法行使國家司法權,獨立自主對敵方戰犯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的非法干涉。向世界展示,中國不但具有維護國家利益和人類正義的強大軍事實力,還擁有懲治戰爭犯罪完備有力的法治。
(二)參與主導戰爭犯罪國際懲治
戰爭犯罪的國際懲治,指國際社會組建的國際司法機構,依據武裝沖突法、國際刑法等有關國際法及該機構章程,對嚴重戰爭犯罪行為進行懲治。中國參與戰爭犯罪國際懲治的實踐,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審判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將來中國參與和主導戰爭犯罪的國際懲治,可以采取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通過一事一設的國際刑事法庭。根據戰爭規模和戰后國際國內形勢,通過一事一設的國際刑事法庭進行懲治,任務完成后即行解散。法庭可由聯合國主導或經交戰各國及有關國家通過協議設立,可設于中國境內,也可設在戰犯國籍國境內,還可設在中立第三國境內。第二種形式,通過常設國際刑事司法機構。這一方式中,目前亟待解決的是中國與國際刑事法院的關系問題。國際刑事法院是當今世界上唯一常設國際刑事司法機構,管轄包括滅絕種族罪、反人類罪、戰爭罪和侵略罪等罪行。中國政府參與了其建立全過程,作出過重要貢獻,但在成立大會上對法院規約投了反對票,至今也未加入,關鍵原因在于規約未能滿足中國的重大關切。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應當重視發展與國際刑事法院的關系。首先,以其“觀察員”身份繼續保持與國際刑事法院的聯系和溝通。其次,在維護國家利益和國際法基本準則前提下,與國際刑事法院展開對話、磋商和談判,視情施加壓力。最后,促使國際刑事法院認識到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對戰爭犯罪國際懲治之重大意義,促成回應中國關切的規約修訂和法院改革,推動中國的加入,擴大法院的代表性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