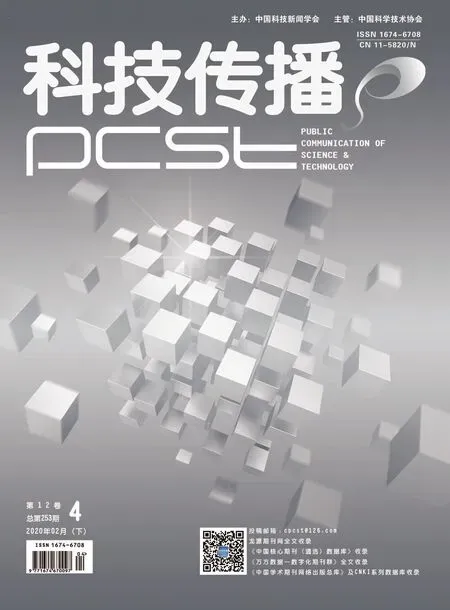淺析算法推薦對網絡公共參與的負面影響
羅雁飛,聶培藝
1 算法推薦與網絡公共參與
1.1 算法推薦
算法推薦系統技術基于計算機技術、統計學知識,將數據、算法、人機交互有機結合,建立用戶和資源的個性化關聯機制,在信息過載的時代,為用戶的消費和信息攝取提供決策支持。算法推薦目前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包括圖書、音樂、視頻、新聞、電影、地圖等。在新聞傳播領域,算法推薦被用作是一種分發形式,基于算法分析用戶喜好從而進行內容的推薦。目前其推薦方式有三種:
第一種基于內容的推薦。通過對用戶日常瀏覽的數據分析,向其推薦與該用戶既有興趣一致的內容或產品。
第二種是基于協同過濾的推薦。這種推薦機制是運用“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原理分別對用戶和物品進行協同過濾。若兩種不同種類的內容經常被同一用戶閱讀,這個時候算法會默認設定兩種內容之間的相關性,向其他閱讀過某一種內容的人推薦與其具有相關性的另外一種內容。
第三種是基于時序流行度的算法引入時間維度。通過考量某一時間的瞬時點擊率,同時綜合考慮新聞的信息熵等指標,將特定時間窗口內較為熱門的內容推薦給用戶。
1.2 網絡公共參與
公共參與是一種政治原則或實踐,也被視為一種權利。公共參與試圖尋求并促進那些可能受決策影響或對決策感興趣的人的參與。公共參與原則認為,那些受到決策影響的人有權參與決策過程,公共參與意味著公眾的貢獻將影響決策。公共參與可以被視為一種賦權方式,是民主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知識管理的背景下,正在進行的參與性過程的建立被一些人視為集體智慧和包容性的促進者,由整個社區或社會的參與愿望所塑造。
網絡公共參與是要以網絡公共領域作為話語空間,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公共領域,指的是一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是一種介于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旨在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公共領域具有開放性和公共性的特點,是和私人領域是相對的一對概念,自媒體時代的網絡公共領域呈現以下兩個特點:
1)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趨向融合。在這個傳統媒體的趨向勢微,新媒體的興起的時期,公共媒介空間被私人化,大量關于個人情感和糾紛的私人話題開始進駐媒介空間,大量無意義的私人話題侵占媒介空間,也是一種對媒介公共資源的浪費。私人空間公共化是公私領域界限消融的一個重要原因,具體表現為私人空間表現化和私人事件舞臺化。網絡的發展賦予個體話語權,在公共空間中充斥海量私人話語,擠壓公共話題空間。網民能快速切換身份與所處空間,公私議題能隨意轉換,公共事務能在私人對話中談及,私人事件也能放到公共領域進行討論,如此以來兩個空間二元分離格局被打破,公私領域趨向融合。
2)泛娛樂化削弱了公共領域的權威性和滲透性。按照心理學原理,刺激性、娛樂性信息更容易引起受眾的注意,進而形成注意力乃至注意力經濟。各互聯網媒體平臺(尤其是商業平臺)基于變現逐利的需要,在經營注意力方面不遺余力,導致整個互聯網媒體生態偏娛樂化。這種泛娛樂某種程度上在解構公共領域的權威性,妨礙公共話題的滲透性。
2 算法推薦對網民公共參與的負面影響過程分析
網絡公共參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筆者借鑒心理學的知覺過程“信息暴露——注意——解釋——評價”進行分析。網絡參與需要經歷“‘公域’信息暴露——網民信息注意——網民信息解釋——給出評價(或建議)”這樣的過程。算法推薦的后臺是信息技術,前臺呈現的是信息場域。以下將對這個過程中算法推薦對網民公共參與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一一分析。
2.1 “公域”信息暴露階段:精準分發導致信息窄化
目前很多客戶端,在其主頁上都有“推薦”一欄,這個“推薦”的區域便是算法推薦應用的區域。用戶通常愿意停留在自己的信息舒適區,關注自己感興趣的某幾個領域,參與的范圍較小。過去很多新聞網頁被分成很多個大的領域,如綜合、時政、經濟、軍事等,彼時對于不同的網民,他們所面對的網頁都是一樣的。媒體為了能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自己喜歡的內容,所做的就是盡可能的放更多更廣泛的內容在其中,網民可以按需選擇自己喜歡的領域進行瀏覽。而現在,雖然這些細分領域仍然能存在,人們卻只需要在推薦這一欄,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內容,不同的手機能夠看到的信息也是不同的,信息精準分發難免導致信息的暴露面或呈現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 信息注意階段:信息繭房導致視野窄化
如果說信息暴露階段主要從信息提供方的角度來看,那么信息注意階段,就是研究用戶如何對推薦的精準信息進行挑選。哈佛大學教授凱斯·桑斯坦提出了信息繭房這一概念,桑斯坦認為信息繭房以“個人日報”的形式呈現。伴隨著網絡技術的發達和信息的劇增,人們可以隨意選擇想關注的話題,可依據喜好定制報紙、雜志,每個人都可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個人日報”。當個人被禁錮在自我建構的信息環境中,生活必然變得程序化、定式化。而現在,我們身邊使用的客戶端都有算法推薦的機制,網民各自關注自己繭房內的內容,對于一些公共事件不管不問。這就使網民沉浸在個人議程中,不被公共議程所影響。公眾之間難以進行文化共享,從較長的時間階段來看,在構建集體認同和維系集體情感上,使大眾傳播喪失了社會化的社會整合功能。
2.3 信息解釋階段:協同過濾導致解碼圈層化
算法推薦除了基于大數據對用戶喜歡的內容進行精準推送外,還使用了一種協同過濾的機制,即它可以通過后臺的分析,將人們分為同類的人群,再向同類的人群去推送算法認為這類人群會喜歡的內容。這種按照標簽進行篩選的協同過濾機制會使同質化的人群繼續在同質的環境中生存,缺乏多元聲音的碰撞。喜歡參與公益事件的網民仍然參與公益事件,喜歡參與環境保護事件的人依然參與環境保護。跨群體之間的人們永遠感知不到其他群體的議程,形成了一種閉塞的、交流不通暢的網絡環境。
2.4 信息評價階段:沉默的螺旋導致觀點去多元化
網民進行公共參與的最后一個階段,也就是信息評價的這個步驟,算法推薦基于網民的某些習慣去推送某種傾向的觀點。這種觀點在擁有更多的支持者后螺旋式增長和龐大起來。而弱勢的觀點越來越趨于小眾,形成沉默的螺旋。而公共參與需要不同意見的人去發聲,多方利益的平衡,不同意見之間激蕩,才有利于實現網絡的自凈功能。只把相同的人推薦到一起,會導致多元化不足,削弱了網絡自凈功能。
3 以媒介素養教育應對算法推薦的負面影響
國內有學者將算法推薦導致的“信息繭房”稱為“信息舒適區”。“舒適區”是一個出自于心理學學科的概念,主要是概括那些在固有習慣、觀念、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心理定勢下,人們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心理舒適區。這個概念“移植”到信息接收上,受眾或多或少存在“信息舒適區”。網民們日漸沉迷在社交媒體中,而算法推薦這種機制又被各種社交媒體采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微信朋友圈”“微博好友圈”各類平臺中的“猜你喜歡”這種形式的內容都被看作是“信息舒適區”。
信息舒適區如溫水煮青蛙,讓網民慢慢喪失對公共話題的敏銳和熱情,政府和社會各方必須通過恰當的媒介素養教育幫助網民走出信息舒適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前主編雷恩尼和加拿大社會學家威爾曼2012 年所著《網絡化:新的社會操作系統》中提出了新媒介素養(Networking literacy)的要求,內容具體包括圖像處理能力、導航能力、信息的組織和聯通能力、專注能力、多任務處理的能力、懷疑精神及道德素養。國家以及重點高校可以聯合推出更多媒介素養相關的慕課,提高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和水平。媒體平臺方也可以在平臺上設置一些動畫和題目幫助網民參與到主動學習的過程中。對于特定的群體,也可以針對性地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比如針對青少年,可以考慮在目前學校課程體系中加入媒介信息選擇素養和媒介參與素養的相關課程。
媒介素養教育在當前這個每個人都使用媒介的時代中至關重要,網絡暴力、網絡謠言、網絡詐騙在我們的生活中并不少見,這需要從教育出發,對整體的網民素質進行系統地提升。
4 結語
大數據背后所依靠的算法,它的初衷是為受眾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但一不小心就結出“信息繭房”的實踐之果,受眾更傾向于關注自己感興趣和自己圈子范圍內的個人議程。本文主要就算法推薦對于網民公共參與的負面影響進行了探討和研究,通過解析網民公共參與的進程逐步分析了負面影響,并在引入“信息舒適區”概念的基礎上提出幫助網民走出“信息舒適區”的對策——網絡媒介素養教育,更準確地說是媒介信息選擇素養教育和媒介參與素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