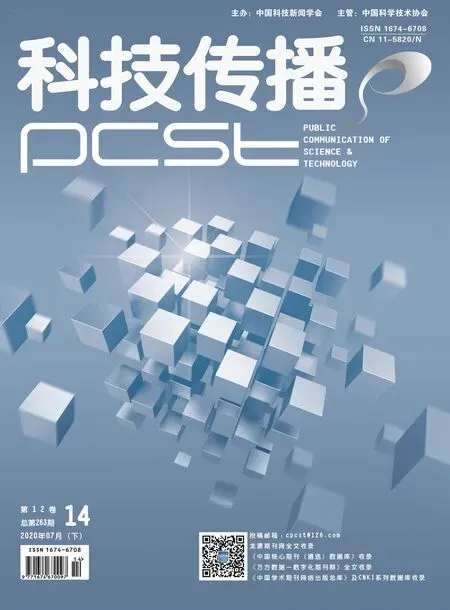消費時代藝術電影的市場化
——以雅各布森言語交際理論分析
張若瑾
“藝術電影”究竟如何定義?在不同的語境和市場環境下有著不同的界定和探討。在約定俗成的觀念里,我們習慣于把藝術片和商業片作為二元對立的存在,這種觀點讓我們在對于藝術片的關注點停駐于“非商業化”“非市場化”。電影是一直處于消費時代的產物,所以電影與市場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說電影的出現是為了表現更加真實的社會現狀,商業片和藝術片作為電影的兩種類型都是建立在生活之上,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商業片和藝術片受眾之差,這種差別是我們進一步探討藝術電影發展的重要問題。
1 以語言交際行為六要素建構電影
雅各布森提出語言交際行為六要素模式,他認為任何一個的語言交際行為都是基于六種因素之上構成的,包括發送者,語境,信息,接觸,代碼和接收者組成。情緒功能以發話者為中心,在發送者的態度之上傳遞給接收者情緒信息。接收者則傾向于對發送者的情緒進行捕捉與感知,獲得其感受和要求。想要準確捕捉這種情緒,要通過語境、信息、接觸和代碼的傳送。而當信息作為單純的表達本身,即強調文本本身和語言特征,那么傳播的詩性功能則會表達出來。因此不同的功能處于不同“主導”位置時,便產生了不同的文體。即使在一個交流系統中,任何一種功能都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織,關鍵是看誰占據主導性。我們從雅各布森的交際六要素中,進而可以考察“藝術片”這個概念是基于哪種功能主導的分類理據。
1.1 側重于發送者——電影創作者的意圖
我們將電影導演作為語言交際行為六要素中的發送者,導演創作的情緒功能,則是他個人的創作意圖。當下電影區分為多種類型,比如故事片,科幻片,喜劇片,動作片等。這些影片類型是由創作主體在一定的自身經歷和思考之下進行創作的,發送者決定創作的形式。
1.2 側重于接收者——電影觀眾的意圖
接受者在六要素中是具有意動功能的,這個意動功能是雙向而非單線的。曾經有學者對于雅各布森的交際模式呈現單線交際,僅僅是發送向接受的單相交流,忽略了接受者對于信息的參與度。當接受者已經作為語言交際中的一個符號,他作為整個交際過程的必備一環,已經作為主體參與整個過程。電影觀眾在選擇電影的時候具有完全的自主權,他根據自身需要如同購物一樣選擇自己期待的影片。因此在觀影過程中,影片的傳播內容和情緒發送,側重于接收者,具有強烈的意動性,需要接收者參與進來才能完全完成整改交際行為。
1.3 側重于接觸——電影傳播方式
在信息快速發展的今天,電影的傳播渠道早已不是單單局限在影院傳播、汽車影院、手機網絡、劇場等環境都可以完成接觸-交際的過程
1.4 側重于代碼——電影基本樣式
電影的基本樣式主要劃分為故事片、紀錄片、美術片、科教片等四大片種。
1.5 側重于文本本身
將電影的文本本身剖析為語境-指涉功能和信息-詩性功能。電影作為記錄場景的一個載體,本身是不具有故事性的,我們在電影中所看到的故事性是創作者通過蒙太奇語言傳遞給觀眾,觀眾通過感知和聯想進行豐富,從而完成了整個影片的藝術創作。在此以一段飛機失事的音頻為例,“語境”指的記錄下這場事故,而“信息”則是這段視頻的影像和聲音本身。那么語境的指涉功能則代表的是視聽本身,而信息的詩性功能則是視聽的代表物。
2 藝術電影的影像敘事
早期藝術片的定義是“二十世紀初為了對抗模式化的好萊塢商業影片而提出的概念”,因此模式化的認為某導演就是拍商業片、某導演就是拍藝術片,這種固化的模式思維并不能區分商業片和藝術片的本質,我們需要摒棄傳統的“藝術性”界定界限。
商業片和藝術片的區分,是以視聽符號的形式風格特征為區分的。同樣是分析一個語境的指涉功能,商業片和藝術片的信息闡釋上發生了變化。藝術片不以傳統電影的沖突-對抗-和解三段式現行敘事結構,而是以多線敘事或者交叉敘事等方式,因此在觀影方式上也與商業片產生不同。商業片強調將視聽本身當作敘事的載體,我們在觀影過程中可以直面的獲得信息,在理解后直接產生情緒,這個觀影過程是及時完成的,影片結束就意味著思考的結束;而藝術片則把重點放在了視聽的代表物上,它通過對于影像和聲音的認知,并不滿足于敘事而是強調在情緒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解,并且這種理解是非及時性的,影片的結束并不是思考的結束。這種區別導致了電影觀眾在觀看一部電影時接受信息的接受程度,當觀眾對直面獲得信息的快餐式的觀影模式成為一種習慣,再要求觀眾用一種藝術欣賞的方式去看藝術片,這種落差是很難調和的。
3 藝術電影的市場化
在談論藝術片的市場化時,應該具體地討論應該區分為藝術電影如何被市場接受,以及市場如何迎合藝術電影的到來,被接受和主動迎合這是一個相互的問題,被接受是需要藝術電影做出改變,而迎合的落腳點則在觀眾層面,這兩個對象是不能單獨分開討論的。
3.1 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共存的兩棲電影
如果我們選擇讓藝術片被市場接受,在不改變觀眾觀影模式的前提下,我們可以改變藝術電影的敘事模式。藝術電影的敘事缺乏故事性,使觀眾在觀看時因為大量的交叉敘事和碎片化處理在接受時顯得疲軟,理解起來更是晦澀。實際上,無論是商業片或者藝術都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但是商業片更遵循固定的創作原則,因此觀眾在觀看時可以有跡可循,但藝術片則大范圍保留導演個人思想的獨特性,并且在藝術呈現導演的個人思想,所以令觀眾不好理解。但是在提出消費時代下藝術片的發展這一命題,并且結合現實主義和藝術電影的特點,我們可以看到電影的藝術性和商業性是可以結合的。一方面對于類型片的模式進行尊重的繼承,另一方面則在繼承之上對其進行消解,融入導演的個人化思想,創作具有商業電影的外衣,藝術電影的內核的兩棲電影。
3.2 市場如何迎合藝術片的到來
市場是一個宏觀問題,市場是由觀眾組成的,票房不能完全決定一部電影的成功與否,但是也具有參考價值。藝術片這種重意義輕敘事,多哲理少趣味,更加隱含內在而拒絕直觀袒露的電影,是因為脫離了大眾的審美習慣才高居象牙塔,才使得市場在接受起來后繼乏力。雖然藝術片因為導演對于個人化的真摯表達和深刻的認知在中國電影藝術發展過程中占據不可忽視的位置,但卻因為觀眾的認知還處于一個比較低的階段無法理解,所以對大排檔的快餐文化津津有味的享受而忽略了藝術家們苦心經營的燕窩魚翅。沒有差距的藝術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高于生活的藝術,又如何提高觀眾的審美能力,藝術家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引導性的存在,如果這個引導都趨于大眾,那怎樣拉開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
4 總結
消費時代藝術片的市場化,我們既要求藝術片創作者需要保持藝術特征,不被類型電影同化,繼續挖掘社會現實,也要求觀眾在觀看電影時,當電影影像呈現出與潛在的文化認同的差異時,這種差異不應該局限于鏡頭語言、影像內容。如果說商業電影代表一個國家的電影文化電影商業的繁榮與否,那么藝術片應該是代表一個國家電影藝術的創造力的高低,它對于市場應該是一個藝術指向標,應該是起到指引電影藝術發展道路的作用。電影觀眾正面臨著欣賞水平和審美情趣的超越,只有藝術片和觀眾的共同超越,才能將二者的沖突減小,藝術電影才不會招致過分的冷落和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