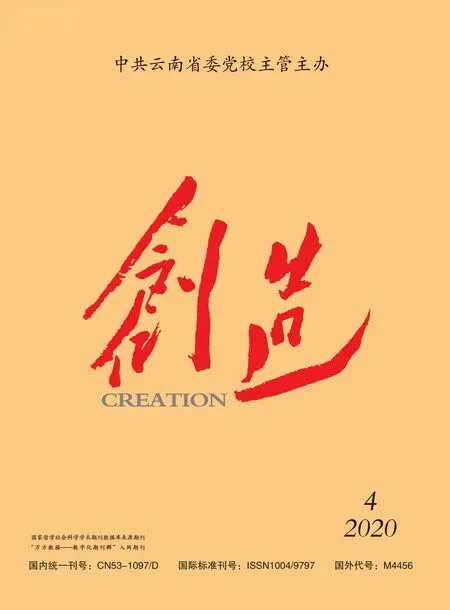儒家民族觀變遷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啟示
——以明清巍山文教發展為例
(云南師范大學 歷史與行政學院,云南 昆明,650500)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以下簡稱巍山縣)位于大理州南部,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云南省四個“文獻名邦”之一。早在西漢時期,巍山地區與中原政權就有了聯系,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朝征服滇國設置益州郡,在今巍山設邪龍縣,劃歸益州郡管轄。后在唐王朝的幫助下,巍山的蒙舍詔入主洱海地區建立南詔國,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封南詔國王皮邏閣為云南王,隸屬于中央王朝。寶佑二年(公元1254年),元朝滅大理國,巍山屬元朝大理萬戶府,后元朝在其控制區域置平緬宣慰司,巍山屬平緬宣慰司蒙舍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于蒙舍地置蒙化州,任當地土目左禾為土知州,巍山屬蒙化州。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明廷升蒙化州為蒙化府,清朝時期沿用明朝舊制,到清朝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依然沿用“蒙化”二字,只不過將蒙化府改為蒙化直隸廳。從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一直到民國時期,巍山一直稱為蒙化,由彝族土官左氏統治。在此期間,巍山地區人才輩出。本文選取明清時段,從中央政策的支持,左氏家族高度重視巍山地區的教育以及儒家思想的滲透等方面對明清時期巍山文教盛況進行初探,以史為鑒,繼往開來。
一、明清時期巍山文教盛況
明清時期,巍山地區教育發展主要體現在廟學的發展、書院的正規化、義學的興起、經堂教育的成熟以及科舉人才輩出。
(一)廟學的發展
儒家思想自漢朝以來,一直作為國家的正統思想。國家興辦教育,特別是在明朝成化以后,科舉考試以八股形式進行,八股文的試題出自“四書五經”,應試的人必須按“四書五經”的歷代圣賢立言,依據格式填寫。巍山地區因此不可避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最具代表的就是當地的文廟。
文廟亦稱孔廟,是儒學文化的載體,是古代人為了祭祀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而修建的廟宇。據史料記載,孔子死后第二年,魯哀公下令將孔子故里的故宅三間改作廟堂,歲時奉祀,此為孔廟之始。府學則是古代府級行政機構為培養人才而興辦的學校。唐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詔令“州縣學省立孔廟”。從此,文廟與縣學、府學合二為一。宋承唐制,元、明、清三朝州縣修建文廟之風仍盛,蒙化府學文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興建。據明代《重修蒙化府儒學碑記》 載:“是故,殿則丹楹刻龍,肇以金飾”,可以看出當時在文廟建設中投入了較大的物力財力,才使它具備了相當規模。截至清乾隆統治之前,巍山為蒙化府,故稱作府學文廟。文廟的建筑規格及布局除遵循基本禮制外,更與當時當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狀況,特別是與地方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推崇程度密不可分。府學文廟建成后,每年都要舉行盛大的祭孔儀式,文人墨客云集。廟學的興起興盛,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巍山地區的儒家思想的接受和滲透程度。
(二)書院的正規化
書院是顯示蒙化時期當地教育興盛的另一大代表。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文化組織形式,它集人才教養、學術創新、文化傳播于一體,在中國文化傳承歷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云南考試史》記載“古代的書院發端于唐代,勃興于宋代,大行于明清,云南雖晚于內地,書院的建立起源于明朝,但建立甚多,分布甚廣,育才甚重”。[1]
明清時期,統治者在云南推行儒學,各州府建立起許多學校,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蒙化土知府左銘在巍山城北邊創建了“崇正學院”,為縣內第一所書院,后廢。嘉靖年間,通判吳紹周重新修葺,并增建了武侯祠、尊經閣講堂及八蠟祠。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紳士等人增修城內東南角文昌宮大門牌坊忠孝樓。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0年),教授盧镎又新建樓房、廚庫、書室。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同知黃大鶴和郡紳籌集薪資聘請院長,開始招學生上課,自此文昌書院建立,不幸的是它在咸豐年因戰爭焚毀。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同知蕭培基在城外東北角舊玉皇閣的故址上進行改建,因為建在文華山麓,所以取名文華書院。建造初期修建了藏書樓、魁星閣、兩廂大門等建筑,內部開鑿了泮池,在建造還未全部完成的時候,蕭培基因任期已滿而被替換,接任的是夏廷燮。夏廷燮繼續修建文化書院,在閣外修廊舍,在泮池后建雁塔坊,在南澗添設毓秀書院,在大倉添設文明書院,漾濞添設瓜汀書院等,大力嘉獎人才,可謂不遺余力,士子學習的風氣一直不變。
《蒙化志稿》中有同知黃大鶴新建文昌文院碑記:“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故教學之地,與學之所資可不隨在而立。古之善學者,其入之者以漸,其取之也務精,然必擇清遠間曠之所,使耳目心思之用,有所斂而不紛,而后奮發有為之氣,畢注于是弗懈,而能及于古。”[2]
明清時期,隨著中央政策的推廣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進步,巍山書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先后建立了崇正學院,文昌書院,文化書院等。書院教育以儒家思想為主,推廣了儒家文化,消弭了巍山地區民族之間的隔閡,有力地促進了文化的傳播,還在培育人才、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端正民風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義學的興起
義學也稱“義塾”,是指中國古時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設立的蒙學。義學的招生對象多為貧寒子弟和少數民族地區學子,讓他們免費上學。義學在宋朝就出現過,但主要以宗族為單位,僅限于教授本族子弟。明清時期,義學有了較大的發展,特別是在清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下,義學在全國各地廣泛設置。清朝義學的發展,為蒙學教育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機構保障。在全國大興義學的背景下,明清時期的巍山義學也有了很大發展。
明朝建立后,在全國范圍內大興教育,義學發展迅速,天啟時云南有社學163所。清朝義學在云南各地分布較廣,順治時期朝廷下令在全國各地設立社學,主要分布于漢族地區的城鄉,以后義學大量出現,多設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清庭批示:設曲靖、澄江、廣西、元江、開化、順寧、武定、景東等八府府學,在尋甸、建水等十七州設訓導員一員,是清朝規模較大的一次興學。康熙年間云南府廳有義學八百六十六所,蒙化府廳有三十五所。《蒙化志稿·義學篇》 中寫道:“蒙化義塾,舊設一十三館,曰城南社學(即舊德育書社,為明廣西左江道兼提學道宣庭式舊宅,康熙間通知張善化改建,紳士孫縉、張景蘊、陳凱等協修,后同知陳文成復延師立義學于內,并置田產,以為生童薪火資),曰城北社學(即舊育英社學,明崇禎時,同知朱統遂及紳士籌建,后李沛、金逢泰、姚鳳儀增修,光緒中又建先師閣于后),曰啟蒙義館(光緒間同知夏燮提租谷入學),曰興文義學,曰北橋義學,曰落馬莊義學,此外則漾濞、南澗、公郎、云川、白川、大倉均置一館,房舍田租罔弗備……光緒初同知蕭培基撥上川回產二百九十六石三斗為束修費,初設九館,后同知夏延燮、卞庶凝先后又添設二十五館,計近城十約,中三上四約,并西外子午兩約共二十館,公郎五館,蒙鄉三館,云川、白川、新鄉、馬來廠。”[3]可見明清巍山地區義學之興盛。
明清時期,巍山地區義學分為官建、民建和官民共建等類型。官建由政府出資興辦,塾師束脩從國庫中支取。民建的形式多樣,多是通過民間捐田、捐銀、捐房設立,教學經費和塾師束脩主要從公款或公田中支取。義學教學內容較為淺顯,針對大部分兒童的學習水平而定。總體而言,主要分為三部分:讀書識字、普及文化知識和傳統道德。有基本的日常起居禮儀教學活動,有識字類的《千字文》 《百家姓》《三字經》 等,有道德規范類的《圣諭》 《小學》、《弟子規》等,還有傳統儒學經典“四書”等,另外還有一些天文、地理、水利、農田、史學、算學等方面內容。多樣的辦學方式和基礎的知識教育促使義學在巍山地區大量建立,這些義學招收少數民族和貧困子第入學,無疑促進了巍山少數民族的蒙學教育發展。
(四)經堂教育的成熟
回族是巍山的主體民族之一,其教育是巍山教育的重中之重。巍山回族的經堂教育作為少數民族教育的一部分,在明清時期走向成熟。
元明時期,忽必烈、沐英等掠徙至滇的回回軍、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亞各族人發展為境內的回輝登、大圍埂、小圍埂等18個回族村寨,他們信仰伊斯蘭教,由回民集資辦“阿文”學校,其中以小圍埂為代表開辦經學較早。至明代萬歷年間,小圍埂的經堂教育發展到了繁榮時期。首先經堂教育完善了小學、中學、高中的學制。小學七歲入學,主要學習28個阿文字文和《雜學》。中學14歲入學,主要學習阿文字法、文法,開始學習《古蘭經》。高中18到20歲,主要學習《文法》 《語法》 《古蘭經》 等著作。其次村中有志振興教門的學子遠赴陜西進行求學,馬舉就是其中之一。馬舉,回族,字子化,巍山縣水建鎮小圍埂村人。明代著名開學阿訇,云南經堂教育的最早播者之一,被尊為“五老師祖”。他曾兩次前往陜西求學,從陜西學成而歸,回到小圍埂村執教,并到全省講學,弟子遍及各地。
(五)科舉人才輩出
科舉制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士人用功讀書的風氣盛行。巍山地區的鄉試舉人這一等級頭銜始于永樂年間,進士始于成化年間。《蒙化志稿》中記載,從永樂到崇禎這284年里,巍山地區有進士8人,舉人有84人。清朝一代,巍山地區進士有15人,舉人有136人。代表性人物如:
張錦蘊,字允懷,蒙化人,貢生,清康熙年間中科舉,擔任景東訓導。一生勤于筆耕,注重文書傳播,在沒有蒙學教育講義的情況下,新編四書講義。康熙丁未年受聘編修《云南通志》,協助蔣旭完成康熙《蒙化府志》。他的主要文學作品有《黑云草》 《學庸輯端》。
彭古印,詩人,被譽為“滇西三絕”之一,明清時期經考試錄取而入府、州、縣各級學校的生員,著作有《松溪集》。
朱璣,字文瑞,號恒齋,祖籍北京永平府灤州人,落籍云南蒙化衛(今巍山縣)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進士,明代正德間官員,官至大理寺評事。
……
明清時期科舉制以儒家文化為核心,讀書人必然以儒家經典為學習的主要內容,巍山地區廟學興盛,側面反映出巍山地區儒學的發展和學習風氣以及教育風氣的濃厚。
二、明清時期巍山文教盛況原因分析
明清時期巍山文教盛況的緣由可分為明清時期的中央政策的支持,“左氏”高度重視巍山地區的教育,儒學思想的滲透三方面。
(一)中央政策的支持
明清中央政策對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的支持是這一時期巍山文教發展的重要原因。明朝是我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時期,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從元朝滅亡中悟出道理,必須將教育作為強國的重要途徑,將發展教育事業置于重要的地位,從而提出“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廣設學校,設立社學,提高全國受教育的范圍,增加全國受教育人數,為國家培養人才。另外,明朝將科舉制的地位提高為國選拔人才,以此來激勵人民參與受教育的熱情。清朝吸取明朝的經驗教訓,加大全國教育的力度,順治十三年(公元1655年),為了興盛教育,確立了“興文學,崇經書,以開太平”的文教政策,提倡尊孔與程朱理學,重視科舉與武舉的固定設置,增加出仕為官的次數,武科也同步進行了改革。這樣既提高武舉的考試地位,又興起一股“凡為士均通過科舉之途”的學習風氣。中央提高了科舉考試的難度,使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也相應改變學習態度,促進教育的發展。并且清朝時期廣興學校,教育場所的規模進一步擴大,給讀書人以良好的學習環境,在地方上設立一個專門管理教育的官職,保障教育事業的穩定發展,還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義學、社學、井學等。
巍山地區在這一時期開始大力發展教育,建書院,講廟學,興義學,在中央頒布的教育福利制度下,巍山地區的人民也更愿意進學校受教育。當地人應國家號召,順時代背景,遵循國家之制度,使巍山人愿讀書,讀書人樂讀書,從而推動當地的教育發展,使得巍山教育欣欣向榮。
(二)左氏高度重視巍山地區的教育
今天我們研究明清時期巍山文教興盛的原因,左氏家族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為中國古代的教育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政教合一”,政治與教育緊密相連,具有一致性,表現為教育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為政治服務,教育與選拔政治人才緊密結合,教育直接通往政治,官學中以吏為師、官師合一。左氏作為明清時期巍山地區的管理者,對巍山地區的教育有著很大影響。
左氏家族興起于明太祖朱元璋征討大理段氏,左氏為征討段氏立下了大功,受到了明朝的嘉獎。明代《土官底簿·云南土司》 記載左禾歸附時言:“蒙化府知府左禾,大理府蒙化府蒙化的羅羅人,系本州火頭,洪武十五年大軍克服,仍充添摩牙等村火頭,十六年正月投首復業,總兵官擬充蒙化州判官,十七年實授,續該西平侯奏,據里長張保等告保,左禾受任二十余年,夷民信服,乞將升任。永樂三年,奉圣旨,他做判官二十余年,不犯法度,好生志誠,升做著他封印,流官知州不動,還掌印,欽此。”[4]《天啟滇志》 也記載說:“蒙化府土舍左禾,蒙城鄉添摩牙里人,其先有左青羅者,元為順寧府同知,傳至禾為九部火頭,順寧司通事。洪武中,平云南,仍以禾為火頭,后大兵征,高天惠等逃竄,禾遂招諭蒙化的人,得受州判官”。這些史籍記載說明,明軍傅友德、沐英平蒙化和大理,利用彝族上層分子左禾打擊了當時的反抗者白族貴族段、高二氏,左禾趁機發展了自己的勢力,并驅逐了自宋元以來就進入巍山的白族統治勢力,以彝族世襲封建領主制取代了白族世襲封建領主制的地位,開啟了對巍山地區世襲的統治地位。根據《中國彝族譜牒選編·大理卷》中記載,“明清時期左氏土官一共承襲17代18人,明朝十代11人,清朝七代7人”。[5]左氏在家庭教育方面也很成功,在明、清兩朝一共出了進士3人,舉人8人,選貢3人,副貢7人,也側面說明了左氏對教育的重視。
明清時期,中央與巍山地區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就使得中央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巍山地區產生很大的影響,在“儒學教育發展”,“衛屯田制度推廣”的影響下,左氏統治“文攻武略”的特點愈發突出。《巍山彝族簡史》記載“從明弘治年間后,先后襲職的左正、左文臣、左柱石、左近蒿、左星海、左世瑞、左嘉謨、左麟哥、左元生、左長泰、左蔭曾等11任土知府,都先后在明、清朝廷設立的各類學堂學習深造過,所以儒學造詣都比較高。以文采出眾、偏重以文治政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左正和左星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6]
儒家注重教育,統治者深受儒文化的影響。因此,左氏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會低。此書還曾記載“左正及其后的土知府都很重視做好發展地方文教事業的工作。一方面積極致力于興建文教設施,修葺佛、道寺觀的倡議,捐資和組織工作。另一方面督促、鼓勵地方子弟人學接受教育,考取功名。嘉靖年間,左正捐資并組織重修了文廟學官,左柱石在上任期間組織興辦了明志書院”。[7]在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的《萬歷云南通志》中記載“成化間,土官舍人左、義官張聰各捐貲重修,弘其規制,易儀門為尊經閣”。[8]從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左氏對廟學、書院的建設很是投入。在古時,廟學、書院是教育的主要場所,這從側面表明了左氏對教育的重視。《萬歷云南通志》記載“一時,世守左軍、鄉縉紳及好義者,亦各以私錢贊助,聚木陶甓,聚食召公,拓書院之隙地以建侯祠,因建祠之余材以補書院。為屋有間計者,凡五十有六,完舊者曰杏壇殿、曰大門、曰學文齋、曰修行齋……曰主進門、曰行恕門,大門之外,鑿池尋泉為泮。規制既備,合而名之曰明志書院”。[9]由此可知,巍山地區的人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很高,在學校建設的過程中紛紛出錢出力,為教育作出自己的貢獻,形成了注重教育的良好風氣。而這功勞左氏有一半的功勞,正是左氏教育者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注重教育,鼓勵百姓學習,加強百姓的教育。最終使得明清時期巍山地區人才輩出。
(三)儒家思想的滲透
巍山文教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儒家思想的傳播與滲透。文廟與儒家文化的關系至為密切,作為儒家文化的聚合場,文廟將文化集團、文化精英、平民階層以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式聚合在一起。作為儒家文化的輻射源,文廟為官方向民眾傳達國家意志和主流話語提供了平臺。作為正統儒學的最高殿堂,文廟傳授正統的儒學,培養了一大批儒家人才。
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在中慶路(今昆明市)建成云南第一座文廟。后來,文廟招收的學生中不僅有官宦子弟、平民子弟,而且有少數民族子弟,明代還明確制定了向“土著之人”傾斜的政策。文廟是行使公共職能的官辦機構,因此官府要正式委派官員主持工作,府級文廟之教授,州級文廟之學正,縣級文廟之教諭,均由儒學之士充任。從支渭興《重修中慶路廟學記》可知,在定期舉行的祭孔大典上,參與者有由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率領的崇儒重道的龐大官僚集團(由于中國推行以科舉取士的文官政治,因此他們幾乎都是飽學詩書后科舉入仕的儒者),有飽習儒學之教官,有渴求儒學的莘莘學子,更有“充庭塞戶”的當地民眾。此時此刻,文廟不僅是祭孔圣地,不僅是宣揚“美俗柔遠之道”的“士夫講肄游息之所”,更成為各層級儒士及儒家文化追崇者大聚會的場所。他們當中既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既有外來移民,也有土著民。文廟成為“萬姓瞻依之所”他們聚合在一起的基礎是擁有共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儒家文化。
明代《重修蒙化府儒學碑記》中可以看出,巍山人對廟學的重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主張“仁政”,“仁者,愛人”,“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仁義之根本為孝悌。儒家主張入仕,認為君子理應考取功名,為國效力。隨著廟學的發展,儒家思想更加地深入人心,認為君子理應考取功名,為國效力,讀書人的數量隨之增加,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也在上升,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在明清兩朝不計其數,在全國各地任職。當地人受到教學風氣的影響,認同教育的積極作用。眾所周知,巍山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自然與內地有所不同,使巍山人認同中原地區的思想文化難度較大。《蒙化志稿》記載,巍山地區的職官從開始時的任命到后來將儒學作為任命的條件之一,再后來加入了陰陽學、醫學等作為官職的條件,所以沒有讀過書的人卑微無比。這樣一來,不僅能夠讓中央可以更好地管理邊疆地區,還讓當地人有了讀書考試做官的意識,進一步促成當地的好學之風。
三、研究明清時期巍山文教盛況及原因對今天的啟示
巍山是我國西南邊陲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明清時期教育發展、人才輩出。研究明清時期巍山文教興盛出現緣由的目的,不僅僅在于了解當時的情況,更重要的是給今人以啟示:
第一,積極發展邊疆少數民族教育。巍山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邊陲名城,彝族和回族是其主體民族,所以發展民族教育是其教育的重中之重。明清時期,中央政府大力支持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巍山的文教走向了空前的繁榮。在彝族左氏家族領導的五百多年里,巍山一直服從中原王朝的領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這啟示我們:教育興則民族興,民族興則社會興,社會興則國家興。積極地發展邊疆少數民族教育有利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有利于民族團結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第二,大力發展公平教育。教育權利的不平等是從古到今普遍存在的問題,表現為階級的不平等、民族的不平等和男女的不平等……明清時期,巍山在左氏家族的領導下,公平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具體表現為:首先是文廟的興建,傳播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原先進文化,整個社會好學之風蔚然興起。然后修書院、考科舉,使天下有識之士都可以考取功名,實現人生抱負。最后是大力發展義學,讓貧困子弟和少數民族子弟免費入學。這啟示我國應該合理分配教育資源,積極促進教育公平,促進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
第三,凈化學術科研環境。明清時期蒙化地區的讀書人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強調“士”氣,為人達觀開朗,笑對人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書院既是教學組織又是學術研究機構,不拘束于一家之言,出現了百家爭鳴之盛況,有利于文化的繁榮。這啟示我們要凈化我國的學術科研環境。首先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保護知識產權、尊重他人勞動和權益,維護學術評價的客觀公正,建立良好的學術環境。然后要建立健全工作機制,防止學術人員世俗化、學術成果“大躍進”等不良現象的產生。制定切實可行的學術行為規范體系,重塑學術道德理念和學術道德原則,形成良好的價值導向。
第四,大力推進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傳承和發揚。明清時期,巍山的教育以倫理教育為主,顯現出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點,這促使巍山文化發展,形成了高尚的道德準則、完整的禮儀規范和優秀的傳統美德。這啟示我們應該積極開展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推陳出新的原則,把我國建設成文化強國。
結 語
明清時期的巍山地區,教育迅速發展。究其緣由可分為明清時期的中央政策積極發展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統治者左氏高度重視巍山地區的教育,儒學思想的滲透等三方面因素。通過對明清巍山教育問題的研究,我們應認識到利用教育進行精準扶貧是脫貧的重要途徑。
首先,發展教育有利于轉變少數民族群眾思想觀念。受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緩慢,一些群眾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觀念,一定程度上導致這些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難以快速提升。大力發展教育,讓少數民族地區一些群眾轉變落后思想觀念,將開放發展意識、開拓進取意識潛移默化地融入少數民族群眾的思想觀念之中,順利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
其次,發展教育是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群眾整體素質的現實需求。受文化素質偏低的影響,在我國文盲和半文盲群體中,少數民族群眾占據著較大比例。基于此,做好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精準扶貧,不斷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群眾的文化素養,對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將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