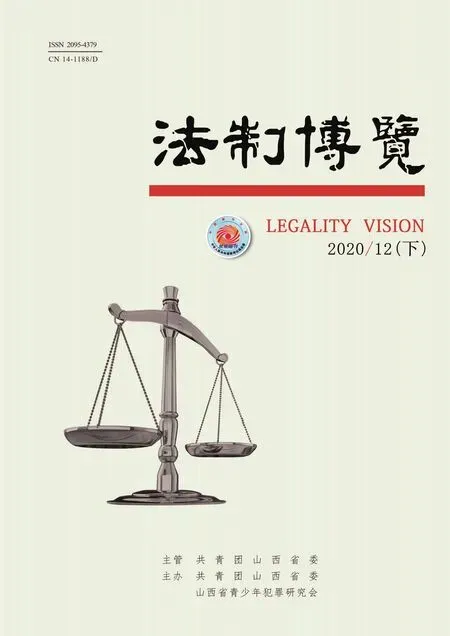繼承合同制度初探
姚 遙
江蘇省南京市南京公證處,江蘇 南京 210000
繼承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享有重要的地位,是財產流轉的主要形式之一。隨著我國公民的私有財產不斷增多以及法制觀念的普及,通過個人意思對扶養、身后財產分配及相關事宜進行安排的需求也不斷增多,甚至成井噴之勢。我國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以下簡稱繼承法)對此提供了三種方式供當事人選擇,分別是遺囑、遺贈和遺贈撫養協議。但是,遺囑、遺贈均屬死因行為,于繼承開始后才發生效力,且立遺囑人生前可以單方修改、廢止,不具有穩定性;遺贈撫養協議雖然于訂立時生效,且被撫養人生前不能單方任意修改,但只能和被扶養人的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體訂立。在司法實踐中,許多被繼承人會在生前與繼承人簽訂協議,內容大多包括對被繼承人的扶養事宜的安排和對遺產的處置。但因缺少相應的法律規定,法院對于上述協議的效力認識各不相同,因協議被判決部分無效導致盡到贍養義務的繼承人無法取得約定的財產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基于此種現象,我國可借鑒相關的外國立法例中的相關制度,建立繼承合同公證制度來滿足社會需要。
一、繼承合同的概念
繼承合同在國外也被稱為繼承契約,目前國外對于繼承合同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種,分別是肯定立法、否定立法、折中立法。由于繼承合同起源于日耳曼法,故受日耳曼法影響較深的國家如德國、瑞士、匈牙利均對繼承合同抱持肯定的態度。而受羅馬法影響較深的國家如法國、意大利,以及禁止共同立法的國家如日本、捷克、西班牙,均對繼承合同予以否定態度。折中立法主要是英美法系國家的立法模式,其與肯定立法的區別主要在于:在肯定立法模式中,繼承合同可以直接作為繼承的依據,而在折中立法模式中,繼承合同無法作為遺產繼承的依據,如果要繼承遺產還需被繼承人依照繼承合同的約定另行訂立遺囑。
目前我國學界對繼承合同并無統一認知,而對繼承合同持肯定觀點的國家的相關法律規定也各不相同。德國的相關法律規定,被繼承人可以以繼承合同的形式設立遺囑、遺贈以及繼承財產的條件,并且受益人可以是合同的相對人或第三人。匈牙利的法律則規定,被繼承人可以通過繼承合同指定合同相對人為繼承人,相對人負有扶養繼承人的義務。瑞士有關繼承合同的規定則與德國類似。通過分析可知,以上各國雖然對繼承合同的立法各不相同,但對于繼承合同應當充分實現被繼承人處分遺產的自由及發揮扶養功能的理念,則基本一致。因此,筆者認同部分學者的觀點,即:繼承合同應是被繼承人與繼承人或者繼承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體就繼承人、受遺贈人的指定,遺囑、遺贈負擔的設定及繼承權拋棄等內容所訂立的合同。
二、繼承合同的法律特征
根據上述繼承合同的概念,繼承合同應當具備以下特征:(1)繼承合同是雙方或多方民事法律行為。(2)繼承合同具有諾成性,雖然涉及遺產繼承的內容無法立即執行,但不影響繼承合同自各方民事主體達成合意時成立。(3)繼承合同可能是雙務合同,也可能是單務合同,這要由繼承合同的內容來決定。(4)繼承合同是要式法律行為,即繼承合同只有在符合法定形式和程序的情況下才能成立。(5)繼承合同的效力具有優先性,即同時存在遺囑、遺贈、繼承合同的情況下,繼承合同的效力優先。
三、繼承合同與遺贈撫養協議的區別
繼承合同目前在我國并無法律規定,不過我國現行《繼承法》中的遺贈撫養協議與繼承合同非常相似。有學者指出,由于我國已經規定了遺贈撫養協議,不需要引入繼承合同制度。但筆者認為,繼承合同與遺贈撫養協議還是有相當的區別的。其一,繼承合同的合同主體沒有限制,而遺贈撫養協議的扶養人只能是除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公民或集體。其二,繼承合同的內容包括設立遺囑、遺贈,為合同各方設立權利和義務,放棄繼承權等等,可以涵蓋被繼承人的生養死葬及遺產處置的所有事宜;而遺贈撫養協議的內容僅包括扶養人負有對被扶養人盡到生養死葬的義務,同時享有受到遺贈的權利。其三、繼承合同的收益人可以是合同的相對方或第三人,而遺贈撫養協議的受益人只能是扶養人。其四、繼承合同可以是雙務合同,也可以是單務合同,而遺贈撫養協議則必然是雙務合同。縱觀上述比較,遺贈撫養協議制度完全可以被繼承合同制度所取代。
四、我國建立繼承合同制度的必要性
筆者在從業過程中,大量遇到這種情況:在多子女的家庭里,由于各個子女的情況各不相同,有的條件好,有的條件差,有的住在外市、外省,對老人扶養不便,有的與老人共同生活照顧方便,不可能做到每個子女都盡到相同的扶養義務。而《繼承法》中所規定的遺贈撫養協議和遺囑制度無法解決此類問題。首先,由于扶養人系被扶養人的法定繼承人,不適用遺贈撫養協議制度;其次,由于遺囑、遺贈系單方法律行為,其修改、廢止無需經過受益人同意,在受益人盡到扶養義務的前提下,一旦被扶養人修改、廢止遺囑,受益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基于這種情況,老人與子女就簽訂協議,內容是由某位條件較差的子女與老人同住,老人的生活起居主要由其照顧,其他子女輔助,而等老人去世以后,遺留的遺產則由這位扶養較多的子女繼承。然而,相應法律規范的缺乏導致法官對于繼承合同的認知也不相一致,相關判決中,有些繼承合同被認定無效,有些繼承合同被認定是一般民事協議,有些則被認定為遺囑。如此既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性,也阻礙了法律的指導、預測與化解糾紛職能的實現。筆者認為,繼承合同制度在我國應當存在與否已經不值得討論,當務之急是盡快建立繼承合同制度,出臺相應法律法規,對現存的大量繼承合同予以司法層面的定性,并對潛在的簽訂繼承合同需求給予法律層面的引導和規范。
五、繼承合同與公證
繼承合同所涉及內容極為廣泛,基本涵括繼承中的一切問題,一旦成立對合同各方都會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然而,普通民眾大多缺乏相應的法律知識,所訂立的繼承合同內容往往漏洞百出、不具備可行性,最終導致合同相對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進而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糾紛。因此在肯定繼承合同的外國立法例中,無一例外都對繼承合同的成立作出了嚴格的形式要求,確保繼承合同形式規范、內容嚴謹、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充分保障。例如德國、瑞士的法律均規定,繼承契約必須經公證方可生效。在我國,公證制度作為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具有預防糾紛、化解矛盾、保障法律實施、維護法律秩序的作用,經過公證的文書具有證據效力、強制執行效力和法律行為成立的要件效力。由于繼承合同可能變更繼承關系,涉及利益重大,由公證機構對繼承合同的真實性、合法性、可行性進行審查,才能最大程度保護繼承合同各方的利益,發揮繼承合同應有的職能。因此筆者認為,我國一旦建立繼承合同制度,也應當嚴格限制繼承合同的形式與成立要件,即繼承合同必須采取書面形式,且必須經公證后生效。
六、結語
隨著我國民眾的私有財產不斷增多,通過個人意思對扶養、身后財產分配及其他相關事宜進行安排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在現有的遺囑、遺贈、繼承撫養協議制度已經無法滿足社會需求的情況下,通過新設繼承合同制度滿足需求,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如何設計繼承合同的相應規范,如何讓這項舶來的制度在我國的土壤中生根發芽,將是我們法律人即將面臨的下一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