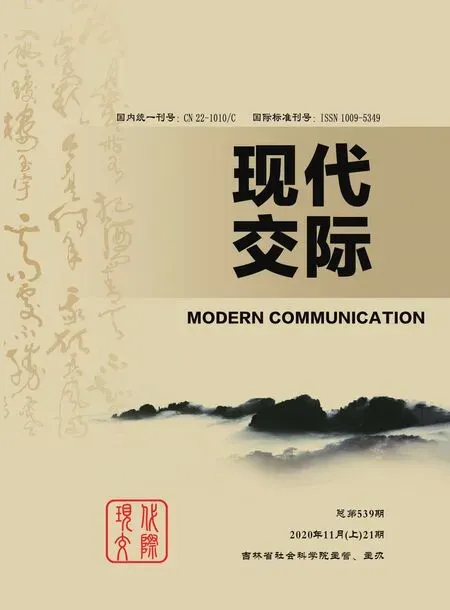Brown和Levinson禮貌理論及其局限性述評
董熙平
(悉尼大學 新南威爾士 悉尼 NSW 2006)
在日常的交際與互動中,我們不僅從事某項任務,還在人際關系中扮演不同角色。在這些互動中,參與者通常采取不同的策略,以進行有效溝通,避免潛在的問題。面子(face)幫助我們理解人際關系中的角色是如何被制定、保護和威脅的,從而解釋我們在交際中存在的一些言語行為。在所有的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是Brown和Levinson(1987)的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雖然這一模型已成為最經典的范式,但仍有許多理論家批評甚至重新定義它。本文將首先討論“面子”的概念,然后總結Brown和Levinson禮貌理論的主要觀點并探討該模型的優勢與局限性。
一、面子的概念
“面子”的概念是在19世紀末從漢語中借用到英語中的。Goffman首先把這個概念引入學術英語語篇。根據Goffman(1967)的說法,“面子”是人們有效地為自己主張的積極的社會價值。換句話說,“面子”是每個人在與他人社交互動時試圖保護的一種公眾形象或身份。Brown和Levinson(1987)將“面子”定義為兩種類型:積極的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極的面子(negative face)。積極的面子指的是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與他人建立聯系;消極的面子包括自主性和獨立性,即不被別人強加或強迫。Brown和Levinson(1987)認為,面子的這兩個方面在人類文化中普遍存在,面子的概念成為他們提出禮貌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心支柱。
二、Brown 和 Levinson的禮貌理論
積極的面子和消極的面子是所有交際行為的基本需求,需要參與者之間的合作來維持彼此的“面子”(Brown &Levinson,1987)。然而,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行為會威脅人們的面子,這就是所謂的“面子威脅行為”(face threatening acts,FTAs)。Brown和Levinson(1987)認為,在對各種面子威脅行為進行分類時存在兩個維度:威脅積極面子與消極面子,說話者與傾聽者。例如,像“關上門”這樣的命令和要求,違背了傾聽者不愿被別人強迫的愿望,從而威脅了傾聽者的消極面子。
為了減少和消除這些面子威脅行為,Brown和Levinson區分了三種主要的言語行為策略:積極禮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消極禮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和非公開禮貌策略(off-record politeness strategy),從而建立了一個系統的模型來識別和區分不同形式的禮貌策略。積極禮貌注重的是說話者和傾聽者之間的相似性和親近性,它通過關注傾聽者的興趣或贊美來維護傾聽者的積極面子。消極禮貌強調不強加于人并通過間接的方式維護別人的消極面子來表示尊重。
三、禮貌理論的優點與局限性
Brown和Levinson的禮貌理論有很大的啟發價值,它幫助我們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一系列交際活動。此外,它還指導參與者在社交中選擇適當的禮貌策略,以維護雙方的面子;因此,該理論自提出以來得到了廣泛的研究和應用。然而,也存在許多批評的聲音,促使理論家們對Brown和Levinson的模型進行改進,甚至建立新的模型。接下來將討論其中的一些局限性。
1.普遍性
Brown和Levinson(1987)指出,積極面子和消極面子的需求是每一種文化中人類經驗的組成部分。總的來說,不同的語言群體存在著相同的禮貌策略,并且Brown和Levinson強調其在所有文化中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受到了許多理論家的質疑和批評,認為他們指出這種模型與許多文化的本質并不適用。
Brown和Levinson的模型對于英國文化似乎是合理的,但對于東亞文化卻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Kadar&Mills,2011)。例如,Gu(1990)指出中國文化對消極面子有不同的定義。在一般情況下,提出邀請和承諾并不被看作威脅傾聽者消極的面子或給傾聽者帶來壓力。雖然傾聽者明確表示不愿意接受邀請,但說話者會堅持邀請傾聽者吃飯(也就是意味著說話者會請客埋單)。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可能認為提出邀請本身就是一種強加于他人的言語行為,而說話者堅持讓傾聽者接受邀請的行為在中國文化中本質上是禮貌的,因為這才能顯示出足夠的誠意。
在中國文化中,消極的面子是建立在維護自己與社會其他成員關系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個人的自由。因此,中國文化在某些方面并不適用于Brown和Levinson的禮貌模型。與Gu的觀點相同,Mao(1994)也指出日本文化的價值傾向是強調集體利益高于個人欲望。造成這種不一致性的原因是由于西方文化價值觀強調個人主義,而亞洲文化的價值觀主要強調集體主義。因此,許多理論家對禮貌理論的普遍性表示懷疑。
2.跨文化有效性
Brown和Levinson(1987)承認不同文化采取禮貌策略的頻率和程度不同。他們用三個社會學變量:距離、說話者與傾聽者之間的權力和強加程度來描述和解釋面子威脅行為的嚴重性及禮貌策略的選擇。
然而,不同的文化對這三個社會學變量有不同的評價方法和標準。人們對面子、權力、距離的理解深深植根于一個更大的文化知識和價值體系中,跨文化可能具有不同的意義(Goldsmith,2006)。因此,一個特定的言語行為,如批評或表現直接,在某些文化中可能對面子的威脅較小,而在別的文化中則更有威脅性。例如,Katriel(1986)描述了以色列的一個演講場景,以色列Sabra人通常直接表達反對或批評。這種直接的言語意味著人們之間的尊重和親密,因為在他們共同的價值體系中,直接解決問題比個人的公共形象和感情更重要。但是在其他文化中,這種言語行為的威脅程度可能非常高,人們不太可能采取這種禮貌策略。因此,不同的文化對面子、距離和權力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對這些概念的判斷也是不同的。這三個社會學變量的有效性可能受到跨文化的挑戰。
3.文化、語言和個體差異性
Brown和Levinson(1987)認為,每種文化要么傾向于積極禮貌文化,如澳大利亞文化,要么傾向于消極禮貌文化,如日本文化。但由于忽略了個體多樣性,這種文化標簽可能無法包含社會交往的各個方面,因為社交的參與者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群體。Kadar和Mills(2011)指出,這些理想化的、刻板的文化和禮貌觀通常是精英群體的規范,因而會受到其他社會階層的挑戰。例如,英國中產階級在提出要求時喜歡使用間接的方式。雖然工人階級承認關心他人是英國文化的一個特點,但他們在提出要求時避免使用甚至嘲笑間接的說法。因為這對于工人階級來說過于禮貌,他們可能會采取其他更積極的禮貌策略(Mills,2011)。這個例子說明精英群體的語言規范并不是表現禮貌的唯一方式。因此,Mills(2011)提出了一種區分文化和語言的話語方法,這就要求禮貌理論家打破對精英群體的刻板印象,轉向關注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群體。
4.實際應用可變性
如上文所述,普遍性、跨文化有效性和個體差異問題是理論模型應用的前提。然而,在運用該理論模型分析或預測實際的社交禮貌策略時,Brown和Levinson忽略了許多實際問題。
首先,個人的語言風格習慣、個性、環境等因素也會影響一個人在社會交往中禮貌策略和言語行為的選擇。Forgas(1999)探索了情緒如何改變人們對禮貌程度的認知。其次,在復雜多變的社交對話中,說話者可能會采取多種禮貌策略來維持傾聽者的面子,而Brown和Levinson的模型只關注一種禮貌策略的選擇,因此排除了同時選擇兩種或兩種以上策略的可能性(Vilkki,2006)。最后,Brown和Levinson忽略了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存在第三方或多方的可能性。如果盲目地維護某一個傾聽者的面子,而忽視第三方或其他傾聽者的面子,他們的積極面子也會受到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參與者可能無法實現有效的溝通,從而違背了禮貌理論的初衷。
四、結語
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禮貌模型由于文化層面和個人層面的復雜性和變異性,在前提條件和實際分析和應用上都存在很多局限性。此外,面子作為禮貌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需要根據不同的文化重新定義,以衡量威脅言語行為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