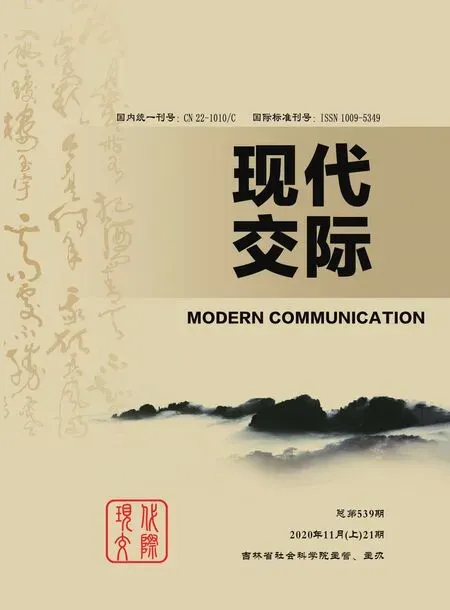淺談儒家誠信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高元攀
(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歷久彌新,其關鍵在于核心價值對于傳統文化的形塑。“誠”與“信”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價值觀。探尋儒家誠信思想的內在含義,有利于持續闡發它蘊含的現代價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重要推動力。
一、儒家誠信的語源
在我國古代,“誠”與“信”起初是既分立又聯系的道德范疇。“誠”源于《周易》,強調內心真實。“誠”字往往表達了誠信思想的多層含義。“誠”不只表現為自然天道的法則,也表現為人的本性。《中庸》中對這兩層含義有充分體現。首先,儒家認為“誠”是自然天道的法則。諸如:“誠者,天之道也。”[1]197從儒家經典文獻對“誠”的定義可看出“誠”是宇宙萬物的根本,說明“誠”在傳統哲學中有著至高的定位及重要的價值。其次,儒家認為“誠”是人性之道、德行之本。諸如“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2]370在儒家文人看來,了解“誠”的道理,就是要順乎自然的規律,就是要把“誠”作為做人的基本原則。因此,在傳統的理論體系中,從哲學層面上講,“誠”屬于天道范疇的本體意義;從倫理的角度來看,“誠”歸為人道范疇的倫理意義。無論從哲學層面還是倫理角度,“誠”都在傳統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信”源于《尚書》,著重強調交往不欺。在《尚書·湯誓》中,就體現了“信”包含了對內不自欺、對外不欺人的重要含義。在儒家著作《論語》中,“信”字出現多次,諸如《學而》篇中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3]2;《為政》篇中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3]12;《述而》篇中有“子四教:文、行、忠、信”[3]62。從這些述論中可知,在古代,“信”的守信用之意較為明顯,誠信不自欺之意也在其中。它強調在交往的過程中遵守信用,表里如一。漢代董仲舒補充和發展了“信”的內容,并將“信”列為“五常”之一,上升了“信”的理論高度,凸顯了它在中國傳統道德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從探究“誠”“信”二字的語源可以了解到,兩者之間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是辯證統一的。在許慎《說文解字》中就通過互訓法闡釋了“誠”與“信”二字。“誠者,信也”“信者,誠也”。可見,“誠”“信”之間存在著天然的意義相通性,兩者的本意都包含了真實、忠實不欺。但兩者的側重點各有不同。“誠”更看重內在的真誠、不自欺,強調主觀的道德素養。“信”更看重外在的真實狀態,不欺人,強調外部的倫理關系。儒家經典《孟子》中的有關論述深刻揭示了“誠”與“信”兩者的差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者也。”[4]173此論述中強調的“誠”側重于外在道義,“信”則側重于內在的德行。“誠”與“信”最初作為獨立使用的兩個字,雖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但我們也經常看到兩者在許多古書典籍中前出后繼,這表明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戰國時期,“誠”與“信”兩字已經開始出現連用。
二、儒家誠信思想的內涵
1.立人之本
儒家先哲認為誠信是立足社會的前提,并把誠信推崇為一種道德規范和自我修養,這是儒家一貫提倡的觀點。把誠信作為立人之本是以個人層面為出發點,強調誠信是加強道德修養的根本途徑,從而使個人生活上有所保障,精神上有所依托。孟子認為誠信是個人所應遵守的道義,是為走上正途所需要的道德品質;一個人若是不信守承諾,不踐行自己的諾言就會招致禍害,更談不上自己的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托。此外,儒家學說中還強調了一個人擁有誠信的優秀品質是區別人與動物的重要標志,認為個人知禮表現為信守諾言,人與禽獸雖都能言語,但人能遵守諾言,做到身體力行,表里如一。可見,誠信自古以來就被人們所尊崇,并作為立德修養的途徑。
2.處世之道
儒家認為在社會交往中需要遵循誠信原則,以此促進社會健康發展。人們在社會交往活動中,想要獲得他人的以誠相待,那么自身也要以誠待人。我們要與他人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方面可以成就自我,給自己帶來便利;另一方面可以成就大我,促進人類社會良性發展。《中庸》曾提出:“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乎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3]260我們發掘出自己本性中的真實無妄的“誠”,因為“誠”不欺騙自己,不欺騙他人,不做那些不合乎規律的事情,所以在社會交往活動中,也獲得了他人的“誠”。做到了“誠”,我們自然而然地成就了自己,養成了良好的行為,而在我們成就自己的同時,我們所生存的社會環境的公共道德也得以提升,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氣,使社會秩序處于安定狀態。換句話說,這使我們人類社會得以良性發展。此外,儒家先哲孔子倡導的“信”具有雙向的要求,不僅要求對他人信任,也要求他人對自己信任。曾參也倡導每日反思自己是否做到“信”,從而來修正自己,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可見,誠信作為為人處世的法則,在人際交往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3.興盛之源
我們在肯定誠信在提高個人修養與人際交往的道德價值時也不能忽視它所帶來的物質利益。之所以說誠信是興盛之源,主要體現在它在商業活動中的作用。在涉及“利”與“義”的商業活動中,儒家反對人們通過欺詐的手段獲取利益,因為這是失“義”的表現。儒家認為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必須遵循“義”,在“義”的基礎上實現物質追求,才是合理的利益要求。儒家所提倡的“義”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包含在經濟活動中講究誠信的。在許多儒家經典中我們會看到“見利思義”“見信思義”等誠信思想,從一個側面表現了在經濟活動之中要踐行誠信的思想。儒家誠信思想認為經商就要講究誠信,只有以誠信作為經商的準則,事業才會成功,才會得到保障。提倡在買賣過程中不以欺詐的手段牟取暴利,不因一己私利而不擇手段,獲取利益應通過合理公平的交易,樹立誠信經營的意識。每個人都想要富貴和安逸,但若不是通過合理的手段獲得,就不要去享受它。由此可見,在經濟活動中。誠信是儒家所推崇的重要原則之一,它為商業興旺提供保證,是經濟活動中的重要策略。
4.為政之基
誠信之所以被儒家先哲認為是為政之基,主要體現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統治者以身作則和信任民眾被儒家先哲認為是穩定社會、鞏固政權的兩大法寶。因此,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要在注重自身“信”的同時還需堅持取信于民。《中庸》就曾提到此說法:“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1]321。當政者要有良好的德行修養,才能取得民眾的信任。孔子在建議統治者治理國家和管理民眾的過程中也遵循這一重要法則,他認為統治者只有不欺民、言而有信、信守對百姓的諾言,才會得到民眾的愛戴和擁護。儒家一直崇尚“為政以德”,而統治者起榜樣作用是前提,統治者要求民眾的同時自身也要達到這種要求。這就涉及了兩者之間的相互守信。由此看來,為政者自身信守承諾的同時還需取信于民,國家方能長治。
三、儒家誠信思想的當代價值
進入現代社會之后,儒家誠信思想完成了現代轉換的時代任務,并以誠信的范疇形式繼續影響著個人乃至社會的良性發展,體現了儒家誠信思想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
1.有助于建設政府誠信,提高政府公信力
傳統誠信被儒家先哲理解為為政之基,突出了誠信在治理國家中的特殊意義。從國家政治的角度來看,孔子主張以“信”治國。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3]2治理大國,要講究誠信,不能朝令夕改,這樣才能取得民眾的信任。又言“自古人皆死,民無信不立”[3]104。認為政府說話算話,取信于民,是國家存在下去的基礎。他認為在執政的三大支柱“足食,足兵,民信”中,唯獨“信”是不可或缺的,“信”對于國家和社會來說,比“食”“兵”更重要,此時他已意識到對民眾講誠信是執政者的基本道德之一。這就要求執政者在政治實踐中要做到誠信無欺,同時也對現代社會執政者的治理實踐提出了要求。它要求政府官員要起帶頭作用,立身守信,相信人民群眾,做到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的一切,從而提升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公信力。
2.有助于建設商務誠信,推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傳統誠信被儒家先賢理解為興盛之源,突出了誠信在商業活動中的特殊作用。儒家先哲提倡人們在進行買賣交易的過程中要通過合理的渠道獲取利益。《孔子家語·魯相》曾言“賈羊豚者不加飾”[5]107,提倡商人在從事商業活動中不能制假售假,應當遵從誠實無欺、公平買賣的行為規范。這種誠信思想與今日的商務誠信建設領域提倡的公平交易不謀而合。同時,儒家誠信思想中還提倡不應為了一己私欲而犧牲他人、社會,乃至國家的利益,學習并弘揚這種利益觀,有利于幫助企業等商業主體強化責任意識,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當前我國商務誠信建設的水平同人民群眾的期望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遍布市場、以變換價格為手段進行欺詐等方面。這些行為不僅威脅到人民群眾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也影響著自身長遠健康發展。現代商業經濟活動的實踐證明,經營者只有秉承以誠信為導向的價值理念,才能實現交換雙方的互利互惠。為此,要在加強商業道德教育的同時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監管體系,從而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為經濟社會提供強大支撐。
3.有助于建設社會誠信,提升社會公民道德素質
首先,社會誠信是維系人際關系的紐帶。傳統誠信被儒家先哲理解為處事之道,突出了誠信在社會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在社會交往活動中,以自身內心真誠為基礎尊重、信任他人,才會獲得他人的以誠相待。孔子認為,君子與人交往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須講究“誠信”。孔子曾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3]40因此,孔子把對朋友守誠信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一。“君子”是數千年中華優秀傳統塑造的理想人格,講誠信是君子文化的重要內容,弘揚傳統君子文化,對開展社會誠信建設具有極大的價值。其次,儒家誠信觀倡導全社會建設誠信,這種誠信思想觀念的提出使我們受益匪淺。我國處于社會快速發展的時期,社會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誠信缺失的現象。主要表現在個人、家庭、職業生活及公共生活等領域的誠信缺失。立足新時代,做出新部署,《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提出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提高全社會誠信水平。當前抓緊建立一套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是建設全社會信用體系的前提。那么,解決在社會生活中的失信現象,就必須加強誠信教育并制定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和監管體系。只有每個公民自身誠信涵養得到普遍提升,才能使全民道德素質達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