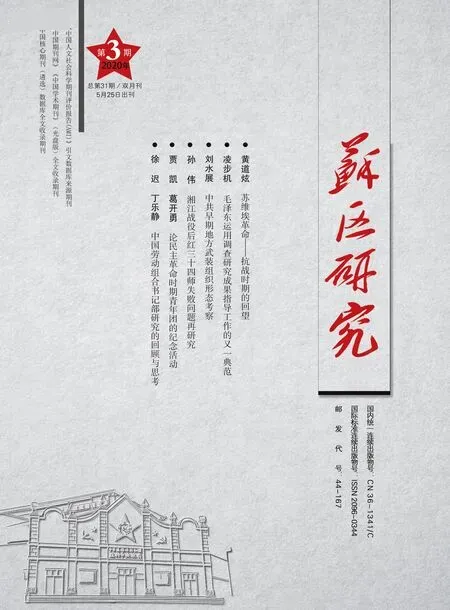“通道會議”相關問題新探
王建國
提要:“通道會議”不是一次會議,而是一系列會議的統稱。洛、毛碰頭會是系列會議的序幕。在流源會議上,軍事將領初步形成“轉兵”共識;在芙蓉會議上,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轉兵”的戰略性抉擇。在播陽會議上,中革軍委決定對有關部隊編制進行大幅度調整。有證據表明,毛澤東當時提出的是“插向滇東”“創建黔滇川邊蘇區”的戰略構想。作為通曉云貴川情況的卓越軍事家,朱德對毛澤東戰略構想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的建議。在“通道會議”期間,盡管發生了激烈爭論,但毛澤東的主張第一次在中央決策層面發揮主導作用。
關于“通道會議”,《中國共產黨歷史重要會議辭典》(下稱《辭典》)這樣寫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緊急會議。博古、朱德、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七人參加。”(1)張啟華:《中國共產黨歷史重要會議辭典》,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頁。但實際上,“是否召開過通道會議、通道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會議的性質、參會人員、通道會議與黎平會議的關系以及通道會議的歷史地位……上述問題均未形成一致的觀點”(2)宋寅桂:《紅軍長征路上的重要節點——通道會議研究綜述》,《湖南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第200頁。。筆者一直關注“通道會議”,對會議有關問題反復推敲,現就多年思考所得進行陳述,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通道會議”應該是一系列會議的統稱
最早對“通道會議”真實性進行求證的是中國革命博物館。1971年7月,鄧穎超這樣對該館人員說:“上次你們提的問題,回去我問了恩來同志,在長征途中是否開過黎平會議和通道會議?恩來同志講是有,開過黎平和通道會議。因為他非常忙,時間很少,也沒多講。”(3)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鄧穎超同志關于通道會議問題詢問周恩來同志后的答復》(1977年11月28日),中共通道侗族自治縣黨史辦編:《紅軍長征過通道》,內部發行,1986年版,第65頁。1984年4月18日,陪同索爾茲伯里沿紅軍長征路線考察的秦興漢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在貴陽召開座談會……介紹說,1934年12月1日在通道開會。鄧穎超同志問過周總理,肯定有這樣的會議,是在通道縣境,不是在縣城,是在一個老百姓家里開的。當時,這家人正舉行婚事,那是個臨時會議,是個緊急軍委會議,是解決軍事方向問題。”(4)《采訪紅軍長征日記》,秦興漢:《讓世界都知道紅軍長征——陪同索爾茲伯里踏訪長征路》,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頁。按:引文中的日期應當為1934年12月10日。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特地予以說明:“黨史學家孫日昆認為,會議是在12月份頭十天也許在10日這一天舉行的。周恩來關于此事的回憶就是他提供的。是周的遺孀鄧穎超轉告他的(孫日昆:1984年4月18日采訪)。”(5)[美]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著,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譯:《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頁。由此看來,周恩來后來又相對具體地和鄧穎超談過“通道會議”。既然得到了周恩來的確認,“通道會議”的真實性自然也就無需懷疑。
由于周恩來語焉不詳,李德在《中國紀事》中的敘述就顯得彌足珍貴。也許正因如此,《毛澤東年譜》才會將《中國紀事》中的相關內容全部錄入。可是,李德只是說,“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會上討論了以后的作戰方案”(6)[德]奧托·布勞恩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24頁。,根本沒有提及會議召開的時間和具體地點。由于沒有任何會議記錄,當事人的回憶又少之又少,所以有關部門試圖通過民間調查來求得真相。毫無疑問,各部門調查所得肯定眾說紛紜,相互矛盾。關于通道會議的地址就有通道老縣城(今通道縣縣溪鎮)、綏寧的芙蓉(今通道縣芙蓉鎮)、通道縣流源(今通道縣萬佛山鎮流源村)、牙屯堡(今流源縣牙屯堡鎮)外寨村和播陽(今通道縣播陽鎮)等多種說法。也許正因為如此,《紅軍長征史》才會這樣含糊其辭地寫道:“12月12日,中央幾個負責人在通道縣境內召開了非常會議。”(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頁。實際上回避了會議的地址和性質問題。《辭典》之所以采用通道縣城的說法,其依據實際是:“根據通道縣委的調查材料……中央縱隊于十一日進入通道縣城。毛澤東同志住城邊一家染匠鋪里,博古、李德與伍修權(秘書兼翻譯)等人住書院(今縣溪完小)。這樣,當時中央縱隊的駐地在縣城即可確定,通道會議召開的地點當為今縣溪鎮。”(8)康健文:《通道轉兵的歷史意義》,《貴州文史叢刊》1982年第1期,第6頁。這種說法除了與周恩來的敘述相矛盾外,還直接被伍修權否定:“我和李德、博古、總理、朱總司令在中央一縱隊。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在中央二縱隊。一縱隊是指揮機關,二縱隊是隨軍行動的機構。我沒有過縣溪浮橋,所以,在通道老縣城開會是不可能的。”(9)《伍修權同志談通道會議》(1983年12月19日),中共湖南懷化地委黨史辦公室:《紅軍長征在懷化》,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頁。毫無疑問,當事人周恩來和伍修權的敘述遠比幾經轉述的間接“知情者”的回憶可靠。由此可見,《辭典》關于會議在通道縣城舉行的說法不能成立。
那么,還有其它多種說法該如何解釋?陳云于1935年2—3月間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寫道:“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10)《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頁。應該說,“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主要是在會議上發生的。如果說陳云的說法不夠明確的話,再請看周恩來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11)周恩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遵義會議紀念館編:《遵義會議資料匯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周恩來明確強調“從老山界到黎平”“一路開會爭論”,顯然是強調開了好多次會議。依據周恩來和陳云的敘述,結合其他史料和田野調查資料,筆者發現“通道會議”實際上是一系列會議而不是一次會議。那么,如何理解李德所強調的“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合理的解釋是李德只參加了最終決定“轉兵”的那次會議。如果認識到“通道會議”實際上是一些列會議的統稱,許多難以理解的問題也就可以得到比較合理地解釋了。
二、軍事將領形成“轉兵”共識的流源會議
在《關于通道轉兵一些情況回憶》中,羅明寫道:“我到毛主席的住地(像學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后……毛主席和洛甫同志在大廳里面談話……洛甫同志……如實地擺出了當前的困難情況……聽到毛主席講話……無論如何不能照原計劃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了,因為敵人已經調集了三、四十萬兵力,部署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企圖消滅我們。我主張現在應堅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12)羅明:《毛主席和張聞天的一次談話》,遵義會議紀念館編:《遵義會議前后紅軍政治工作資料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223頁。《羅明回憶錄》這樣寫道:“我們紅軍在通道縣休整……我去看望毛澤東同志,適值洛甫同志與他談話……毛澤東聽后很鎮定地說……現在應改變計劃,不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敵人已調集三四十萬兵力準備消滅我們。我們應堅決改向敵人比較薄弱的貴州進軍,否則后果難以設想……過了3日,紅軍就攻占黎平。”(13)《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頁。羅明的兩次回憶相互補充,比較清晰地重構了毛澤東與張聞天交流的場景:張聞天向毛澤東通報有關情況,毛澤東提出了自己的個人見解。鑒于兩人根本無權做出任何決定,這次“以互通情況為主要內容的短會”,只能稱作“碰頭會”(14)李行健主編:《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語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87頁。。然而,正是在這次與張聞天交流的過程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戰略構想。鑒于紅軍占領黎平的時間是12月15日,可以推斷:張聞天主動找毛澤東通報情況,探尋破解之法應該是在12月11日。論者大多把這次碰頭會看作一個無關緊要的歷史細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都沒有提及。其實,正是張聞天與毛澤東這次“私下進行”的碰頭會拉開了通道系列會議的序幕。
關于“通道會議”,毛澤東警衛班戰士吳吉清這樣介紹:“過了湘江以后……一天晚上,在一個寨子,又不像廟的屋子里,主席、總理、總司令、劉總參謀長,還有幾個人我不認識,在一起開會,提了一個馬燈看地圖,我正在屋子前面守衛,會議時間不長,我沒有看見外國人參加……”(15)李仲凡:《“通道轉兵”和“通道會議”》,《紅軍長征在懷化》,第186頁。吳吉清對會址的描繪與羅明的說法相似,應該是在毛澤東住處。由此推斷,會議是在毛澤東與張聞天會談的當天晚上進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吳吉清除強調“沒有看見外國人參加”,還特地說明“還有幾個人我不認識”,而沒有提及張聞天、王稼祥、博古。在回憶錄中,吳吉清再次強調:“紅軍在行軍到湖南通道時,時局已相當危急。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周副主席、劉伯承總參謀長等,在行軍中研究了情況。主席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貴州前進。”(16)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頁。同樣沒有提及張聞天、王稼祥、博古和李德。“通道會議”召開時,吳吉清年僅25歲,正是記憶力最佳的時段,他對這件事的記憶應該比較可靠。那么,吳吉清的說法為什么與李德的《中國紀事》有這么大的差異?合理的解釋是吳吉清所記錄的并不是李德筆下的“飛行會議”。
弄清楚會議前的細節,有助于理解李德等人沒有參加會議的緣由。時任李德翻譯的王智濤寫道:強渡湘江之前,“毛澤東的具體主張是:紅軍不能西渡湘江,而是留在湘南……周恩來說,李德對毛澤東成見太深,凡是毛提的意見,無論如何都不會接受……”不出周恩來所料,當毛澤東提出自己的建議時,李德對毛澤東吼道:“毛澤東同志,這是中央制定的,經共產國際批準的戰略方針。對此,你是清楚的。我實在不明白,為什么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和共產國際挑戰?為什么你總是在背地里,今天竄通這個,明天竄通那個,專門針對我們三人團?你要是再這么搞下去,我們就不得不對你執行紀律了。”(17)《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頁。毫無疑問,毛澤東西進貴州的主張必將遭到李德、博古的強烈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先召集朱德、劉伯承等軍事將領開會以統一認識,自然成為周恩來的明智選擇。可以肯定,吳吉清所不認識的幾個人應該是臨時召集的軍事指揮員。至于張聞天、王稼祥沒有參加會議,顯然是為了堵博古、李德之口。
學術界大多認為“通道會議”不可能在流源舉行。理由是: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在中央一縱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中央二縱隊。實際情況如何?請看《伍云甫日記》:12月11日,“隊伍7時自平等出發……17時左右到流源宿營。”(18)《伍云甫日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2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99頁。伍云甫是中革軍委三局副局長,一直跟隨中革軍委行動。這說明12月11日晚周恩來、朱德、博古、李德都在流源。請看《長征大事記》:“11日……軍委(中央)二縱隊到辰口。”(19)陸定一:《長征大事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1冊,第34—35頁。由此看來,毛澤東等人應該在辰口。不過,從李德指責毛澤東“不顧行軍的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20)[德]奧托·布勞恩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119頁。來看,無法排除毛澤東在流源的可能性。關于毛澤東的行蹤,筆者最終在《彭紹輝日記》中找到了可靠的證據:12月11日,“我師今日受領掩護‘紅星縱隊’的任務。上午‘紅星縱隊’在龍坪未動,下午尾‘紅星縱隊’行進,‘紅星縱隊’到流源宿營。”12月12日,“部隊上午7時準備出發,因‘紅星縱隊’未過完,我師也未動。朱、周、博、洛、毛同志也隨‘紅星縱隊’在此通過。”(21)《彭紹輝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1冊,第322頁。彭紹輝時任少共國際師師長,當時擔任“紅星縱隊”即中共一縱隊的掩護任務。既然彭紹輝12月12日早晨在流源親眼看到毛澤東、張聞天和周恩來、朱德在一起,那么就可以斷定在前一天晚上他們召開過一次重要會議。
在流源召開過軍事將領會議的一個有力證據是朱德12月11日18時半給林彪、聶榮臻發出的電令:“我一軍團主力及九軍團,明十二日應集結在通道及其附近地域,向靖縣、綏寧方向派出偵察,向城步方向警戒……一軍團應另派不大于一團兵力的偵察部隊,并帶電臺前出至崖鷹坡,向新廠、馬路口偵察入黔的道路……執行情形電告。”(22)《朱德令一、九軍團集結通道》(1934年12月11日),《紅軍長征過通道》,第35頁。從電令中可以看出,朱德事實上已經著手西進貴州的軍事部署。流源會議時間不長,應該在晚上6時半之前結束。可見,毛澤東與軍事將領之間的溝通是比較順利的。由于改變共產國際批準的行軍路線必須經過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所以這個重要命令最終以朱德個人名義發出。換言之,在流源會議并沒有正式作出“轉兵”的決定。
三、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轉兵”的芙蓉會議
流源會議剛剛結束,國民黨追剿軍第一縱隊司令劉建緒就發出電令:“務期殲匪于湘、黔邊境……部署如次:1.著第一路陶司令所部,除以一部趕筑綏寧大道封鎖干線堵匪北竄外,迅以主力向臨口、通道方向覓匪截剿。2.著第四路李司令所部,迅速進駐遂寧,策應第一路截剿。3.著第五路李司令所部,迅即進駐長鋪子待命。4.著劉代旅長所部,除留團隊守備城步外,迅向巖寨、木路口尾匪追剿。但到巖寨后,須派團隊向長安營方面警戒。5.著何主任所部由長鋪子經黃桑坪,向木路口、石壁道上截擊……真戌參。”(23)《劉建緒關于務期消滅中央紅軍于湘黔邊境給李云杰、李韞珩、陶廣等的命令》(1934年12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155頁。“真”,韻目代日,指“11日”。“戌”地支代時,指“19時—21時”。不料,劉建緒的這份絕密電報被中革軍委二局截獲并于12日凌晨成功破譯。(24)曾希圣傳編纂委員會:《曾希圣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0頁。電令的破譯證實流源會議的抉擇完全正確。12日6時,朱德電令林彪、聶榮臻等將領:“甲:我軍西進路線一軍團應經崖鷹坡、新廠、馬路口入黔,三軍團應經團頭、播陽入黔,望以此分界線自定前進路線。乙:在目前湘敵向我追來條件下,一軍團應稍集結,不宜過于分散不利作戰。丙:你們行動仍應遵昨日十八時半電令執行。”(25)《我一、三軍團入黔路線得注意集結兵力》(1934年12月12日),《紅軍長征過通道》,第38頁。不難看出,朱德實際上已經向主要將領下達了西進貴州的動員令。
據《伍云甫日記》記載:12月12日,“大隊伍6時出發,余守候一分隊發‘5393’、‘5413’、‘5458’等臺電報,下午到達芙蓉宿營。”(26)《伍云甫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2冊,第699頁。陸定一《長征大事記》這樣記載:“九軍團進到通道縣城。軍委二縱隊到芙蓉市附近。野戰軍司令部到芙蓉。”(27)陸定一:《長征大事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1冊,第35頁。在行軍過程中,各部隊加緊進行西進貴州的準備工作。擔任紅九軍團供給部部長的趙镕在12日日記中寫道:“軍團政治部今天發出通知,要全軍團干部研究黔敵二十五軍的情況,對貴州省的政治、經濟、地理、人口分布、天然氣候和各地出產情況以及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等等進行調查。估計部隊要向西進入貴州省境了。”(28)趙镕:《長征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2冊,第432頁。在13日的日記中,趙镕又這樣補記:“昨天下午我到軍團司令部、政治部匯報有關調查黔省情況的具體執行辦法時,聽說中央同志對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軍事策略可能有改變。”(29)趙镕:《長征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2冊,第433頁。
部隊一到芙蓉,就緊急召開了李德所說的“飛行會議”,并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李德這樣寫道:“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系。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肖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李德憤憤地告訴世人:“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30)[德]奧托·布勞恩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124頁。幾十年后,李德還強調“粗暴地拒絕”,一來說明當時的爭論十分激烈,二來說明李德對自己方案被否決耿耿于懷。不過,李德無奈地承認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大家的認同。最叫他難以忍受的是,連一向支持他的博古態度也發生了改變:“博古認為,從貴州出發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31)[德]奧托·布勞恩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125頁。博古態度的改變與劉建緒電令的破譯有關。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會對曾希圣說:“沒有你的情報,博古可能只會‘博古’不會‘通今’,不會同意改變行軍方向。不去貴州,何談遵義,遑論遵義會議了。進軍貴州,你是出了大力的。”(32)蘇振攔、夏明星:《曾希圣:隱蔽戰線上的傳奇英杰》,《黨史博覽》2007年第11期,第50頁。
12日19時半,中革軍委給各軍團、縱隊首長下達了“萬萬火急”(33)《軍委關于我軍十三日西進及進占黎平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紅軍長征過通道》,第38頁。的命令:“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如下:1.一軍團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前進至新廠、崖鷹坡、溶洞地域,向靖縣派出警戒,向白(馬)路口及黎平方向派出偵察部隊。其第一師,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占黎平……2.三軍團以迅速脫離桂敵之目的,明日應以主力進至平(牙)屯堡、團頭、頭所地域……3.軍委一、二縱隊擬進至播陽所以北地域。4.五、八軍團應趕進至土溪、元心園地域……告軍團依實際情況得變更其前進位置,但須嚴格的遵守前進的主要路線及其分界線,以免障礙運動,并將部署電告。”(34)《軍委關于我軍十三日西進及進占黎平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紅軍長征過通道》,第39頁。該電令的下達,標志著中央紅軍邁開了戰略性“轉兵”的第一步。由此可見,通道系列會議中最重要的一場就是在芙蓉進行的。有學者認為,“芙蓉或芙蓉里當時屬綏寧管轄,解放后才劃歸通道。如果會議是在這里召開的,就應該叫做芙蓉會議,并注明芙蓉原屬綏寧、現屬通道,而不應該叫做通道會議。”(35)郭德宏:《通道會議會址考證》,《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62頁。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釋。其一,芙蓉會議只是系列會議中的一次。其二,芙蓉只是中央紅軍長征路過的眾多集鎮之一,紅軍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自己經過的每個集鎮的歸屬都搞得十分清楚。再說,僅憑芙蓉當時不屬于通道管轄就否定曾經在此召開過會議,顯然證據不足。
如前所述,《辭典》強調決定“轉兵”會議是“中革軍委……緊急會議”。實際情況究竟如何?由于疏忽,張耀祠兩次對毛澤東有關回憶的記錄不夠一致。《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這樣記錄:“他們在湖南通道召開了中央(革)軍委會……請我去參加會議。”(36)《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在其它場合,張耀祠又這樣轉述:“那個時候,中央政治局開會。在會上,李德、博古仍主張按原定計劃向湘鄂西方向行軍。”(37)喻偉誠:《通道轉兵:而今邁步從頭越》,《新聞天地》2011年第6期,第47頁。到底哪一種說法可靠?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都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是候補委員。同時,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博古、張聞天、毛澤東是中革軍委委員。博古、周恩來、李德還是“中央三人團”成員,掌握中央最高軍事指揮權。從與會者身份上看,這兩種說法都講得通。要弄清楚會議性質,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考察。請看王智濤記載:“毛澤東……力主放棄北出湘西同賀龍、蕭克所部會合的原定計劃……他將此意見與張聞天、王稼祥商量后,由張聞天向周恩來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建議。周恩來說,洛甫是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們三人有權建議召開會議,而且他們的意見我也贊同。現在是扭轉危機關鍵時刻,趁敵人還沒上來,我們抽空召開會議,統一認識,明確方向并做個決定,這樣,有利于紅軍今后步調一致的行動。此時的博古已不完全信李德的,對執掌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大權,也有些心灰意懶,就同意了。”(38)《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回憶錄》,第134頁。由此看來,這次會議應該是政治局會議。請看伍修權回憶:“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議……中央迫于形勢,只得接受了這一正確建議,毛主席的意見被通過了。”(39)《伍修權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頁。再請看權威的“遵義會議決議”:“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在當時不利的敵我情況下,卻還是機械的要向二、六軍團地區前進,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因政治局大多數同志的堅決反對而糾正了。”(40)《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1935年2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文獻》第2冊,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頁。此外,會議的進程也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周恩來、王稼祥是副主席。如果是中革軍委會議,主持并拿出主導意見的應該是朱德。實際上,主持會議并拿出主導意見的是周恩來。再說,改變“中央制定的,經共產國際批準的”的進軍路線,顯然超出了中革軍委的權力范圍,而應該由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決定。由此可見,芙蓉會議應該是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不是中革軍委會議。
四、中革軍委決定部隊編制調整及進軍路線的播陽會議
針對“通道會議”會址可能是播陽的說法,伍修權明確強調:“在播陽開會也不可能,因為播陽離貴州很近,如果在播陽開轉兵會議,時間上講也遲了。”(41)《伍修權同志談通道會議》(1983年12月19日),《紅軍長征在懷化》,第127頁。筆者認為,伍修權所說如果在播陽召開“轉兵會議”“時間上講也遲了”是事實,但開一個全面落實“轉兵”的軍事部署會則是完全可能的。據跟隨中革軍委行動的伍云甫12月13日記載,“自芙蓉出發,經蘆溪到播陽(所)。”(42)《伍云甫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2冊,第699頁。從時間上來講,在播陽開會也是具備條件的。此外,還有證據證明中革軍委在播陽召開過一次重要會議。請看以下三個重要電令:
其一,中革軍委12月13日20時下達了“關于紅八軍團并入紅五軍團的決定及其辦法”。主要內容如下:“甲、軍委決定八軍團并入五軍團,其辦法如下:1.八軍團全部人員除營以上干部外應編入十三師各團,為其作戰部隊……2.八軍團之工兵連、排,補入十三師各團加強各工兵排……3.十三師師部取消,五軍團司令部直轄十三師各團……4.五軍團后方部,應依照軍委四日電令立即縮小為師的編制……5.凡八軍團及十三師師部下級指揮員及工作人員,應盡量編(入)作戰部隊……乙、劉伯承調回軍委,陳伯鈞為五軍團參謀長,周、黃待改編完后即回軍委,羅榮桓為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畢占云調回軍委,馬良駿留五軍團為團長,其他軍政人員除加強五軍團各團外,余應送軍委四局及總政。丙、五、八軍團應利用行軍中的間隙執行此電令中一切規定,限十八號前全部完成。首先須進行解釋,并將結果電告和用書面報告軍委。”(43)《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關于紅八軍團并入紅五軍團的決定及其辦法致董振堂等電》(1934年12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文獻》第1冊,第188—189頁。
其二,中革軍委緊接著下達了“關于取消第二縱隊,合編第一、二縱隊的命令”。主要內容如下:“軍委決取消二縱隊的組織,將一、二縱隊合編為一個縱隊,并規定其序列如下:第一梯隊轄……第二梯隊轄……第三梯隊轄……三個梯隊外,另以干部團、保衛團為獨立的作戰部隊,歸屬軍委縱隊司令部直轄……軍委縱隊以劉伯承為司令員,葉劍英為副司令員,陳云為政委,鐘偉劍為參謀長,縱隊司令員、政委、參謀長均兼第一梯隊司令員、政委、參謀長,第二梯隊以何長工為司令員兼政委,第三梯隊以羅邁為司令員兼政委……分編第二縱隊限十五日進行完畢,并于十五日起以軍委縱隊名義直接指揮所屬各部隊。”(44)《中革軍委關于取消第二縱隊,合編第一、二縱隊的命令》(1934年12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文獻》第1冊,第190—191頁。
其三,中革軍委13日21時半(45)《林彪、聶榮臻關于十三日繼續西進的部署》(1934年12月13日),《紅軍長征在懷化》,第76頁。下達了調整西進貴州部署的命令。主要內容如下:“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的目的,明十四號部署如下:1.一軍團主力應經馬路口入黔,向黎平以北地域前進。對黎平方向派出偵察……2.九軍團應經馬路口入黔,向錦屏方向偵察前進,并有相機占領錦屏之任務……3.三軍團主力應進播陽所地域,向林溪及來路嚴密警戒,其先頭團應前進至洪州司馬西地域……4.軍委一、二縱隊進至洪洲司、老地塘地域……5.五、八軍團應進至深渡地域,向靖縣、綏寧兩方向警戒,并準備隨十五師后入黔……”特地強調:“一、三、九軍團在前進中如遭遇黔敵堵截,有突擊和驅逐該敵以便西進之任務。”(46)《朱德令各軍團十四日進入貴州的行動部署》(1934年12月13日),遵義會議紀念館編:《遵義會議前后紅軍軍事電文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9頁。
毫無疑問,將八軍團并入五軍團,將軍委一、二縱隊合并重組軍委縱隊,如此重大的決定必須由會議作出。如果決定在12日芙蓉會議上已經作出,上述命令就不可能拖到13日夜里才下達。由此看來,13日晚上在播陽曾經召開過有關部隊合并重組的專門會議。與“轉兵”必須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不同,作出這樣的決定應該屬于中革軍委的職權。再從電文中的“軍委決定”“軍委決”來看,在播陽召開的應該是由朱德主持的中革軍委會議。從第三道命令看,這次會議上還具體討論了紅軍主力部隊14日進軍貴州的戰略部署問題。
五、毛澤東的戰略構想是“插向滇東”“創建黔滇川邊蘇區”
關于毛澤東的戰略構想,《辭典》這樣寫道:“毛澤東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47)張啟華:《中國共產黨歷史重要會議辭典》,第44頁。《中國共產黨歷史》這樣寫道:“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北上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辟新的根據地。”(4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頁。二者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明確指出是“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后者只是說在貴州開辟新的根據地。可是,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新說法:“中央紅軍是從通道轉北,還是先西行到黎平,再轉北?這兩種意見發生了爭論。李德堅持要在通道轉北,理由是沒有必要繞道黎平,走黔東,這樣要多走十天路程才能到湘鄂川根據地。毛澤東的意見走黎平再北上,理由是:‘通道轉北,路雖然近了,但走的是直線北上,全在湘西邊走,現在蔣介石已清楚我們要和賀龍會合,肯定會在這條必經之路上設封鎖線,所以走這條路,吉兇難料。’”(49)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頁。作者秦福銓是博古的侄兒,從他強調“父親……知道不少與博古有關的事情”(50)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第2頁。來看,這部分內容似乎來自博古的敘述。按照這種說法,毛澤東只是在如何向湘西前進的問題上與李德存在分歧。
其實,秦福銓的說法并不可靠。李德這樣寫道:“毛澤東……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四方面軍)會合。”(51)[德]奧托·布勞恩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124—125頁。《康克清回憶錄》這樣寫道:“他(毛澤東)在會上分析形勢作出判斷,提出改變紅軍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軍司令部會師的打算,避開敵人給紅軍設下的口袋陣,向西進入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爭取紅軍有個喘息和整頓的時機,爾后再定行止。”(52)《康克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頁。康克清是朱德夫人,她應該是從朱德口中得知會議上的情況。王智濤寫道:“中央召開了‘通道會議’,改變紅軍立即北上湘西的方向,轉兵立即西進黔東,但仍堅持要相機北上。這個決定僅僅是戰術變化,并無改變戰略,毛澤東很不滿意,堅持要繼續開會解決。”(53)《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回憶錄》,第134—145頁。無疑,毛澤東的有關回憶最有價值。1962年夏,毛澤東曾告訴張耀祠:“中央紅軍過了第四道封鎖線之后,紅軍發生了行動方向問題。紅軍要到湘鄂西與賀龍會師?還是打到貴州去?……在會上,李德、博古仍主張按原定計劃向湘鄂西方向進軍。我當時就發言說:建議中央紅軍放棄與賀龍會師的計劃,改變路線,不向湘鄂西挺進,而揮師向西,爾后向北進入貴州。貴州情況要好很多,因為黔軍力量較弱,類似在廣西走廊遭受兩面夾擊的可能性極小。所以在貴州有可能獲得喘息的時間,一邊整頓被打散的部隊,研究今后的行動計劃。而如果按原定路線前進,就會遇上蔣介石埋伏好了的二十萬軍隊,一路上大山也多,我軍就有被消滅的危險。”(54)《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10—11頁。可惜,毛澤東只是詳細介紹了主張西進貴州的理由,卻沒有介紹進入貴州后的打算。
毛澤東的戰略構想究竟是什么?筆者最終在蕭鋒12月13日的日記中找到了極為珍貴的記錄:“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個祠堂里,我們又見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顯得特別高興,連水也沒顧上喝一口,就召集我團幾個領導開會,親自交待搶占黎平城的光榮任務。周副主席高興地告訴我們,插向滇東的行動計劃,是毛主席在通道會議上提出的。毛主席認為,在現在的條件下,要放棄在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改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北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打幾個勝仗,創建黔滇川邊蘇區,扭轉紅軍出征以來的被動局面。”(55)蕭鋒:《長征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第3冊,第1065頁。這是蕭鋒在芙蓉會議第二天的日記,而且是對周恩來親口敘述的記錄,其可靠性遠非幾十年后的回憶可比。這一來說明毛澤東的戰略構想是“插向滇東……創建黔滇川邊蘇區”,二來說明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十分贊同。筆者將日記與黎平會議決議進行比對,發現日記中的敘述在黎平會議決議中得到了有力印證:“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之西南或更西。”(56)《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黎平會議)》(1934年12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文獻》第1冊,第197—198頁。如果黎平會議前沒有“插向滇東……創建黔滇川邊蘇區”的戰略構想,決議中不可能出現“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這樣的論述。蕭鋒日記不僅使我們確認毛澤東在通道會議上提出放棄同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而且告訴我們毛澤東提出的并非眾所周知的和四方面軍會合的計劃,而是“插向滇東……創建黔滇川邊蘇區”戰略構想。
六、朱德可能認為毛澤東的戰略構想需要完善
有部分學者認為,朱德沒有參加過“通道會議”。《毛澤東年譜》寫道:“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秦邦憲和李德仍主張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439頁。沒有提及朱德。無獨有偶,《毛澤東傳》同樣沒有提及朱德。不過,《朱德年譜》這樣寫道:“毛澤東從敵軍重兵阻攔紅軍北上去湘西這一情況出發,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西進,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朱德首先表示同意這一意見,接著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多數同志也表示了贊成。”(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頁。朱德究竟有沒有參加會議?他對毛澤東戰略構想究竟持何種態度?對此,我們有必要進行相應的考察。
早在12月9日,朱德就下達命令:“三軍團……先頭師或團應進至隴城,向長安堡及其以西通黎平道路偵察、警戒。”(59)《朱德關于我軍十日行動部署致各軍團、縱隊電》(1934年12月9日),《遵義會議前后紅軍軍事電文選編》,第14頁。10日23時,朱德下達命令:“一軍團主力及九軍團應占通道及其東南與以南的地域,向綏寧、靖縣兩方派出偵察部隊,向城步來路排除警戒;其先頭部隊(應)前進至崖鷹坡,向新廠、馬路口偵察入黔的道路……(三軍團)先頭部隊……偵察通播陽所及黎平的道路。”(60)《朱德關于各軍團、縱隊十一日西進的部署》(1934年12月10日),《遵義會議前后紅軍軍事電文選編》,第16—17頁。這至少說明,在毛澤東與張聞天初步探討“轉兵”之前,朱德就已經認真考慮西進貴州的可能性。流源會議剛結束,朱德便向林彪、聶榮臻下達了“偵察入黔的道路……執行情形電告”的命令。11日20時,林彪、聶榮臻向朱德報告:“我二師今日應在通道城并向靖縣、綏寧嚴密警戒與偵察,并收集洋油、布匹、糧食及其它資材和調查西進入黔路線……軍團直屬隊后方部隊及一師今日經雙江進到距黎平六十里之牙屯堡宿營。”(61)《一軍團來電:一、九軍團十一日繼續西進之部署》(1934年12月11日),《紅軍長征過通道》,第36頁。12日1時,林彪、聶榮臻再次向朱德報告:“九軍團及二師主力(明)十二日在通道不動,并向綏寧、靖縣、城步等方向嚴密偵察與警戒。二師應派出一個團及電臺由左參謀長率領前出至崖鷹坡地域,偵察新廠、馬路口入黔路線……據調查由金殿往播陽所、洪州府到黎平一百一十五里,牙屯堡往洪州府到黎平二百里,由金殿往通道到黎平一百八十五里。”(62)《一軍團來電:一、九軍團十二日行動部署》(1934年12月12日),《紅軍長征過通道》,第37頁。正是在朱德的直接指揮下,紅軍進入貴州的準備工作得以有序進行。既然如此,朱德不可能不支持毛澤東西進貴州的主張。
遺憾的是,朱德沒有留下只言片語。不過,《康克清回憶錄》這樣寫道:“在群眾的強烈呼聲、老總和周恩來的推動下,會議破例請毛澤東參加。”(63)《康克清回憶錄》,第131頁。由此可見,朱德不應該缺席如此重要的會議。其實,關于朱德是否與會和基本態度,毛澤東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記錄。毛澤東這樣告訴張耀祠:“我當時就發言說:建議中央紅軍放棄與賀龍會師的計劃,改變路線,不向湘鄂西挺進,而揮師向西,爾后向北進入貴州……我這么一說,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著,周恩來、王稼祥也表示了贊成。”張耀祠感嘆:“毛主席對這段歷史實在是記得太清楚了。”(64)《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11頁。所以,朱德不僅參加了會議,而且對毛澤東西進貴州的主張是堅決支持的。
應該說,贊同西進貴州的主張并不等同于全盤同意毛澤東的戰略構想。作為優秀的軍事家,朱德對于“轉兵”肯定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朱德是四川人,云南講武堂畢業,長期在云貴川一帶領兵作戰,對云貴川一帶的情況極為熟悉,他肯定看出了毛澤東戰略構想存在的不足。如前所述,毛澤東“插向滇東……創建黔滇川邊蘇區”戰略構想在黎平會議上進行了很大的調整。細數參加黎平會議的領導人,只有朱德具備對這一戰略構想提出重大修改的能力。由此推斷,朱德在通道時對毛澤東“插向滇東……創建黔滇川邊蘇區”戰略構想會有所保留。
結語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其實,歷史性的轉折不可能在一個時間節點上瞬間完成。在通道,歷史性的轉折的大幕已經悄然拉開。“通道會議”包括洛毛碰頭會、流源會議、芙蓉會議和播陽會議,每次會議的議題各有側重。談及“通道會議”,周恩來說:“那是個臨時會議,是個緊急軍委會議,是解決軍事方向問題,毛主席參加了這次會議,是被排擠后參加的第一次會議。”(65)《采訪紅軍長征日記》,秦興漢:《讓世界都知道紅軍長征——陪同索爾茲伯里踏訪長征路》,第21頁。周恩來所說的會議,指的就是正式決定西進貴州的芙蓉會議。盡管在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大家(包括博古在內)團結一致、共克時艱,最終達成“向西進入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爾后再定行止”的共識。通道系列會議期間,毛澤東的主張雖然沒有被全部接受,但第一次在中央決策層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通道系列會議期間,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已經呼之欲出。通道系列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會議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