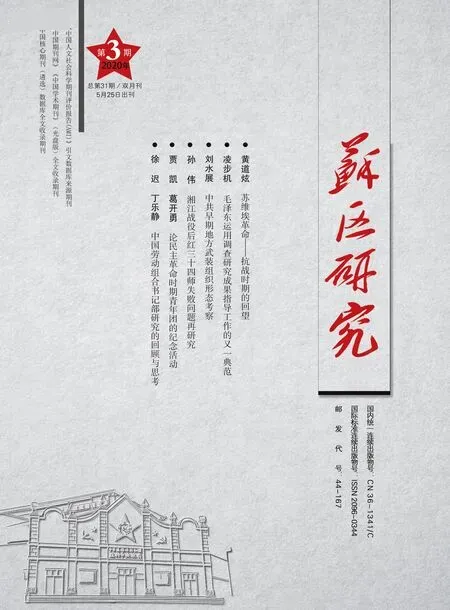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徐 遲 丁樂靜
提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共黨史研究的興盛,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研究價值逐步被人發現,經過海內外學者的努力耕耘,圍繞書記部史料整理及具體問題研究,都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但總體而言,囿于史料、研究視角與方法所限,目前研究成果不可避免仍有一些未能盡意之處。回顧與展望對書記部的研究,在史料發掘、主題與內容拓展、路徑改進等方面都可作進一步開拓與討論。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于上海,它是由中國共產黨黨員出面籌辦,聯絡工會、聯合工人的公開社會團體(1)筆者查閱現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所作原始文獻,均未發現對書記部有明確定義。其宣言指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由上海——中國產業的中心——的一些勞動團體所發起的,是一個要把各個勞動組合都聯合起來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共產黨》第6號(1921年7月7日),第21—22頁。僅此定義未能突出書記部于建黨初期的特殊性,更不能反映書記部與其他勞動團體的區別。文中使用“社會團體”概念源自社會學,“團體”(group)或“社會團體”(social group)的概念是指社會一部分成員,他們共享一種集體歸屬感,或通過相對穩定的互動模式結合起來。這一術語常被應用于共享歸屬感或否(如社會階層團體)和參與常規社會互動或否(如少數族裔)的人群聯合。(John Scott.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96.)。從1921年8月11日成立至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書記部除成立總部外,亦于中共重點開展工作的城市設立分部、并在北方鐵路沿線派駐特派員,成為地方黨組織工運的重要領導機關,亦是中共于工運方面的發聲團體。京漢罷工失敗后,書記部僅在上海保留總部。盡管中共三大會議仍通過“勞動組合書記部今后之責任”的議案(2)《勞動運動議決案》(1923年6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頁。,但各地方黨組織工運時已極少倚靠書記部,至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后,書記部遂成為歷史名詞。
有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的海外,1980年以來,隨著中共黨史研究的興盛,尤其是工運史研究的蓬勃發展,書記部的研究價值逐步被人發現。在隨后30余年中,經過海內外學者們的努力耕耘,圍繞書記部史料整理及具體問題研究,都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這些新的材料與觀點增加我們對建黨初期工運態勢的感性認識,加深對20世紀初期社會政治變遷與中共革命起源問題的了解。
作為一個存在時間不長的社會團體,囿于史料、研究視角與方法之限,目前研究成果不可避免仍有一些未能盡意之處。鑒于尚未有學者專門梳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研究發展歷程,筆者嘗試總結書記部研究的起步與發展,探討其發展脈絡及熱點問題,并就其未來研究方向提出一些淺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研究之起步與近況
一方面由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存在時間短暫,研究資料相對缺失,另一方面出于對其激進性質的顧慮,雖然關于1920年代早期的上海、京漢、粵漢路等地罷工事件的論述不少,然而1949年前大陸研究勞工問題的學者一般不提黨派勢力于罷工背后的作用,以書記部為主題的規范學術研究幾乎是空白(3)陳達在述及有關共產黨工會運動時以“局外人”自稱,以表其除尋常報紙報道外不知內部詳情的態度。參見陳達:《中國勞工問題》,商務印刷館1929年版,第593、602頁;陳達:《我國南部的勞工概況》,《統計月報》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2頁。。書記部多在中共領導者回顧黨內歷史及工運歷史時被提及并被高度評價(4)參見張特立:《“二七”前后工會運動略史》,《新青年》第2期(1925年6月1日),第16—34頁;李立三:《中國職工運動概論》,唐山市總工會辦公室工運史研究組編:《唐山工運史資料匯輯》第1輯,內部發行,1985年版,第30頁;劉少奇:《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頁;等等。。中共黨內最為完整分析書記部成立及作用的著作當屬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是書辟出專章勾勒了書記部的性質、活動范圍與作用(5)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東北書店1947年版。。由于作者早期工運領袖的身份,使得書中關于書記部的敘述被學界認可為最重要的研究資料。
國民黨檢視工運得失時亦會注意書記部。因個人經歷,馬超俊對書記部有著深刻印象(6)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時馬超俊任廣東機器工人維持會主任,他曾就主理的機器工人維持會與中共廣東地方黨員譚平山、譚天度等有過交集。[日]木村郁二郎:《馬超俊略年譜稿》,中國労働運動史研究會編集:《中國労働運動史研究(季刊)》1980年第1號,第7頁;梁復燃:《回憶譚平山》,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編:《譚平山研究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9頁。,他在討論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時亦專門談到書記部問題(7)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上,商務印書館1942年版,第95—96頁。。海外很早有人關注書記部這一組織,日本記者橘樸在1926年考察南滿洲勞動運動問題時指出了書記部的性質(8)橘樸:《支那労働運動と南満州》,《滿蒙》第二十九卷,第七年第八十冊1926年,(東京)不二出版,1996年復刻版,第2—17頁。。其文雖非規范的學術作品,但也能成為學者可資利用的史料。前蘇聯研究者葛薩廖夫與米夫(П·A·МиФ)都肯定書記部于工運初始階段的積極作用(9)葛薩廖夫:《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齊齊哈爾師范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內部發行,1980年版,第35—78頁;米夫:《英勇奮斗的五十年》,北方文化出版社1938年版,第10—11頁。,這一認識同樣存在于美國記者尼姆·威爾斯(Nym Wales)關于工運的論著中(10)Nym Wales.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5,pp.23—24.。據筆者目前所見,1949年前尚無專門討論書記部的論著問世,嚴格意義上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的一些成果。
(一)1980年前研究情況
1950年代開始工人運動史進入主流學術話語體系。論者在述及中國工運起源、上海工運失敗之原因時都會談到書記部(11)劉立凱、王真:《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學習》1952年第1—3期;馮伯樂:《1922年帝國主義者破壞上海工運的罪證》,《學術月刊》1958年第3—4期。。各地企業出版較為普羅通俗化和以老工人回憶為基礎的廠史礦史中,書記部組織工運的作用可見一斑。盡管工運研究成果頻繁見諸報端、出版物,但是學者一般仍未將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時期的罷工事件與書記部聯系起來考察,書記部專題研究未有出現。由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編寫《上海工人歷年斗爭大事記(初稿)》總結梳理書記部于上海成立及其活動的簡要歷史(12)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編:《上海工人歷年斗爭大事記(初稿)》,內部發行,1952年版。,這也為1980年代上海學者從事書記部研究奠定很好的基礎。
與專題研究的冷清相反,書記部研究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卻呈現出蓬勃推進之勢。一方面關于建黨初期工運及重要罷工事件的回憶一般都會兼及回顧書記部,其中有兩項格外值得注意:其一是來自于上海書記部干事、武漢分部主任包惠僧的回憶(13)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包惠僧從1950年代就開始撰寫黨史資料、回憶錄與工運史資料,但除《“二七”回憶錄》在1957年出版過單行本外,其余內容都是直到80年代才被編輯出版。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包惠僧關于書記部成立時間、緣起與分部情況的回憶,與當時學界認知存在出入,故被學者指出厘清這些史實“是研究我國早期職工運動史的重要線索”,相關史實考證有待進一步討論(14)《“二七回憶錄”提出的幾個歷史情況》,《中國工運史料》(第1—8期匯編)上,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631頁。。其二是1950年代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收集,反映大革命時期上海工運情況的口述史料,這其中不乏有與書記部從事活動、人物相關的材料。
另一方面被編輯出版的工運史料中,除與書記部分部相關的新史料陸續被整理發布外,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職工運動史研究室編輯《中國歷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中國工會歷史文獻(1921.7—1927.7)》兩冊互作補充,成為比較完備的書記部史料匯編。同由該室在1958和1960年各出版4期《中國工運史料》,收錄書記部機關刊物《勞動周刊》與《工人周刊》,為書記部研究又作有力史料補充。
海外學界對書記部研究起步較早,這與1949年以后海外學者對中共關注度提高密切相關,書記部因與中共成立后開展工作的緊密聯系而日益引起不同國家學者的注意。1953年中村三登志撰寫《中國工人運動史》,使書記部的史實在海外學界首次有了新的突破(15)[日]中村三登志著,王玉平譯:《中國工人運動史》,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6頁。。謝諾(Jean Chesneaux)出版于1962年的博士論文拓展了書記部的研究深度。他著重分析書記部成立后領導重要工業城市及京漢、隴海鐵路罷工、組織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經過(16)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77—201.。盡管他過于強調上海工人的集體意識受到左派群眾革命的影響,相對忽略其他經濟、社會因素(17)陳明銶:《中國勞工運動史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633頁。,但是這并不妨礙他的論述成為這段時期西方學術界認識中共早期工運的開創性成果。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工人運動史成為蘇聯中國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И·И·格拉西莫娃指出書記部于共產小組的工運基礎下成立(18)[蘇]B·H·尼基福羅夫著,馬貴凡譯:《蘇聯學者對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的研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譯處編:《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譯文集》第1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509頁。。這以后,前蘇聯史學界圍繞中共成立是否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產物這一問題進行過討論,由此促成對書記部研究的重要突破(19)[蘇]A·И·卡爾圖諾娃、E·Ф·科瓦廖夫著,馬貴凡譯:《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問題問題(1917—1921)》,《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譯文集》第1集,第120頁。。1973年,A·И·卡爾圖諾娃考證書記部成立時間、與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等組織關聯及成立后工作任務等問題。可以說,她的研究對厘清書記部基礎性史實具有開拓性意義(20)[蘇]A·И·卡爾圖諾娃:《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國際援助(1920—1922年)》,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9頁。。
(二)1980—1990年代的研究進展
國內學界關于書記部研究的發軔得益于工運史研究的興盛。1980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發文要求“各省、市、自治區總工會要把工運史工作作為經常的重要業務之一,設置必要的工作機構(工運史研究室)”(21)《1980—2010年工作筆記選錄》,劉功成:《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30年文選》,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510頁。。由此,工運史料的收集、整理與出版工作、工運史研究都大大加強。
1.史料整理與出版
中華全國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出版的工運史文獻,各主要省市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以期刊形式出版的工運史資料,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時期工運主要事件及文獻檔案,共產黨干部和早期工運領袖回憶文章,黨與工運領袖傳記、文集、研究史料等,都為書記部研究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史料。其中曾任北方分部主任的羅章龍與書記部首任主任張國燾的回憶一經問世引起學界高度關注。由于羅章龍曾于西北聯合大學執教,他在憶錄史實的同時也輔以考證,故他的回憶兼具史料與研究價值。張國燾寫作自傳時身處海外,其文須結合撰寫時的具體背景加以分辨,但他所描述書記部的豐富歷史細節仍為研究者的考證提供了可深入挖掘的空間(22)參見羅章龍:《記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3期;羅章龍:《椿園載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84年版;羅章龍:《談談唐山建黨與早期工人運動》,《河北黨史資料》第2輯,中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審委員會1985年版;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印社1980年版。。
80年代末,書記部研究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現新的突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章程》的發現,為學界研究書記部的初期活動提供了第一手資料(23)關素賢:《十年來新公布的中國工運文獻史料概述》,《中國工運學院學報》1990年第3期,第64—65頁。。除《章程》這樣的稀見史料之外,上海書記部史料也通過整理匯總而編訂成冊。由上海學者陳衛民領銜完成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一書,對書記部成立及在上海開展活動和斗爭情況所涉及的相關資料進行匯總(24)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上海市總工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該書所選史料均為與書記部活動相關的報刊、檔案和當事人回憶,史料價值極高。
1977年日本學者創辦、編輯大陸以外唯一的中國工運史學術性期刊《中國勞動運動史研究》創刊,中國勞動運動史研究會同時也出版木村郁二郎編《中國勞動運動史年表》《中國勞動問題勞動運動史文獻目錄》這兩部工具書(25)[日]木村郁二郎編:《中國勞動運動史年表 1559—1927年》,油印本1966年版;《中國勞動運動史年表 1928—1949年》,油印本1967年版;[日]中國勞動運動史研究會編:《中國勞動問題勞動運動史文獻目錄:解放前》,汲古書院1978年版。,都成為可供書記部研究參考的重要史料。
2.研究拓展
作為地方工運史研究重鎮,各省市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推進了對書記部的研究工作。1984年,天津市總工會圍繞書記部天津支部展開專題調研,對支部成立背景、負責人、活動與存續時間等內容進行考證(26)天津市總工會:《關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專題調查報告》,《工運史研究資料》1984年第2期,第13—15頁。。1986年,值書記部成立65周年之際,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牽頭,在山東蓬萊組織關于書記部的研討會,北京、上海、長沙、武漢等各地工運史研究室均有代表列席(27)張秋生訪談記錄,訪談時間:2018年12月12日。。會議之后,各地結合當地工運歷史的特色開始組織撰寫本地書記部的發展沿革,以湖北省總工會工運史室對書記部武漢分部始末的考證尤為典型(28)湖北省總工會工運史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始末》,《工運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除工會界外,80年代黨史研究領域也開始關注書記部。以上海學者姜沛南、陳衛民的研究為代表,考證了書記部的成立時間、書記部名稱的由來、總部和各地分部的組織狀況以及書記部何時結束等具體問題(29)姜沛南、陳衛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始末考》,《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3輯。。隨后,學界圍繞書記部成立時間、性質定位、組織狀況等問題展開討論,推動研究走向深入。另外,書記部所參與的活動多見于中共早期工運論述中,此類論文的數量大大超過此前。
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陳衛民撰文考察上海書記部多階段的歷史演變(30)陳衛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任武雄主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文集》,百家出版社1991年,第557—575頁。。陳對書記部的研究成果還在《上海工人運動史》中充分展現,尤其陳詳細論述書記部領導工會與招牌工會既聯合又斗爭的關系(31)沈以行等主編:《上海工人運動史》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使行文突破“黨史的架子”“工運史的例子”,大為拓展了研究范圍(32)張注洪:《〈上海工人運動史〉(上卷)評介》,《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83頁。。其他書記部的整體研究,還包括唐玉良對書記部性質、歷史貢獻與經驗層面的總結(33)唐玉良:《略論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歷史和貢獻——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北京“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1991年。。
縱觀這些研究著述,研究內涵與素質的提升不容置疑,不過“黨領導工人反抗資本家壓迫”的革命史話語依然存在。論者們幾乎將共產黨等同于工人階級本身,忽略了黨和工人階級的差別,對于書記部領導工人中出現的問題很少論及。這一時期大陸書記部研究也缺乏與海外學者的積極對話。
大陸以外工運史研究的熱度持續,也使得書記部的研究向更深層次邁進。在臺灣的多篇研究中共及國民黨早期工運的碩士論文中都述及書記部,并在論述中各有偏重:如陳嘉慧尤其注意到廣東分部的動作及書記部總部北遷后對北方工運的組織(34)陳嘉慧:《聯俄容共前后(1920年代)國共與工運關系的比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杜梅生、樸貞薰先后都討論了中共建黨后張國燾對工運的態度與角色問題(35)杜梅生:《張國燾與早期的中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年碩士學位論文;樸貞薰:《張國燾與中國共產黨》,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年碩士學位論文。。Lynda Shaffer關于湖南的工運研究和陳明銶對五四運動后期中共工運起步的論述中也都討論到書記部(36)Lynda Shaffer.Mao and 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NewYork:M.E.Sharpe,1982, pp.42—49.Ming Kou Chan.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895—1949:A Critical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s Source Materials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1, pp.86—92.。K·B·舍維廖夫在研究中共成立歷史時,提出書記部成立與遠東局代表的關系(37)[蘇]K·B·舍維廖夫:《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略》,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第38頁。。此說也是對A·И·卡爾圖諾娃研究思路的拓展。荷蘭阿姆斯特丹社會史國際研究所收藏的《斯內夫利特卷宗》對荷蘭學者托尼·賽奇(Tony Saich)的研究起到推動作用。他明確了馬林親自起草書記部成立宣言,并把它譯成中文的史實,說明馬林對書記部于上海英美煙廠罷工及京漢鐵路罷工的組織都感到滿意(38)[荷]托尼·賽奇著,王作求譯:《斯內夫利特與第一次聯合戰線的起源(1921—1923年)》,《史林》1987年第4期,第150頁。。
(三)新世紀后的發展
90年代末開始,對書記部的研究主要在黨史領域中進行。各省市新出黨史著作能代表地方黨史領域對工人運動最權威的研究成果。2000年以后,書記部研究又出現新趨勢,即以書記部的早期參與人員為中心(39)參見《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5—14輯中相關文章。。張國燾、李啟漢、王荷波等與書記部相關黨與工運領袖傳記同屬此類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記相對更注意使用最新發掘的史料(40)如蘇若群、姚金果在2018年重新編撰出版《張國燾傳》時,尤其注重結合俄羅斯公布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有關中國革命的檔案。其他可見2016—2017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中國工運歷史英烈傳。。
進入新世紀,書記部全國性史料的整理與匯總取得新的突破。劉明逵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資料長編,其中第四冊匯集從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中共三大期間領導工人運動的資料,該書幾可被視為是對當時期國內書記部及工人運動相關材料的集中匯總(41)田剛、劉明逵:《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然而,由于資料集編纂時間晚于書記部的研究高潮期,學者們對新出史料的利用率相對較低。
書記部研究獲得更進一步拓展。北方分部的成立時間、早期部員及初期工作被重新考證(42)李自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成立情況及初期工作的新考釋》,《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0期。。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背景與會議內容,孫中山、譚平山等與大會淵源(43)參見卜穗文主編:《廣州農講所紀念館論叢》第2—4輯相關文章。,大會對中國共產黨早期發展的意義(44)王繼凱:《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發展》,《黨的文獻》2012年第6期。等研究主題被深入挖掘。書記部應對幫會、宣傳及組織工會等具體工作內容也被專門考察(45)陳思:《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研究》,鄭州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
近年中共革命研究被納入歷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46)應星:《略述歷史社會學在中國的初興》,《學海》2018年第3期,第22頁。,這一新動向也促進書記部研究的深入。馬學軍以組織社會學的視角分析書記部對工人的組織方式——特派員制度。這種新視角不僅使書記部研究在黨團制度上有了新突破,而且通過安源特派員的實踐探索,使得特派員的形象與實際行動都更為生動化(47)參見馬學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淵源與演變再考察》,《學術交流》2016年第2期;馬學軍:《特派員制度與中共早期工人運動:以安源工運史為中心(1921—1925)》,《社會》2017年第2期。。
此階段港臺與海外學界涌現的中共建黨與工人運動的研究成果,無一例外均會提及書記部,以陳永發、裴宜理、石川禎浩等為代表學者。書記部被視為中共實踐建黨的綱領性內容、發動與組織工人的重要動作,其在長辛店、安源、京漢鐵路線等地罷工中的領導作用受到重視(48)參見[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馬林與書記部的關系亦仍被關注,道夫·賓(Dov Bing)重新梳理出書記部建立初期在上海和全國領導的主要罷工運動。該文以馬林對中國工運的關注與指導為研究重心,使用了西文《論壇報》以及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等資料,都為國內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史料和研究角度(49)道夫·賓:《20世紀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建立》,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576頁。。
二、相關研究的主要問題與論點評述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研究發展至今,涵蓋了許多問題,具體討論亦隨著研究深入和時代演進而漸漸變化。筆者將側重學者們關注最多的幾方面問題展開論述,以體現各種觀點的互動。
(一)書記部的起止時間
明確書記部的起止時間對進一步研究中共建黨早期工運的方針制定與路徑實施均有影響。對書記部成立時間的認定曾引起一部分學者的爭論。曾長林、楊洪范等人均認為書記部成立于中共一大以前。他們依據《共產黨》月刊第6號的出版日期于1921年7月7日,刊載《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以宣告書記部成立,推知書記部成立時間比中共一大(7月23日)早半個月。同時,此說也有羅章龍的回憶作為輔證(50)曾長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于“一大”以前》,《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280—281頁;楊洪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何時成立?》,《歷史教學》1983年第4期,第37頁。。
蔚宗齡、姜沛南等人均認為書記部成立于1921年8月以后。蔚宗齡考辨《共產黨》第6號應是在《勞動周刊》第4期與第5期期間出版,時間在1921年9月中旬(51)蔚宗齡:《關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時間的問題》,《南充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第52—54頁。。輔以包惠僧與張國燾的回憶錄,蔚宗齡指出書記部“是在黨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成立”。姜沛南、陳衛民引用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穆爾基斯的信件,信中明確書記部成立時間是1921年8月11日(52)姜沛南、陳衛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于“一大”以后》,《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301—304頁。。這一史料早于1973年被A·И·卡爾圖諾娃挖掘并注釋。在未有更有力史料證明的情況下,2002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修黨史時,吸收姜、陳的觀點,“中央局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5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頁。
關于書記部的結束時間,學界尚未形成定論。姜沛南、陳衛民在1980年指出,1923年10月以后,沒有再發現書記部的活動材料,到1925年春黨決定不再使用書記部名稱,至此書記部完成歷史使命(54)姜沛南、陳衛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始末考》,《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3輯,第114—115頁。。1990年,陳衛民又對書記部結束之說做了一些修正,他指出1923年2月中旬“二七”罷工后至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這是書記部轉入地下秘密活動時期。相比之前的考證,陳衛民補充梳理上海書記部在1923年以后的相關活動,尤其他使用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記錄,強調1924年“二七”周年紀念活動也是以書記部名義參加(55)陳衛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任武雄主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文集》,第574—575頁。。后陳又進一步補充史料說明,該次紀念大會被1924年2月8日《民國日報》報道,但出席的15個團體中既無書記部,也沒有王荷波與施存統的演說,可見書記部是不能公開進行活動了(56)陳衛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成立及其在上海的主要活動》,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征集研究室:《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 黨的創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8頁。。
王健英在對中共三大后中央機關各部門的考證時發現書記部的新史料:1923年8月5日,中共中央局秘書毛澤東代表中央在上海地方兼區委第六次會議上提出:“勞委會與勞書部負責人應一致”。王健英認為中共三大后上海同時并存書記部總部與分部,鄧中夏負責書記部總部全責,王荷波僅為上海分部主任(57)王健英:《中共三大及其后的中央機關》,《上海黨史與黨建》2003年第5期,第33—38頁。。筆者認為,王的考證至少存在兩方面問題:其一,《勞動周刊》早于1922年6月9日被會審公廨勒令停刊(58)力紅:《黨的創立時期重要的工人報刊介紹》,《中國工運史料》(第1—8期匯編)上,第285頁。,不會持續到1923年三大后,仍由“鄧中夏、張秋人等負責《勞動周刊》的出版”;其二,鄧中夏被視為三大后書記部“負總責”無確鑿史料證明。
在既有研究與史料的基礎上,筆者發現,1923年12月6日上海地委兼區委會議記錄也充分證明書記部于1923年末的存在。上海第五小組詢問“上海尚有勞動組合書記部及勞動委員會否,漆業工人罷工日久,書記部有沒有去參加”。地委會“答以勞動組合書記部仍在,勞動委員會已取消(此本附屬于地方委員會),漆業工人罷工時因知他們非常渙散,且手工業工人屢次組織俱經失敗,而該時又值書記部他事甚忙,故未往接洽。”(59)《上海地委兼區委第二十五次會議記錄——杭州組、上海第二、五組報告及梅坤辭職問題》(1923年12月6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內部發行,1989年版,第58頁。總結來說,書記部在1923年“二七”大罷工后轉入地下秘密時期,至1925年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時撤銷。但我們應該清楚認識,目前關于書記部結束的討論仍以上海總部的結束為準。對各分部的結束時間,除中央及地方組織史資料進行過有限整理外,尚無更多的研究成果。
(二)書記部的性質及其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關系
書記部是工會組織還是黨的組織,學界對此看法不一。筆者認為,結合書記部成立的淵源考慮,對理解其性質很有幫助。早于1970年代A·И·卡爾圖諾娃就已指出,書記部的成立受到駐東方民族處、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以及國際工會聯合會代表的幫助。書記部是中共組織和領導職工會的合法機構(60)[蘇]A·И·卡爾圖諾娃:《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國際援助(1920—1922年)》,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第53—59頁。。駐赤塔赤色職工代表斯穆爾斯基的信件對書記部的工作體制描述被學者反復引用:“書記部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工作,而在工作中又有充分的獨立性”(61)《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Ю·Д·斯穆爾基斯的信件》(1921年10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等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第3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0頁。。
就此,王繼凱強調書記部的本身性質是黨領導下的工會聯絡機構。作為工會組織,書記部與黨的組織在嚴密性、組織性、紀律性等方面有較大差異。中共二大的決議案中對黨與工會區別的分析也可被視為最為直接的厘清黨與工會的本質、功能及其相互關系的證據(62)王繼凱:《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發展》,《黨的文獻》2012年第6期,第67頁。。馬學軍總結一大召開之際共產國際遠東書記部代表馬林對書記部成立持“勞動組合”與尼柯爾斯基的“黨領導工會”的觀點。盡管尼柯爾斯基暫未有確鑿史料能確證其觀點,然而同樣結合斯穆爾斯基的記載,書記部是一個黨領導下的工會聯合機構(63)馬學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淵源與演變再考察》,《學術交流》2016年第2期,第145—146頁。。
劉功成將書記部完全等同于中共組織機構:“書記部及其分部是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組織的工作機構”。其立論依據引用鄧中夏之語,是“一公開的做職工運動的總機關”。輔以包惠僧在《二七回憶錄》中所說,“勞動組合書記部是中共中央為實現勞動運動的計劃,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工作部”。(64)劉功成:《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性質辨析》,《工會理論與實踐》1996年第6期,第49—50頁。與以上兩極觀點不同,唐玉良認為書記部具有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人群眾團體的雙重性質(65)唐玉良:《略論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歷史和貢獻——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北京“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第2—3頁。。在唐看來,書記部既是后來黨的職工運動委員會和職工部等部門的前身,又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雛形。
筆者認為,承認書記部在黨的領導下發揮工會聯絡作用,而非直接的工會性質更符合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書記部同時期并立于上海的其他勞動團體曾不止一次指出書記部“并非勞動者組織”,“書記部的組織原動力,為外國舶來品;內幕牽線人,為廣東謀叛匪魁陳炯明”(66)《兩工團對勞動法案之爭辨》,《民國日報》1922年9月6日,第10版。。
除發揮工會聯絡作用之外,筆者認為也應重視書記部于工界“聯合”的功用。其成立宣言所述,“是一個要把各個勞動組合都聯合起來的總機關。要聯合或改組已成的勞動團體,使勞動者有階級的自覺,并要建立中國工人們與外國工人們的密切關系”(67)《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共產黨》第6號(1921年7月7日),第21頁。。章程第二條也明確“本部以‘促成各業工人組織團體,增高工人地位及促進工人國際聯合’為宗旨”(68)《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章程》,《工人周刊》第52期(1922年9月17日),第4版。。這都體現了書記部的雙重工作對象部署,即便其實踐成效值得再觀察。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就指出“書記部”是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一個工具——一個只要它能為工人贏得好處,就會受到歡迎的工具,只是與工人沒有多少密切聯系的工具(69)[美]本杰明·I·史華慈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頁。。時人對書記部籌辦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宣傳話語與回憶錄中,“聯合”用語更為突出。李達撰文對一勞大表示期待“中國勞動界既然感到有大聯合的必要,舉行這個大會,就應該有永久的結合”(70)李達:《對于全國勞動大會的希望》,《先驅》第7號(1922年5月1日),第2頁。。述及一勞大召開的背景,張國燾指出“中共中央認為如果建立各革命黨派的民主聯合戰線,中共必須首先獲得代表工人發言的資格”(7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213頁。。
對書記部性質的爭論亦波及書記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關系的判斷。學界普遍認為書記部是全總前身,主要出自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所述:在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上,通過“在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承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案”(72)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62頁。。同樣認知在陳公博文章中也有體現,他在說明共產黨起源團體時,將全總與社會主義青年團視為最強大的組織。他以“全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例說明兩個團體革命活動的積極表現(73)陳公博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95—96頁。。由于陳兼具研究者與親歷者雙重身份,作為廣東早期黨組織的籌建者之一,他對書記部的印象體現了書記部在地方黨領導者心中的真實狀態,即此時書記部已被視為全總的代表團體。
也有學者對此說法提出質疑,如劉功成兩度撰文,梳理“職工委員會”的沿革,認為書記部是職工運動的最初專職機構(74)劉功成:《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性質異說》,《史林》1991年第2期,第58頁。;并分析書記部與全總在領導方式、組織原則和經費來源等方面不同,故非繼承性的組織關系(75)劉功成:《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性質辨析》,《工會理論與實踐》1996年第6期,第50頁。。馬學軍也將書記部與全總組織方式進行對比,指出從決定負責人與基層工作方法角度,兩者均有差異,因此可以認為,書記部只是“借用”對外聯合各產業工會團體之名,而非全總前身(76)馬學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淵源與演變再考察》,《學術交流》2016年第2期,第149—150頁。。
筆者認為,對一勞大中“書記部作為通訊機關”決議案再分析也可為解決此問題提供新思路。研究者多忽略這項決議案是大會臨時動議,而鄧中夏所言書記部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案,事實上便是公認它為全國唯一的領袖”,這一“公認”的程度與范圍由于與會成員成分復雜還可再做商榷,書記部的確經由此次大會在全國有了影響力。由于當時工人在整體素質、組織方式與斗爭程度等方面水平參差不齊,使得工人運動必須有一個能夠發揮聯合、聯絡作用的團體居中協調、領導,書記部由此應運而生。盡管相比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運作方式,書記部的組織結構尚不成熟,但其組織工會的工作內容與全總有一致性,并為后期全總誕生奠定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全總前身。
(三)總部與分部的組織狀況
書記部在上海成立后不久,相繼在各地建立分部的史實為學界認可。但是,各地分部何時成立,共有多少分部,分部名為何,負責人是誰,有關這些問題說法頗不一致,需作進一步分析。
關于書記部從上海遷往北京的時間與原因,姜沛南與陳衛民有過細致考證:書記部總部遷往北京的時間大體確定為1922年8月;遷移原因是在上海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無法立足,在北京當時尚可公開活動,有利于對全國職工運動的領導(77)姜沛南、陳衛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始末考》,《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3輯,第110—112頁。。對于這種提法,學界也基本認可。書記部從上海遷往北京的時間與北方書記部的結束時間吻合。張秋生援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章程》第五條內容“本部設總部于北京”,上海暫設分部。張考辨《章程》是1922年9月17日被《工人周刊》公布,由此可以確定總部遷移北京,《章程》中便不提北方分部,北方分部存在時間是1921年9月至1922年8月(78)張秋生:《關于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兩則考訂》,《北方黨史通訊》1988年第1期,第32頁。。
李自華對書記部北方分部的成立情況進行新的考證。需要特別解釋的是,他所提出“書記部北方分部”的稱呼,是成立于1921年北方分部與1922年北方總部的統稱。李依據新披露《北方分部報告》,指出分部成立于1921年11月1日,略晚于張秋生1921年9月的說法。李又對北方分部早期部員進行考證,指出共包括羅章龍、楊之君在內的10人(79)李自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成立情況及初期工作的新考釋》,《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11—116頁。。
與之相關的書記部分部人員分工問題,研究成果較少。張秋生對鄧中夏是否擔任北方書記部主任進行考證,指出鄧中夏僅擔任遷京后書記部總部主任(80)張秋生:《關于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兩則考訂》,《北方黨史通訊》1988年第1期,第32—33頁。。馬學軍提出特派員制度的新研究視角對分部人員研究無疑具有開拓性。但他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梳理特派員制度的基礎上,研究特派員實際工作過程及效果(81)馬學軍:《特派員制度與中共早期工人運動:以安源工運史為中心(1921—1925)》,《社會》2017年第2期,第193—215頁。,未分析書記部湖南分部組織結構、特派員群體構成。
山東分部的組織狀況研究見于李曙新的考證。李指出,凡1922年8月以前的文獻均使用的是“山東支部”,1922年8月以后的文獻均使用“山東分部”,即8月前后,山東書記部的名稱出現改變。同時,他還強調了山東分部直到1923年還繼續存在,并未被合并至北方分部。(82)李曙新:《關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分部的兩則史實》,《山東工會論壇》2014年第1期,第69—71頁。但遺憾的是,除山東外,武漢分部與廣東分部依然存在名稱混亂、多種說法并存的現象,尚無學者進行深入研究。根據已公開的史料,這一問題實已具備繼續研究的條件(83)廣東分部考證研究,可參見徐遲、丁樂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分部幾個問題的考辨》,《上海黨史與黨建》2020年第1期,第27—32頁。。
(四)總部與分部的主要活動
書記部的活動體現了中共誕生后對工人運動的著力推動,書記部參與過哪些活動,發起這些活動的內在動因與實際影響如何,學者關于書記部總部與分部的主要活動及某些具體工運事件的研究對以上問題進行積極回應。葛薩廖夫認為,中共通過成立一個“部”領導工人運動。繼1921年純粹經濟性罷工潮發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工會網開始布滿全國(84)葛薩廖夫:《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上,第47—61頁。。謝諾指出,書記部是中共能夠積極參與工人運動的手段。它傳播關于組織與行動的新思想,介紹赤色職工國際的出版物,培養能夠提高罷工行動水平且精力充沛的領導者,并建立了大量工會(85)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p.198.。實際而言,書記部于工運中的努力是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從事工運的思路延續。
從陳衛民分析上海書記部三階段的具體內容,我們可發現書記部的活動在逐漸減少。上海工運取得的成就與工商業中心、工人隊伍集中壯大的歷史地位頗不相稱。究其原因,除租界對上海工運的警惕及鎮壓外(86)馮伯樂:《1922年帝國主義破壞上海工運的罪證》,《學術月刊》1958年第3期,第56—62頁。,黨的主觀因素、流氓幫會、地方幫口阻礙及女工童工分散工人階級的戰斗力都有關系(87)陳衛民:《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的上海工人運動評估》,《史林》1988年第4期,第72—79頁。。
李自華以“春云漸展”表現出北方分部工作地域范圍擴展,宣傳教育、籌組工會及領導大規模罷工所取得的成效(88)李自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成立情況及初期工作的新考釋》,《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15—119頁。。由于山東分部存續時間過短,分部前后主任王盡美與鄧恩銘都接受北方書記部的領導(89)山東省總工會編:《山東工人運動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3頁。,山東分部研究相對缺乏,僅見津浦鐵路大槐樹機車廠工人俱樂部的成立(90)《山東成立的第一個工會組織——津浦鐵路濟南大槐樹機車廠工人俱樂部》,濟南市總工會調研室編:《濟南工運史料》第1輯,1982年版,第59—65頁。。
武漢分部在“二七”罷工前的活動以成立粵漢鐵路工會與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為重要歷史功績(91)湖北省總工會工運史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始末》,第16—19頁。,在分部領導下頻起具有政治性訴求的罷工。經肖甡、孔蘊浩辨誤,得出書記部及武漢分部是二七大罷工領導者的結論(92)肖甡:《也談京漢鐵路大罷工的領導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11期,第19—22頁;孔蘊浩:《“二七”罷工是我黨單獨領導的》,《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312—313頁。。孫自儉雖是從工人角度出發分析工人愿意發動罷工及罷工失敗的原因,但他同時也承認中共對罷工極為重視,派出包括張國燾、包惠僧在內50余名黨員參與罷工前后的工作(93)孫自儉:《“二七”大罷工時期的京漢鐵路工人論述》,《歷史教學》2015年第12期,第29—36頁。。由其思路出發似可繼續挖掘中共指導思路對罷工發動及結束的影響。對京漢鐵路線罷工的深入討論中,劉莉不僅指出中共為消除京漢鐵路的幫口組織問題所采取的策略與方法(94)劉莉:《中共對京漢鐵路工人幫口組織的利用和改造》,《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44—54頁。,還著重分析了京漢鐵路大罷工的發生源于深刻的社會根源,提出工人群體的地緣文化、生存策略及社會生態環境等因素都應被重視(95)劉莉:《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再研究——以原因、影響為重點的探索》,蘇州大學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5—46頁。。
湖南分部成立后在長沙的工運活動借由湖南勞工會開展,論者關注到湖南勞工會接受中共湖南區委領導、干事張理全陪同毛澤東考察安源的史實(96)支國華、劉善文:《湖南勞工會與毛澤東考察安源的有關史實(草稿)》,大庸“湖南勞工會學術討論會”論文,1984年。。論者常就湖南工運的成功原因進行總結,裴宜理以強調一系列符號資源戰略性運用在政治說服中發揮作用的“文化置位”說來解釋(97)[美]裴宜理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馬學軍以李立三與劉少奇,這兩位安源特派員為討論中心,認為李立三利用個人資源開創安源工運,作為繼任者的劉少奇則未能維系安源工運,由此表明特派員的組織制度的運作效果是引發安源工運興衰的重要原因(98)馬學軍:《特派員制度與中共早期工人運動:以安源工運史為中心(1921—1925)》,《社會》2017年第2期,第212—213頁。。
與其他分部相比,由于輾轉嬗變的廣東政局,處理與其他勞動團體的關系、加強革命宣傳是廣東分部的工作特點(99)《黨成立初期廣東工人運動的幾個問題》,《盧權集》,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9頁。。學界就其是否領導香港海員大罷工引起爭論。劉麗認為盡管書記部對罷工予以支援,但是罷工是由國民黨發動和領導(100)劉麗:《香港海員大罷工是國民黨領導的》,《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282—283頁。。禤倩紅、盧權對劉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香港海員罷工是由蘇兆征、林偉民為骨干的香港海員工會發動和領導,罷工過程得到國共兩方的支持(101)禤倩紅、盧權:《香港海員大罷工是國民黨領導的嗎?》,《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177—186頁。。這個觀點與И·И·格拉西莫娃的看法部分接近(102)[蘇]B·H·尼基福羅夫著,馬貴凡譯:《蘇聯學者對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的研究》,《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譯文集》第1集,第508—509頁。。葛坤英、周文順亦贊同國共雙方共同領導海員罷工,他們著重分析書記部在全國范圍內對罷工的支持(103)葛坤英、周文順:《國共關系史上劃時代的一頁——香港海員大罷工探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第22—25頁。。
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與勞動立法運動是書記部存續期間于全國公開發聲的兩項重要活動。鄧中夏參與一勞大與直接領導勞動立法運動的經歷,使得他的論述幾乎成為國內學界公認的信史。論者對這兩項活動的研究大多仍沿襲鄧中夏的解釋框架與觀點,闡述中共領導下大會的籌備、議程、決議案與《勞動法大綱》的具體內容(104)王永璽:《中國工會統一之先聲——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述評》,《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中國工人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333頁;李剛:《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勞動立法運動》,《史學月刊》2002年第2期,第134—136頁。。王繼凱從一勞大對中共早期發展的角度分析該次會議帶來的影響,他指出中共影響力的迅速擴大肇始于一勞大(105)王繼凱:《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發展》,《黨的文獻》2012年第6期,第64—65頁。。書記部于兩次活動中的召集聯絡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國民黨員與其他勞動團體領袖在大會籌備階段的努力與召開期間的影響被相對忽略;勞動立法運動中全國其他勞動團體對書記部身份的認同與否及對立法運動的態度值得研究者更進一步思考。
以上問題的討論深化了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認識,為今后的研究構建了一個堅實的平臺。從以往的研究方法來看,多數論者更愿意使用實證的方法來重建書記部的史實,偶有借助社會科學中的概念、視角。盡管如陳耀煌通過同儕、同鄉與師生傳統的特殊聯系角度來理解建黨早期河北與北方地區的工運(106)陳耀煌:《內生抑外塑: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國立政治大學2005年博士學位論文。,然而海外工運研究常采用的西方社會科學理念與方法尚未被運用于討論書記部問題中。就研究內容而言,國內絕大部分研究多指向于中共革命動員自上而下的運作狀態。究其原因,論者從中共政策出發解讀書記部的工作效果,使得書記部分部研究同質化傾向明顯。近年來涌現出對安源的個案研究無疑頗有洞見,但是若以特派員來概括中共早期領導工人運動的運作模式,又似乎有點以偏概全。裴宜理的“文化置位”說也被質疑是否是可復制的抗爭政治“典范”,或只不過是革命歷史發展中的一個“例外狀態”(107)唐小兵:《何種革命?誰的傳統?——裴宜理〈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讀后》,《開放時代》2015年第5期,第222頁。。
書記部所領導的工運罷工結果被廣泛關注,但是書記部組織結構上的一些具體問題卻缺少足夠深入的研究。如組織仍屬分散、行動具有自主化特色的地方黨組織如何甄選出書記部工作人員,如何維持書記部的有效運作?各地分部的組織成員構成如何,他們的個人資歷、社會資源等因素如何影響到組織工運的效果?這些問題均鮮有人研究。應該說,各地分部的模式很難歸納出一套總體性的特點。然而除劉莉對京漢鐵路線罷工的深度分析外,學者對中共早期工運的推進與社會背景的互動仍著墨甚少,有深度的區域實證研究仍很缺乏。論者或許可從各城市不同的歷史情態出發分析書記部是如何切入當地社會與工人之間,討論書記部與既有的社會環境之間發生了什么樣的互動。同樣,書記部居于不同時段的角色與功能也不相同,需要做認真的動態考察。因此,書記部的研究仍有大可發掘的余地。
三、未來研究的方向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研究發展至今,已有30余年的歷史。研究者們努力挖掘史料,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書記部的歷史原貌。然而,如何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推陳出新,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未來的研究或許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新史料的發掘
目前書記部研究所依據的史料,主要以回憶史料與報刊資料為主,原始史料雖有使用但尚不豐富。盡管由書記部直接出版的期刊大都散逸(108)據筆者統計,目前保存較為完整的書記部機關刊物為湖南勞工會《勞工周刊》(全14期)。其他書記部機關刊物散失嚴重。,但是同時期建黨史料卻非常豐富。筆者嘗試總結以下幾種與書記部有直接關聯的史料,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線索。
第一,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愈發被重視的《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系列叢書。在建黨初期黨團工作交織的地區,青年團的工作匯報中亦常混雜與工運相關的有價值史料。第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中的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及警務處日報。這兩份幾乎為專家學者研究公共租界之必備史料。上海書記部選址于公共租界內,研究者尤應關注檔案中相關記錄。第三,蘇聯方面的檔案資料。近年來學界已通過各種渠道挖掘整理相當數量的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相關的珍貴材料。其中,中共代表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中的活動記錄尤為值得關注,參會者報告時都會結合到中國工運的情況(109)特別如《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收錄1920年至1923年間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共創建關系的專題檔案資料。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除集結成冊的出版物外,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共產國際卷宗檔案的公開發表,也使得研究者不斷有新的收獲(110)李玉貞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關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中共創建的五份文獻》(一九二一年六月——一九二三年六月),《黨的文獻》2011年第4期;《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大及其籌備會議和第一屆團中央執委會會議記錄》(一九二二年五月——一九二三年八月),《黨的文獻》2012年第1期。。第四,臺灣國民黨黨史館所藏檔案。有學者介紹,擔任廣東書記部主任馮菊坡任職國民黨工人部秘書時的相關檔案達108條之多(111)趙慶云:《工運先鋒馮菊坡》,《環球人物》2011年第18期,第51頁。。自1923年起,原與書記部相關的多位中共黨員都加入國民黨相關部門工作,故對國民黨成立的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和商民這五部的檔案材料,研究者應予以高度重視。第五,來源于其他海外途徑的史料。英國公共檔案館中藏有同時期英國駐上海情報局發回英國的情報,其中涉及到陳獨秀的活動(112)李丹陽譯:《英國檔案中所見有關陳獨秀1920—1922年間活動的情報》,《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類似對租界的情報關注,不僅僅是英國一國。20世紀20年代前后日本政府對上海、北京及中國其他地區革命活動進行監視,建黨早期的勞工行動、書記部人員的活動痕跡散見于原始檔案之中。這些檔案保存于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和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已被編印出版(113)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中共建黨前后革命活動留日檔案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除以上已經出版、公開的史料外,筆者也試列舉一些值得深度挖掘的史料線索。譬如鄧中夏在《北游雜記》中提到“茲由日記中摘錄十數條,公之于示”(114)《北游雜記》(1924年),《鄧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頁。。鄧中夏的完整日記或是研究此段歷史最值得期待的史料。另外,湖南江華縣李啟漢故居所藏李啟漢日記,上海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藏“工運史口述資料”都是暫未得到足夠重視的重要文獻。
(二)研究主題與內容的拓展
對書記部內部的研究,似仍較缺失。書記部的總部與分部的內部運作是否有一定的共通性?任何團體均是由個體所構成,討論總部或分部自然不能脫離對書記部負責人、干事或特派員的考察,他們是如何被確定從事工運活動,其間的互動關系又如何?其人員更替的原因如何,對工運實際效果又有何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均需要深入研究。
既往的書記部研究,由于論者過多重視書記部在中共領導下工運機關的性質,往往忽略了書記部與“他者”的關系,以及其中所富含的許多實際政治層面的問題。如書記部與中共早期團組織都是中共領導的外圍組織,他們在領導人員構成是否有交疊,領導方針與工作開展時是否有互相輔助的一面?書記部與其他勞動團體關系又是如何,在一些共同參與的事件認識方面,是否有分歧?書記部與其他黨派成員、地方精英、工界人士、同鄉會的關系如何?書記部在不同地域必將面臨不同的組織效果與工作方式,研究者需以地方史視野來考察書記部的成立與組織問題。這些問題的厘清都有助于深化理解書記部在各地植根土壤與活動開展方式,但需要個案研究的支持方能弄清楚。
除組織工會、領導罷工外,另一些與書記部相關的動作往往不被重視。勞工運動與媒體的相互作用在現代若干罷工運動中得到證實。書記部以如何的策略與形式借助地方傳媒力量擴大其宣傳效應,爭取大眾同情與支持?媒體受眾對相關工運議題秉持何種態度,對具體事件的觀點是否因報道發生改變?媒介對工運報道在多大程度上引導甚至塑造輿論?中共借鑒俄國革命的先例和同時期中國的諸多試驗,強調無產階級教育。“教導革命”是一種頗有說服力的群眾動員方式(115)[美]裴宜理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第42頁。。對不同產業、不同地域工人教育時采取如何相應的策略,成效如何?工人學校的教材編訂中如何寓革命目的于其中?教育機構的形式轉換的原因與成效如何?工人教育與中共基層組織之間的關聯如何?革命宣傳下帶來的工人左傾是否與工人教育有關?(116)丁樂靜:《以革命為目的——芻論安源工運中的工人教育》,《工會理論與研究》2016年第5期,第44頁。這些都值得研究者繼續深入的思考。
(三)研究路徑的改進
時至今日書記部的研究尚未完全達到產出嚴格學術規范、科學研究方法的狀態,尤其書記部領導下的工運研究尚呈現出僵化和教條化色彩,都與以往慣用的黨史、工運史中的研究局限分不開。早在60年代,謝諾即從社會、經濟與人口統計等方面對工人運動進行深入研究;裴宜理對上海罷工的研究則運用“新工人史”視野,探討工人的文化與生活狀況(117)蔡少卿、劉平:《中國工人運動與幫會的關系——兼評六卷本〈中國工人運動史〉》,《學術研究》2000年第3期,第76頁。。前輩學者的研究方法都為我們提供了借鑒。筆者試從以下三個層面對研究路徑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重視史料的考證與勘誤。盡管對史料謹慎的收集、整理與考辨是從事史學研究的基礎,似無過多強調的必要,但是目前研究成果仍存在前后說法矛盾、訛誤相沿的固有弊端,使得我們對基礎史實重視度不亞于研究方法與視角的創新。石川禎浩針對中共“一大”研究,提出目前研究的需要相比對“現有各種資料進行比對的‘考證學’”,更需要“充分斟酌、分析資料內容的‘史料學’”(118)[日]石川禎浩:《由考證學走向史料學——從中共“一大”幾份資料談起》,《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第93頁。。這樣的方法同樣適用于書記部研究,如1923年書記部總部再次遷滬后是否繼續存在的問題,陳衛民與王健英都參考上海地委會議記錄,但結論卻有本質區別。即使是各省的地方革命歷史文件也可能存在錯漏狀態(119)如某些日期是由檔案館工作人員經過自己的考證后在文件中標明,某些標題是編檔者后擬。應星:《“地方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的收集與利用:點滴體會》,《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1期,第24—25頁。,更為重要的是在書記部研究中很多史實考證仍與“一大”研究類似,需要依靠回憶錄來確認,無疑更需要反復比對,以避免因記憶錯誤或誤解,甚至主觀判斷造成的偏頗,以及“政治立場”上的顧忌等問題(120)[日]石川禎浩:《中共一大研究與回憶錄》,《中共創建史研究》第3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頁。。
第二,從微觀史的視角切入進行比較研究。在建黨早期,陳獨秀就將上海、北京、湖北、湖南黨組織工作成效比對分析(121)《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的報告》(1923年6月),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陳獨秀在廣州的創黨活動》,廣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頁。,可見,這種分析方法并不很新鮮。馬學軍對安源工運的研究向我們充分展現出微觀比較歷史分析方法之于書記部研究的可能性。書記部未來的研究亦可循著這樣的嘗試進行,如在分析中共群眾動員的理念與策略時,有論者指出中共選擇從易于發動學生運動入手,使學生充當動員工農群眾的媒介與橋梁(122)黃金鳳:《從學生運動到工農運動:中共早期動員策略再討論》,《黨史研究與教學》2018年第5期,第11—22頁。,故對比同期書記部與團組織的人員構成、活動方式應為題中應有之義;亦可在分析分部工作成敗因素時從比較視角出發,對比安源與京漢鐵路罷工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工會運作基礎及兩地功能的差異性(123)陳偉忠:《從文化戰線觀點論中共之生存與發展(1921—1945)》,中國文化大學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4—65頁。。
第三,堅持政治史與社會史的互動,并兼顧文化史的作用。英國關于工人運動史的討論,曾經一度掀起與社會史緊密相聯的研究熱潮(124)錢乘旦:《從韋伯到湯普森——英國工人運動史研究簡介》,《世界歷史》1984年第6期,第90頁。。裴宜理亦從社會史視角出發,靈活運用交叉學科的方法,為我們研究近代中國早期革命問題帶來了新的啟發和思考。對工人運動的研究往往可以超越單純罷工的討論,而看到更深層次的中國政治運作(125)參見畢仰高對陳明銶關于孫中山與華南勞工運動發展問題的討論。(《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1冊,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5年版,第281頁。),因此在承認書記部研究重要的政治意義之外,突破目前研究的當務之急是結合社會史視角的互動。這就要求我們不再緊盯單次罷工的沖突過程,而更需要思考如何看待不同地域下罷工發生的原因,如何將書記部置于更大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下來討論廣義的政治史問題。如各城市的具體情態決定了書記部切入當地社會與工人的方法,其工作效果也隨之受影響;采取“去精英化”路徑,推及考察非黨團員干事、非黨員特派員及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工人代表。
政治史中的文化面向同樣值得我們留意。所謂文化面向并非意指那些簡單對政治活動中的文藝工作、文教宣傳或其他內容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而是我們應對當時文化中更為豐富和流動的“政治性”加以認識,如作為符號的標語、口號如何傳播,如何發揮其動員效力,如何喚起集體情感;又如具有物質和圖像特征的匾額、橫幅、徽章、宣傳畫等如何在視覺上構筑一個屬于工人群體的空間與氛圍;再如流行于安源煤礦的《勞工記》《煤礦歌》或流行在北方工人群體中的白話詞等音樂體裁,傳統研究往往將其作為發動群眾,啟迪工人的宣傳策略加以論述,我們則可以繼續追問,其發生史與接受史各自如何,在工人運動中產生了哪些變化等一系列問題。古人論詩教,謂之可以興、觀、群、怨,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近代工人運動中,仍然有大批的文藝形式不同程度、不同側面地承擔了傳統詩教的責任,引發集體性的文化認同,并加入新的時代音符。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甚至看到了中國政治傳統在革命時代的某種微妙延續。
即便是單一政治史層面,書記部研究亦有繼續深入挖掘之處。重視從組織史新視角著手研究中共早期革命史,這一方法上的可行性已被陳耀煌證明(126)陳耀煌:《陜西地區的共產革命,1924—1933——一個組織史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9月),第41—86頁。。書記部研究的基礎是在考察總部與分部的組織模式與工作特點上,但僅僅史實上的梳理并不足夠,我們需更加關切影響書記部組織發展與維系的因素,既存的地方網絡體系與外來政治、軍事力量的影響,都應在被納入被考慮之列。
王汎森曾言:“新史料的發掘或對舊存史料不同層次的解讀,仍是成功寫出經典歷史著作的重要前提。”(127)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論衡》2004年第11期,第5頁。筆者認為,這一論斷也適用于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未來研究的瞻望。
(本文獲得同濟大學高峰學科建設經費的資助,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