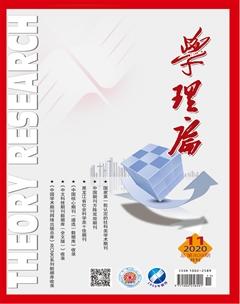從舜到月氏
牛政威
摘 要:先秦至秦漢時期民族關系問題,一直是先秦、秦漢史研究領域中的重點內容。過去在進行西域民族月氏族源問題研究時,依據的資料主要是史籍中有關月氏體貌特征與語言形態等方面的記載,故所得觀點往往不足以令學界信服。山西虞弘墓葬中刻有虞弘墓志銘石碑的出土,為月氏族源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根據虞弘墓志銘所記載內容以及對虞弘及其夫人DNA的解析,并與史籍記載內容相結合進行研究,可得出西域民族月氏之族源與舜帝有虞氏密不可分的結論。
關鍵詞:月氏;族源;虞弘;媯水
中圖分類號:K2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0)11-0078-03
“族源”這一概念,具有專業性和針對性。民族族源特指該民族的源流根底,即該民族之祖先。回溯源流,中國古代并沒有“民族”一詞,該詞出現于近代中國,最早由梁啟超所使用,但西漢著作《淮南子·真訓》所載“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1]卷三21中,“族”字已被用以表示有共同屬性的群類,后又多被限制為表示同一文化范圍內的社會群體,因此可認為今天常用的“民族”一詞所指內容與中國古代“族”所指同一文化范圍內形成的社會群體這一含義相同,月氏群體作為有其獨特文化圈的古代社會成員,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痕跡,故可言月氏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支民族。
一、史籍及學界所見月氏族源
自先秦起,中原王朝就已經形成中原地區建立的文明與非中原地區文明有極大差異的思維方式,故而中原統治者通常將王朝范圍以外,西部、北部等地區所形成的非華夏族群統稱為戎狄,并隨之形成了中原文明為正統的觀念,因此,中原王朝所編寫的史籍中,對當時與其共存民族的記錄都相對較少。
關于月氏這一秦漢時期已經活躍于今甘肅省河西走廊地區,且曾在西域諸國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民族,中國古代史基本史籍《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均有記載;但這些史籍所載內容都集中在月氏族群的活動范圍、軍事力量、體貌特征、生活習慣等方面,均未涉及其族源問題。雖然月氏族源歷來被學界重視,但因資料匱乏,古往今來學界在利用史籍研究月氏族源問題時,能依靠的僅有月氏民族群體的分布、習俗等特征和月氏的起源地、發展演進過程等內容,關于月氏族源的研究,自明清至今已歷二百余年,中外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雖比較豐富,①但因史籍記載內容較少等客觀原因,大多研究成果僅是靠字音、字義等進行簡單梳理和羅列,故至今,中外史學家提出的關于月氏族源觀點大都不足以令學界信服。
二、考古及地理資料所見月氏族源
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學領域進入科學考古學階段,隨著考古隊伍不斷壯大和發掘水平的提高,先秦文物不斷出土,彌補了昔日研究月氏族源問題時僅能依靠史籍猜測的缺憾,依據已發掘與月氏相關的遺跡、器物等考古資料,并與史籍所載其分布、活動地理區域等信息相結合分析,在月氏族源問題研究中顯得尤為重要。
(一)虞弘與舜
1999年7月隋朝虞弘墓葬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王郭村,虞弘(533年—592年),字莫潘,他生活于南北朝多個政權并存,再到隋大一統的這段時期,曾擔任多個政權的大臣,也是著名外交家,出使過波斯、吐谷渾等國。此墓葬中發掘的文物大多藏于今山西博物院,其中包括刻有虞弘墓志銘的石碑,虞弘墓志銘言:“公諱弘,字莫潘,魚國尉紇城人也。高陽馭運,遷陸海□□□;□□膺策,徙赤縣于蒲坂。奕葉繁昌,派枝西域;倜儻人物,漂注□。曾祖奴棲,魚國領民酋長……水行馭歷,重瞳號奇。隆基布政,派胤云馳。潤光安息,輝臨月支。”
該墓志銘記載內容中,前部分提及的“高陽”即“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2]卷一11,“徙赤縣于蒲坂”中的“蒲坂”即“蒲坂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二里,即堯舜所都也”[3]卷二51,“重瞳”司馬遷言“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2]卷七338,這些記載都與《國語·魯語上》中關于有虞氏世系的記載:“故有虞氏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4]卷四110一一對應。按照此墓志銘的記載,虞弘當是舜帝后人,有虞氏一族,虞弘先輩曾如墓志銘記“遷陸海……派枝西域;倜儻人物,漂注□。曾祖奴棲,魚國領民酋長”,有關虞弘曾祖曾擔任酋長的魚國文明,20世紀70年代初,我國考古工作人員就已在今陜西省寶雞市渭濱區茹家莊附近發現過魚國遺存墓葬,此后又于1976年、1980年兩次在當地發掘出含有青銅器的較大規模古墓群,這些青銅器銘文中明確載有墓主的名稱,如“魚季”“魚伯”等,經過研究,專家確定這批古墓群為魚國早期墓地,墓主生活時代大約是西周初期,班固在《兩都賦》中把今關中一代稱為“陸海”正與之呼應。虞弘墓志銘的記錄與寶雞魚國墓葬的發掘,有力證明了舜帝有虞氏的后人在發展過程中,曾有部分族人在西周初期于今寶雞市西北建立起魚國政權,著名歷史學家榮新江先生在談及虞弘墓葬發掘相關問題時也曾在其論文中指出:“從虞弘祖父仕任于柔然,推知為西北地區的小國。虞弘應當屬于西北民族”[5]171,可見虞弘是舜帝有虞氏后人這一結論應當是可信的。
(二)虞弘與月氏
山西省虞弘墓葬經科學發掘后,吉林大學謝承志等學者,曾于2007年對山西虞弘墓葬主人虞弘與其夫人的DNA進行過研究與分析,其結果顯示“虞弘屬于主要分布在西部歐亞大陸的單倍型類群U5,而虞弘夫人的單倍型類群G主要分布在東部歐亞人群中”[6],這一結論說明虞弘及其夫人攜帶的是今甘肅省河西走廊以西人種的基因,虞弘墓志銘的后半部分明確記載其先祖“潤光安息,輝臨月支”,其中的“月支”即“月氏”,故此處可將虞弘先祖與月氏相聯系加以思考。
民族之起源地雖不能直接得出民族的族源,但二者息息相關,前文筆者已指出現存史籍記載內容均未涉及月氏族源,但關于月氏起源地的記載頗豐,《史記》關于月氏起源地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張守節注:“敦煌郡今沙洲,祁連山在甘州西南)”[2]卷一百二十三3162,《漢書》載:“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余萬,故強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顏師古注: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7]卷九十六上3890,結合眾多史籍中關于月氏起源地的記載,目前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主流觀點有二:一為清朝著名地理學家何秋濤提出,他認為月氏就是《逸周書》中的“禺氏”,此后王國維先生又對這一觀點加以發展,明確指出月氏的起源與形成時期:“周末月氏故居,蓋在中國之北。《逸周·王會解》‘伊尹獻令列禺氏于正北,《穆天子傳》‘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禺知亦即‘禺氏,其地在雁門之西北、黃河之東與‘獻令合。此二書疑皆戰國時作,則戰國時之月氏當在中國正北”[8]第十四卷283,但王國維先生的觀點主要依據僅是“禺氏”與“月氏”的讀音相似,除此之外并無其他史籍與實物以佐證,且試想若當時有一支已經形成且比較強大的民族進行過自古雁門至西域的大規模遷徙,在這個過程中沿途應當或多或少能留下印記,然而至今并無相關史籍明確記載,也無文物出土,且假設真如上述觀點所言,月氏大規模遷移可能的原因應當是躲避戰亂或原本居住地生態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那么經過了長途遷徙的月氏,是否能在短期內迅速崛起,達到可以同東胡、匈奴相提并論的實力呢?答案是否定的,春秋戰國雖戰火紛飛、諸侯林立,然而到戰國中期后,中原地區格局已定,此時有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勢必引起各諸侯國巨大反響,沒有理由各諸侯國都選擇忽視,不在史籍中記載;另一觀點則由岑仲勉先生提出:“小月氏可能是一個羌族,吾人固未絕對證明大小月氏之同屬一個族類,但亦無道理說大小月氏之非同一族類,據是以推,并注意其官有侯,則認為大月氏介于氐羌、突厥之間”[9]218,岑仲勉先生所言月氏最初就形成于今中國西北地區一帶,演進過程中可能與其他民族分化與交融,且在西北范圍內有所遷徙,但規模不會很大的觀點,正好與虞弘墓志銘所言其先祖初任寶雞魚國首領,后又“潤光安息,輝臨月支”相契合,到了張騫出使西域時,月氏已因“匈奴所敗,乃遠去”[2]卷一百二十三3162移居至“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西可二三千里”[2]卷一百二十三3161,正因月氏的不斷遷徙,這一民族勢必需要與周邊各民族進行密切交流,甚至進行通婚等行為,伴隨著這些融合,使得秦漢時期的月氏,其群體構成與最初形成時相比,已有了很多變化,但“月氏”作為本民族名稱一直使用,因此根據虞弘墓志銘的記錄、史籍記載月氏的起源地和其活動范圍以及謝承志等學者對虞弘DNA的研究,可得出虞弘及其先祖與月氏有一定聯系的結論。
(三)舜與月氏
舜帝為中華民族文明始祖之一,關于舜帝,《史記·陳杞世家》有載:“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其后因為氏姓,姓媯氏”[2]卷三十五1575,舜始居于“媯”(河流名稱,在今山西省運城市永濟市南,源出歷山)附近,故“媯”便被舜及舜之后人作為姓氏。“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2]卷一43,正因舜帝在中華文明演進中具有特殊定位,故此后很長時間內史籍中記載“媯”的使用途徑只有兩種,一是單獨作為舜帝及其后人之姓氏使用;再者是在“媯”一詞中作為河流名使用。
秦因暴政歷二世而亡,后由劉邦一統天下,建立起西漢王朝。統一初期的西漢就已多次遭受匈奴的威脅與侵擾,但因王朝貧弱,除高祖劉邦初期與匈奴發生平城之戰并以白登之圍收場外,西漢初期并未再與匈奴發生過較大沖突。此后經“文景之治”休養生息,西漢積累起一定的財富與軍事實力,終于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決定聯合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2]卷一百二十三3157的月氏共擊匈奴,故武帝命:“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隴西”[2]卷一百二十三3157,這便開啟了張騫出使西域的美談。張騫出使西域十余載,過大宛、康居、大夏等西域政權后,終于得知“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2]卷一百二十三3162的消息,此處的“媯水”是正史中“媯”字除了之前當作舜帝姓氏和“媯”這條河流名稱所使用以外再次出現,張騫在月氏居住地所見的媯水是指由帕米爾高原冰川融化形成發源于中亞,最后于烏茲別克斯坦注入咸海的一條內陸河流。初見該河時,張騫將其稱為媯水,之后媯水的名稱發生過多次變化,據相關史籍記載,隋朝時期人們稱媯水為烏滸水;玄奘西行游歷西域后,經其口述,辯機整理編寫的地理史籍《大唐西域記》中稱媯水之縛芻水;元朝時民間又稱其為阿母河;明朝改為阿木河;今天將其翻譯為阿姆河。上文中筆者已指出“媯”僅作舜帝有虞氏及其后人之姓氏或與舜帝初居地有關的河流名稱使用,既然如此,為何到了西漢張騫見到此時連西漢王朝統治范圍之邊疆都不算的月氏群體時,會將其居住地的一條河流用舜帝姓氏來命名作“媯水”?若張騫是出于前文中筆者提及的自古中原王朝認為其王朝以外的西部、北部民族均為戎狄的觀念,而借用商、周時期位于中國西北的部落鬼方之名,以表達月氏為戎狄之意,出于音近,此處應當使用“鬼”“歸”“詭”等字,這也更符合當時中原王朝的民族觀,但西漢時期的張騫并沒有這樣做,正因為當時的他對月氏族源清楚明了,才會在初見月氏時,將月氏居住地的河流稱為媯水,這也成為月氏是舜帝有虞氏后人的確鑿證據。
三、結語
月氏等中國古代民族,其誕生與發展、演變非一朝一夕可成,而是經過漫長歲月,甚至常歷多個朝代。然而,正是這種緩慢的演變恰恰更容易被史家忽略,其原因是:我國古代史家修史時往往秉承“常事不書”的主導思想,這在戰國時期公羊高所著釋《春秋》之作《公羊傳》中已有記載。清華大學侯旭東教授研究日常統治史曾言“這樣(常事不書)一套機制乃是古已有之的老傳統”[10] 78,如此一來,中國古代少數民族的循序漸進與點滴累計,在時人看來正是日復一日、循環往復的日常瑣事,而非短期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故彼時史家修史時,通常忽略民族群體發展、演變等“日常事件”,僅書寫民族群體對外戰爭、交往等要事。當代歷史研究中,大事、要事固然重要,但要透過重大事件看古人社會的本質卻需要借助大量的“日常事件”,古時“常事不書”的修史思想,給今天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族源等日積月累而成的問題研究帶來極大困難,好在當今考古發掘技術提升,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研究結合的方法已越來越受學界重視。
綜上所述,結合虞弘墓志銘內容、虞弘及其夫人DNA解析結論、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關于月氏族源的問題,可以得出結論,即:舜帝初居于今山西媯,故而得姓為媯,舜帝有虞氏后人在西周初期,有部分族人西遷至今陜西省寶雞市渭濱區西北部建立魚國,虞弘便是昔日魚國的后人,歷史上月氏這一民族,就是舜帝有虞氏的后人在西周初期建立起的,魚國衰亡后,小部分族人又再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與西北地區原有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由盧連成、胡智生兩位學者及寶雞市博物館所編著的《寶雞(弓魚)國墓地》[11]一書中,就將魚國族人稱為氐羌,這也與上文提及的岑仲勉認為月氏是與氐羌、突厥等交融而形成的觀點不謀而合,故可知由舜帝有虞氏后人所形成的月氏群體至少在戰國中期以前,就已經完成了在西域地區的形成與強大的過程,到了西漢時期,前往西域的張騫已經對月氏的族源有清楚的認知,所以初見月氏時,張騫便將月氏所居地的河流翻譯為“媯水”,以表示西漢王朝對月氏民族的重視以及對月氏先祖舜帝的尊重。
參考文獻:
[1]劉安.淮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李泰,等.括地志輯校[M].北京:中華書局,1980.
[4]左丘明.國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6]謝承志.新疆塔里木盆地周邊地區古代人群及山西虞弘墓主人DNA分析[D].長春:吉林大學,2007.
[7]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8]謝維揚,房鑫亮.王國維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9]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0]侯旭東. 什么是日常統治史[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
[11]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市博物館. 寶雞弓魚國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