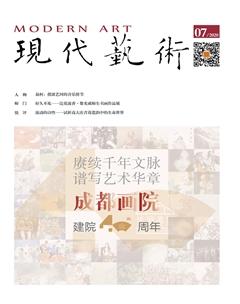康杰:山水的清音
羅繢沅



康杰的畫似乎追求著靜寂美學的尚意氣韻,在清寂、高逸、素潔中散發出一種古典主義的氣息。
靜與凈是他的繪畫追求。從作品中可以見出他是從宋元山水一路走過來的。傳統中國山水畫是中國士人構建出的一個自我世界與獨立的精神系統。它的核心是“歸宿之心”,是為人為己建造的精神的棲居之所,它不止于可居可游,更是放置靈魂的所在。于是,北宋李成追尋“山水比德”,營造出“氣象蕭疏,煙林清曠”的愿境;元人倪瓚情寄清寂、高逸、素凈,播下的是一段段澄懷觀道的體驗;康杰的畫始終追求著一種與真山真水的疏離感,那少有的靜氣與清渺,許是他安放心靈超然于世的地方。惲南田說:“畫至于靜,其登峰矣”,看重的也是這種“歸宿之心”。
康杰對清寂的摯愛,也許是他與生俱來的一種基因。能與靜作伴,內心定然含存著心靈的空寂和品性的堅持。他出生于川北梨鄉的大山中,他的童年充滿了泥土的芬芳和草木的清香,由山居的寧靜滋養出的靈性伴生了清寂玄遠肅穆的繪畫主張,把依依的眷戀變成與紙墨筆硯的緣份。
他的畫有一種明度較高的悠遠與對比偏低的節制。他用平穩的節律去架構畫面,營造出一個個肅穆的情緒空間。那渴筆淡墨卻不縱橫的虛靈猶如獨對天地氣機后的凝結,好像隱去了俗世中的小我而歸正于大化,又似乎把山川調節為他的呼吸,讓人在清冽靜謐的況味里同他一起發出輕輕的吟詠。人說“至味必淡”,康杰的畫也予人這種感覺。也許,那攪和著云淡風輕平和溫婉的況境比起那些棱角分明劍拔弩張的硬朗恰如一杯淡淡的香茗;也許,它更像一首舒緩的樂曲,不狂放不粗野卻從從容容,狀如洞庭清水不疾不徐不舍不漫潤澤一方;也許,它亦如易安居士“聲聲慢”的纏綿,淺斟低唱,在意的只是纖毫細膩思緒流動中的杯水波瀾。
康杰作畫好用點染。畫史中的董源、巨然、黃公望、沈周一脈都善用點作畫。被詩圣杜甫稱贊過的王宰的畫:“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也多因用點積成。有人認為“明以后畫之薄弱,失其法也。”然,康杰宗法其間,研習頗深,不時回歸到具有原點意義的“點”的點虱中,醉心于石與巒的解構與重組,以一種用筆的純粹性描繪出山水清寂空靈飄逸的意態。其實,這種貌似細筆的點簇大約更與靜與凈的表達合拍,更能表達出他尊祟的清雋靜寂。
無庸置喙,所有的皴法都源自于自然,范中正師法秦隴山麓,才有他的“芝麻皴”與“雨點皴”;賓虹老有了蜀山之行,“沿皴作點三千點,點到山頭氣韻來”,才有了他晚年“打點作皴”的筆墨特色。康杰的點虱既不是范寬的也不是虹翁的,他銘心于董源、巨然、黃公望、沈周一脈,這些蟄伏于筆下的窖藏,當然在寫山摹水間與親近自然中體悟到的生命精微及情懷寄托,變成清寂的意象。
誠然,意象都不是拿來去簡單附會的。古人的胸中溝壑,山林中的那份自然,都是士人精神性的純粹構造,自然才成為他們的參照與心象。你站在人心的高處,才能獲享山水的精神,在他們的畫作中才會有那種內生的境界與心臆。那些斷岸煙微、晴嵐疊嶂、小橋流水、細雨騎驢的清寂才與他們的內心合拍。“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佛教密宗中那些誦辭,許是佛在靜定冥想中發出的真知的聲音。那些真知之想通過個體堅韌的禪定與持誦,通過戒、定、慧、聞、思、修才能化人修為者的血脈。對繪畫者而言,靜,是心靈的一種渴望,它澄明無遮,了無掛礙,心靈才能融入致廣大盡精微的天宇。心中有什么,筆下才會有什么。在康杰筆下,靜,許是玄想妙思涌流到指腕間的神示,焉能不成為他畫幅的起首章?
他堅定地走在清寂的畫路上,在探索古典語言在當下語境的呈現中,也多了不少現代氣息,卻仍把清寂的本源頑強地存留于畫幅里。中華文明素來祟尚平淡天成氣韻天生的審美形態,人們越是缺少的東西,就越有可能成為人們的精神文化奢求。長松點雪,古樹號風,新涼滌暑,淡月橫秋……康杰把纖塵不染的清寂、靜謐、空靈、幽潔用畫筆輕梳于畫卷中,棲逸守恬,返璞歸真,不時生發出那種我們期待的圓融。
最愛山居養性靈,便引輕舟入深峽。
從來,志于藝者,畫紙無端,畫筆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