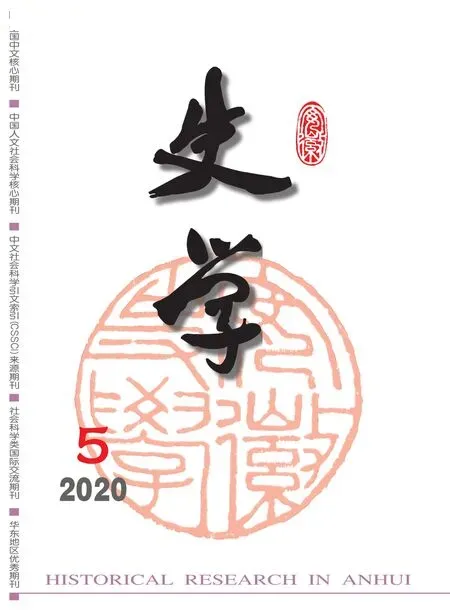20世紀50年代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認識演進探析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中共黨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1)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通過手工業合作化的形式,逐步引導手工業勞動者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實際上就是手工業合作化的對象,二者是一致的。但在一般情況下,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前,一般稱為手工業合作化;之后,稱為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本文為了一致,除了引文外,把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前后手工業合作化的對象,一律稱為“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一直為學界所關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首先要弄清楚對誰進行改造,也就是改造對象問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能不能納入改造范圍,取決于中共能不能認識到客觀存在的改造對象。當前學界對這一問題已有一定研究。(2)有論著認為: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對象就是個體手工業者,“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三大改造任務之一”。(《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2卷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頁。)有論著指出:“我國解放初期的手工業,就其與農業分離的程度來說,大體有四種類型:一是從屬于農業的自然形態的家庭手工業,如自制農具、衣服等;二是農家兼營的商品性手工業;三是獨立經營的個體手工業;四是雇工經營的工場手工業。按照黨和政府的有關規定,作為三大改造之一的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主要是第三類,即個體手工業,但是也包括第二類中以經營商品性手工業為主的兼業戶和第四類中雇工不足四人(學徒不算雇工)、本人參加勞動而且是手工勞動出身的工場主。至于第一類和第二類中以農為主的兼業戶,都歸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范圍。第四類中雇工超過四人的工場主,一般歸入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范圍。”(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310頁。)有論著指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主要組織對象為手工業獨立勞動者(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和手工業工人;手工業資本家不應該吸收入社,對他們要通過加工定貨、統購包銷、公司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進行改造。”(《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集體工業》上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頁。)但這些研究有的沒有涵蓋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部對象,有的沒有動態考察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認識的過程。前人的研究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基礎。對于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中共是隨著改造實踐的推進,對改造對象的認識不斷深入,整個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改造對象并不是一個完整一致的群體。在改造對象上出現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改造的實施者們。本文擬就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認識演進作初步的探討。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的認定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新中國的經濟形態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并將合作社確定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對于手工業,明確指出要引導其走向合作化。“我國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走合作化的道路,這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就確定下來的。”(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313頁。基于當時的政策,手工業合作組織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開始發展,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問題隨之出現。
(一)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的初步認定
進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首先需要確認改造對象,也就是把手工業行業中哪些人組織到手工業合作社當中來。
1.小手工業者和家庭手工業者
1950年7月25日,劉少奇在報告中指出:“關于手工業生產社問題,應以組織獨立手工業者和家庭手工業者為主。”(4)《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頁。什么是獨立手工業者?1950年8月,政務院通過的《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指出:“小手工業者。占有少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生產資料,自己從事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以其成品出賣,作為全部或主要生活來源的人,稱為小手工業者,或獨立生產者。小手工業者一般不雇用(5)時代因素,原文用的是“雇用”而不是現在常用的“雇傭”,以下引用部分出現“雇用”不再做解釋。工人,有時雇用輔助性質的助手和學徒,但仍以本人的手工業勞動為其主要生活來源。這種小手工業者的社會地位,和中農類似。”(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352頁。《決定》還對手工業資本家和手工業工人進行了明確界定。(7)《決定》指出:“手工業資本家。占有多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資本,雇用工人和學徒以進行手工業生產,取得利潤,作為收入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人,稱為手工業資本家。小手工業者只雇用輔助自己勞動的助手和學徒,而手工業資本家雇用工人和學徒則不是為了輔助他自己勞動,而是為了獲取利潤。這是小手工業者與手工業資本家的主要區分。”“手工工人。完全沒有生產資料,或者只有很少的手工工具,向消費者,或向手工業資本家,或向小手工業者出賣勞動力,為雇主從事手工業生產,領取工資,作為全部或主要生活來源的人,稱為手工工人。手工工人的社會地位,與工人、雇農相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351—352頁。這個標準是比照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來定的。對小手工業者、手工業資本家、手工業工人的明確界定,就使手工業改造對象的劃分有了具體的政策依據。
當時認為改造對象是以小手工業者和家庭手工業者為主。《決定》沒有對家庭手工業者給出明確的概念,但可以推斷是指在家庭中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但實際上在家庭中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并不能都稱為手工業者。比如農民在農閑時從事手工業生產,給家人做衣服穿,但很難說農民就是手工業者。因為家庭手工業者的概念不準確,后來隨著中共對改造對象認識的深化,不再使用這個概念。為什么當時中共沒有把手工業工人作為主要改造對象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我們目前組織手工業生產的方針,不是以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為目的,而是首先自恢復生產著眼。”(8)《天津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手工業工人沒有生產資料,或者只有很少的工具,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手工業合作社多采取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的形式。這種類型的合作社主要通過發原料收成品的辦法組織手工業者。“經驗證明組織分散生產的手工業者最簡而易行的一種方式就是發原料收成品。”(9)《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頁。與手工業工人相比,小手工業者和家庭手工業者有一定的設備和技術,更適合供銷生產合作社的形式,有利于當時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2.手工業工人
手工業工人當然也是改造的對象,但建國初期中共并沒有把手工業工人與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并列為手工業改造的主要對象,對于這樣做的原因以上已有論述。1952年國民經濟基本恢復,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幫助手工業工人組織生產合作社。中央指示,這一時期手工業合作事業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在一些同國民經濟關系最密切并有發展前途的行業中,選擇覺悟較高又具有代表性的手工業勞動者,重點試辦合作社。”(1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314頁。通過這樣的典型試辦,起到引導廣大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的目的。這一時期受到全國合作總社表彰的4個著名合作社,其中有3個是由手工業工人發起成立的,當然其組建都離不開國家的幫扶。1952年8月第二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指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對象是城市和農村中的手工業工人、半手工業工人、小手工業者和家庭副業勞動者。”(11)《組織與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過程中的若干問題》(1952年10月),《中央合作通訊》1952年10月號。這就說明隨著改造的不斷深入,中共已經認識到手工業工人同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一樣,都是手工業改造的對象。
但要認識到,組織手工業工人成立生產合作社有其階段性。到1953年底,中共認識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一種是由手工業工人自愿聯合起來,湊集股金,租借生產工具,集體生產,在國營經濟、在供銷合作社或消費合作社幫助下,逐步壯大,人數多了,規模大了,積累了公積金,正式成立起來的;這是在大城市解放初期有失業工人存在的條件下產生的,今后可能性已不大。”(12)《關于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若干問題》(1953年12月),《中央合作通訊》1954年8月號。但這并不影響手工業工人作為手工業改造的對象。
3.部分手工業資本家
對于手工業資本家能否加入手工業合作社,1950年7月劉少奇明確指出:“手工業資本家是不能加入手工業生產社的。什么是手工業資本家,就是雇用很多工人生產,自己從事剝削的。”(13)《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85頁。但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小的手工業資本家的日子并不好過,他們愿意放棄資產,重新回到手工業者隊伍中來。鑒于當時的情況,中共對這一部分手工業資本家開了特例,允許他們加入手工業合作社。
為什么要給這些人開特例?1951年6月全國合作總社理事會副主任孟用潛解釋說:“今天有一部分小作坊主,他們本來是工人,現在卻是雇用著兩三個工人的手工業資本家。他們一方面剝削著雇傭勞動,另一方面又受著大資本的剝削。他們的經濟地位本來很不穩固,現在再加上勞資關系等等問題的糾纏,處境愈加困難。其中有一小部分,鑒于大勢所趨,愿意摘掉資本家的帽子,放棄作坊主的地位,重新歸入工人隊伍,并愿意完全遵照生產合作社章程,參加合作社為社員。這也是目前在新舊交替中的一個社會問題。這類有熟練技術的小作坊主,經過社員大會通過,參加合作社為社員是可以允許的。”(14)《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與手工業生產》(1951年6月),《中央合作通訊》1951年6月號。可以看出為少數這樣的手工業資本家開特例,允許其加入手工業合作社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樣的人如果拒絕其加入手工業合作組織,不利于手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二)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出現的認識混淆及解決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有了初步認識。但在實際合作化過程中,卻出現了把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弄混淆的現象。
1.對小手工業者和手工業資本家的混淆
按照《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小手工業者只雇用輔助自己勞動的助手和學徒,而手工業資本家雇用工人和學徒則不是為了輔助他自己勞動,而是為了獲取利潤。這是小手工業者與手工業資本家的主要區分。”(1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352頁。由于生產需要,有些小手工業者常年雇傭工人或學徒,從表面看,這些小手工業者和手工業資本家的區分并不明顯。1951年3月,松江省勞動局關于呼蘭手工業中一些問題的調查顯示,在雙城縣“至今仍繼續著四九年建政時期的原則:有工具無原料者為手工業工人,有工具與原料未雇人者為手工業者,有工具與原料并雇人者為手工業主,一般不分雇工、收徒弟均視為勞資關系。”(16)《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工商體制卷》(1949—195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51—752、759頁。這樣就容易出現把小手工業者當作手工業資本家的問題。特別是1952年2月到10月開展“五反”運動期間,這一現象更加嚴重。
“五反”運動是針對資本家這個階級的。手工業由于自身的產業特點,手工業資本家在手工業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小手工業者和手工業工人在手工業當中占絕大多數。但現實當中不容易把小手工業者和手工業資本家區分的那么清楚,在運動當中就出現了把小手工業者當作手工業資本家來斗爭的問題。在“湘、鄂、贛、粵、桂五省的幾個主要城市中,均存在著把手工業生產者當作資本家看待的情況。”(1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工商體制卷》(1949—195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51—752、759頁。可見當時在全國范圍內,在“五反”運動中,都有把小手工業者誤作手工業資本家看待的現象。對此,1952年10月孟用潛指出:“今天關于生產社組織對象,在思想上比較混亂的是小手工業與手工業資本家的區別。”(18)《組織與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過程中的若干問題》(1952年10月),《中央合作通訊》1952年10月號。他重申界定小手工業者、手工業資本家、手工業工人的標準。這個問題后來受到湖北省的高度重視,在1953年2月召開了全省手工業代表會議,解決了這個問題。(19)1953年3月2日,《湖北省關于貫徹手工業代表會議的指示》中指出:“一般說大部分手工業者都屬于小生產者,純粹依靠剝削為主、不參加勞動的手工業資本家為數不多,因此手工業階級界限的劃分,宜寬不宜嚴。有的業主為主要技術勞動,雇有一二個輔助工及學徒,雖有部分剝削,但其所得主要靠自己勞動,應算作小生產者。有的雖雇有數個工人,業主參加主要勞動,也不要算為資本家。根據有些城鎮典型調查,可劃為手工業資本家的不過占戶數的百分之五上下,亦資本不大雇工不多,多為手工業者發展起來的。不屬手工業資本家而雇有工人者,只能算作勞動者之間的雇傭關系。”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08頁。中央對湖北省的經驗高度重視,進行了肯定和推廣,“湖北省委注意到在目前維持手工業經濟的必要,由湖北省政府召開了一次手工業者代表會議,很好。這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會議,各省可在適當時間仿照湖北的辦法召開一次。現將湖北省報告轉去,供你們參考。”(2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104頁。之后各地高度重視這一問題,把小手工業者當作手工業資本家的現象得到了緩解。
2.對小手工業資本家和大手工業資本家的混淆
手工業合作社原則上是不允許手工業資本家加入的,但建國初期形勢復雜,中共鑒于當時的形勢,允許一部分小手工業資本家加入合作社。趁著這種便利政策,一些大手工業資本家,甚至一些地主、反動軍官等都混進了合作社,甚至導致一些合作社性質發生變化,不再是勞動者的合作組織。
鑒于合作社中混進了大手工業資本家以及其他不應該加入合作社的人,1951年6月,全國合作社第一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對手工業合作社決定先整理后發展。1952年第二次會議也明確要求:“手工業資本家不得參加生產合作社為社員。生產合作社的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有不少地主、商人、資本家、舊軍官以至反革命分子目前尚潛伏在各地生產社,甚至盤據在領導地位。這便成為阻礙合作社發展的內部主要障礙。各地在三反五反過程中即開始清除這些分子,這一清洗工作必須繼續進行,一定要保證生產合作社是勞動者自己的生產組織。”(21)《組織與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過程中的若干問題》(1952年10月),《中央合作通訊》1952年10月號。隨著合作社的整頓,一些大手工業資本家混入合作社的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總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百廢待興,中共以獨立的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為手工業改造對象,以供銷生產合作社為主要組織形式,同時兼顧了手工業工人和小手工業資本家,特別是對小手工業資本家網開一面,允許其加入手工業合作社。但期間對小手工業者與手工業資本家的區分并不是特別清楚,導致了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的混淆。混淆手工業改造對象導致出現了很多新的問題,不過這些問題被及時發現并得到了解決。
二、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認識的深化
1953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不斷深入,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的認識有了深化。
(一)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中組織重點的判斷
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對富農限制到逐步消滅”的階級路線。這個階級路線抓住了占農村人口70%以上的貧雇農,對順利推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階級路線的影響,中南、華東地區許多省的代表在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上,提出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中應該明確“依靠手工業工人,團結獨立勞動者,發展手工生產合作互助”的階級路線。(22)《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246頁。1954年11月,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央手工業管理局,負責手工業的生產和改造,白如冰任局長,鄧潔任副局長。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是中央手工業管理局成立后召開的。如果制定這樣的階級路線,手工業工人就成為了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重點對象,就改變了之前主要依靠小手工業者的政策。對這個提法是肯定還是否定,直接反映了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的認識程度,關系到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能否順利推進的問題。這個提法最終被大會否決了,原因如下:
第一,手工業工人在整個手工業從業者中不占多數。中央手工業管理局關于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給中央的報告指出:“現在對手工業從業人員數量的估計是:獨立手工業者約九百萬人左右(城市家庭手工在外),農業兼營商品性手工業生產的從業人員約一千萬人左右,受雇十人以下的工廠手工業資本家的手工業工人約一百余萬人。農業兼營商品性手工業生產的,除特殊行業外,一般以由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附屬小組為好。雇傭十人以下的工廠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目前還在試點。因此,目前手工業合作化的組織重點應該是獨立手工業者。”(23)《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246、211頁。從當時的統計數據看,納入改造范圍的手工業工人人數只占獨立的小手工業者人數的九分之一。在改造當中只有抓住占絕大多數的獨立手工業者才能順利推進改造,而不是少數的手工業工人。
第二,這個提法不利于手工業勞動者之間的團結協作。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副局長鄧潔在會議總結報告中指出,手工業獨立勞動者、手工業工人都是手工業勞動者。手工業獨立勞動者和學徒之間是師徒關系,和雇工之間是主要勞動和助手的關系,因此“提出這樣的‘階級路線’,可能在手工業勞動人民內部引起糾紛,影響雇工、學徒不鉆研技術,而斗爭師傅;掌握主要技術的獨立勞動者生產情緒不高,傳授技術的興趣不大,這對搞好生產是不利的。”(24)《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246、211頁。獨立手工業勞動者雖然雇有工人、學徒,但他們和工人、學徒之間不是剝削關系,這與手工業資本家和手工業工人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提“階級路線”只會造成手工業勞動者內部的不團結,不利于改造的順利推進。
(二)對地主、富農等事實存在的改造對象的處理
手工業改造中,還有一些逃亡的地主、富農、反動會道門分子等與手工業生產毫不搭界的人,也進入了手工業合作組織。這些人存在于手工業中,在事實上已經成為手工業改造的對象。如何處理這些人是中共在手工業改造不斷深入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1955年3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北京市1954年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給中央做了一個綜合報告。報告指出:“在1954年3月以前,組織進手工業合作組織來的,不但有一批資本家,而且還有一些地主、商人、偽軍官、反動黨團分子、反動會道門分子及流氓分子,其中有許多人還成為基層社的領導干部。”(25)《北京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頁。列舉的典型例子就是北京市第34縫紉社,在該社的7個籌備委員中,有6人為資本家、一貫道壇主或血債嫌疑分子。地主、商人、偽軍官、反動黨團分子、反動會道門分子及流氓分子等這些人本來與手工業毫不搭界,現在也混進了手工業合作組織當中,他們在事實上成為了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并且這種情況在當時不止北京市存在,在其他的省份也存在這種情況。
對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195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對北京市委的匯報進行了批示。綜合各地的情況,中央認為,“對流入手工業和混進手工業合作組織的逃亡地主、富農、商人、偽軍官、反動黨團分子、反動會道門分子等,凡非被剝奪政治權利、不是潛藏的反革命特務,不能回鄉生產的逃亡地主,而有生產技藝者均仍應在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進行改造。并須掌握以下原則:(1)不要過早地吸收他們加入合作組織,注意在手工業中進行改造;(2)根據他們改造的程度與合作社的鞏固情況和需要,可分別吸收他們入社;(3)入社后,絕不能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并加強社員群眾對他們的監督;(4)現已混進合作組織并篡奪領導權者,應堅決撤除其領導職務。如系一般社員,應根據情況,分別適當處理,不宜一律開除出社。”(26)《北京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料》,第190頁。對于這些混入手工業組織中和手工業其實不搭界,在事實上已經成為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的人,中央認為“凡非被剝奪政治權利、不是潛藏的反革命特務,不能回鄉生產的逃亡地主”,其他人只要有生產技藝的,仍應該留在手工業組織中對他們進行改造,并且對這些人的改造確定了四項原則。
(三)對雇傭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手工業資本家的處理
手工業資本家不是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這是一個大的原則。但是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已經出現了雇傭兩三個人的手工業資本家被作為改造對象納入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因為這些人實際上和小手工業者相似。對于雇傭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手工業資本家該怎么處理?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對這部分人的情況摸清楚。“據典型調查的推算,全國十人以下的手工業戶中,約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是勞資關系(有的大城市在百分之十以上)。”(27)《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212、212、212、246—247頁。也就是說這些人并不全是手工業資本家,其中有些處境和小手工業者類似。對于這類和小手工業者情況類似的人,當然可以采取對待雇傭兩三個工人的手工業資本家的辦法,吸納他們進入手工業合作組織。
但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是手工業資本家,不過規模比較小罷了。在當時的大形勢下,這些人“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他們‘上不接天,下不踏地’,既輪不上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合作社也不要他們,處境很困難。”(28)《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212、212、212、246—247頁。這些手工業資本家,因為其資本小而不能通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又因為其是手工業資本家,合作社對其也不吸納,處于一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尷尬境地。對于這種新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試點來積累經驗。“目前改造手工業小資本家尚是一個新的問題,個別地區已開始有條件地吸收他們入社(如南京、北京、濰坊等地)。但這一工作,還沒有成熟的經驗。今后應有步驟、有條件地加以試辦,這對改造手工業小資本家可能是一種有效辦法。”(29)《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212、212、212、246—247頁。
中央手工業管理局關于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給中央的報告,對于這種新出現的情況提出了以下建議:“關于雇傭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工廠手工業小資本家的改造問題。根據中央批轉全國總工會黨組《關于手工業工人中工會工作的請示報告》中指示,由手工業聯社負責。這一改造工作,尚無經驗,今年各省市應選點試辦,取得經驗。在吸收工廠手工業小資本家加入手工業合作社時,必須掌握:(1)資本家放棄剝削,參加勞動;(2)讓他們參加較大的和基礎鞏固的手工業生產社,并須報社員大會通過: (3)入社后,將他們分散編入不同的生產組內,并不讓他們擔負領導職務;(4)生產資料及其他所需固定資產,除折價入股部分外,多余部分可以存款計息,利息大小由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籌委會和中國人民銀行商定;(5)接收小資本家入社的合作社,要繼續對這些小資本家進行思想改造,并對他們提高警惕。”(30)《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212、212、212、246—247頁。中央對手工業管理局的建議表示同意,原則認為應該由手工業部門負責改造。經過試點后,中央又改變了這種看法。(31)中央認為仍應該主要通過公私合營進行改造,改變了之前由手工業管理部門負責改造的看法。但對于已經參加手工業合作社的小資本家,也做了具體規定。參見《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39—340頁。按照蘇聯工藝合作社的經驗,雇傭15人以下的小型工業和一切服務性行業,全部由手工業部門負責改造。中共結合中國的改造實踐,認為這部分人應該由工商部門負責改造。這反映了中共在改造對象問題認識上的獨立自主。
總之,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一些人認為改造對象中的組織重點是手工業工人,主張提出一條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階級路線;一些地主、富農等與手工業不搭界的人在實際上進入了手工業合作組織;還有雇傭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手工業資本家問題。結合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中共對這些問題都進行了妥善的解決。這意味著隨著改造實踐的不斷深入,中共突破了原來只把獨立小手工業者、手工業工人作為改造對象的框架,對改造對象的認識更加深化。
三、改造高潮到來后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范圍的認識
1955年下半年,農業合作化高潮帶動了手工業改造的步伐。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問題上,之前兩個時期,中共解決的主要問題為判斷哪些人是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哪些人不是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在改造高潮的推動下,既要快速地對改造對象進行改造,又要避免發生遺漏、重復等現象,把所有應該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手工業者都納入改造中,這一階段中共主要的任務是弄清楚這些改造對象存在的范圍。
(一)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范圍的判定
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推動下,1955年12月9日,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召開了全國重點地區手工業組織檢查工作座談會,檢查“與總路線要求不相適應的保守思想”,緊接著在12月21日至28日,召開了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這次會議著重批判了不敢加快手工業合作步伐的“右傾保守”思想,研究制定了“一五計劃”期間基本上完成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規劃。
既然要在“一五計劃”期間基本完成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那么弄清楚改造對象分布的行業和人數就成為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期間,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局長白如冰在報告中對改造對象所處的行業、人數以及相應采取的改造方針進行分析。報告認為除了手工業這個行業之外,在農業、半工半商、工商界限不甚分明的行業、服務性的行業、建筑修繕行業當中,都存在著手工業勞動者,這是中共對手工業改造對象所處范圍的基本判斷。這些行業當中哪些人應該由手工業部門負責進行改造,報告當中也有相應的標準。
除了手工業行業本身外,對于農民兼營商品性的手工業,根據其是否以手工業收入為主,對他們的改造又細化為三類。總體原則是:手工業收入為主的,由手工業部門改造;農業收入為主的,由農業部門改造;農業收入與手工業收入持平的,分別建社,社員可以跨社。(32)《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39、340、340、340、360頁。對于半工半商、工商界限不甚分明的行業:凡以制造產品為主的,應通過合作化的道路進行改造;凡以販賣商品為主的,則歸商業部門改造。(33)《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39、340、340、340、360頁。對于服務行業中的手工業者:凡利用資金、設備獲取利潤而工藝性較小的行業,如飲食、屠宰、旅館、澡堂等,應劃歸商業部門改造。凡工藝性較大、商業性較小的行業,如理發、照像、洗染、織補、擦皮鞋等行業,原則上由手工業部門改造;但其中非個體部分,可由商業部門改造。凡各種修理業,如修理鐘表、自行車、收音機、火爐等,除商店中附設的修理人員外,應由手工業部門負責改造。特別在城市和鄉村中分散零星、修修補補的各種手藝人,都應該組織起來,對居民進行服務。至于鄉村中純粹臨時性的個別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可劃給農業合作社。(34)《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39、340、340、340、360頁。
對建筑修繕業,第一,在城市中一般由建筑行政管理部門改造。第二,為適應民用建筑和修繕的需要,其中國營建筑公司尚未吸收安排的小型戶以及小城鎮和農村中的泥瓦匠、木匠等,也可以由手工業部門組織合作社。第三,對木材砍伐業的個體部分,原則上由手工業部門改造,產品分配由林業部門歸口。第四,婦聯、民政等部門所組織的手工業單位和基層供銷合作社附設的加工小組,原則上應劃歸手工業部門統一領導。(35)《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39、340、340、340、360頁。這是對尚未進行改造的行業部門改造對象的劃分。至于手工業部門已經組織起來的合作社(組)則都不劃出,以免造成改造工作中的混亂。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明確改造對象的范圍,盡可能地找出所有的改造對象,按照規劃安排完成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二)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范圍的擴展
隨著改造高潮的不斷推進,1956年1月,北京市率先宣布進入社會主義。在確定改造對象的范圍問題上,北京市的經驗是:“事前必須將改造范圍弄清楚,以免造成混亂。”“凡是手工業勞動者,只要不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入社(組織起來后再審查),但領導成分必須保持純潔。”(36)《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39、340、340、340、360頁。按照北京市的經驗,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手工業勞動者都可以加入合作社,這實際上就大大擴大了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的范圍。中央手工業管理局雖然對北京市的經驗表示認可,但在后來的執行中因為種種原因,并沒有按照北京市的辦法來做。
1956年3月5日,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就手工業的情況向毛澤東主席做了一個匯報。對于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除了重申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所確定的改造范圍,認為還有幾種情況的人員需要納入改造。對于無照戶(俗稱黑戶),有一定的技術、長期從事手工業生產、并以此為主要生活來源者,應該吸收入社,不能單純以有無營業執照作為批準入社的標準。對于臨時工和失業工人,凡系長期性的臨時串連工,雖無固定主顧,但有一定的技術、依靠手工業為生、并在本地有長期戶口者,都應該吸收入社;凡屬短期性的、時來時去的臨時工,一般暫緩吸收;對于本行業的失業手工業工人,只要有技術,都應該按照生產發展需要,逐步吸收入社。對于“連家鋪”的家庭輔助工:凡過去大部分時間參加手工業勞動,本人有一定技術,家庭牽累較少者,原則上都應該吸收入社;其余可通過社外加工等辦法,適當地安排他們生產。對于老弱殘疾應按照不增加社會失業和合作社負擔的原則處理。對于政治不純分子,原則上除現行反革命分子外,都可以入社參加勞動,但對其要做一定的限制。(37)《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60、396、396、416—419頁。
這些改造對象被納入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范圍,是隨著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實踐的不斷深入發生的事情。一方面說明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問題的高度重視,怕遺漏一部分改造對象;另一方面說明原本認為已經比較全面的手工業改造對象的范圍,在實際當中還存在著空白的部分,這些空白的部分只有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中才會被發現。
(三)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范圍的重申和微調
1956年3月5日,毛澤東在聽取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匯報的時候說:“個體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我覺得慢了一點。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點慢。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組織了二百萬人。今年頭兩個月就發展了三百萬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這很好。”(3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頁。在加快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下,1956年3月、4月,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分別召開了全國城市和農村手工業改造工作座談會,研究改造中存在的問題,加快改造的進程。
雖然之前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已經對改造對象的范圍做了比較詳細的劃分,但是在改造的過程中依舊出現了亂象。白如冰在座談會的總結發言中指出:“手工業行業復雜,分散面廣,同工業、農業、商業各方面都有密切聯系。但在高潮中,因某些行業改造范圍劃分不清,不是無人負責改造,就是多頭進行改造,搞得較亂。”(39)《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60、396、396、416—419頁。他隨后在講話中列舉了各地出現的亂象。如上海市18萬個體手工業者中,劃歸工業、商業部門改造的有7萬人。(40)《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60、396、396、416—419頁。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問題?在當時的手工業管理者看來,除了手工業行業本身的從業者需要改造之外,其他行業中的手工業者被錯劃,主要是沒有合理劃分手工業同工業、農業、商業等部門的改造范圍。為此,白如冰在總結發言中,從手工業和工業部門分工,手工業和農業部門分工,手工業和商業部門分工,對建筑業的改造四個方面,重新申述了這些行業當中的手工業從業人員,哪些應該歸手工業部門負責改造。這個劃分基本上和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上對手工業改造對象范圍的劃分一致。
繼全國城市手工業改造工作座談會之后,1956年4月全國農村手工業座談會召開。由于農村手工業和農業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情況復雜,手工業與農業之間界限不易截然劃清,認識也不完全一致,產生了一些問題。(41)《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360、396、396、416—419頁。這些情況的出現影響到了農業、手工業兩方面的生產和改造,必須妥善地加以處理和解決。對于如何把握好農業當中的手工業從業者的改造,國務院在1956年4月3日明確指出:“除了城鎮中的手工業者和鄉村中比較集中的以從事手工業生產為主的手工業者,單獨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以外,應當允許鄉村中分散的和以農業為主兼營手工業的手工業者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4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3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頁。這和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關于農業當中兼營手工業者的改造意見一致。
但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中,發現之前劃分的改造范圍有弊端。1956年6月5日,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中,我們曾對手工業改造范圍的劃分,進行了討論,提出了分工歸口管理的意見。當時的情況是,不進行劃分會增添全國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被動和混亂,因而這樣做也是對的。但是現在看來,機械地劃分還是有問題的,主要是過去從改造分工考慮較多,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整體性考慮不足,因而把一些行業人為地割裂開來了。為了做到對生產、對改造更加有利,為了不影響手工業者的工資收入,我們認為可以按照生產與銷售習慣,進一步劃分手工業和工業、商業等部門的管轄范圍。”(43)《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第1卷,第447—448頁。之后進行了調整。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白如冰在八大上的發言中說:“到今年六月底止,全國組織起來的手工業者約占手工業者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左右。”(44)《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9—580頁。絕大多數的手工業者進入到手工業合作組織中來,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與改造過程中,改造實施者們不斷識別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對象有著巨大的聯系。
總之,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后,改造的實施者們按照手工業分布的行業,按照一定的標準,對改造對象的范圍進行了劃分。但隨著手工業改造實踐的不斷推進,人們發現在實際改造過程中,出現了錯劃的現象。對出現的情況,改造的實施者們一方面不得不重申改造范圍的劃分,一方面對不適當的范圍劃分做出調整。
結 語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把哪些手工業者組織進手工業合作組織中來,一直是中共思考的一個重要政策性問題。中共作為改造的實施者并不是在改造一開始就對改造對象有著非常準確的認識,而是隨著改造實踐的不斷深入,才對改造對象的認識越來越清晰明確。改造的實施者們最開始思考的問題為哪些人是改造對象,哪些人不是改造對象。隨著改造的不斷深入,改造的實施者們思考更多的是改造對象分布的范圍,避免出現改造對象遺漏或者重復。隨著改造實踐的不斷深入,中共作為改造的實施者發現不論是改造對象本身的確認,還是在改造對象范圍的劃分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以致不斷地調整。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逐漸呈現在人們面前的。
改造對象是客觀存在的,但中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改造的實施者們在確定了改造對象之后,發現仍有遺漏;在改造高潮到來后,改造的實施者們對手工業改造對象所處的范圍盡可能全部涵蓋,做到不遺漏,但發現還是有不合適的地方。甚至在改造結束之后,仍有一部分個體手工業者存在于手工業合作組織之外。這說明人對客觀對象的認識是不可能一次窮盡的,必須在反復的實踐當中,通過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這樣一個反復的過程來把握事物內在的規律。在手工業改造對象問題上是這樣,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例如中國革命、建設問題上,中共對客觀對象的認識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