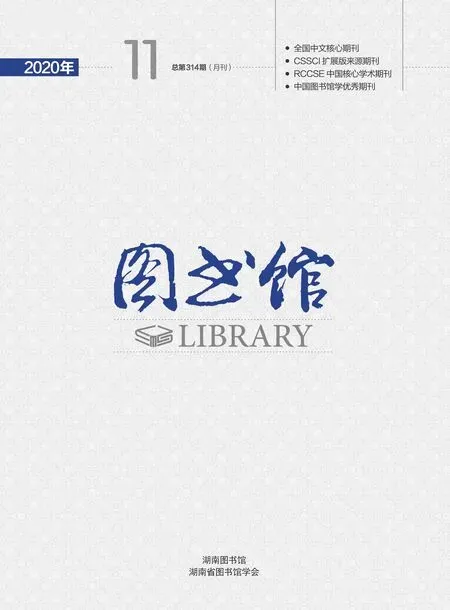圖書館評價的變化特點和發展趨勢
——以國際影響力評價標準為例
楊曉偉
(東莞圖書館 廣東東莞 523071)
1 引言
新世紀以來,我國圖書館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盡管城鄉差距和地區差異還比較明顯,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公共圖書館法》《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以及各種地方圖書館法規的頒布,為圖書館的發展提供了經濟保障、制度保障和政策保障,各級政府對圖書館的投入隨之增加。無論是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還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圖書館新館的建設如火如荼,館舍面積和軟硬件配置都有了較顯著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公眾和社會比以往更迫切地關心一個問題:公共資金加大了對圖書館的投入,圖書館為社會又貢獻了什么?圖書館的社會貢獻是否隨著政府投入的增加而有所提升[1]?此外,隨著信息化浪潮的到來,圖書館的受眾有了更廣泛的信息獲取渠道,是否還需要利用圖書館來滿足自身的信息需求?圖書館迫切需要回答這些問題,證明其在社會經濟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效益,以此來獲取更多的政府投入和政策支持。因此,要證明圖書館的社會貢獻與服務效能,就需要對圖書館開展全面的評價。
圖書館評價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對圖書館的一個價值判斷過程,是指評價者以圖書館整體或者某一方面作為評價對象,根據特定的評價標準和評價方法做出客觀判斷的過程[2]。其內容應包括圖書館的資源、服務以及用戶的評價。因此,無論是圖書館的建筑設施還是服務內容、日常活動,或用戶評價,都需要權威的評價標準,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數據或結果。本文試圖通過對圖書館評價標準進行回顧、比較和分析,發現圖書館評價工作的變化特點和發展趨勢。
2 國際圖書館評價標準回顧
早在20世紀70年代,國際組織就開始圖書館評價研究,如ISO2789:1974 International library statistics國際圖書館統計,最早提出了圖書館評價的統計方法。隨著評價工作的深入,評價的標準建設經歷了從研究圖書館資源的投入產出到建立績效指標,再到開展圖書館影響力評價三個階段。
2.1 研究資源投入和效益評價階段
在20世紀70—80年代,圖書館評價強調的是對圖書館的文獻、館員、設備設施、投入經費等資源要素以及服務效果的評價,重視輸入性的資源要素及資源的產出效益。具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國家圖書館在1979年頒布的《聯邦圖書館績效評價手冊》以及美國圖書館協會1982年提出的《公共圖書館服務成效評價:規范化操作手冊》,后者對圖書館輸出的結果和效益從5個方面、12個評價指標來進行評價,為美國公共圖書館績效評價提供了指南,也使得圖書館評價從理論研究進入了實踐應用階段[3]。
2.2 開發績效評價指標階段
在20世紀80—90年代,圖書館評價主要是研究評價的績效指標,并對學術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服務進行評價。代表性的是國際圖聯(IFLA)1998年出版的《關于大學圖書館績效評價的標準》,它提出從目的、組織和行政管理、館藏、服務、設施、員工、預算和財政、技術、保存、維護合作10個方面對大學圖書館服務質量進行評價。該標準得到國際廣泛認可,成為大學圖書館績效評價的指導性文件[4]。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很多國家開發了圖書館評價的指標體系,但名詞術語、評價范圍、評價方法不一致,使得各國圖書館的評價不能按統一的規則進行。因此,國際標準化組織(ISO/TC46)以各國圖書館與國際圖聯的研究成果為依據,起草了有關圖書館績效評價的國際標準ISO 11620,來指導各國圖書館的評價工作。
2.3 探索和形成影響力評價標準的階段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圖書館評價從績效評價轉向成效評價,即圖書館影響力評價。1998年,美國大學和研究圖書館協會(簡稱ACRL)發布了《學術圖書館成效評價報告》白皮書,厘清了投入、產出和成效的概念,明確了學術圖書館成效評價的定義和原則。該規范也成為了國際圖書館界關于學術圖書館成效評價的里程碑[5]。2003年,英國國家圖書館學會啟動了為期3年的“影響力評價”工作,按照圖書館特定的服務指標,來觀察用戶的變化及相關證據,并于2005年在英國圖書館界全面啟動影響力測評[6]。在此基礎上,英國文化和傳媒體育部在2007年發布了經過三次修訂的《英國公共圖書館服務標準》,從服務便利程度、圖書館利用程度、讀者滿意度、資源保障程度等4個方面評價圖書館的影響[7]。德國、法國、澳大利亞以及美國也紛紛對圖書館的影響力評價進行了更廣泛的探討。如英國博物館、圖書館及檔案館理事會(MLA)在2008年發布的《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的社會產出框架》中明確了圖書館的社會價值,并利用此框架評價圖書館對社區的社會影響[8];美國對圖書館影響力的評價側重于經濟價值方面,通過各種不同規模的社會調查,利用成本效益法和經濟影響分析法等經濟學手段來評價圖書館對社區直接的經濟效益及對地方經濟的影響[9]。隨著各國各種圖書館成效評價理論和體系研究的不斷深入,制定統一的影響力評價標準被提上了議事日程。2010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TC46)啟動了影響力評價國際標準的制定,并在2014年正式頒布ISO 16439:2014(以下簡稱影響力評價標準)。
從國外圖書館評價標準的發展歷程來看,業界開展了長期的研究和實踐探索,圖書館評價已逐步形成了側重圖書館資源投入、服務效果、效率的績效評價和側重圖書館服務對讀者的影響、效果的成效評價兩大體系,并都建立了相關的標準,如圖1。

圖1 圖書館評價體系
伴隨著業界對圖書館評價工作的廣泛重視,國際圖書館統計標準ISO 2789(以下簡稱統計標準)和國際圖書館績效指標ISO 11620(以下簡稱績效指標標準)歷經多次補充及完善,見表1。

表1 ISO發布的圖書館評價系列標準
3 圖書館影響力評價標準背景及內容結構
通過對圖書館評價標準的回顧,我們可看出新世紀圖書館的評價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影響力評價階段。圖書館“影響力”指的是圖書館及其服務對個人或社會產生的變化[10]。圖書館開展影響力評價,其目的是確認圖書館對個人以及社會產生哪些影響,這些影響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降低負面影響,使得正面影響最大化。影響力評價作為圖書館整體策劃、實施、評價和改進這一管理循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圖書館評價的重要環節。
3.1 影響力評價標準的誕生背景
影響力評價標準的制定始于2010年12月,由ISO/TC 46/SC 8委員會負責。2012—2013年,ISO/TC 46/SC 8委員會的主席,該項目的主要負責人Roswitha Poll對標準中應該包含的評價指標、方法與流程進行了初步探討,并從圖書館評價標準的變化角度對標準的框架和內容進行了深入論證[11]。2013年,美國學者Sarah M. Passonneau在《圖書館評價活動》中進一步肯定了完善影響力評價標準有利于圖書館評價工作[12]。同年,ISO/TC 46/SC 8委員會發布了ISO DIS 16439:2013,即標準草案。一年后,標準正式發布。
影響力評價標準發布之后引起了國際圖書館界廣泛關注,荷蘭、斯洛文尼亞、英國、丹麥、西班牙、葡萄牙、日本、法國、愛沙尼亞、芬蘭等10余個國家紛紛采用了該標準。標準制定的主要負責人Poll為了讓業界更好地理解和運用該標準,對標準中的內容、方法、重點及難點等進行了解讀[13]。各國學者在此基礎上,也展開了廣泛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運用。如:2014年澳大利亞的Susan Henczel運用標準的方法對圖書館聯盟的影響力進行了定性調查與分析[14];2017年,英國的Claire Creaser 總結了標準的作用和關鍵方法[15];同年,南非的Karin de Jager和澳大利亞的Sputor也運用標準分別對開普敦高校圖書館與澳大利亞學術圖書館的影響力進行了評價[16-17];2018年,葡萄牙的Leonor Gaspar Pinto則依據標準的方法和葡萄牙國家可持續發展目標,對葡萄牙公共圖書館和可持續發展項目進行了評價[18]。
我國也是最早注意到該標準的國家之一。2014年,經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批準,由東莞圖書館主導的《信息與文獻 公共圖書館影響力評價的方法和流程》成功立項,并于2019年正式發布。該標準通過引進國際影響力評價標準,填補了我國在該領域的空白。
3.2 影響力評價標準的體例和內容結構
影響力評價標準按照國際標準的編寫規范,分為四個部分,每個部分都有其獨特的作用[18],詳見表2。

表2 影響力評價標準的框架結構
影響力評價標準的發布為圖書館的影響力和價值評價提供了方向指引,使不同級別、不同規模的圖書館開展影響力評價工作時有了科學指導和統一規范,為全面衡量圖書館的價值提供了依據。
4 影響力評價標準與績效指標標準比較
由統計標準、績效指標標準組成的圖書館績效評價標準和圖書館影響力評價標準,共同組成圖書館評價的標準體系。但由于三個標準制定的時代背景有所不同,因而標準的主要目的、作用范圍、局限性存在差異[19-20],見表3 。
通過比較可知,三個標準都是圖書館評價的重要工具,都可以為圖書館的評價工作提供規范指導,但側重點又有所不同。統計標準重在規范數據來源;績效指標標準重在統一指標、術語、定義以及計算方法;而影響力評價標準關注的是圖書館對個人學習、社會和經濟產生的作用或影響,以及這些作用或影響與圖書館的戰略規劃、預期目標的差距。因為這些差異的存在,統計標準、績效指標標準和影響力評價標準的主要內容也有很大的不同,見表4。

表3 三大標準制定目的、作用范圍及局限性比較
統計標準與績效指標標準的頒布,推動了國際圖書館界對圖書館評價的標準化,為圖書館的評價提供了指南。但統計標準只是圖書館相關數據的統計工具,強調的是資源投入,如館藏、設備、支出、圖書館的利用數據等,未論證過這些資源投入和服務質量的關系,同時缺乏對圖書館成效的描述,即用戶的改變,因此并不能對圖書館的真實質量進行評價。而績效指標標準,雖然評價的內容相對全面,能夠對圖書館大多數的服務進行評價,但未能覆蓋圖書館服務的全部內容,尤其是圖書館深層次服務,如:圖書館給用戶、社會帶來的變化,圖書館的經濟價值等。因此,僅僅利用績效評價標準中的方法并不能證明圖書館是否產生了預期的影響。完整的圖書館評價除了績效評價外,影響力評價不可或缺。圖書館全面的評價必須包括三種類型:資源投入、效益產出和影響力評價,才能形成一個從輸入到輸出、從量到質、從微觀到宏觀的整體評價體系。
雖然三個標準的目的、范圍和內容存在許多差異,但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三個標準之間互為基礎,互相支撐。統計標準是評價的基礎,它按照績效指標標準的要求,為其指定了數據來源;此外,統計標準中包括大量的投入和產出數據,雖未能直接描述圖書館績效水平的高低和圖書館對用戶產生的直接影響,但這些數據在某些情況下能用于確認圖書館的發展態勢,反映圖書館在某些方面的影響力。例如:如果對圖書館一定時期內的用戶數據進行分析,就可以看出用戶在利用圖書館后觀念和行動上產生的改變。
績效指標標準體現了圖書館評價的內涵與重點,可以評價圖書館服務及活動的質量、效果以及成本效益,讓圖書館的用戶、社區或上級機構更好地了解圖書館服務的優劣,從而為圖書館管理提供決策支持。績效指標標準雖不能直接評價圖書館的影響力,但績效指標可被視為公共圖書館影響力的信號燈。我們僅憑某一項指標很難評價圖書館的影響力,但通過綜合運用多種指標,并關注指標結果的變化,就能夠判斷出圖書館的影響力產生及改變的原因,有助于對影響力評價結果進行分析。
影響力評價標準對圖書館服務的全面價值及評價流程進行了規范和統一,通過利用圖書館統計數據及績效指標,并綜合其他學科領域評價方法,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圖書館評價體系。
三個標準隨著圖書館評價工作的深入得到了不斷完善,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標準并不適用于所有圖書館,也未能涵蓋圖書館服務中所有統計數據、績效指標以及成效評價的方法,這也充分說明了圖書館評價的復雜性。

表4 影響力評估標準、統計標準以及績效指標標準的內容比較
5 圖書館評價的變化特點
我們通過以上對圖書館評價三個標準的背景、目的以及內容的分析,發現圖書館評價在評價內容、評價角度、評價方法以及評價手段上呈現出以下特點。
5.1 評價內容上更加重視圖書館價值的全面探索
無論是統計標準,還是績效指標標準,重點仍是圖書館的投入和產出。影響力評價標準第一次將影響力概念納入圖書館的評價體系中,評價的對象更加全面,涵蓋范圍也更加廣泛,除了關注傳統意義上的圖書館社會效益,更關注圖書館對個人的影響及經濟價值,全面探索圖書館的社會貢獻。
5.2 評價角度上更加重視用戶的感受
傳統的圖書館評價,更多的是以圖書館為中心,關注的重點是圖書館為用戶、社會做了什么?而影響力評價,是以用戶為中心來計劃和評價圖書館服務或活動。它顛覆了圖書館與用戶的關系,將用戶的感受放在首位,它關注的重點不是圖書館做了什么,而是用戶從利用圖書館中獲得了什么改變。圖書館通過跟蹤這些變化,實現圖書館服務質量的提升。
5.3 評價方法上更加重視客觀公正
影響力評價需要進行大量的長期的抽樣調查、街頭調查、小組訪談等,這些調查直接來源于圖書館的廣大用戶,并且多數是面對面的接觸,因而其結果更能體現用戶對圖書館最真實的感受。此外,影響力評價需要一些專業的工具和方法,除了圖書館工作人員,專業的調查公司、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參與也必不可少,這樣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證結果的客觀公正。此外,影響力評價強調定性法和定量法的組合運用,以佐證對評價結果的判斷,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評價結果的客觀公正。
5.4 評價手段上更加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無論是統計標準,還是績效指標標準,都來源于各國的評價理論及實踐,不斷經過評價實踐的驗證,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修訂和完善。影響力評價標準也是如此,它在借鑒各類評價標準優點的基礎上,強調在評價中對各種方法的靈活運用,并提出在評價實踐中要注意的問題;同時,也提供了眾多的評價案例,方便更好地指導圖書館的評價活動。
6 圖書館評價工作未來的發展趨勢
影響力評價標準作為國際上首個圖書館成效評價標準,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圖書館評價體系,其提供的評價方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可以為圖書館開展成效評價提供依據。它在一定程度突破了以往績效評價標準的局限性,使圖書館評價呈現出以下趨勢。
6.1 評價內容豐富化和多元化
影響力評價的內容更加豐富,不僅全方位地評價了圖書館對個人、社會和上級機構帶來的變化,更首次將圖書館的經濟價值評價納入了評價標準。無論是統計標準,還是績效指標標準,對圖書館的經濟價值涉及較少,這會使圖書館對社會的經濟作用難以量化。近年來,雖然各國從不同的角度開展了圖書館經濟價值評價研究,但一旦將其納入國際標準,將讓業界對圖書館經濟價值的評價更加重視,使圖書館評價更加多元化。
6.2 評價方法綜合化和多樣化
早期的圖書館評價以定性評價、主觀評價和專家評價為主,通過圖書館自我評價或專家考察后對圖書館各項要素打分,得出評價結果。這種方式主觀性較強,容易產生偏差,評價結果的可信度不足。隨著評價方法的改進,圖書館評價的各類數據更易獲取,定量評價以及其他領域的評價方法也逐漸受到重視。影響力評價標準在評價過程中不僅綜合利用了定性法與定量法,還引入其他領域的評價方法,如:消費者剩余法、條件價值評估法等,實現了圖書館評價方法上的多樣化。
6.3 評價活動規范化和制度化
目前,各國都意識到了圖書館評價的重要作用,紛紛在圖書館法或相關法律法規中規定了圖書館評價的內容。與此同時,國內外諸多與圖書館評價相關的政策、文件、規范、標準、手冊、指南等也相繼出臺,并以此為依據開展了一系列圖書館評價活動,推動了圖書館評價不斷走向科學化。隨著統計標準、績效標準以及影響力評價標準的出臺,圖書館評價的指標、方法和流程均已有明確規定,圖書館評價的機制將更加成熟,圖書館評價可以逐漸從短期的靜態化評價向長期連續性的動態化評價轉變,使圖書館評價工作逐步走向常規化、制度化和規范化。
6.4 評價活動國際化和社會化
隨著圖書館界國際交流和社會交流的加強,圖書館評價國際化和社會化是必然趨勢。一方面,世界各國先進的、豐富的評價實踐經驗、評價標準規范和評價理論研究為我國圖書館評價的實踐和理論研究提供了有益參考;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科技一體化和全球化已逐步深入,中國與世界接軌,我國圖書館評價將步入世界圖書館評價行列,利用國際標準,如影響力評價標準,來衡量我國圖書館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水平,可以使我國的評價工作與國際接軌,找出差距,促進我國各級各類圖書館的發展。此外,當今的圖書館和圖書館事業發展處于一個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無法脫離各種社會因素。一方面,圖書館參與政治、科技、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活動的程度日益加深,貢獻日益加大,影響日益顯著;另一方面,隨著公眾民主意識、權利意識的增強和知識、文化、學習需求的增長,公眾和社會對圖書館的期望日益上升,建立在圖書館資源、服務以及影響力基礎上的圖書館質量評價也受到了社會普遍關注。因此,無論是圖書館的績效評價、還是影響力評價都將更多與社會接軌,體現社會的迫切需要。
正如李國新教授所言:對一個圖書館做出完整的評價,對一個圖書館的社會貢獻做出完整的描述,需要多元互補的體系[21]。雖然影響力評價標準的出臺為這一體系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圖書館事業發展和評價工作不斷演進,未來圖書館的評價體系還需要不斷補充和完善,以更好地指導圖書館的評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