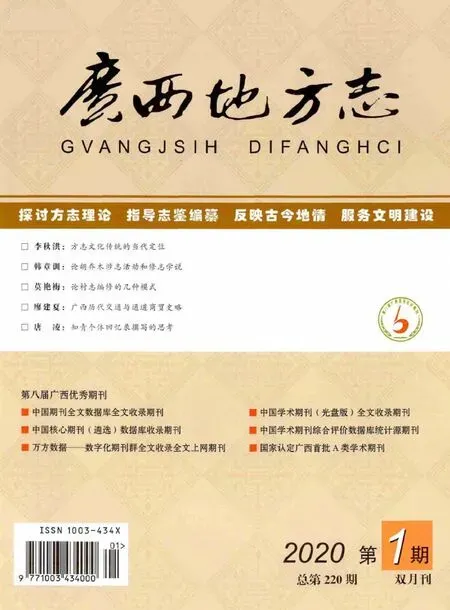廣西歷代交通與通道商貿史略
廖建夏
(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6)
廣西沿江沿海,地理位置重要,歷代是聯系內地與東南亞國家的紐帶。歷代政府出于南控邊疆和經濟開發的考慮,對廣西的交通建設非常重視,構建了通達內外的交通網絡。交通的建設為維護大一統國家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起到了橋梁作用,也為維護邊疆的安定起到了安全保障,同時在促進廣西城市繁榮、社會經濟發展、文化振興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廣西交通史一直以來受到學界較大關注,謝日升曾經對相關成果做了較為全面的梳理[1]。從1938年陳暉發表《廣西交通問題:廣西大學經濟研究室研究報告》[2]一書以來,有關廣西交通方面的研究就沒停止過,20世紀90年代是廣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時期,其中主要的成果有:由廣西地方政府組織編纂的《廣西通志·交通志》[3]《廣西交通》[4]《廣西航運史》[5]《廣西公路運輸史》[6]等著作相繼出現,為研究廣西水陸交通運輸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鐘文典主編的《廣西通史》[7]一書中用了不少篇幅介紹了廣西交通和商業貿易的發展情況。楊聰《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交通運輸史略》[8]一書中,第二章介紹從秦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西交通運輸的發展歷史。陳偉明《全方位與多功能——歷史時期嶺南交通地理的演變發展》[9]一書,分析了從秦漢到明清時期嶺南地區(包括今廣東、廣西和海南)交通地理的歷史發展狀況,其中對廣西交通也做了深入探討。覃主元主編《廣西對外交通史》[10]一書是廣西交通史研究上的一部重要著作,該書從陸路和海路兩個視角,對先秦到近代廣西地區的對外交通進行了深入客觀的分析。在論文方面,主要有方鐵《明代以前廣西地區的交通》[11],系統回顧了自秦迄元1500余年間廣西交通發展的歷史進程,陳代光《論歷史時期嶺南地區交通發展的特征》[12],分析了南北過嶺通道在各歷史時期的發展特征,周長山《廣西歷代對外通道》[13]介紹了廣西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在歷代扮演著溝通中原與南海地區交通要道的角色。斷代史方面論文主要有:王元林《秦漢時期南嶺交通的開發與南北交流》[14],李珍,藍日勇《秦漢時期桂東北地區的交通開發與城市建設》[15],廖幼華《唐宋時期邕州入交三道》[16],陳偉明《宋代嶺南交通路線變化考略》[17],吳小鳳《明代廣西交通建設述略》[18],劉祥學《明清時期廣西少數民族地區交通發展略析》[19],賓長初《新桂系交通建設述論》[20]等,也都對歷代廣西交通發展情況進行研究。
廣西商貿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吳小鳳《明清廣西商品經濟史研究》[21],研究明清時期廣西商品經濟的歷史基礎及廣西的交通、商品經濟的發展情況;鐘文典主編的《廣西近代圩鎮研究》對廣西近代圩鎮進行了綜合考察,并就農業、手工業、工業、礦業、交通、廣東商人等方面與廣西近代圩鎮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唐凌主編《廣西商業會館研究》[22],以商業會館為切入點,讓人看到了明清邊疆經濟開發是一個以政府為主導、以民商為主力的生產要素投入與重組的過程;陳煒《近代廣西城鎮商業網絡與民族經濟開發》[23],以近代廣西城鎮為研究對象,著重分析其商業網點布局與商業網絡結構,探索了新經濟形式下區域民族經濟開發的模式與途徑。論文方面主要有:何海龍《走出荒蠻——交通與秦漢時期的嶺南越族社會淺析》[24],研究了秦漢時期嶺南水陸交通的拓展強化對區域社會經濟的影響;吳小鳳的《漢唐廣西經濟史述略》和《明代廣西城市圩市建設研究》[25],研究了漢唐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對廣西商品經濟的繁榮作用以及廣西城鎮基本格局形成原因;陳煒《明清時期廣西城鎮商業網絡研究論綱》[26],分析了廣西一批以商業貿易為核心的城市與口岸,依托所在江河流域構建了四個相對獨立的具有明顯區域性經濟和文化的城鎮商業網絡形成發展情況;蔡良軍《唐宋嶺南聯系內地交通線路的變遷與該地區經濟中心的轉移》[27],論述了唐宋時期嶺南交通主干線與經濟中心轉移的關系;唐凌《論近代廣西商埠的經濟聯系》[28],探究了依托現代交通,廣西商埠如何與國內外市場加強經濟聯系等。這些論著讓我們認識到交通發展與經濟發展間的互動聯系,揭示了經濟對交通變遷的決定作用。
交通對廣西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各時期水陸交通的拓展強化了廣西的政治地位,加強了中央與廣西的聯系。交通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定社會經濟發展的標志。本文試圖在梳理總結學界研究成果基礎上,分析廣西歷代內外交通發展與通道商貿的關系,以求更全面了解廣西交通與商業貿易發展的演變歷程,從中揭示出交通事業的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與規律,為當今廣西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一些借鑒意義。
一、先秦至南朝時期:廣西交通的初步發展與早期市鎮、港埠的興起
雖然南嶺阻擋南北,但先秦時嶺北與嶺南的民間往來就已存在。廣西各部族向商周王朝朝貢各種特產,都是利用山脈間形成的天然徑道往來。秦漢之際,隨著嶺南驛道的開辟和水道的整治,廣西水陸兼程的道路北可抵中原,南達交趾(今越南北部),東通南海(今廣東),西至夜郎(今貴州)。廣西初步建立了內外交通驛道和外貿港口,主要以南嶺通道、瀟賀古道、交趾道、牂牁道等陸路和以合浦為起點的海上絲路為主。
(一)嶺南地區交通網絡的初步形成
秦漢是南嶺交通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央王朝主要通過修筑“新道”,開通“交趾道”和牂牁道,加強對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影響。秦始皇在統一嶺南之前,就伐木修筑“東窮燕齊,南極吳楚”的馳道[29],馳道可至楚地湘水流域。根據譚其驤先生的考證,楚國有水路可通達廣西[30]。嶺南山高林密,開山辟道不易。古道是各地之間最便捷易行的道路,利用古道擴筑成新路,最為經濟簡便。秦朝利用原有古道,沿著秦軍打通的路線進行擴建,開辟驛道,整治水道,并設置關隘,在嶺南進一步開辟“新道”[31],先后開辟了四條主要道路:第一條,擴建自湖南進入今廣西全州經興安、桂林、陽朔、平樂至鐘山的驛道,開通了“湘桂走廊”;第二條,擴建自湖南道縣經江永、廣西富川、鐘山、賀街、信都至蒼梧的驛道,該古道“于瀟永臨封,為秦尉屠睢督帥征駱越所辟也”[32],被稱為“瀟賀古道”。該道主體部分可分為東西兩道,東道即修筑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桂嶺通楚古道,連接湖南江華縣大圩,經廣西賀州開山鎮到達桂嶺鎮,與桂嶺河相連;西道即秦代的“新道”,經湖南江永至謝沐關、富川朝東、城北或經江永到廣西富川古城,入賀江水路。兩條道路經水路在臨賀古城匯合,然后向東通珠江入海。這兩條驛道成為中原入廣西并通往東南亞各國的主要驛道。第三條,修筑自蒼梧貫通嶺南三郡的驛道。東部沿西江通南海郡治所番禺(今廣州),西路沿潯江至桂林郡治所布山(今貴港),再向西沿郁江、左江至象郡治所臨塵(今崇左),向西南經今龍州、憑祥通往越南北部地區。第四條,開辟連接北流江、南流江間的驛道,即自今北流經玉林至合浦。這些驛道連接水道,構成以水道為主、驛道為輔,水陸兼程或水陸并行的交通路線,在軍事上具有重要作用[33]。
漢朝幾次大規模對嶺南用兵,往往在舊道基礎上擴筑,或者新辟道路,水陸兼程,平定地方。如建武十六年(40)交趾二征叛亂,馬援奉命“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余人討之”[34]。其軍隊從靈渠道、臨賀道等南下西江,經北流江越鬼門關達南流江直至合浦,“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余里”[35]。沿海路線為抵達合浦港后,向西經過大觀港、烏雷嶺到達交趾。這條橫跨中國南部的千里水路,后世稱之為“馬援故道”。
牂牁道原為民間商貿之路,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南夷之端,見蒟醬番禺,大夏杖、邛竹”[36]。南越能得到蜀地的蒟醬,應是西南地區蜀、夜郎與嶺南交通發展的結果。唐蒙經過考察后,發現蜀地經青衣江達青衣縣(治今四川蘆山)、南安縣(治今四川樂山)、僰道縣(治今四川宜賓),可進入云貴地區,他主持修筑了“南夷道”作為官道,即從僰道經南廣縣(治今四川高縣、筠連縣一帶)、汾關山(今云南威信境)、平夷縣(治今貴州畢節)、漢陽(治今貴州赫章、六枝一帶),連接牂牁江(今北盤江上游),順牂牁江(今紅水河、西江)而下番禺[37]。北盤江—紅水河—西江水路成為聯系巴蜀滇黔與嶺南乃至直下南海的主要通道之一。
雖然海路艱險,然而較陸路便捷。靈渠—合浦成為連接中原至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重要水路。永初八年(83),大司農鄭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于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38]。交趾及嶺南西部各郡特產主要經零陵郡嶠道轉送,自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經靈渠,入漓江,經桂江至蒼梧,沿郁江入北流江,轉陸行入南流江,可至合浦出海。通過嶺南交通網絡,國內交通與國外交通融為一體,中外陸海交通網已初步形成。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造船和駕駛技術比漢代有所提高。隨著以番禺為起點的深海航線逐漸開辟,合浦的樞紐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依然是廣西海外交通的主要港口。秦漢嶺南交通網絡的逐步形成和發展,將嶺南與內地有機地連接起來,使中央與地方建立了強有力的聯系,對大一統國家交通體系的完善發揮著重大作用。
(二)早期市鎮、港埠的興起
先秦時期,廣西尚無城市。自秦統一后,隨著郡縣制的推行,開始形成了以郡縣治地為中心的城鎮。秦漢時期新修和改建的道路,雖然是出于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目的使廣西的陸路和水路平整通暢,為廣西與中原地區的各項交流奠定了基礎,帶動了廣西早期市鎮、港埠的興起與繁榮。城鎮不僅是郡縣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當地的經濟中心和商人、手工業者活動的主要基地。湘桂走廊成為嶺南與中原地區經濟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水陸通道之一,古道上形成的居民點往往是當地的軍事要地和經濟中心。今廣西確知的秦漢古城址有興安的秦城,全州的洮陽城、建安城,灌陽的觀陽城,賀州的臨賀城等,大都集中在桂東北的交通要道附近[39]。桂東北水路沿線的市鎮主要有全州、興安和桂林等。桂林“奠五嶺之表,聯兩越之交,屏蔽荊衡,鎮懾交海,枕山帶江,控制數千里,誠西南之會府,用兵遣將之樞機也”[40],是廣西最靠近中原文化核心地帶和中央王朝統治中心的區域。柳江沿線的融水和融安則成為牂牁江古水道的主要中轉港埠,經濟也有了較大發展。
漢元鼎六年(前111),漢武帝平定南越國,遂于嶺南設蒼梧等九郡,因此嶺南地區重歸中原政權的管轄,其中廣信縣即蒼梧郡治所在。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將交趾刺史部由羸(今越南河內西北郊)移治蒼梧郡廣信縣,統轄嶺南的蒼梧等九郡。廣信縣地處離水與郁水的交匯處,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嶺南要地”,作為重要水路交通樞紐的廣信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對接點,作為統領嶺南九郡的政治中心長達三百余年。漢代蒼梧郡包括今桂江、臨賀水及西江中游郁江等流域區,作為漢代的蒼梧郡“物富民殷之地”[41],在兩晉以前是嶺南最主要的經濟區。作為漢代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對嶺南地區的開發及嶺南與中原地區的經濟交流和文化交融產生了重要作用。東漢建武年間,馬援南征交趾,不僅打通便于行軍的水陸通道,而且“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42],道路通暢,有利于商貿發展,對廣西城市發展意義極大。合浦郡治所在地農業開發較早,是“魚鹽珠璣”及桑麻稻薯的產地,物產豐饒,水陸交通方便,通過南流江及驛道與經濟腹地有密切往來,以海船與沿海地區溝通。漢代,朝廷于合浦設置專門機構和官員來管理中外貿易,商人云集,海外貿易也有較大的進展,合浦是當時對外貿易的港口之一。三國時期,孫權派宣化(今南寧)從事朱應及中郎康泰前往打通與南海國家的交往通道[43]。
據考古資料,可以看出漢代的廣西農業有了較大的發展[44]。酈道元《水經注》中記載嶺南一帶有“兩熟之稻”[45]。兩季稻的耕種,提高了嶺南地區的糧食總產量,為市場提供商品打下基礎。銅器、漆器、玉石加工、陶器制造業和紡織工藝等都有相當高的水平[46]。“處近海,多犀、象、瑇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47]。一些漢代墓葬出土了漢代的錢幣,有秦半兩、漢五銖、王莽時的貨泉等[48],貨幣的使用表明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今桂林、梧州兩地區大部分,玉林、欽州、柳州三地區的部分及南寧、百色、河池地區的河谷平地,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開發。
漢代廣西社會經濟的發展并不平衡,由于地理環境和社會制度不同,如東部大致以柳江為界,東半部比較平坦,土地肥沃,交通方便,實行封建制,發展迅速,而西半部多為山高水寒地區,土質貧薄,交通不便,仍然處于奴隸制的統治之下,社會封閉,發展十分遲緩。
二、隋至宋代廣西交通體系的基本形成與商貿發展
隋唐以來,廣西通往各州縣的陸路交通網逐漸形成,通往安南、滇黔、湘粵等周邊地區的道路也不斷開通,廣西交通依舊有所發展。宋代安南脫離中央王朝的管轄而獨立,廣西成為通往嶺外周邊國家的水陸門戶,交通基本格局除了沿襲隋唐之舊,還有兩個明顯的變化:一是交通道路的增辟,二是交通路線的整治與管理水平的提高[49]。廣西驛道的修筑從桂東北、桂東南地區逐漸向桂中和桂西地區擴展,并初步形成驛道網絡骨架,形成以桂州(今桂林)、邕州、梧州等幾個中心城市為支點,輻射四方的水陸交通網絡。經過隋唐宋三代的開拓,廣西驛道網絡的干線已基本形成,以廣西為通道,中原、云南、貴州經廣西出海的路線逐漸明晰。廣西區域內以欽州、邕州為主體通往安南的對外交通路線形成,以后各個朝代主要是修筑驛道支線。唐宋時期,嶺南地區的交通路線主要有兩種功能,一是政治型,二是軍事型,尤其以后者最為明顯。到了宋代,嶺南交通的主要功能開始向經濟型轉變,其中以廣南西路干線的轉變尤為明顯。
(一)交通體系的基本形成
唐中期,隨著對邕江上游土著民族的屢次用兵及控制力的增強,勢必需要積極開拓道路,以確保軍事行動的順利開展,逐漸形成了聯絡邕交兩州以及各羈縻州的交通網絡。《元和郡縣志》敘述了嶺南道各州縣的“八到”情況,形成了北通長安和洛陽、南至海南島、西接南詔、東到閩浙的交通網絡。宋仁宗以狄青為宣徽南院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率13萬人馬征討儂智高,打擊自唐代以來盤踞在左江地域的廣源蠻勢力,中央力量深入到桂西土著豪酋的領地,內外交通路線也因此逐漸發展。
1.建立以桂州、邕州為中心的省內通道
咸通三年(862),唐懿宗將嶺南道分為東、西兩道,邕州成為嶺南西道的政治中心。宋代,廣南西路的行政中心設在桂州(南宋改為靜江府)。桂州路是廣西的主干道之一。從邕州到桂州,有經由象州和藤州兩條路可選擇。象州路是從邕州北上經澄州(今廣西上林)或賓州(今廣西賓陽)到達嚴州(今廣西來賓),再經象州到達桂州。北宋咸平(998—1003)中,王舉任賓州知州,改建了古漏關路段[50]。藤州路則由邕州沿江而下至橫州,再經貴州(今廣西貴港)、潯州(今廣西桂平)、藤州(今廣西藤縣)、梧州,沿漓水而上桂州[51]。
唐長壽元年(692)開鑿桂柳運河,溝通了漓江和柳江,打通了滇黔地區通往荊湖、嶺南的便捷通道。開寶四年(971),宋太祖“詔令嚴州、桂州據管界道路,接續修持,各置鋪驛”[52],著力建設桂州通往邕州的驛傳體系,而邕州通往大理的陸路,在北宋末期開始的馬綱貿易中,也逐步得到開發和完善。以桂林為起點,有三條主要干道通往外地。北路即湘桂走廊,這是廣南西路與北方中原地區和西部四川地區聯系的主要交通干道,同時也是與東部江南地區聯系的通道之一,北接荊湖,通往開封,“自荊渚至桂州,水遞鋪夫數千戶”[53]。東路以陸路為主,從桂林出發,經湖南、江西,可至南宋都城杭州,由原先的支線道路變成了東西交通的主干道之一。南路是從桂林南下梧州,沿西江至廣州及沿海地區的通道,這是一條可全程通水路的道路。梧州向東可與廣東驛道相接,不僅是陸路交通要道,更是水上交通樞紐。這三條主干道是廣西與東、南、西、北各地聯系的主要通道,被納入以首都為中心的全國交通網絡系統之中,同時也將中、西、南、東各大區域的中心城市聯系起來。
2.邕州至安南的通道
唐代以前,史書對于中越交通線路的走向記載過于粗略。唐代由邕州進入交趾的交通路線,大致仍依循伏波故道。東漢的馬援故道與隋朝劉方道、唐代明江道雖名為三道,實際上可能是同一路線不同時期的名稱[54]。隋仁壽二年(602),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朝廷令欽州刺史寧長真“以步騎萬余出越裳”,輔佐交州道行軍總管劉方前往討伐[55],劉方于是重開此路,置鎮守[56]。史書將此次征討交州的行軍路線稱為“劉方道”。唐貞觀十二年(638),清平公李弘節派遣欽州首領寧師京尋訪“劉方故道”,修復欽州通往瀼州(今上思西南部)到達交趾的道路[57]。從邕州沿馬援故道至瀼州,再到祿州(今越南諒山市東面辨強隘附近)、交州,可水陸并行[58]。開元十年(722),梅叔鸞反叛時,楊思勖以召募的“首領子弟”十萬,經由馬援故道征討安南[59]。
自從宋代越南獨立為國,廣西是中央王朝對外防御的前沿陣地,戰略地位陡然上升。《嶺外代答》記載了三條由廣西入越南的通道:一是“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機榔縣,過鳥皮、桃花二小江,至浦定江,亦名富良江,凡四日至其國都”;二是“自太平寨東南行,過丹特羅江,入其諒州,六日至其國都”;三是“自右江溫潤寨入其國”[60]。桂州經邕州通安南的大道貫通,成為廣西南北重要驛道干線。由桂州路北上長安,不僅是安南以及嶺南西部地區與中原地區聯系的重要交通干線,而且不少海外國家也由此北上長安進行朝貢貿易。
唐宋以來,中國對外交通的重心逐步由西北轉向東南,由陸路轉向海路,廣西的海路交通出現了新的變化,欽州對外交通的地位開始上升。邕州、欽州至安南的道路暢通后,欽州與廉州同為至安南的重要港口,舟楫往來不絕,是與安南貿易的海上交通線。
3.邕州至西南的通道
由邕州西出南詔的道路被稱為邕州道。貞觀十三年(639)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開道,經西趙(貴州遵義至都勻一帶),出邕州,以通交、桂”[61]。牂牁道溝通廣西與云、貴及至安南的交通要道。此外,一些重要的道路上均設有驛站,有利于官商往來,販運貨物。據《唐會要》記載,邕州至善闡府水路共47日程,再經11日程可到羊苴咩(今云南大理),但是對具體的路線卻缺乏記載[62]。宋代邕州至大理國的交通線,以橫山寨(今廣西田東祥周)為樞紐,并由唐代的一條干線發展為三條主線:一是由橫山寨經歸樂州(今廣西百色北)、泗城州(今廣西凌云西南)、自杞國(今貴州興義)至善闡府(今云南昆明)、大理;二是由橫山寨經富州(今云南富寧)、特磨道(今云南廣南)至大理;三是由橫山寨至羅殿國(今貴州普定、安順一帶)。上述三條道路均以邕州橫山寨為起點。
(二)唐宋時期的道路修護與管理
唐敬宗寶歷年間,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渤征調農民對靈渠進行了大修整,修筑鏵堤,置石陡門十八處[63]。懿宗咸通年間,魚孟威任桂州刺史,再次調集“五萬余工,費錢五百三十余萬”修治靈渠。[64]整治后的靈渠通航能力大為提高,成為廣西最主要的交通干道。既使漕運得到通航之便,又讓附近的農田獲灌溉之利。宋朝將交通路線的擴修整治納入地方行政管理的職責范圍內,如“嘉祐四年(1059),提刑李師中領河渠事重辟,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65],廢靈渠陡門三十六,以通舟楫。紹興二十九年(1159),地方官員看到靈渠自“兵興以來,縣道茍且,不加之意;吏部差注,亦不復系銜,渠日淺澀,不勝重載。乞令廣西轉運司措置修復,俾通漕運,仍俾兩邑令系銜兼管,務要修治”[66]。“令兩知縣系銜兼管靈渠,遇淤塞以時疏導,秩滿無闕,例減舉員”,管理更為完善。經過修整的靈渠“深不數尺,廣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內置斗門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門,則復閘之,俟水積而舟以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67],通航能力進一步提升。
北宋時,中央王朝鑒于邕州道的重要地位,對桂州至邕州段驛道進行建設。開寶四年,“知邕州范旻言本州至嚴州約三百五十里,是平穩徑直道路,已令起置鋪驛,其嚴州至桂州請修置鋪驛”,“詔令嚴州、桂州據管界道路,接續修持,各置鋪驛”[68]。太宗年間,廣西轉運使陳堯叟“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渴死”[69]。對廣西一些交通干線主要采取移民實道、兵民結合的辦法,鋪兵與居民相互依倚,鼓勵民眾配合地方交通行政機構進行養路護路。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漢唐以來交通布局不平衡及大部分線路通行條件惡劣的落后狀況,主要交通干線基本上暢行無阻。
(三)商貿及城市發展
唐宋時期,隨著交通體系的基本形成、農業手工業技術的進步和移民的進入,廣西商貿與城市有了一定的發展。唐宋兩朝的地方官員都重視農業生產,通過推廣牛耕、開荒屯田、興修水利、擴大農產品的品種等措施發展農業,如貞元年間,李去思任容州刺史時,曾“減塞卒四千余人”,以“便農墾田”“開置屯田五百余頃”[70];元和初(806),韋丹任容州刺史,教民耕織,種茶麥,在當地設“屯田二十四所”[71];景龍年間,王晙任桂州都督時,為了解決屯兵和百姓糧食供應不足問題,他開屯田數千頃。[72]南宋寶祐年間,李曾伯任廣西制置大使時,他向朝廷建議“許耕者復三年租,后兩年減其租之半”[73],以提高民眾墾荒積極性;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間,組織力量在城北打井,解決了當地居民的飲水及灌溉問題;[74]天寶年間,昭州(今廣西平樂)刺史敬超先在當地“鑿井得泉,郡人感其德,名為敬公井”[75]。宋朝廣西水利除建筑陂塘堰壩蓄水、運用竹筧引水灌溉之外,興安縣已經使用水翻筒車灌溉農田[76]。咸平年間廣西轉運使陳堯叟教人們鑿井取飲用水奏請允許廣西農民以種苧麻田畝之數準折種桑棗之樹,獲準實行。[77]極利于苧麻種植的發展。
唐代,廣西所產的“桂布”色白密實,穿著溫暖,暢銷市場;纻布的產量和技術都達到了較高水平。據《嶺外代答》記載:宋代“邕州左右江峒蠻,有織白緂,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以中都之紋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廣西觸處富有苧麻,觸處善織布,柳布、象布,商人貿遷而聞于四方者也。”靜江府古縣(今廣西永福)民間織布,結實耐穿,“以稻穰心燒灰煮布縷,而以滑石粉膏之,行梭滑而布以緊也”[78]。上貢物品除了制作精美的金銀銅器、丹砂、水銀外,還有纻布、蕉布、筒布、斑布、麻布、藤器等[79]。據考古發掘,廣西出土不少有較高工藝的唐代陶瓷器,如北部灣地區的青瓷窯,北流河下游西江左岸藤縣雅窯村就發現了晚唐至五代的窯址[80],釉下彩等唐代制瓷的新工藝也已傳到廣西。廣西發現四十多處宋代窯址,它們多設在河流旁邊、水路交通方便的地方。窯田嶺出土的花腔腰鼓印證了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所記載的富有地方特色的腰鼓。[81]據考古專家推測,至少到南宋時期,窯田嶺窯已燒造腰鼓供應市場。藤縣中和窯是以生產外銷瓷器為主的民間瓷窯。出土的遺物標明,當地在青白瓷燒造的生產經營和技術方面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82]
宋代北人南遷廣西激增,他們不僅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也增加了廣西的勞動力,促進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以及交通網絡的形成,為商業貿易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條件。宋代政治經濟重心南移,特別是南宋偏安江南,進一步加劇了對南方乃至嶺南地區經濟的依賴。廣西地區糧食的市場價格甚低,粵商借助水道運輸,將廣西的米運至廣東一帶出售,“田家自給之外,余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富商以下價糴之,而舳艫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83]。依托交通網絡,廣西匯聚了云南、貴州、安南等地特產,各地商人在廣西各城鎮進行物品交換,貿易興盛,促進了城市發展。
桂林是地處要沖的城市,官員從水路來嶺南各地以及北往嶺北各地都必經桂林。唐代李靖任桂州都督時,曾對桂林城進行較大規模的改造建設。到了宋代,作為廣西政治中心的桂林己是“崇墉復宇,顯敞壯麗,通衢之廣衍,阛阓之阜盛,稱其為一都會之府”[84]。靜江城內陽橋左右商賈云集,交易的商品中不乏寶物番貨,貿易額達到每日以千萬計。柳州是柳江沿線的重要港埠城市,唐代鑿通桂柳運河以后,水陸交通更加發達,形成以柳州為交易中心的地區圩市網絡。北流河縱貫容州,是通往合浦出海的古航道,當地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瓶、漆碟、藍料玻璃杯、盤發鏡等,可知其當年商貿的繁盛。欽州距離交州僅一日水程,“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欽,舟楫往來不絕也。博易場在城外江東驛。其以魚蚌來易斗米尺布者,謂之交趾疍。……所赍乃金銀、銅錢、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齒、犀角。吾之小商近販紙筆、米布之屬”。商業經濟貿易不只局限于鄰近地區的交往,還出現了大宗長途販運,“富商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85]。
廣西圩場在隋唐時期逐漸興起,“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謂之僚市”[86]。廣大農村地區出現不少定期圩市,市場上的商品也很豐富,除了農業、手工業、礦冶業的產品,土特產品在市場上的種類也較為繁多[87]。宋代出現不少商業城鎮,據統計,廣南西路共有58個商業鎮[88],就連邊遠的左右江地區也有圩市,如宜州城外的圩市,“百姓多隔日相聚,交易而退”[89]。各州縣設立稅務機關向商民收稅。桂南地區出現了橫山寨博易場、永平寨博易場和欽州博易場三個大型博易場,是當時西南地區的重要集鎮和與安南貿易的國際市鎮。南宋政府為了解決戰馬的供應問題,特地在邕州、宜州等地設置官市,用食鹽、錦等物品同大理、諸蕃交易馬匹。邕州馬市的規模比較大,紹興七年(1137),“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其后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絁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得馬千五百”[90]。馬市的交易帶動了其他商品貿易,邕州永平寨博易場“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銀、鹽、錢,與吾商易綾、錦、羅、布而去”[91]。一些位于水陸交通要道的城鎮,由單一的政治中心或軍事重鎮逐步發展為具有經濟功能,反映出廣西交通路線的社會功能已由軍事型轉化為經濟型,交通路線的經濟功能日益凸顯,對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影響極大。
三、元至清中期廣西交通體系的日益完善與商貿的逐步繁榮
元代以前,廣西的對外交通主要表現為中原出海過路通道型交通。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宣布政令,通報軍情急事”,運送軍用物資,元朝設置站赤(驛站)和急遞鋪,“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布,脈絡相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92]。各行省驛站相連,廣西的道路也接入全國交通網絡之中,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明清兩朝繼承元代驛站網絡體系和制度,廣西區域內驛道網絡穩步發展,并延伸至憑祥、龍州、寧明等邊疆地區,以欽州、邕州為主體、以驛道為依托的對外陸路交通網絡基本定型,與中原、云南、貴州經廣西出海的道路構成了廣西對外交通的境內干線。明代以驛道為依托的廣西對外陸路通道日漸清晰,區域內以水運和陸路為主,主要驛道與水路相互連接。
(一)修筑、改建道路,建成廣西驛道網絡
元至清代修筑或改建的道路較多,主要有:一是改建桂林官路盤石腳等路段。此處是南通桂林、北行湖湘的要沖。至元三十年(1293)冬,宦粵大使曹橫舟捐出水田101畝,“命工伐山首及兩旁之巨石,驅水涯填壘以為基,漸次加石,增砌而高,封以石塊”[93]。耗時大半年,改建成盤石官道,路幅拓寬至3.2米,成為通行車馬的坦途。二是改建蘭麻至理定路段。道光八年(1828),永福知縣林光棣募集資金4000余兩白銀,填石筑路修橋,修路約12千米,修建數十座木橋[94]。三是修建府江路。萬歷二十一年(1593),廣西巡撫陳大科籌劃,由桂林、平樂、梧州三府分段施工,歷時一年,改建石路約18千米,土路約24.3千米,改建和新建橋梁157座,置渡船18艘、路鋪19所[95],開通了從平樂沿府江經昭平至梧州的道路。雍正年間,昭平知縣錢兆灃捐俸開鑿接米嶺跨嶺道路上下四十里[96]。該道路在道光年間再次修建。四是開辟通往八寨的道路,修通賓州經三里至忻城的道路。五是康熙和乾隆年間,修建奉議州(今田陽那坡鎮)山口通往鎮安(今德保)的蓮花峺路。
元代廣西所轄各地站赤,形成以靖江(今桂林)為中心的驛道網絡,站赤的設置有陸站和水站。據統計,元代廣西共有驛站89 處,其中陸站42 處,水站47 處[97]。陸站集中分布在經濟較發達的桂北、桂中南地區,水站集中分布在漓江和西江流域。據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對《明會典》所載、未載及已革驛站的考證統計,明代廣西(包括時屬廣東的廉州府)共設驛館125處[98]。以邕州為起點,向北可達湖南湘潭,向西可抵云南中慶(今云南昆明),向南可至安南。元至元年間,廣西開通了通往云南的驛道,該驛道由邕州經武緣縣(今武鳴)、歸德州(今隆安)、奉議州(今田陽)、上隆州(今百色)、泗城州(今凌云)、利州(今田林)、路城州(今田林)進入云南后西行,有兩條道可通達中慶[99]。云南、貴州兩省同屬一個地理單元,明朝時貴州才正式建省。自古以來黔桂之間就有交通往來。明代黔桂通道主要有三條:一是紅水河水路;二是右江—郁江水路;三是龍江或都柳江—柳江—黔江—潯江—西江至廣東水路。陸路主要為右江——郁江道,從南寧府出發,經由田州橫山驛80 里至客莊驛,50里歸洛驛,120里往泗城州廛驛,120里城驛,120里安隆長官司,40里打饒寨,可行60里北樓村,50里過橫水江至板柏村,70里板屯土驛,60里洞灑村,20里安龍所,60里魯溝,即可達貴州。[100]主要沿著右江河谷而行,沿途多山嶺,路崎嶇,路窄草木密。
安南貢道由太平府屬憑祥州鎮南關入,貢道分布的地區,其交通發展也比較迅速。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軍自永平寨入安南(今越南),每30里立一寨,60里置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后又立堡,此路后來成為元朝與安南之間的官道[101]。明代邕州至安南有三條道:經邕州至崇左后分道入越,北道從龍州經平而、水口二關入越,中道由憑祥經鎮南關入越,南道自太平府思明府(今廣西寧明)經思陵州、祿平州入,三道會合于安南安越縣市橋江北岸,各路行程6-8日。[102]明政府為了加強對朝貢使者的管理,規定貢使入貢的貢道,要求安南貢道由廣西憑祥州入境,經龍州,順左江而下,到南寧,然后抵京。從邕州北上,分為兩條道:一道自南寧順江東進,經橫州(今廣西橫縣)、貴縣(今廣西貴港)、桂平、梧州至廣州,與廣東驛路相接,取道北江、湞水一線逾嶺北上;另一道經憑祥州陸行至寧明州后,登船沿左江、郁江水系舟行至梧州,溯桂江北上,經昭平、平樂、陽朔等地抵達桂林。陸路則由南寧經賓州(今廣西賓陽)、遷江(今廣西來賓)、柳州、洛容(今雒容)、蘭麻(今廣西永福西南)、蘇橋(今廣西永福東北)至桂林,與京師至廣西驛路相接,經湘桂走廊沿漓江——湘江水路至岳陽,或順長江東下,或走陸路經湖北、河南、直隸進京。[103]
廣西可經欽州、廉州的海路而達安南。明朝時期,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沿岸而行則需七日。從海東府經熟社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到達安陽海口后南行至塗山海口,這些海口均有支港進入安南[104]。永樂六年(1408)增設“交趾云屯(今越南海防)市舶提舉司”[105],用以接待西南諸國朝貢。從廉州至云屯鎮僅150千米,兩地商船來往不絕。
官府還加強對驛道的維護。廣西驛道多通往邊防要塞,軍事防御上的沖要之地也多是交通要道,明朝衛所的重要職責是“控制蠻夷,聲息援接,五屯以備藤峽,昭平以續江道”[106]。既要控制當地溪峒蠻夷、守衛邊疆,又要保護廣東、湖廣通往南寧一帶的交通[107]。清朝沿襲明制,根據道路的遠近及沖僻,選擇合適之地設置驛站,負責郵遞之事,并由各個州縣官吏及各驛站驛丞負責管理。各汛塘的主要任務則是防守驛道、護衛行人和稽查匪類[108]。
(二)修建橋梁,維修靈渠,疏浚河道
元明清時期的地方政府重視維護驛道干線,修筑橋梁,開辟碼頭,設置渡口,方便民眾、商旅往來,如正統四年(1439)“令各府、州、縣提調官,常巡視橋梁道路,隨時修理”[109]。據嘉慶《廣西通志》記載,廣西各地比較重要的橋梁有1007座,渡口340處,其中元代橋梁22座,明代168座,清代148座,修建年代不詳者638座[110]。
靈渠溝通南北,地位重要。明朝曾經六次維修靈渠,如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監察御史嚴震直發動民眾,“修廣西興安靈渠三十六陡,其渠可溉田萬頃,亦可通小舟”[111]。疏浚水渠5000余丈,筑渼潭及龍母祠土堤150余丈,又增高中江石堤改作滑石陡。凡陡磵之右礙舟行者,悉以火煅鑿去。清光緒十一年(1885)夏,興安發生水災,靈渠多處被沖壞,巡撫李秉衡下令桂林府同知和興安縣知縣踏勘修理,計修大小天平各口共需石4266丈,修鏵嘴堤和崩塌陡門共需石2986丈,計工匠材料共需銀9407兩8錢[112],歷時半年,整修過的靈渠“河流宣暢,旱潦無憂,桔槔聲聞,沃野千頃,舳艫銜屋,商旅歡呼”[113]。明清政府多次下令疏浚河道,提升通航能力。從粵桂北上以及從湖南南下的船只必須經漓江、府江航行,而府江兩岸深林密箐,水流湍急,險灘多,行旅艱難。明萬歷十六年(1588),廣西按察司副使韓紹召集商人砍伐樹木,開辟官路。此次疏浚工程,共“鑿石五千二百五十二丈,為橋梁四百七十有五,鋪亭一百三十有三,渡船十有三”[114],府江兩岸的交通狀況得到很大改善。萬歷三十六年(1608),廣西巡撫蔡應科會同兵備道翁汝進、平樂知府陳啟孫籌劃排除府江險灘,找到曾主持過疏辟思勤江的黃仲拙負責。黃仲拙為提高工效,創制了三角船、千斤飛撞、五龍爪和蜈蚣鏟等新型的開江劈石工具,歷時三年,削平了20個險灘,“自是舳艫絡繹,上下無大虞”[115]。廣西鹽和陶瓷主要通過北流江、南流江運輸,為了使運輸更便捷,郁林州民李友松上書請求開鑿兩江之間的運河,得到批準。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朝下令鑿通兩江運河,“通舟楫,以便行旅。仍乞蠲其所侵田稅及設石陡諸牐”[116]。《明英宗實錄》載:“廣西郁林州北流縣言:‘洪武末,設容山閘。其后水塞閘廢,至今四十余年,閘夫三十九人,統無所事,宜裁革為便’。從之。”[117]從中可知當年該運河運輸繁忙,雇用了大量閘夫,可惜僅使用了四十多年,就“水塞閘廢”。
雍正年間,清政府派鄂爾泰前往貴州平定苗疆,清政府“檄文武官弁通勘都柳江的上下”[118],疏浚都柳江河道,使得榕江、都江、車江(連接清水江)三江互相通航。都柳江航道疏通后,乾隆三年(1738),貴州巡撫張廣泗奏請疏浚貴州獨山州屬三腳屯達來牛、古州經廣西直達廣東的水路,得到朝廷的支持,“準修治自貴州省獨山州之三腳屯達來牛、古州,至廣西省懷遠縣通往廣東之河道,鑿開纖路,以資挽運而資商民”[119]。
(三)商貿的逐步繁榮
交通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南寧、桂林、柳州和梧州這四大廣西城市在明以前已經逐步形成和發展,到明代有了進一步發展。明朝對漓江、府江進行治理后,桂林府、平樂府的糧食源源不斷地經由水路通過梧州運往廣東,而食鹽則由此北上,至桂林府、平樂府各州縣乃至湖南。清康乾年間,形成桂林、梧州、南寧、柳州等一批區域性商品集散地,出現了行莊大鋪,如絲綢店、金銀樓、廣貨鋪、洋雜行、國藥局、錢莊、鹽行等。隨著大量廣東、湖南、福建、江西等地商人入桂經商,廣西城鄉商貿進一步發展,人口增加。據崇禎《梧州府志》記載,明代梧州城有10坊、3市、10多條街道。萬歷三十年梧州府城有6698戶、35300多人[120]。成化年間,僉都御史韓雍為了籌集軍餉,在梧州設立鹽廠,抽收鹽稅,梧州成為廣西食鹽集散地,據萬歷《廣西通志》記載:“惟梧為兩粵三江都會,其(榷商)利頗巨,歲可四萬計。……復設船頭、牙用、備用三款,歲不下六千。”[121]足見其商業繁盛。
桂林位于湘江、漓江交匯處,占據了區域內運輸網絡中最有利的位置。桂林城在洪武八年(1375)曾進行過大規模修建,擴展了南城,城區面積擴大將近五分之一[122],是全國33個大城市之一[123]。至清中葉,城區面積擴大到3平方千米以上,城內已有135條大街小巷,而城外的街巷則達54條[124]。“日仰于鄉農的城內外街巷居民多達2萬戶”,約10萬人[125]。據推算,明代桂林商業的營業總額應在54萬6840貫以上,加上紡織業的營業額,則合計80萬貫以上[126]。販鹽有利可圖,每年經由桂林運銷湘桂流域各地的生鹽不下二三百萬擔。乾隆年間,桂林僅東門橋一處征收的年雜稅就達5400多兩[127]。明代的南寧“人物繁庶,糧食便易,昔號小南京,猶然樂土”[128]。商貿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長推動了南寧城市市場的日趨繁榮。清中葉城區內街道的職業分工明顯,出現山貨街、鹽行街、棉花街、竹木街、打鐵街、布行街等多達55個市場街區。
明代至清中前期廣西圩市的數量不斷增加,如宣化縣由13個增加到40個,橫州由19 個增加到30個,博白縣由5個增至32個[129]。南寧城郊的亭子圩為邕江南岸重要的農副產品集散地,每逢圩期,周邊地區商民將谷米、生豬、生油、柴炭、山貨、黃糖等以及從左右江一帶趕來的牛只等販運到此交易[130]。梧州戎圩、平南大安、桂平江口成為當時廣西著名大市場,以糧食、土布、土紙、銅器、生油、煙葉、礦產品、生豬、家禽、雜貨為大宗,輸入以食鹽為主,出現鹽市、米市、豬市、牛市、布市等專業市場。
明清時期,廣西與越南之間的貿易活動一直沒有停止。明成化十四年(1478),“命禁安南國使臣多挾私貨……其國(指安南)朝貢使人多挾私貨營利”[131],為此明朝政府大為不滿。廣西“所屬思明、鎮安、龍州,與交趾接連。土民貪圖微利,潛從小路往來交易”[132]。乾隆九年(1744),清廷同意廣西從平而、由隘、水口三關出關同安南互市,并規定只準在太原牧馬、諒山駈驢附近地方交易[133]。桂越邊民進行貿易往來,以瓷器、鐵鍋、糖、茶葉、桂皮、牛皮、鹽、海味等為出口大宗,進口貨物主要是呢羽、香料以及大米等。
四、晚清至民國時期廣西現代化交通的起步與商貿的發展變化
晚清至民國時期,在繼續維護使用原有驛道的基礎上,廣西引入了輪船、汽車、鐵路、飛機等現代交通設施,對外交通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水運開始向近代化交通運輸過渡。盡管近代化的交通占比較小,但它開啟了廣西交通的近代化之門,商貿也有了相應的新變化。
(一)現代化交通的起步
1896年,廣西提督蘇元春在原來官道的基礎上重新修筑道路,建立了以龍州為中心,北經大新碩龍至靖西、那坡,龍州至寧明愛店、那犁,龍州至鎮南關、平而關、水口關,龍州至太平府、南寧府的軍事公路運輸網[134],開啟了廣西交通近代化的進程。這些公路可通馬車和轎車,一些支線直接通往邊防線上的各個據點、炮臺、關隘卡口。龍憑大路后來修筑那堪至鎮南關路段,可與越南同登—諒山的公路對接。1915年,陸榮廷在舊驛道基礎上修筑長53千米的邕武公路,這是廣西第一條現代化省道。
廣西的公路建設起步較晚,路況比其他省要差,所以在整個交通運輸中發揮的作用有限。1925年,鑒于當時百業凋敝、經濟落后的狀況,主政廣西的黃紹竑提出,首先從發展交通著手,以期有助于整個建設的發展[135]。1926年秋,廣西建設廳擬定了《全省修筑公路網》規劃,采用省辦與地方民辦相結合的方針,推進省內公路建設。省建設廳擬定出在全省修筑由湘桂邊界的黃沙河到梧州,龍州至梧州,南丹至欽州、北海,西林至懷集,三江到陸川的五大干線,貫通南寧、桂林、柳州、梧州幾大重鎮,初步構成了廣西近代公路網絡的雛形。1927年,廣西的建設經費總額為大洋590余萬元,其中“用于交通事業者,約占十分之七八”[136]。1930年,廣西公路通車里程已達4007 千米,居全國第8 位[137]。1937年縣道有7500千米,其中能通車3500千米,鄉村道15000千米,能通車的有1300多千米[138],初步構建起公路網絡骨架。公路運營里程由1931年的1105千米,增至1937年的2127千米[139]。新建溝通黔桂交通的重要干線——丹池公路。1936年,桂全路黃沙河至湖南邊界路段開通,實行兩省公路聯運,湘桂交通大為改善。自桂南戰役后,廣西成為西南國際通道必經之地,戰略地位重要,廣西著重整修、改善重要干道和新建溝通國際、省際間的公路,1944年增至4247千米[140],該年各縣市鄉村道路達36132千米,1945年為35233.7千米[141]。
水路是廣西的主要通道。在湘桂鐵路、黔桂鐵路通車運營前,水路一直是廣西對外包括溝通鄰省的主要通道。隨著清末北海、龍州、梧州、南寧相繼辟為通商口岸,外國的航運勢力紛紛涌入廣西沿海和內河。梧州是廣西、云南、貴州順江直下廣州出海的主要港口。1897年2月,英國迫使清政府將廣西梧州府辟為通商口岸。英國“輪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廣東至三水、梧州往來”[142],英商組建洋商怡和、省港澳輪船公司,太古洋行有限公司設一行,在梧州專理船務,每周往返梧州和廣州三次,亦有香港直航輪船[143]。由梧州東下西江,可通廣州及香港,溯桂、潯二江而上,可深入廣西腹地。于是廣西以西江為主干,以梧州為樞紐,發展現代輪船內河航運業。華輪與外輪展開激烈競爭,1908年在梧州商船總會的主持下,由梧州商人集資籌建“梧州西江航業股份公司”。1912—1934年,梧州先后興辦了20多家航運公司[144],與外商在西江航道上展開競爭。1906年南寧自開商埠后,航運業得到迅速發展。南寧航商先后成立了20家航業公司,擁有輪船70余艘,航行于西江、左江、右江各線。民國期間,北海有8條定期或不定期的輪船航線,可到達廣州、香港、海口、海防、新加坡、仰光、臺北、上海、大阪、海參崴等[145],成為重要海運基地和對外貿易口岸。這一時期輪船運輸與帆船運輸互補發展。
清政府于1896年允許法國將越南同登鐵路修至龍州,但堅持鎮南關至龍州一段“由中國自行建造”[146],同時派人勘測龍州至同登的山河、橋梁、官地、民地情況并制圖說明,但這條鐵路僅修成部分路基,1900年7月便停工。張鳴岐從廣西邊防總體戰略部署出發,提出以南寧為樞紐,以桂邕鐵路為基礎,建設由南寧通達北海、梧州、湖南、云南的廣西鐵路網[147]。1907年,清政府同意工部主事梁廷棟提出的修筑鐵路規劃,著手勘測修建滇桂鐵路,可惜這條鐵路因技術和經費等原因停辦[148]。1937年,廣西修建湘桂、黔桂鐵路。湘桂鐵路自湖南衡陽至廣西憑祥,廣西段干線長821千米,1938年10月投入營運,營運里程僅440千米;黔桂線廣西段通車207.8千米[149]。湘桂、黔桂鐵路在戰時調動兵力、運輸物資、轉移難民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抗戰及整個廣西經濟的發展意義深遠。
20世紀30年代初期,為了適應民用航空業發展和戰時航空運輸的需要,廣西省政府征調數十萬民工在柳州、桂林、邕寧、梧州、龍州、百色、都安等地新建、擴建了一批機場。1933年6月,兩廣合辦西南航空公司,購買4架飛機[150]。1934年10月開通了廣州至龍州的廣龍線,1936年開辟廣州至河內的廣河線,并把廣龍線改為廣州至南寧的廣邕線。這些航線均飛經南寧,因為主要承擔軍事交通功能,經濟價值不大。此后經行廣西省內的民用航空線主要由中國和歐亞兩個航空公司共同經營,開辟了滇、渝、桂、港航線,1938年、1944年因廣州失陷和桂林、柳州失守而先后停航。
(二)現代商貿與城鎮的發展
近代交通的建設對商業貿易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輪船、公路、鐵路為對外貿易提供了新的運輸路線,推動了城鎮的發展。大批外地商人進入廣西各地,從事米、糖、茶、絲、洋貨等商品的收購、運輸、銷售活動,廣西商業貿易愈加繁榮。梧州是廣西乃至西南諸省的水路出口,也是廣西最大的貿易集散地,“商業之盛,實為全桂之冠”。1937年,在全國十大商埠中,梧州港進口貨值排第9位,出口貨值排第7位[151]。北海與南洋、越南和廣東沿海以及香港的貿易發展起來,是中越海上貿易在北部灣地區的中心口岸。1877—1911年,北海口岸進出口總值9780.40萬關平兩,其中進口總值6750.59萬關平兩,出口總值3029.81萬關平兩[152]。城市化進程加快,至光緒中葉,北海已有5條街道,港口市鎮已初具規模[153]。柳州自民國二十九年湘桂鐵路延伸到柳州以后,這個廣西腹地的集散市場,己經披上了現代化都市的外衣,而商業漸漸呈現出繁榮的面貌[154]。全州在湘桂公路、湘桂鐵路相繼開通后,商品流通日漸增多,市面也日漸繁榮,據統計,1932年全州有大小商店355家[155],幾年后便增至500余家[156]。
清末民初,廣西的邊境城鎮也得到了發展。憑祥隘口“每逢圩期,均有馬車十余架來往運輸貨物,資本達三千元的商店有四五家”[157]。龍鎮公路修通后,商販更是絡繹不絕,隘口圩因路而繁榮,圩市的繁榮又推動了憑祥的城鎮建設。另一座邊境城市龍州自從被開辟為商埠后,外國商品源源不斷地從水口、平而和左江運抵龍州,成為廣西最早步入近代化的邊貿重鎮。清宣統以后,龍州商賈擁有20 余艘輪船,航行于各地[158]。廣西省內以及湖南等省桐油、茴油、茶油等貨物,都通過湘桂鐵路再轉公路由龍州出口。1934—1941年,由于大批沿海企業遷入廣西,進口的物資以及由于國際市場對于礦石等原材料的需求上升,對廣西外貿產生很大的影響。借助現代交通,廣西進入歷史上外貿發展最好的時期,廣西組織大量桐油、家禽等農產品出口,這期間進口51361萬元,出口55592萬元,第一次出超4231萬元[159]。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高速發展的廣西交通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于地處援越抗法前線,為了及時運送軍需物資,廣西將交通建設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1950年,廣西公路里程僅有3622千米。1990年,廣西公路總里程達到36214千米,橋梁達到5492座,總長167032米[160]。2014年,自治區政府部署實施縣縣通高速公路建設,交通建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2018年11月,自治區政府制定了《廣西高速公路網規劃(2018—2030年)》,圍繞南寧、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區、環縣城經濟帶、周邊地市環線的多層次高速公路環線,形成橫貫東西、縱穿南北,覆蓋全區、連接“三南”,溝通泛珠三角等多區域和東盟國家的高速公路網絡。到2018年底,廣西公路里程達12.54萬千米,其中高速公路5563千米,縣縣通高速率達91%,農村公路突破10萬千米[161]。基本形成以出省出海出邊高速公路為主骨架、市縣二級公路為干線,水陸聯運、城鄉連接、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西對鐵路進行了大規模建設。1950—1998年,廣西鐵路投資達131.02億元。至1998年末,國有鐵路延展長度為4119.9千米,其中廣西境內2012.6千米,新建的地方鐵路、鐵路支線及專用線共1050.671千米[162]。在新建的干線中,相繼建成了與越南鐵路接軌的湘桂鐵路來鎮段,通往中原的焦柳鐵路,聯通大西南的黔桂鐵路都桂、都貴段和南昆鐵路,通往南海和北部灣港口城市的黎湛鐵路、南防鐵路和欽北鐵路。以柳州、南寧為中心的廣西鐵路網絡,成為加強廣西與中原、西南地區以及中越聯系的路網骨架。廣西鐵路在全國路網中的地位、格局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997年,南昆鐵路建成通車運營,構成中國西南地區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和南方東西向運輸大干線,發揮了貫通大西南、連接海南、通往東南亞的大通道作用。截至2018年,全區鐵路營運里程5202千米,其中高鐵線路7條,營運里程1771千米[163]。
廣西民航在全國各省區中起步較早,1952年,昆明—南寧—廣州航線開通。1956年,廣州—南寧—河內航線開通,拉開了拓展國際航空大通道的序幕。1958年,開通南寧—梧州區內航線。2014年,南寧吳圩國際機場T2航站樓正式啟用。截至2019年,廣西通航線路320條,可通航國內外110個城市。民航機場由1978年的2個增至7個,成為中南地區民航運輸機場最多的省區之一。
建設現代化的港口和開辟通往港口的交通線,是建設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的重要基礎。196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將防城建設成為運輸援越戰備物資的起運港口,開通中越隱蔽的海上運輸線,為廣西的港口建設帶來了契機。1973年4月,自治區黨委成立防城港建港領導小組,決定由地方財政開支搞港口建設。1975年2月,國務院同意廣西壯族自治區提出的建設南寧至防城港的鐵路,還同意在防城港已建兩個萬噸級深水泊位的基礎上,再建五個萬噸級以上的深水泊位和相應的配套設施。一年后,廣西第一個萬噸級深水泊位順利建成。近年來,廣西加快推進北部灣港口的基礎設施建設。2019年9月底,北部灣港擁有生產性泊位82個,萬噸級以上泊位64個,20萬噸級以上泊位2個,最大可靠泊20萬噸級散貨船和10萬噸級集裝箱船;擁有3條鐵路專用線,共48條裝卸線,到發能力近4000車/日,集裝箱裝卸能力4300標箱/日,是全國鐵路布局最完善的港口之一[164]。2014年7月,《珠江—西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批復,覆蓋人口超過5000萬的珠江—西江經濟帶上升為國家戰略。作為西江黃金水道建設的咽喉工程,位于西江梧州段的長洲水利樞紐三四線船閘已經建成。
縱觀廣西交通發展史,可以看到交通在廣西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交通線路的興衰,影響到廣西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形成和轉移,以及與鄰國的交往。隨著中國與東盟貿易往來的不斷深入和擴大,廣西逐漸在對外貿易、對外文化交流與人員往來中展現其自身價值。廣西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有機結合點,對發展我國邊境貿易、擴大國際經貿交流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與周邊高速公路網銜接,形成中南、西南地區連接粵港澳大灣區和東盟地區出省出海出邊干支結合的高速公路網絡,正在從曾經的國家交通的“神經末梢”發展成面向東盟、連接多區域的“國際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