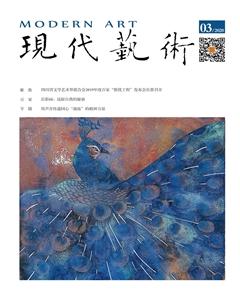對“詩言志”的再認識
這些抗疫詩,摒棄了華麗的辭藻,正視現實災難,“我手寫吾口”,直抒胸臆,在“文以載道”中鼓舞了瀘州人的抗疫意志,堅定了抗疫必勝的信心,是中國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詩言志”最美的傳承和發展。
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從武漢、從湖北蔓延至大江南北,危及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時,面對嚴重的疫情,瀘州市廣大文藝工作者走出“象之塔”,滿懷激情,創作出許多感人的抗疫文藝作品,如歌曲、金錢板、微電影、小型話劇、書法、繪畫、攝影、舞蹈等,以表達自己的心聲。在眾多抗疫文藝作品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井噴似的詩歌作品,它讓我看到了一個滿血復活的文學現象。
這種復活就是中國詩歌在一種特定的現實場景即歷史需要它的緊迫時刻重新認識了自己,回到了它本真的軌跡和固有的傳統。中國詩學傳承至今,有一條清晰鮮明的現實主義美學路線和審美創作原則,即:“詩言志。”“《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所以載道也。”之所以看重它,尊重它,在于當今的詩歌曾因形式主義和庸俗、低俗、媚俗之風泛濫,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它,讓我們實實在在地久違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的詩歌了。
毋庸諱言,一開始,當瀘州抗疫詩攜著激蕩的抗疫情懷潮水一般澎湃而來時,其表達的抗疫思想、人間真情令我們震撼。但是嚴格來看,有的“詩”并非是詩,主要是缺乏藝術的表現方式,沒有形象思維,但我們仍然喜歡它,包容它,因為它表達了一種精神,瀘州人在災難面前的一種家國情懷,是一種我們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聲音,愛在人間讓愛永遠的聲音,是中國“詩言志”精神在災難降臨時的直抒與弘揚。
令人欣慰的是,瀘州抗疫詩并不缺乏既有思想性又有藝術性和欣賞性的好詩。這些詩歌,“思與境偕”,蘊含意境,藝術地表達了我們抗擊疫情的共同心聲,讓我們感同身受之時,也給予我們或婉轉或壯麗的審美享受。
疫情來勢洶洶,一時間湖北武漢成為萬眾矚目之也。關心武漢,支援武漢,瀘州詩人以真誠而急切的詩行表達著自己的愛心。李曉梅被武漢的疫情牽動著,以焦慮沉痛的心情寫下:“九省通衢的武漢/成了病毒肆虐的焦點”“昏暗的天光下,蒸騰著毒霧/瀲滟的波浪中,蕩漾著惆悵/空蕩蕩的街市,回響著凄涼/冷冷的綠草里,漫生著哀傷”(《春天·病毒·考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全國人民都把溫暖的手伸向武漢,把春天帶到武漢:“全國,全民族/心,向武漢/發出同一個聲音/武漢,我們來了”(彭懷明《眾志成城,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豬鼠交接的冬春讓人心寒/紅梅吐艷卻沒有山花爛漫/武漢的疫情如洪流蔓延/中國又面臨嚴峻的挑戰/誰能向前,誰能擔當/誰能成為打贏這場戰爭的脊梁/專家學者,醫生護士,人民子弟1都向武漢出發”(龍啟權《向武漢出發》)簡潔、質樸、溫馨的語言,讓人看到了希望,增強了戰勝病魔的勇氣和信心。
在抗疫第一線,奔忙著人民子弟兵、科技工作者、白衣戰士,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日以繼夜,為的是打贏這場防疫阻擊戰。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抗疫戰中,他們被廣大人民群眾親切地譽為“最可愛的人”。
瀘州詩歌作者同全國人民一樣,深情的目光緊緊地注視著這群“可愛的人”。公安民警趙卓在堅守崗位之際,創作了朗誦詩《對不起,我有必須去的原因——謹以此詩獻給那些連續奮戰的醫生和警察》:“媽寶貝,對不起,/這次任務很緊急。/疫情形勢十分嚴峻,/這關系著每個人的生命。/一線需要我們,/我們必須去。/因為,我是醫生,/因為,我是警察。/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黨員,必須沖在最前面。”錚錚誓言,樸素地表達了一個基層民警的心聲。
抗擊疫情,離不開科技工作者,他們深入第一線,采集病毒樣本,研究實驗,把脈疫情,科學決策,開出治理處方,控制病毒蔓延,為打贏這場防疫戰,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詩人們感動著,懷著崇敬的心情,為他們的科學精神致敬點贊。特別是84歲高齡的鐘南山院士:“揮揮手逆行而去/背影是如此堅毅/穿梭在死神之間/用生命搏擊瘟疫/仰望穿梭的背影/叫不出你的名字/你就是南山勁松/把民族脊梁挺起”(易國璋《背影》。正因為有鐘南山一樣的科技工作者的奮力逆行,我們在抗擊疫情中才充滿了底氣,如此的自信和高效。
我們忘不了奮斗在戰疫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可親可敬的白衣戰士們晝夜不息地穿梭在病房,精心治療,細心呵護,用精湛的醫療技術托起臨危的病人,攙扶起一個個即將倒下的生命:“這些日子我總在凌晨醒來/在前線與新型肺炎拼命的白衣衛土/那臉上的一道道深深的勒痕/那被汗水泡白泡皺的手/那流淚揮別親人的臉/那蜷縮在地上的睡姿/那同行好友病危而只能低頭閉目/用手指扼住眼淚的姿式/一直在我身體里,往來穿梭1激蕩著我良知的血液”(商西恒《這些日子我總在凌晨醒來》)細致人微的描寫,真實動人的形象,讓我們對白衣戰士升起無限的敬畏。有的醫務工作者,既參與一線的醫療工作,又以筆為矛,以詩為刃,抗擊疫魔,祝焱即是如此。作者在《手機里的笑臉》一詩中,以女兒的口吻向病中的父親告別,寫得情真意,催人淚下:“如果,不是抗戰肺炎/我想,我會陪在您身邊/幫您捶捶背揉揉肩/把孩兒的愛/溫暖您的房間/也會做上幾道您喜歡的菜肴/再和您聊聊春晚//武漢告急/抗擊肺炎在召喚/眼前浮現出醫者的感人誓言/收起糾結的內心/將信,悄悄地/藏在您的枕下面/堅定地走出家園1”。但是還未等到她歸來,父親卻悄然地走了。“看著手機里您的笑臉/我淚流滿面,爸——/為何不信守/等我歸來的諾言?/何時還能見您一面?”
此次的抗疫是全方位的,,上到中央,下至社區,全民動員,全體參與,男女老少,一個不拉。倘若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無論街頭巷尾,還是小區角落,總有一個個忙碌的橘黃色身影——環衛工人,他們低俯著身軀看不清面龐,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但他們的精神卻是那樣的偉大。李定林以獨特的視角,發現了城市中這道特殊的風景線,速寫似的,創作了《那一抹橘黃》,盛贊環衛工人:“在這個城市/大街小巷/時時刻刻/晃動著橘黃的身影/一會兒彎腰/一會兒下蹲/一會兒揮動掃帚/寒風來了,迎著/太陽高照,著/塵埃飛起,罩著/病毒飛沫,滅殺/一個個猶如城市的衛士”。
為了抗擊病毒,防止病毒傳播,家家戶戶都被分片似的隔離,大家都自覺地宅在家里。這是個特別的時刻,苦悶、焦灼、恐慌……無端地升起,彌漫在空氣中。然而,陳宗華卻不同,對隔離抱以樂觀的情緒:“武漢有一群詩人正在閉關/我也在瀘州閉關/但不是詩人//窗外仍然下著雨/我看我的肺/像呼吸著的兩片嫩葉”(《窗外有雨》)這樣的詩,無疑能幫助那些消極惶恐者走出失望的陰影,增強戰勝病魔的信心。面對隔離,程琴則從大局出發,表達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人生境界:“今夜,我住進了隔離所!/但是我們一點也不寂寞!/多少普通民眾自發隔離,暫別傳統的年俗!/多少城鄉干部不顧安危,安撫民間的慌亂!/多少城鎮自封交通,壯士斷腕!/華夏兒女眾志成城,早日重現清新家園!”(《今夜,我住進了隔離所》)表達的,不啻是程琴個人,也是面對災難,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高尚品格和美好愿景。
當病毒突然而至的危情時刻,瀘州人同全國人民一樣,相信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同舟共濟,萬眾一心,定會戰勝疫情,對我們的民族和未來充滿了希望。瀘州詩人們積極反思,憧憬著陽光燦爛的時刻,熱情向往和平安寧的生活:“值班路上看見九獅大道兩邊的油菜花/露出了鵝黃的茸/昭示的是一份新鮮的期冀/惟愿春天早來/疫情遏/山河無恙/朝天闕”(汀《元宵記》)“等疫情過后,/我要去登龍透關,/去緬懷戰時的烽煙,/去找尋英雄的足跡,/去懷想一些驚天動地的片段,/去重溫那些平凡的人,/演繹出的不平凡故事。”(孫孝蓮《等疫情過后》)我們堅信,只要我們患難與共,共克時艱,春暖花開的這一天一定很快會到來。
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是一場可怕的災難,威脅著所有人的生命,在災難面前,猶如兩軍相遇,唯有勇者勝。瀘州詩人,在殘酷的災難面前,沒有悲傷逃避,而是勇敢前行,大無畏地向疫情全方位出擊。初步統計,截止目前瀘州的廣播電視、微博、自媒體、微信公眾號等媒體平臺已發表上千首抗疫詩。這些抗疫詩,摒棄了華麗的辭藻,正視現實災難,“我手寫吾口”,直抒胸臆,在“文以載道”中鼓舞了瀘州人的抗疫意志,堅定了抗疫必勝的信心,是中國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詩言志”最美的傳承和發展。見微知著,通過瀘州,我們再看全川、全國,抗疫詩可謂數不勝數,猶如浩瀚的大海,那樣宏偉壯觀,激情澎湃,而這充滿時代精神深深扎根于人民生活的詩的海洋,足以淹沒那些以專寫“下半身”等為榮的陰暗潮濕的詩人,不僅如此,它對安慰和鼓舞民心起到巨大作用。抗疫詩表達了國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彰顯了崇高的時代精神,一定會傳承下去,成為歷史永久的記憶。
王應槐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瀘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曾主編《審美大辭典,教育科學審美》,參加過《閱讀辭典》等10多部書的編寫。著有文學評論集《文學的真諦》、文學評論專著《張中信創作論》和美學文集《走進美學》《美學風景》等,作品被收入多種選本,曾獲四川文藝理論獎等多種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