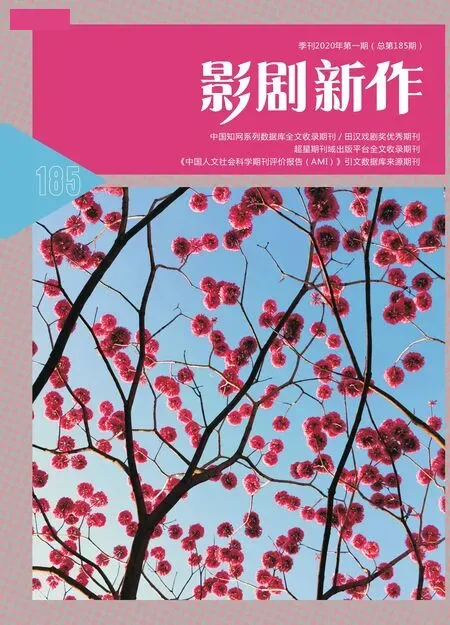淺論喜劇語言的修辭方法
張文慧
喜劇劇作家在進行喜劇創作時會有一定的動機,或是試圖傳達自己的喜劇意識,或是想要逗人發笑等等,正是在這諸多的心理動機和社會動機的合力驅使下,喜劇語言作為喜劇創作的重要工具承擔著一定的功能。
喜劇語言的首要任務是逗笑,而喜劇語言又是喜劇人物的直觀外化,劇作家在創作時既有傾向的對象,那么喜劇語言也將被劇作家當作勸誡的工具來使用,使喜劇人物在喜劇沖突中能攻擊對方,以及解脫自我。
一、喜劇語言逗笑中的修辭
(一)喜劇語言逗笑的兩方面
“喜劇來自笑,笑來自言詞表現和事物內容。”[1]喜劇語言的首要任務是逗人發笑,而這種逗笑則分為兩個方面,即喜劇語言表達的逗笑以及喜劇語言本身的逗笑。
喜劇語言表達的逗笑所指為語言表達的內容是滑稽可笑的,即事物內容可笑。這些內容有時是純粹的逗笑,有時也代表著劇作家的某種思想意識。例如《費加羅的婚禮》中,
1.瑪絲琳:……我認為干的最壞的事,就是長久以來,他對我的那份討厭的愛情。
霸爾多洛:換了我,早就擺脫了他的追求。
瑪絲琳:有什么好法兒?
霸爾多洛:嫁給他呀。[2](P399)
2.費加羅:……我天生就是當官的料。
蘇珊娜:據說干那行特別難!
費加羅:收錢,拿錢,要錢,這三句話就是當官的秘訣。[2](P420)
以上兩例的語言平淡無奇,但是所表之意卻會令人忍俊不禁。例1中,霸爾多洛建議瑪絲琳擺脫巴吉勒的“好法兒”竟是嫁給他,這種與慣常思維的不一致必然制造出笑料來,同時也表明了霸爾多洛對瑪絲琳的拒絕。例2中費加羅對當官以及政治別出心裁的解讀一方面使人產生同笑,一方面也寓意著劇作家對當時政治官場腐敗虛偽的諷刺。
喜劇語言本身的逗笑是劇作者運用一定的技巧手法使得喜劇語言本身聽來可笑,即言語表現可笑。例如喜劇小品《英雄母親的一天》中:
趙大娘:孩子啊,聽話,奶奶給你講故事。
導 演: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馬光砸缸。
趙大娘: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馬缸砸缸。
導 演:司馬光砸缸。
趙大娘:司馬缸砸缸。
導 演:司馬光砸缸。
趙大娘:司馬光砸光。
趙大娘將“司馬光砸缸”誤讀為“司馬缸砸缸”及“司馬光砸光”,語言本身就取得了逗笑的效果。
又如,喜劇小品《今天的幸福》中:
郝建:等會兒,剛才說我什么,說我長得像個人,但從來不干人事兒,你告訴我,我怎么長得像人,你憑什么說我長得像人?
郝建情急之下的言語邏輯失誤便構成了喜劇語言本身的好笑。在這類逗笑呈現中,喜劇語言常常純粹是為了逗樂。
(二)喜劇語言逗笑中常見的修辭手法
喜劇語言的逗笑性無論是集中在表達內容上還是語言本身都常常運用豐富的修辭手法來制造笑料,這些修辭手法在此即是指修辭格的運用,它們是最直接最簡易的逗樂手段,效果極佳。自古以來,眾多喜劇理論研究者都深入研究了喜劇語言的修辭手法。古希臘時期的《喜劇論綱》中談到:“笑來自言詞,即通過同音異義字、同義字、嘮叨話、變形字、指小詞、變義字(由讀音或這類的辦法造成)、言詞的形式”來達到逗樂效果。此后,一些喜劇理論研究者也歸納出許多喜劇語言修辭手法,盡管喜劇創作主體們慣用的修辭手法各不相同,但其中歸納起來常見的有夸張、比喻、雙關、曲解、仿擬,在喜劇作品中發揮出無盡魅力。
1.夸張
夸張是指故意言過其實,對客觀的人、事物作擴大、縮小、超前的描述的辭格。在喜劇語言中,事物本身與夸張的修辭將形成不協調的狀態,逗人發笑。同時,夸張的運用可以突出事物的本質特征,將不合理變成為合理,也將作者對事物的鮮明感情態度表達得更為準確,從而引起觀眾的強烈共鳴,增強逗樂效果。而愛好夸張的心理傾向亦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夸張的運用亦更能滿足觀眾的需求。例如:
(1)白云:我年輕的時候那絕對不是吹,柳葉彎眉櫻桃口,誰見了我都樂意瞅。俺們隔壁那吳老二,瞅我一眼就渾身發抖。(《昨天 今天 明天》)
(2)白云:還有一個是院長,拉著我手就不松開,那家伙可勁搖啊:“大姐啊,大哥這一嗓子太忽然了,受不了哇,快讓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錢,他唱歌要命啊。”(《小崔說事》)
例(1)中的“看我一眼就渾身發抖”,白云運用夸張來形容自己當年的美貌,大有言過其實之意,令觀眾不禁覺得夸張可笑;例(2)中,白云為了表現黑土唱歌難聽,故意夸張其唱歌要命,而“要錢”與“要命”的對比恰恰又增強了喜劇效果。
2.比喻
比喻就是打比方,是用本質不同卻有相似之處的事物描寫或說明事物的辭格,它一般能收到具體、鮮明、形象、生動的語言效果,化常言為妙語。但喜劇語言中的比喻手法與一般的比喻差別很大。一般比喻中本體與喻體常常恰當貼切,但喜劇語言中兩者間則有變異放大或是不協調不一致的成分。這在喜劇作品中比比皆是。例如:
(1)白云:你咋不實話實說呢。你讓大伙瞅瞅你那老臉,長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追你啊?
黑土:這么不會審美呢。
白云:怎么地?
黑土:這叫鞋拔子臉哪?這是正宗的豬腰子臉!(《昨天 今天 明天》)
(2)老大爺:(打電話)老王大哥,我,小陀螺,你們的千手觀音還缺人嗎?……如果信任我的話把我放在第一個也行。
老太: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老大爺:那你們的高蹺隊還缺人嗎?……那多高啊?兩米四呀?
老太:那不竹竿上插一土豆嗎?(《想跳就跳》)
例(1)中白云用鞋拔子比作黑土的臉,以顯出自己被追求。而黑土卻根據自我形象特點故意降低準則將豬腰子的輪廓與自我聯系在一起,形象卻又有些不協調,著實令人捧腹;例(2)中毒舌老太以“千手蜈蚣”“竹竿上插一土豆”來作形容,畫面感十足,所傳達出的不一致以及觀眾對老大爺個矮的共鳴,笑料由此而生。
3.雙關
雙關是利用語音或語義的條件,有意使語句同時關顧表里和內里兩種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辭格。它使表面之意與暗含之意組成不協調的重合交叉,從而產生曲解或引申,引人發笑。例如:
(1)白云: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來到你門前,請你睜開眼,看我多可憐。今天的你我怎樣重復昨天的故事,我這張舊船票還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主持人:大叔啊,后來么樣了?
黑土:濤聲依舊了。(《昨天 今天 明天》)
(2)老太:你倆干嘛呢?這是我的地盤!
男龍套:我礙你啥事兒了?我今天就礙你了!我礙(愛)你!我礙(愛)你!我礙(愛)你!
老太:聽見了吧姑娘?
女龍套:你口味真重!(《想跳就跳》)
例(1)中“濤聲依舊”本是一首歌的歌名,在此卻暗含兩位老人在一段風波之后重歸于好。歌詞“我這張舊船票還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與歌名表里呼應,暗含請求原諒,重修舊好的訊息,含蓄幽默,令人捧腹,回味無窮;例(2)中男龍套本正在與老太發生沖突,有意妨“礙”老太,卻被誤解為“愛”老太,最終被女友認為口味重,引人發笑。
4.曲解
所謂曲解,就是指對某些詞語或句子有意進行歪曲解釋的辭格。所釋之意與本意的不一致,打破了人們的慣用思維,容易制造笑料。例如:
(1)白云:他就是主動和我接近,沒事兒和我嘮嗑,不是給我割草就是給我朗誦詩歌,還總找機會向我暗送秋波呢!……
黑土:……秋波是啥玩意?
白云:秋波是啥玩意你咋都不懂呢?這么沒文化。
黑土:啥呀?
白云: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昨天今天 明天》)
(2)白云:恩,然后再整整容,做個拉皮兒。
黑土:我拍個黃瓜。(《昨天 今天 明天》)
例(1)中白云嘲諷黑土沒文化,讓觀眾誤以為她懂得其意。當她曲解“秋波”為“秋天的菠菜”時,詞語與解釋的不一致以及她營造的自我博學與實際情況的不一致,驟然制造出十足的笑料;例(2)中黑土將美容名詞“拉皮兒”曲解為一種食物,所以接出了與“拉皮兒”全然無關的“拍個黃瓜”,出人意料,引人發笑。
以上四種即是在喜劇中較為常見的修辭格手法,它們的運用使得喜劇語言本身及表達更為生動,暗含之意浮于言表,逗笑效果極佳。當然,此外還有對比、仿擬等多種修辭,在此將不予贅述。
二、喜劇語言中的攻擊與修辭
喜劇語言單純為了逗笑而運用修辭技巧如同玩弄語言游戲一般,它服務于一種智力興趣且其中包含的思想看似是無傾向性的。但當這種逗笑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即并非單獨服務于產生快樂時,它便同時服務于其他目的。其中,喜劇語言中的攻擊便是目的之一,即攻擊性目的。
弗洛伊德認為,人作為動物種類之一是具有攻擊本能的。從兒童時代起,人們天生就有一種強烈的敵意性情,常常通過謾罵或斗毆的方式來宣泄解決。但隨著社會的文明發展,人們被要求不能謾罵他人或是攻擊他人。如此,人的本能表達在正常途徑上常常遭遇來自文明之下的冷漠的第三方的阻礙。因而,人們在謾罵上做了創新,發現一種新的技巧,即旨在將第三方爭取到自己這邊一同對付敵人的技巧。攻擊者運用詼諧的喜劇語言進行攻擊,貶低、鄙視或使敵人顯得低劣,通過間接的形式享受征服敵人的樂趣,而對于第三方而言,他們則毫不費力地獲得了極大樂趣。于是,攻擊者通過笑聲來賄賂第三方,使最初介入的他們成為了同盟。
如此,喜劇人物利用喜劇語言的逗笑即詼諧來勸說第三方即觀眾,使他們站在自己一方。詼諧允許攻擊者說出那些敵人不允許的有意識的滑稽可笑的東西,它得以使攻擊者逃避開種種限制,把原本可能存在的批評趕出視線之外,并制造著無盡的快樂。同時,它以其所產生的快樂賄賂聽者,把開始時并不關心的聽者變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嘲笑者,在原來只有一個反對者的情況下創造出一群反對者,使其不需要進一步觀察而站在攻擊者一方。總之,這種傾向性詼諧成功地使笑者轉變到攻擊者一邊來,使笑者從最初可能的嘲笑轉變為了同笑。
下面以喜劇小品《想跳就跳》為例,喜劇語言中有著大量攻擊話語,以“毒舌老太”的典型形象而備受觀眾青睞。究其原因,正是傾向性詼諧使得老太通過制造笑聲使觀眾轉變到自己一方。如:
老 太:總算能清靜了!唉呀!(矮個跳舞的老大爺出場)
老 太:那小孩兒!
老大爺:管誰叫小孩兒呢?我是成年人!
老 太:成年人的災難呀!你在這兒干嘛?
老大爺:我在這兒練國標呀!
老 太:國標?我看你像鼠標!我這個人呀,喜歡清靜……
老大爺:咱們素不相識,你就跟我親近親近呀?
老 太:親近!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縮的,你心還是猥瑣的!(《想跳就跳》)
在此,因場地之爭,“毒舌老太”與剛剛到來、素不相識的老大爺產生了沖突,她抓住對方個頭矮的特點展開了攻擊。“小孩兒”“成年人的災難”“鼠標”“人是微縮的,心還是猥瑣的”一系列喜劇語言令人忍俊不禁,她也正是利用詼諧的幫助,保證它們為觀眾所接受,而非被觀眾以非詼諧的形式所發現其背后所含有的惡意。其中,“人是微縮的,心還是猥瑣的”作為對老大爺個頭強力的攻擊,可能是給觀眾印象最為深刻的。這個詼諧使觀眾大笑,并把觀眾的興趣從這樣做是否對這位無任何過錯的老大爺太不公平這個問題上完全轉移開。同時,詼諧又使觀眾嘲笑老大爺本身。老大爺被作為“微縮的”形象介紹給觀眾,觀眾嘲笑的對象也正是老大爺的個頭。受過教育的人或許早已改掉了取笑他人生理缺陷的習慣,況且也并不把個子矮看成是可笑的生理缺陷。但不可否認,當老大爺的形象被詼諧的語言形容時是真實的,也變得滑稽可笑了。如此,“毒舌老太”用詼諧的方式讓自己免于被批評厭惡,同時將觀眾拉攏到自己一方,使觀眾能像自己一樣取笑老大爺的矮個頭,使嘲笑變為同笑。
當然,以上事例中,詼諧幫助攻擊者避開的障礙是一種內部障礙,即是對謾罵的反對,同時攻擊者在攻擊時對敵人也并無明確的意圖。然而在一些情況下,障礙可能是純粹的外部障礙,如敵方身份地位等處于優勢,這時攻擊者所做出的攻擊則有明確的意圖,即巧妙的反擊。《塞利維亞的理發師》中便有情形即是如此:
伯 爵:……還記得你給我當差那時候,就不是個好東西。
費加羅:噢!天哪,大人,那是因為富人要求窮人完美無缺。
伯 爵:你懶惰,胡來……
費加羅:照主人要求仆人具備的品質,大人,您見過很多主人夠格當仆人嗎?[2](P317)
伯爵訓斥費加羅懶惰、胡來,但費加羅無法直面反擊,因為嚴厲的對象是地位顯赫的伯爵,直面反擊不但不會擊敗,甚至也不會使其受辱,反倒有惹怒對方招來橫禍的風險。于是,機智的費加羅通過詼諧顯示了報復侮辱的安全方法,使用反問的技巧使攻擊轉回攻擊者自身,他的回答無疑擊敗了苛刻的伯爵。同時,此例中詼諧印象也全是由費加羅企圖反擊伯爵的意圖所決定的。
又如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則名人笑話。一位大腹便便的富翁在街上碰到蕭伯納,便對他說,“先生,一看到你,便知道目前世界上正在鬧饑荒。”蕭伯納立刻反唇相譏,“先生,一看到你便知道目前世界上正在鬧饑荒的原因了。”與上例相同,蕭伯納反擊的意圖非常明確,既要使自己躲開侮辱,又要擊敗富人,他利用詼諧成功反擊,使富人成為被嘲笑者,保證了自身安全。
如此,阻止謾罵或侮辱性反擊的情況十分普遍,以至于傾向性詼諧常被用來攻擊或批評那些權威的貴族們。傾向性詼諧代表著一種對權威的反叛,非常適合攻擊那些被內部抑制和外部環境保護而不受直接攻擊的有尊嚴有勢力的大人物,因而某些確定的詼諧也常被聯系到社會底層人士以及無權勢的人身上。這也是喜劇作品中劇作家所傾向的底層人士大都是機智的肯定性喜劇形象的原因所在。
綜上,喜劇語言的攻擊性是一種傾向性詼諧,它使喜劇沖突中劇作家所傾向的喜劇人物輕易安全地躲開障礙,占據優勢,通過笑聲賄賂觀眾,把笑爭取到了自己一方,最終使嘲笑變為同笑,拉近了觀眾與喜劇人物之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