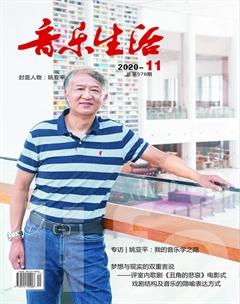文化古韻
郭建民 郭溢洋
從狹義方面,“水上民歌”是流行于南海地區的船上小調、疍家歌謠;從廣義方面,凡是疍家人創作并流傳下來,反映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宗教、家庭、愛情、民俗等內容的民歌,均可稱之為南海“水上民歌”。
南海“水上民歌”流行傳播范圍從廣東、廣西、福建、海南乃至香港、澳門及周邊地區。本文從疍家人生活習俗、崇拜信仰、審美情趣等多個視角,對其藝術特征進行分析和研究。
一、自娛自樂——大眾特征
南海“水上民歌”是疍家族群的吟誦調,生成于疍家人生產勞動和互訴衷腸的“對話”當中。他們巧妙地把“生活、勞動、歌唱”集合在一起,“歌中有你、有我、有她”,審美情趣濃郁,文化特征鮮明。疍家人唱著屬于自己的歌,在自娛自樂中共同分享音樂帶來的愉悅和快樂。
南海“水上民歌”作為疍家人海上精神和情感表達的獨特方式,為族群進步發揮重要作用,作為生動鮮活的藝術載體,為千百年來疍家族群的繁衍生息、引領美好生活產生了積極影響。
鮮為人知的是,早年海上生活,疍家人迫切需要一種交流媒介或載體,進行情感和心靈溝通,他們苦苦追尋并試圖創設一種與陸地生活一樣的“文化”場域。后來欣喜地發現:心靈深處的律動和情愫合二為一“詠嘆”(唱)出來,是最好的“對話”方式。來自內心深處的“詠嘆”不僅帶來了愉悅和快樂,悠揚的歌聲消解了船與船之間距離的阻隔,生活——勞動——情感互動甚是酣暢。于是,“水上民歌”成為疍家人與天海之間,與親朋好友之間“對話”的“橋梁”。
張口即來的歌謠成為疍家人真誠交流與對話的聲音媒介。“水上民歌”聲入人心,“以歌為媒”的精神文化活動,不僅廣受到疍家人歡迎,也加深了疍家族群之間吐露真情的親密關系。
丁亞平認為“任何一種形而上的抽象理論,卻無法抑制藝術(精神追求)的‘對話欲望,不能限制他們表達自身感受的需要。這種欲望作為人與文化雙向建構的連接關系,本身就是人的生命所潛藏的文化與精神的本質所在。”[1]南海“水上民歌”是疍家人渴望實現的一種“對話”,體現了人類本能和欲望的不懈追求,具有鮮明的大眾文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常年的海上生活造成疍家族群生存條件艱苦,而無法向陸人一樣走進學校讀書獲得知識,疍家人心知肚明,知識文化對于自己族群未來的意義,但又苦于海上窘迫生活條件的種種局限。于是,南海“水上民歌”是疍家人相互傳授文化知識的媒介和載體,人生哲理、文化知識、處事智慧等統統濃縮進歌里頭。經過了“口傳心授”,疍家人的歷史和文化融進歌里,慢慢沿襲下來、傳播開來。疍家人古老婚禮儀式,也融進了這種傳統文化習俗,但凡疍家女兒出嫁,按照族群傳統習俗要唱“哭嫁調”,疍家女大多采用嘆家姐調演唱。據傳承人回憶:過去疍家人海上生活隨著大海的潮汐潮落以及氣候變化隨波逐流,大海的洋流和海上季風,把疍家人的漁船被吹來吹去,居無定所。陸地居民不然,有一個穩定的家。因此,疍家女兒出嫁,多半意味著與家人永別。一望無際的大海,險惡的海上生活條件,與家人很難再見上一面。所以女兒出嫁前,要與父母、弟兄姐妹以及姑嫂依依惜別,這個情節,慢慢演變為一種習俗傳承下來。婚禮中唱“哭嫁調”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疍家人女兒出嫁前抒發與宣泄內心五味雜陳情感的特定場景。
疍家婚禮,新娘唱得傷心,聞者落淚,一直要唱到日落雞啼。今天,疍家婚禮唱“哭嫁調”的古老習俗,在兩廣、福建和海南當地仍然保留和沿襲著。
事實上,“水上民歌”作為疍家人一種無可替代的精神文化方式,在海上勞動和日常生活當中影響深刻、意義凸顯,南海“水上民歌”的廣泛傳播,不斷地豐富疍家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不斷地滿足疍家人對未來美好生活的追求。
南海“水上民歌”讓疍家人在單調乏味的生活中,尋找到了大家能夠共同分享、自娛自樂、娛樂他人的方式,人生“喜、怒、哀、樂、愁”在歌聲中得以釋懷。表達愛意和忠貞的有愛的贊歌;崇拜心中豪杰的有英雄之歌;祭海儀式上有祭祀之歌;傳授捕魚經驗(掌舵、撲魚、織魚網等)有“織魚網”和“漁歌”;追思祭奠親人有悲歌;贊美、褒獎兄弟姐妹有家姐歌;慶賀豐收歸來有喜歌……疍家人把唱歌當做生活,從搖籃唱到成人,直至唱到生命的終結,疍家人通過口傳心授傳承喜歌、好歌的文化基因。
南海“水上民歌”口語化的演唱形式,凸顯了親切自然的對話特點,旋律簡單,音樂質樸而又不失深情,張口即可吟唱,形成了易學、易傳播的特征。“以舟為家,向海而歌”是疍家人生動形象概括,是疍家人情感表達最真實的寫照。“水上民歌”唱出了疍家人昨天的歷史敘事,傾注了對明天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盼。《十花贊》(木魚詩調):“一贊桃(呀)花 樹尾(呀)掛 桃花花開(呀)好榮(呀)華。二贊牡丹(呀)花 花咁(呀)輝? 牡丹花開(呀)好富(呀)貴。 三贊石榴(呀)花? 花咁(呀)紅 石榴花開(呀)好臉(呀)容。四贊海棠(呀)花 無怕日(呀)曬 海棠花開(呀)好華(呀)麗。五贊茉莉(呀)花 花咁(呀)香 茉莉花開(呀)滿街(呀)香。六贊黃菊(呀)花 花咁(呀)黃 黃菊花開(呀)遍地好(呀)黃。七贊蘭(呀)花 花好(呀)樣 蘭花花開(呀)好收成。八贊油菜(呀)花 花咁開(呀)好靚 油菜花(呀)好收(呀)成。九贊葵(呀)花 樹頂(呀)上 贊葵花(呀)面向太(呀) 陽。十贊水仙(呀)花 綠葉(呀)圍 水仙花開(呀)好光(呀)輝。” [2]
這是一首疍家人十分喜愛的“水上民歌”,抒發了疍家人對大自然盛開之花的贊美之情,音樂優美動聽,曲調朗朗上口,流傳范圍廣泛。
二、即興發揮——演唱特征
早在明代,王驥德“論腔調”中就有“依心抒懷”的精辟論點,“樂之框格在曲,而色澤在唱。曲有格范而唱可生變”。民歌表演即興創作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經過了時代更迭,故有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也有不變的藝術規律。
悠揚凄美的南海“水上民歌”即興演唱特征突出,史上出現許多具有良好音樂天賦的疍家歌者,他們為了追求更好的演唱效果,博得更多人的掌聲,會依據現場觀眾和環境,增加即興成分,編新詞、唱新調,隨興演唱,憑其洪亮優美的嗓音和樂感以及長期演唱實踐經驗的積累,即興演唱能力頗為嫻熟,以“創始之音,初變腔調,定自渾樸,漸而婉媚,而今之婉媚”來形容。即興演唱、即興發揮、即興編創,根據現場效果和觀眾反映,4-5個音調之間靈活轉換,隨機應變、任意發揮,博得滿堂彩。
即興演唱考驗著演唱者的經驗和快速反應應變能力,要求演唱者深厚的功力以及大量民歌積累。即興演唱表演增強了演唱者與觀眾的互動,消解了演唱者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感,豐富了“水上民歌”表現內容和表演形式,延展了疍家“水上民歌”的審美效果,拓寬了“水上民歌”的傳播范圍。
看似簡單重復的旋律往往伴有自由隨性和靈動發揮,溫婉的樂句中往往有華彩的歌詞以及優美如歌的旋律,在不經意間流淌出來,深入人心,聲臨其境,親切而生動,熱情帶著幽默,營造出其不意的演唱效果。
從音樂表演視角分析,即興特征是一種不拘泥于音樂的均勻、規則之節奏律動,靈活多變的演唱表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于音腔規律部分的有意偏離(音樂專業術語稱之為轉調、離調或者是變奏),在旋律、節奏、裝飾音、滑音的隨意添加;在語言表達上的語氣強弱、歌詞修飾變化的“臨場發揮”;在唱、情、表以及形體等實踐中與觀眾的“熱情互動”等等,正是這種有意無意的偏離和隨性發揮,強化了“水上民歌”真實自然和生動鮮活的感染力,凸顯了“水上民歌”音樂變化再現特征,以及自由奔放與多姿多彩的美學特質。
“水上民歌”往往在出海、歸來、打漁、出網以及婚嫁、祭祀、喪葬等活動上演唱和表演,與陸地許多地區的民歌有異曲同工之妙。
南海“水上民歌”之所以有如此之妙的即興特征,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疍家人長期處于社會底層,把唱歌作為學習、掌握和傳播文化知識的機會,把海上生活中捕捉到的奇聞異事以及左鄰右舍之間的好人好事等,編創到民歌里,使其地得到不斷補充和完善,反映了疍家人生活觀察的機智和對藝術的敏銳。
南海“水上民歌”即興演唱特征曲目很多,比如《開書唱習文》《菜味詞》《八杯美酒》《青樓悲曲》以及《十送英臺》等,帶著疍家人中原地區的文化基因,融合了嶺南曲藝說唱藝術元素,從即興演唱發展到即興編創。十分有趣的是,南海“水上民歌”吟誦調式的即興演唱與西方歌劇中的宣敘調頗有相似之處。
三、融合變異——多元特征
一種音樂藝術形式的發展、變化是以社會變化為前提的,“水上民歌”也無例外。眾所周知,所有的文化絕不是完全通過“生物遺傳”一代代地繁衍而來,“社會遺傳”,即通過社會化的傳播,“水上民歌”才能很好傳承。
早年疍家人生活、歌唱、欣賞呈現出三位一體原始文化形態,慢慢疍家族群中出現了以唱歌為職業的(巫師)歌者,有了不同的社會分工。總而言之,疍家人對于“水上民歌”的需求和摯愛滲透著強烈的文化觀念和習俗,用屬于自己的“水上民歌”證明了一個藝術真諦——人類生存有了藝術的參與才會感受到幸福和溫馨。南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有了“水上民歌”的融入才變得如此豐富。
疍家人的文化觀念、生活習俗以及精神情感、心靈世界等,在南海“水上民歌”的演唱表演過程中,在不經意間的歲月流淌中,傳播開來并傳承下去。然而,“音樂有傳承,就有變化,傳承帶來變化;反過來,變化又促進了傳承,這是音樂文化傳承傳播的定律。” [3]
南海“水上民歌”做為一種流動的音樂,歷經了千百年的傳承,特別是在口傳心授的方式,尤其是歷史流變、社會發展以及時代的進步影響,包括來自政治、經濟和文化,海上生活的方方面面,“水上民歌”將這些受到影響之后的生活內容轉化為一種新的表現元素,自覺不自覺地滲透在演唱、表演實踐當中,加上演唱表演即興發揮、即興編創的習慣,都會加劇“水上民歌”內容和形式的變異。比如:疍家人在不斷地遷徙和漂流中,為了適應異地社會習俗和環境氣候,首先語言習慣會慢慢變化,語言的變化會導致歌詞修飾的“入鄉隨俗”,為適應于當地文化習慣填上或加上新歌詞,表達疍家人新的情愫和新的生活內容。歌詞的不斷變化會帶來音樂表達形式的部分變異,比如旋律、節奏、變化音、裝飾音等一定會表現出新的音樂形態。兩廣、福建到海南的“水上民歌”經過了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口耳相傳之后,在完成了融合異地文化習俗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變異,許多民歌向著更加豐富多彩的方面發展。具體闡述,疍家人常年的遷移漂流既帶來了“水上民歌”新的融合,也帶來了“文化基因”蛻變”即“推陳出新”。伴隨著融合與變異,“水上民歌”不斷地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關于這一點,也許正是南海“水上民歌”長久不衰、流傳至今的緣故。
筆者在田野考察中,錄制了三亞及陵水幾位傳承人演唱的《十月種花》《祖宗漂流到海南》《漂流》,根據記譜比較和分析,發現一個現象,雖然同屬海南“水上民歌”,但是在音樂形態上,比如調式調性、旋律、節奏、速度以及滑音、裝飾音等方面,卻不盡相同,并且差別還很大。這進一步證實了“水上民歌”在傳唱過程中,常常會出現“跑偏”的現象,具體表現在演唱和表演細節等方面會衍生出一些新的音樂元素和內容,因此有學者稱,現在聽到的疍家“水上民歌”是多少失去海洋咸味的“咸水歌”。
深入研究疍家人漫長的遷徙史、曲折的漂流史、復雜的變遷史,發現疍家人大部分是逃難遷徙到嶺南地區的中原人,他們首先到達廣東南部沿海,而后又從廣東沿海相繼漂流到廣西、福建、海南等地沿海,疍家人的遷徙帶來了語言的遷移,久而久之,疍家人適應了異地生活習俗,屬地的母語逐漸遺忘并被異地同化,疍家人在廣東生活的時間較長,因此受廣東粵語的影響最深,這就解開了疍家人為什么至今仍然習慣操廣東粵語的諸多疑惑。
文獻記載:“雍正禁除舊俗之后,疍民逐漸放棄打漁轉為陸地,隨著生活方式的轉變包括音樂在內的各種形態都發生了變化,由此出現了地方性、區域化的音樂曲調。例如大繒歌、擔傘調、高堂歌等即是如此。疍家咸水歌在各地流傳的曲調類型中,有一組同名曲調,即木魚歌與木魚詩調。據考察資料顯示,木魚歌主要流傳于廣東地區,木魚詩調的稱謂則出現在海南地區。莫日芬在對廣東地區的咸水歌研究中,將咸水歌與木魚歌并列,認為:“木魚歌,古稱沐浴歌、摸魚歌。它的古稱與咸水歌的古稱是相同的,由此可見,它與咸水歌是同源異流的關系。咸水歌在水上居民中發展,木魚歌則在陸上居民中流傳。”[4]
以舟為家的疍家人婚禮習俗頗為獨特,他們以船代轎、以唱歌謠相賀吉祥形式為主,有時以接親拋新娘取樂或顛船賀喜。筆者在海南陵水采風,巧遇疍民排練“哭嫁”。表現疍家古老傳統婚禮女兒“哭嫁”習俗。“哭嫁調”原本是一首民歌,有悲調特征。陵水“水上民歌”傳承人郭世榮進行了編創,發展成為有人物、有故事情節、又有戲劇沖突的一部“話劇加唱”式的歌舞短劇。值得一提的是,劇中有疍家人海上習俗的戲劇情節。按照疍家人的古老習俗,新娘在進婆家之前,須經過“顛船”考驗,迎取新娘的親朋好友,前往在大海上有意搖擺小船,造成新娘在船上左右搖晃、顛簸,其寓意是婆家對即將進門的新娘進行一次海上考察,看一看新娘是不是真正的疍家姑娘,是否經得起未來海上生活的曲折考驗。這是北方陸地婚禮習俗中不曾見到的。比如《婚日升棚》:“新即搭棚棚向東 今日娶妻心又松 谷字上頭倫篷宀 新婚喜慶臉歡容 新郎搭棚棚向南 胸戴紅花結金蘭 坍字無要土字監 擇朵芙蓉配牡丹 新郎搭棚棚向西 今日結婚識高低 羅字丟拋四字仔 夫妻和順守羅維 新郎搭棚棚向北 夫妻團結度難關 佳字則邊又字參? 積權創業不怕難” 。[5]
“哭嫁”顯現出疍家傳承中原婚禮習俗。幾條漁船連在一起搭起婚慶大棚,宴請客人。新娘帶著紅蓋頭,拜過天神、地神、海神之后,再拜公公、公婆。婚禮上“哭嫁歌”自始至終相伴相隨。
還有《改革開放好》等,民歌通過舊歌填新詞的方式突出了民歌的變異性特征,反映了疍家人與時俱進、不懈追求新生活,反映了傳統民歌社會化傳承的一種常態。
四、隱忍低調——神秘特征
探索南海“水上民歌”的歷史,中原人、疍家人、咸水歌三個概念和維度可以勾勒出一條清晰的歷史線索。從遙遠的北方中原一路遷徙,逐步演化蛻變的疍家人,其中封建朝代遭受政治迫害、躲避追捕的一部分文人也加入南遷徙的百萬難民之中,復雜卑微的身份和社會地位,逼迫著疍家人的海上生活,深居簡出、謹慎小心。潛在的提防和戒備心理,促成了疍家人“隱忍”“低調”“神秘”等行為特征。
疍家人海上風里來、雨里去,“神出鬼沒”、“來去無蹤、去無影”,疍家人的這種行為特征,既神秘又充滿了傳奇和遐想。同時,疍家人海上勞動和生活,練就了海上航行和捕魚勞作的出手敏捷以及膽大心細的生存本領。常年遷徙的身份漂流以及海洋特殊的環境氣候造就了疍家人的性格,滋生了疍家“水上民歌”生成的條件。“藝術源自生活”,疍家人在海上神出鬼沒的生活中所創造出來的民歌,除了具備音樂的幾個基本特性比如:優美抒情、歌頌、真誠以外,神秘性特征格外突出。不論是出海捕撈的漁歌、海上情歌;還是夫妻、姑嫂、家兄之間的贊美之歌,以及疍家女兒的哭嫁歌等;特別是祭海儀式和海上寺廟演唱的宗教信仰一類的民歌,音樂帶著口語化吟誦調特點,歌詞表達充滿了神秘性特征。究其緣由,其一是因為疍家族群長期與陸地分離,長期以來的遷徙、漂流經歷促使其隱藏自我、明哲保身成為生活習性,民歌內容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二疍家人低微的身份造就了民歌的簡單樸實和低調;其三長期海上漂流形成極不穩定的生活狀態,也成為民歌不追求奢華的實用功利的特性十分鮮明;其四南海熱帶地區變化莫測的氣候環境,促使疍家人神出鬼沒生活習性以及相互一致的音樂特征。總之,疍家人飽經苦難顛沛流離生活造就了“水上民歌”成為中國海洋民歌文化中,既神秘又獨具風情的一種音樂形式。
疍家人作為海上特殊族群,“以舟為家、捕魚為業、浮游而生、向海而歌”,躲避災難和漫長的遷徙漂流經歷,形成了疍家人相對隱蔽的生活和文化習俗,同時讓一水之隔的岸上人對于疍家人產生“只可遠觀難以猜測”的懷想,甚至有時產生諸多誤解與褻瀆。海南疍家人與兩廣、福建疍家人一樣,是早年漂流至熱帶海域的族群之一,這個特殊的海上族群,結網探海,以舟為家,向海而歌,用民歌記錄自己的經歷,為后人留下豐富的歷史敘事和多彩神秘的傳奇故事。
數量龐大的南海“水上民歌”中,至今依然留存著許多原始奇風異俗,而這些奇特的風俗習慣,許多都帶有濃厚的神秘特質。
長期以來,疍家人以海為生、與海抗爭,神出鬼沒的生活方式,充滿了曲折和傳奇,疍家人的海上生活,練就了他們不畏風險的挑戰精神,也使得疍家音樂飽蘸海洋滋味,這種滋味恰恰又與其獨特的海上漂移的“海上吉普賽游牧”族群物質和精神生活息息相關、緊密相連。
疍家人為什么在海上漂泊生活?疍家人在海上真實的生活現狀是什么樣?遇到臺風暴雨疍家人如何進行自我救贖?險惡的海上環境,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度過?疍家人為什么愛唱歌?“水上民歌”究竟有多少首?疍家人與生俱來的唱歌技巧是怎么掌握的?天賦好、嗓音好、樂感好?還是另有原因?廣受疍家人喜愛歌者與早年的巫師有無區別?數量龐大的疍家“水上民歌”怎么進行口耳相傳?疍家“水上民歌”里面鄉音俚語又富含哪些含義?等等,“水上民歌”體現了疍家人的聰明和智慧,也留下諸多歷史傳奇和疑問,留給研究者太多的學術沉思,等待著深入發掘、分析和品讀。
南海“水上民歌”除了具有一定的娛樂、審美、撫慰心靈等特征以外,還具有醫用功能,這是因為神秘性特征衍生而來。比如《十送英臺》,這首看似表達男女情愛的歌,蘊含的卻是疍家人對神靈的無限虔誠與頂禮崇拜,歌中唱到:“哥送我又到廟堂 幾多男女去燒香 四邊都是靈神像 亦有未雕坭塑郎。”中原宗教信仰習俗,讓疍家人的許多行為充滿神奇和浪漫。
早年疍家人缺醫少藥、沒有文化,歌唱是她們生老病死的精神依賴和心靈寄托。疍家人希望通過“水上民歌”——充滿了美妙和神秘(奇)的歌聲,實現與天地、與大海、與神靈之間的互動與“對話”,完成心靈與天地、與大海之間的對接與互通。
至今疍家人的傳統習俗難以用科學來解釋。事實上,也不需為此去尋找科學依據,從心理學視角,即音樂可以平復凈化心靈、調節心理疾病,抑或更易鋪捉到疍家人的神秘特征。
五、比喻起興——文學特征
兩廣、福建、海南及周邊地區與中原相比,沒有一望無際的平原和大面積的良田覆蓋,卻擁有寬闊的海洋,海鮮魚類資源豐富。作為常年生活在海上的疍家族群,與生活在同一片區域的少數民族一樣,崇尚自然,敬畏大海,他們追求幸福和平安生活,追求“海天一體”、“天人合一”。疍家人“詠物言志、以海抒懷”。“雖然過去大部分的疍民沒有多少文化,在編唱歌詞時就只能記著生活中經常接觸的東西和經常看到的事物作為素材,于是看到什么,就觸景生情地唱什么。它常用“比喻”“起興”“直敘”“夸張”“對比”“重復”“序列”等的文學藝術手法來抒情,表現人的思想感情,加深形象思維。” [6]
從南海“水上民歌”音樂形態和歌詞修飾方面,可以捕捉到宮廷梨園流亡人員文人參與創作改編的一些痕跡,他們將原本音樂結構單一的“水上民歌”發展成表現力豐富的多段曲式,原本演唱簡單的調式發展具有4-5個音調靈活多變的聲腔系統,原本松散自由的歌詞發展具有詩詞格律規范、修辭手法凝練的五言體,甚至發展成具有戲劇特征的敘事短劇,生動自然、恰如其分,內容豐富、題材廣泛。
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人類的本能促使著疍家人創造屬于自己的幸福和快樂,雖然她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們卻創造富有文化內涵的“水上民歌”,凸顯了疍家人藝術水平和審美情趣。經過了多年的傳承和傳播,南海“水上民歌”的歌詞結構規整、前后押韻,比喻特征突出。所謂比喻:顧名思義打比方,托事于物,以彼物比此物,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詞。用某些有類似的事物來比方相說的某一事物,以便表達得更加具體生動。比喻可分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種,咸水歌中大量運用“比喻”中的“借喻”藝術手法,比如:“妹坐船頭眼望哥 哥妹雙雙渡銀河 織女前面把歌唱 牛郎后面猛打鑼。” [7]
再如:“三亞古井深有圓 妹知此井多少年 三亞古井深有圓 此井疍民用百年 古井泉水清又甜 飲水不忘我祖先。”[8]看似簡單平實的幾行歌詞里,比喻樸實生動,親切自然還不著痕跡地應用了漢語詩詞諸多修辭手法,如起興、想像、擬人、暗喻、隱喻、反復、設問等等,營造了含蓄雋永的美雅意象。這也說明,嶺南地區雖處邊陲沿海,但在長期的人口遷徙和海上絲綢文化交流中,中原文化、嶺南文化以及外來文化,表現倫理道德習俗和審美情趣,有了廣泛的交流碰撞和高度契合,也許這正是南海“水上民歌”引發族群共鳴和文化認同的藝術密碼。
為了便于傳唱、記憶,南海“水上民歌”的歌詞一般都善于用簡潔、精練和形象生動的語言,敘述疍家人海上生活故事,抒發疍家人的喜怒哀樂,提升了“水上民歌”的審美情趣和藝術感染力。南海“水上民歌”大多采用比興等修辭手法,由一個自然樸實的短句開始,然后慢慢展開,常常借助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抒發情感、表明情誼,吳競龍將其概括為“起興”,所謂起興就是由歌手隨口即唱,借景抒情,聯想回憶。雖然沒有固定文本,但頗具即興發揮和聯想回憶之藝術特征,“起興”、“比興”渾然天成,均可達到很好的藝術效果。
六、奮發向上——勵志特征
精神和情感的表達是音樂文化的動力。南海“水上民歌”的文化力量不斷地激發疍家人生活和勞動中的精氣神兒,引領著疍家人積極向上、奮發圖強。
多少年以來,疍家人流浪漂泊,居無定所,演變成為特立獨行的族群,孤獨寂寞的海上生活方式,急切盼望一種解憂排遣、逗樂打趣式與其夕夕相伴。南海“水上民歌”非但沒有成為疍家人的精神束縛,相反,通過抒情和宣泄,找到生活樂趣,把歌唱帶來的快樂轉化為人生勵志的動力,為單調乏味的海上生活鼓舞和奮進。
疍家人在物質生活上需要自力更生,精神生活方面,依靠自己去發現、自己去創造。充滿了智慧和樂觀精神的疍家人,在自娛自樂(吟誦式)的歌唱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快樂,“向海而歌”是對疍家人精神形象生動而真實的寫照。
史料記載,疍家人男女老少人人喜歡唱歌,喜歌、好歌的風氣在疍家人生活的海域蔚然成風。疍家人用唱歌抒發情感消除疲勞驅散痛苦和憂郁。唱歌——成為不斷激發疍家人奮發向上的精神動力。三亞疍家“水上民歌”傳承人郭亞清說:我們小的時候哪里都去不了,從懂事的時候我記得,祖祖代代都是在海上漂流,疍家人飄到哪里就在哪里唱,因為沒有別的好玩的(精神娛樂方式)疍家人就喜歡唱這個疍歌,親情、愛情、疍民之情啊,都唱在了歌里頭。“水仙花以及香芹菜 昨晚應承今晚開來 難為舍心丟妹甘耐。”
“以舟為家·向海而歌”不僅是疍家人“找樂”的精神生活方式,也是精神升華和未來向往和寄托。表達愛情要唱“水上民歌”;祭祀海神要唱“水上民歌”;海上歸來要唱“水上民歌”;婚喪嫁娶要唱“水上民歌”……總而言之,疍家人用屬于自己創造出的美妙音樂,如泣如訴地講述著自己族群的傳奇故事,默默無聞地扮演者屬于自己的角色,細膩而豐富的情感體現出疍家人的樂觀向上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水上民歌”成為疍家人生活中傳遞情感和信息的最佳方式。
“水上民歌”既不顯得華麗也不曲折復雜,無需奢華的外表裝扮,更沒有千回百轉的華彩看似的樂章。自然簡單朗朗上口的“水上民歌”,依靠疍家人特有的“樂器”——嗓音已經足夠了。可以說,南海“水上民歌”凸顯了疍家人睿智選擇。從歷史成因視角,又何嘗不是疍家人生活的一種無助與無奈呢?
與其它地方民歌一樣,“歌中找樂”是南海“水上民歌”是的特征之一。從誕生那一刻起,就已經具備了娛樂大眾、引領大眾的文化特質。哪里有“水上民歌”,哪里就是一片歡樂的海洋。蔚藍色的大海之上,出海和歸來的碼頭,古井旁或古樹下,到處都可以聽到疍家人的歌聲。出海撲魚有漁歌,出海歸來有豐收之歌;婚禮慶典有升棚之歌,新娘入門有拜神之歌,八月十五賀中秋,疍家人節慶唱酒歌,孝敬老人孝之歌,青年男女唱情歌,嬰兒睡夢中搖籃曲,少年兒童有兒歌……“水上民歌”作為疍家人直抒心懷和升華心靈(審美和娛樂)、最易掌握和普及(流行和傳播)的民歌,其精神內涵,文化抒懷,深深地扎根于疍家人的精神生活和審美情趣之中。
疍家人通過口耳相傳方式,把大量抒情優美和充滿了正能量的“水上民歌”傳承給下一代。南海“水上民歌”也許是疍家族群唯一的文化娛樂形式,她對于疍家人文化素養的構成起到了重大作用,疍家人的道德價值觀念、人生理想等,都是建立在“水上民歌”基礎上。 比如 《成功之路》[9](略)
日出東方要起身,早早起身就精神,欲求達上成功路,首先不要做懶人。懶惰始終窮苦困,沒有幸福的人生,等如一箱大珠寶,拋落大海往下沉。做人總要有計劃,光芒萬丈過一生,須知生命的意義,不是白白一世人。一年之計在于今,,一生之計在于勤,千萬不能交白卷,幸福一定要追尋。現在就是好機會,即時快點下決心,不可輕看你自己,成功一樣有你份。從今日起要發奮,盡量表現你所能,別人雖然有八兩,自己亦都有半斤。世上根本無難事,在乎有沒有信心,有了信心有辦法,運用辦法去實行。以為不可能的事,努力就會變可能,加多一點點勇氣,與及苦干的精神。只要能夠吃得苦,成功之路便接近,無論風雨怎么樣,堅定意志往前行。路上小心和謹慎,勿讓志氣去消沉,得到一雷天下響,便是一個人上人。
大海告訴疍家人生活是怎樣走過,水千條山萬座,手拉手要講的太多,遷徙漂流灑滿了疍家人的記憶,小船把疍家人的歷史訴說,民歌給予疍家人美好和憧憬,痛苦與歡樂給了疍家人同一首歌。南海“水上民歌”中所蘊含的奮發向上和積極樂觀精神自然而又生動,她鼓舞疍家人堅強不息,勉勵疍家人勤奮努力,引領疍家人樂觀面對美好未來。
七、意蘊綿綿——情歌特征
長期海上生活,艱苦孤獨,寂寞難熬,夜晚來臨,唯有唱歌是獲得心靈釋放和精神娛樂的最佳方式,尤其是疍家年輕人到了談情說愛的年齡,一望無際的大海、居住地的分散,阻礙了她們低聲細語的情感表達,加上疍家漁船狹小空間又使得她們難以暢快淋漓、互訴衷腸。因此,男女二人對唱“水上民歌”,恐怕是他們渴望獲得對方心儀最含蓄、最舒心的表達方式,當然也是最為恰當的浪漫方式。
南海“水上民歌”也被廣泛地稱為“南海情歌”,與全國許多地方的民歌一樣,寫情、表情、抒情類——民歌往往居多。相比之下,南海“水上民歌”所抒發的“情”究竟又有什么獨到之處呢?
早年疍民貧窮孤獨,以舟為家的海上游牧方式,居無定所,隨時面臨著轉換地方。特殊的生存環境,相戀的青年男女,無法耳鬢廝磨朝夕相伴。為謀生,疍家青壯年男子(早年疍家女子不允許出海,留守家中照顧孩子和老人),結伴出海勞作、流浪漂泊,風餐露宿,抗擊狂風暴雨,防兇禽惡獸,常年累月,音訊不通,生死未卜,不測安危。守候在船上的阿妹們,終日無邊無際的思念、牽掛與擔憂,而在安土重遷,封建禮教嚴苛的偏遠海域,癡情的阿妹,沒有文化社交活動,來彌補和稀釋這種刻骨銘心的思情,每日只能皺下眉頭,又上心頭,時刻聚焦于遠在深海那邊的阿哥們。這種鄉村農耕時期的愛情現象,現代青年,很少發生,難于體會深切。每當疍家阿哥、阿妹能夠獲得機會孤身獨處風清月明、萬籟俱靜之夜,定會思緒紛揚,心中長久積聚的萬千情思,猶如熾熱奔突的熔巖,噴涌而出,在遼遠空闊的大海上,盡情地釋放,忘情地渲泄。她們在亦真亦幻地想像,情真意切地表白,撕心裂肺地詠嘆……這種真摯濃烈的情感表達,自然會深深地打動用心感受的歌者與聽者。
南海“水上民歌”中,意蘊綿綿詠嘆題材的情歌頗為廣泛。如果有青年男子在海邊或岸邊偶遇心儀的女子,就會“以歌探情”:
隔河一朵花兒鮮啰,取支竹仔探深淺心,想采摘怕水深啊啰,唱支歌兒試妹心啊啰女子聽到表白,如果中意男的就會唱:蓮葉盛水清又甜啰,蓮花出水香連綿,阿喬好比綠荷葉啰,摔起蓮花笑盈盈。這樣,不相識的男女一唱一和,便把情絲牽住了。倘若女子不中意,她就會婉然拒絕而唱:不是楠木不架橋,不是好柴莫求燒,不是金子勿下火,阿妹不想攀哥門。
這種類型的情歌大多表現的是疍家男女青年以歌定情,偕結秦晉之好的。如果海上相遇,男子開唱:站睇船頭見妹搖舢板,突然轉頭搖來兩邊篩。妹你有意搖給哥來睇,還是艇仔造來有問題。女:阿妹搖艇搵哥來傾鬼,老豆睇見叫妹搖回歸。搵哥來傾鬼真是艱難,心情唔好搖艇兩邊篩。歌中“搵哥來傾鬼”意思是找哥來說話。海南咸水歌除了使用粵語用詞發音,融入了海南本地方言的拖腔發音,三亞、文昌一帶尤為典型。
再如《水鄉情歌》:遠遠路路見妹戴頂盒帽子,帽綁甘長拖甘底。妹哎,你另臉被哥睇一睇,等哥賺錢帶你回歸。盒帽子是海南特有的帽子,既可遮陽避雨,又十分美觀。《魚歌對唱》也是一首典型的情歌。
男:乜魚出世是孵石底,乜魚入石又入泥。乜魚頭大尾巴細,乜魚頭尖尾巴齊。女:泥鰻出世是孵石底,立追入石又入泥。石斑頭大尾巴細,沙吹頭尖尾巴齊。男:乜魚出世是大口鋤,乜魚出世跳高來。乜魚出世噴墨水,乜魚出世帶只袋。女:鯊魚出世是大口鋤,浮魚出世跳高來。墨魚出世噴墨水,八爪出世帶只袋。男:乜魚出世是水面跳,乜魚海底叫嘈嘈。乜魚出世空中飛,乜魚出世著紅袍。女:蝦仔出世是水面跳,畫魚海底叫嘈嘈。飛魚出世空中飛,紅魚出世著紅袍。
疍家男女一問一答,一唱一和,問的是什么魚,答的是南海特有的漁產,如浮魚、沙吹、飛魚等。這些民俗、自然意象包含著日常生產生活的各個場景。”[10]無論是獨唱,還是對歌,與侗族大歌、苗嶺山歌、西北“花兒”比較,男女之間的愛與忠貞表達是其顯著特征,因演唱環境和社會場域不同,方顯異曲同工。
南海“水上民歌”在特定社會生活和氣候環境中生成,逐步發展成為具有多元風格的藝術形式,詮釋了疍家男女愛情的含蓄之美和深情守候,凸顯了中國民歌情意綿綿的情歌藝術特征。
注釋:
[1]丁亞平 著《藝術文化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出版,P451-452(括號內筆者加注)。
[2]三亞港——“水上民歌”油印本 。
[3]郭建民《聲樂文化學》上海音樂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頁。
[4]馮建章《疍家咸水歌稱謂與曲調類型辨析》中國音樂學2019年2期。
[5]三亞港——“水上民歌” 油印本 。
[6]吳競龍《水上情歌》——中山咸水歌 廣東教育出版社,第85頁。
[7]三亞港——“水上民歌”油印本 。
[8]三亞港——“水上民歌”油印本。
[9]三亞港——“水上民歌”油印本。
[10]花靖超《海南疍家咸水歌的敘事主題與表現特征》2019年10月,開封教育學院學報。
郭建民 三亞學院音樂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
郭溢洋 黃河科技大學藝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