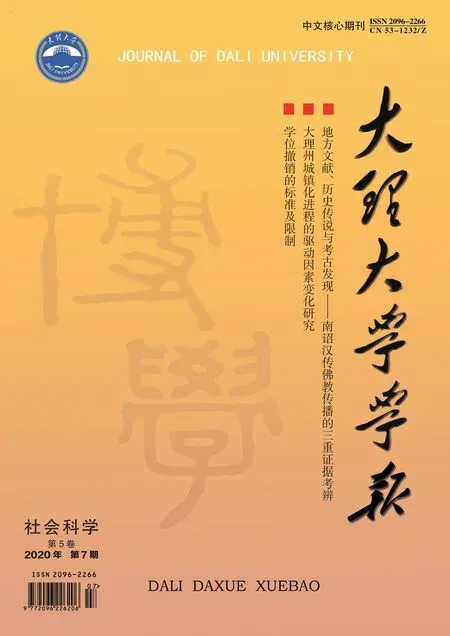主題、類型與前文本:評影片《綠皮書》
苗 瑞
(大理大學文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
美國電影《綠皮書》自2018年9月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以來可謂叫好又叫座。影片在獲得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男配角三項大獎的同時,還收獲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人民選擇獎第一名、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音樂類最佳影片、美國國家評論委員會最佳電影、年度和平電影最有價值電影提名等榮譽。截至2019年4月,制作成本為2 300萬美元的《綠皮書》在北美獲得了8 476萬美元的票房收入,成為自《國王的演講》(2010年)以來北美票房最高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影片在海外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尤其是在中國,票房超過7 070萬美元,在奧斯卡最佳電影中僅次于《泰坦尼克號》。其全球票房收入超過3.06億美元。
《綠皮書》的成功得益于它成功地游弋于因襲與創新之間,在繼承“類型范式”和“前文本”的基礎上實踐藝術創新,很好地平衡了藝術與商業之間的關系。在影片的創作生產過程中,編劇和導演面臨著如何處理影片與同題材、同類型影片,以及自身與經典“前文本”之間的關系問題。互文性理論認為“一個文本只有通過與那些在其之前產生并通過變化對其發生影響、產生作用的文本加以比較才能讀懂”〔1〕。與《綠皮書》形成互文性的影片主要有《為黛西小姐開車》(Driving Miss Daisy,1989年,以下簡稱《黛西》)、法國影片《無法觸碰》(Intouchables,2011年),及好萊塢翻拍片《觸不可及》(The Upside,2017年)等。它們都講述了“一名白人與一名黑人以雇傭關系為契機建立起跨越種族的友誼”的故事。其中《黛西》獲得了第6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編劇本和最佳化妝四項大獎,以及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最佳表演團隊和金熊獎提名等;《無法觸碰》則打破了法國電影票房最高紀錄,同時收獲了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和法國凱撒獎最佳影片提名。由于該片的巨大成功,印度、阿根廷也先后翻拍了它。基于《綠皮書》的成功與非議,本文從主題、類型與前文本等方面對《綠皮書》游弋在因襲與創新之間的平衡藝術進行討論分析。
一、政治主題:白人救世主與黑人的身份追問
當分析解讀一部影片時,我們會首先嘗試概括它的主題,因為掌握了一部影片的主題就掌握了它的核心內容。影片的主題相當于“情節動作的概要、情節動作的中心立意或組構原則”,是“作品的意識形態的或事件的中樞”,它能夠“確保作品結構嚴密”,是“限定著對作品的任何解釋的一個常數”〔2〕。影片的主題必須反映人們生活中的意義和價值,否則影片會空洞無實,不能引起觀眾的共鳴。
在主題上,《綠皮書》回應了長期困擾美國的種族問題,這是影片“政治正確”的保證。美國是世界三大移民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之一,“百衲衣”的比喻準確生動地表明了美利堅民族的多樣性。民族之間的沖突與融合,不僅貫穿于美國歷史,也是當今美國社會的重要課題。在美利堅民族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以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與種族壓迫最為尖銳。美國南北戰爭后,1863年頒布的《解放奴隸宣言》理論上使黑人獲得了自由與平等權利,但對黑人的種族隔離與壓迫卻長期存在,終于在19世紀中葉爆發了長達十余年、反對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爭取政治經濟和社會平等權利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綠皮書》的故事設定在民權運動高潮前夕的1962年,講述了在紐約夜總會“當差”的意裔美國人托尼·瓦萊隆加(Tony Vallelonga)在夜總會歇業期間被優秀爵士鋼琴家、黑人唐·謝利(Don Shirley)聘用為鋼琴巡演的司機兼保鏢,在旅途中建立起跨越種族和階級的友誼的故事。影片以交易性的雇傭和服務關系為契機,通過兩位主人公的路上遭遇和心靈轉化,想象性地彌合了美國種族之間的矛盾隔閡并達成和解,從而整合了當代美國種族問題上的個體認知與民族身份問題。
影片的尾聲通過三個頗具意味的標志性段落達成了這種彌合與和解。第一個段落是在種族隔離最嚴重的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因為主辦方不允許自己在餐廳就餐,謝利拒絕了演出,標志著謝利一改以往的軟弱態度,開始對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說“不”。第二個段落是“橘鳥酒吧的合奏”。西裝革履的謝利在酒吧與黑人朋友們歡快地合奏,找到了久違的輕松快樂,象征性地完成了謝利向黑人這一“自然身份”的認同與回歸。第三個段落是“平安夜的歡聚”。影片的最后,在結束旅程回家后,孤單寂寞的謝利走進了托尼家,與他的家人歡度平安夜,標志著謝利突破黑人的身份認定,象征性地完成了謝利對家庭港灣的回歸。作為《綠皮書》片名來源、最早出版于1938年的真實出版物《黑人司機綠皮書》正是美國30年間種族歧視與隔離制度的真實寫照。該書的作者是一位名叫維克多·雨果·格林的郵遞員。它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指南,介紹了在吉姆克勞南部歡迎黑人旅行者的飲食場所和住所,并警告他們哪些城鎮對黑人來說是危險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有媒體批評《黛西》《綠皮書》等影片“對歧視背后的制度和系統問題視而不見,息事寧人地把種族議題處理成個體之間增進了解達成偉大的友誼”〔3〕。“從消除種族隔離到融合、到平等、到真正的友誼,種族進步中所有的樂觀主義都是由服務條款規定的”,它們“把工作場所浪漫化,把黑人角色當作封閉的白人思想和與世隔絕的生活的理想撬棍”。同時,《綠皮書》還延續了“白人救世主”的刻板印象,結合了“白人救世主的比喻與偏執”。的確,影片以黑人與白人個體之間跨越種族和階級的友誼來彌合“血雨腥風”的種族沖突與斗爭只不過是一種“美麗的幻想”。這一方面映照了當時美國政治上解決黑人種族平等問題的乏力,也是現實生活中經濟和就業的平等在解決黑人種族問題上的基礎地位的反映。實際上,此種花錢買玩伴的現代消遣,只有在20世紀80年代一體化后的美國,民權運動或多或少地平息下來,資本主義和開玩笑的白人家長式作風肆虐之后才有可能。
《綠皮書》的主題創新,體現在它揭示了非裔美國人的階層分化以及謝利對自我身份的追問。在前往北卡羅萊納州的旅途中,汽車出現了故障,謝利和托尼都下了車,他們看到了田地里勞作的作為“他者”的黑人,同時勞作的黑人們也在凝視著作為“他者”的謝利和托尼。這種互為“他者”的凝視深化了影片的主題,引發了觀眾對美國種族內部階級分化問題的思考。在結束密西西比州圖珀洛(Tupelo)的演出后,因托尼毆打辱罵自己的警察而被拘禁的二人被釋放后爭吵了起來,在雨中謝利情緒激憤,向托尼痛陳自己的身份困境:
是的,托尼,我住在城堡里,孤身一人,有錢的白人付錢讓我為他們演奏鋼琴,因為這讓他們覺得自己很有文化,但當我一走下舞臺,在他們的眼里我立馬變成一個黑人,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正的文化。我獨自忍受輕視,因為我不被自己人所接受,因為我和他們也不一樣。所以如果我不夠黑,也不夠白,我甚至不夠男人,告訴我托尼,我是誰?
謝利是美國社會精英、社會上層人士。但他同時也是一名黑人、同性戀,他屬于美國社會中真正的少數群體——白人群體視他為“玩物”異類,黑人群體也不接納他,他既是白人眼中的“他者”,也是黑人眼中的“他者”。于是發出了“我是誰”的追問,把影片的主題引向對特定時代背景下人的“身份認同”的思考。
二、類型范式與前文本:藝術與商業的平衡路徑
除了“政治正確”外,“藝術與商業的平衡”是奧斯卡最佳影片獲獎的標準之一。自1929年奧斯卡金像獎誕生以來,盡管奧斯卡的評審規則做了多次改革,但這一原則卻始終未變。最為顯著的例子是被奉為影史經典的《公民凱恩》雖然獲得資深影評人九項提名,但因平庸的票房成績和冷淡的公眾反應,最終只獲得了一項最佳編劇獎。“藝術與商業的平衡”其尺度很難拿捏,但繼承基礎上的創新無疑是一條成功的實踐捷徑。《綠皮書》正是這樣一個成功案例。
“藝術與商業的平衡”在具體影片中并非無跡可尋。導演對藝術與商業的考量最終投射在文本中,為我們分析導演的創作動機提供證據。當導演以“追求影片的藝術品味”為創作動機時,意味著文本要打破通俗的商業電影的敘事成規和慣例,強調人物性格和視覺風格,抑制動作性和關注內在的戲劇沖突;當導演以“票房和商業利潤”為創作動機時,意味著文本主題要契合社會熱點和公眾關切,遵循類型片的敘事規則,擁有明星陣容,并以院線放映為主;而當導演以“藝術和商業的平衡”為創作動機時,則意味著在尊重觀眾的審美經驗基礎上的藝術創新,既尊重觀眾的觀影經驗,又適當挑戰觀眾的審美能力,在創作中采用繼承“類型范式”和“前文本”的成功經驗基礎上的藝術創新策略。在好萊塢的電影生產體制下,《綠皮書》以“藝術與商業的平衡”為創作動機,在“治愈式旅途片”的基本敘事范式和“前文本”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實踐藝術創新,是影片取得成功的關鍵。
從類型上看,《綠皮書》遵循了公路片中“治愈式旅途片”的敘事范式。公路片是美國對世界電影的類型貢獻,到今天發展成了“以旅程和道路為敘事載體,以主人公在路上的遭遇和人物內心的轉變來推動劇情發展,表現人們疏離、孤獨、尋找、溝通、反叛等內容”〔4〕的電影類型。作為公路片的子類別,治愈式旅途片著意于“對現代人的心靈拯救,解決其精神焦慮,并最終投奔‘家庭’,曾經被‘公路片’的主人公所摒棄的‘家’的意象重新回歸為‘愛的港灣’”〔5〕。《綠皮書》沿襲了治愈式旅途片的類型敘事結構:影片的開端把謝利設定為身處19世紀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中、孤單壓抑的非裔美國人,通過深入南方腹地的鋼琴巡演旅途,解決了其精神焦慮,從心理和行為上達成了種族和解。《綠皮書》的創新在于,率先在同類題材中開創了“治愈式旅途片”的敘事范式,這是它與《黛西》《無法觸碰》等“前文本”不同的地方。《綠皮書》中“汽車的移動性帶來了希望,暗示著種族隔離制度終將結束,以謝利博士為代表的黑人也將擁有更多的社會移動性及自由”〔6〕。
與“前文本”比較,《綠皮書》的創新還體現在人物設計上,并通過細節塑造了立體的人物性格。同樣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黛西》,雇主猶太老太太富有高貴、固執吝嗇,黑人霍克樂觀仁厚、身份卑微;《綠皮書》則做了相反的人物設計:黑人雇主謝利來自上流社會、文化水平高、舉止高雅,白人托尼則是底層平民、生活窘迫、文化水平低、舉止粗俗。影片不但塑造了兩位性格迥異的主角,以增強影片的戲劇沖突和喜劇效果,而且還顛倒了白人優越論或白人至上的傳統觀念和固定人設。《綠皮書》在黑人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故事開始于1948年的《黛西》中出現的黑人都從事家仆工作,社會地位低下。黑人司機霍克雖樂觀善良,但目不識丁、身份低賤。而《綠皮書》中的黑人謝利則是高貴優雅的上層精英。固然,這樣的人物設計來自故事原型,但它增強了影片的幻想特征,反而凸顯了當時的黑人社會地位普遍低下的社會現實。
為了達到“藝術與商業的平衡”,除了因襲“治愈式旅途片”的類型范式外,《綠皮書》還增加了不少商業元素。如影片把謝利設置成“離群索居、孤僻壓抑”者。影片上映后,謝利的后人因此產生質疑與不滿,因為現實生活中的謝利不僅有三個兄弟,與家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而且參與了民權運動,在其他非裔美國藝術家和領袖中也有許多朋友。謝利的朋友作家大衛·哈伊杜說:“我認識的這個人與阿里在《綠皮書》中描繪的一絲不茍的優雅形象大相徑庭。(謝利)理智,但是樸實得令人不安,機智,自我保護,不能容忍一切事物的不完美,尤其是音樂,他就像他那獨特的音樂一樣復雜,無法分類。”影片之所以違背現實把謝利塑造成這樣的形象正是為了滿足商業類型片“先抑后揚”、形成“角色弧線”的戲劇化要求。另外,影片的喜劇成分也為影片增色不少。在世界電影的范圍內,“笑”與“性”“暴力”一起被稱為最受歡迎的類型元素。由于題材的限制,在缺乏“暴力”元素的情況下,“笑”與“性”成了《綠皮書》重點開掘的類型元素,而這正是擅長低俗喜劇的彼得·法拉利導演的優勢。
總之,《綠皮書》在主題上回應了社會熱點和民族關切,通過一名白人與一名黑人在旅途中建立起跨越種族與階級的友誼的故事,想象性地彌合了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矛盾隔閡并達成和解,從而整合了當代美國種族問題上的個體認知與民族身份問題;同時,影片在因襲“類型范式”和“前文本”成功經驗基礎上的適應性創新,使其藝術性和商業性得到了很好的平衡。任何一部影片的創作與生產,都受到政治意識形態、類型范式、前文本、市場因素等的影響,這些因素如隱藏的暗礁,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最終投射在電影文本中。在影片的敘事框架內,尋找它們之間的最佳平衡狀態,成了考驗影片編劇、導演等電影創作者藝術水準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