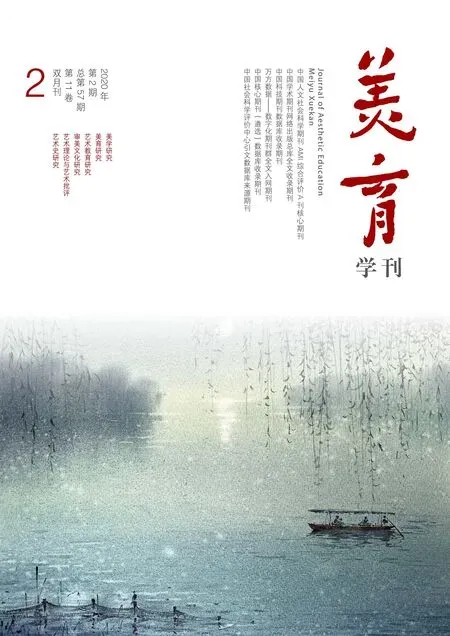身體感性的凸顯
——論西方身體美學的美育觀
張文彩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當前方興未艾的身體美學,是在美學整體轉向生存和生活的大背景下出現的,它反過來又對人的生存活動和生活觀念做出了新解釋,帶來了新啟示。這種啟示是多方面的,僅就美育觀念來說,身體美育觀不僅沖擊了傳統的美育觀念,而且為美育的性質、對象、途徑等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本文以身體美學具身實踐觀為基礎,具體討論它在上述方面對美育觀念的啟示。
一、身體感性從掩蔽到解蔽——一個美育史的視角
在整個美育史上,受強大的身心二元論傳統的影響,美育所堅持的主流觀念是一種“心育”觀念,這種觀念認為,我們可觸可感的感性世界是雜亂無章的,只有通過對它的壓制和對理性的推崇,才能到達某種理想的境界。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不獨身體感性,事實上整個感性世界都處于一種被輕視、被掩蔽的狀態。我們看到,在西方,在最早對美育做出討論的柏拉圖看來,情感和感性極容易引起人的“感傷癖”,從而有害于公民的理性和德性的培養,為了達到理念的目的,柏拉圖排斥和壓抑感性情欲。亞里士多德則稍好一些,他肯定了人的感性情欲的現實性存在,但依然認為美育就是借由理性而對感性加以節制,從而達到凈化的效果。而在隨后的中世紀里,在宗教的統攝下,心靈的陶冶凈化成為皈依上帝的基本方式,而身體感性則被視為罪惡,上帝并不居住在混亂不堪的此岸世界,在奔向上帝的不斷“提純”過程中,身體感性被拋棄。正如普羅提諾所說:“心靈一旦經過了凈化,就變成一種理式或一種理性,就變成無形體的、純然理智的,完全隸屬于神。”[1]
西方現代美育的代表人物是席勒,他也是傳統“心育”觀念的典型代表。在《美育書簡》中,席勒顯然承認了感性的存在以及人對感性現實的欲望和情感,并在此基礎上認為美育就是感性教育和藝術教育,主張陶冶人的感性,以此糾正單向度的理性范疇的片面、缺陷和狹隘,這對于美育學科的發展來說可謂厥功至偉。然而,席勒對感性的承認是不徹底的,因為在席勒的邏輯里流淌著傳統形而上學的血液,它突出表現為心靈和觀念對感性現實的絕對領導。《美育書簡》在修辭和觀點上,都將感性現實作為理性規則的對立面來看待。例如,席勒說:“只要粗野的自然還過于強大,除了不斷地從一種變化走向另一種變化之外不知道有別的規律,那么它就用自己不可抑制的任意活動來對抗必然性,用自己的不安定來對抗恒定性,用自己的依賴性來對抗獨立性,用自己的不滿足來對抗崇高的樸素。”[2]在席勒的邏輯中,感性自然和理性精神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用美來調和二者,最終卻是以理性精神自上而下地改造感性自然。感性的陶冶,其實是形式法則對感性沖動的抽空與馴化。很顯然,席勒所主張的感性教育事實上是理性對感性的秩序化。我們看到的,是“假扮成審美的理性為了盡力認識和控制對手,悄然鉆進了感覺的空帳”[3]100-101。審美事實上并沒有從物質感性生發并自下而上地建構,相反,席勒用游戲沖動褫奪了感性沖動的動態力量,這樣,被抽空的感性和情感才和理性相協和,在此,身體感性被巧妙地掩蔽了。
擴而大之,席勒的美育思想是德國古典美學思想的代表,而后者依然堅持著西方強大的身心二元論傳統。因此,雖然西方美學自鮑姆嘉登開始,美學作為感性學就已經被奠定,但那種感性卻總是一種被理性秩序化的感性。在鮑姆嘉登之后,在康德、席勒、黑格爾等人的龐大體系中,美學作為感性學仍僅僅被作為低一級的認識論而被提及,它總是呈現為心靈、思想、靈魂的侍從,被看作認識論的婢女,感官和感性僅僅獲得了有限的地位。我們已經看到,在席勒那里,是理性“悄然鉆進了感覺的空帳”,而在康德那里,審美判斷拒絕了感性世界的內容,審美愉悅不可摻雜任何私人的快適和激動,感性經驗因被先驗形式灌注而不斷消解。在黑格爾那頗具陽剛氣的體系中,美則成了理念的感性顯現。非常明顯,為現代美育奠定觀念基礎的整個美學思想,雖然把美學設定為感性學,但事實上并沒有站在感性現實這一面來發展感性,而是都用理性形式把感性圈了起來,然后將其整體性地忽視了,感性地位已如此低微,更遑論與感性直接相關的肉體性或身體性了。
在中國古代主流的美育觀念中,身體感性同樣沒有得到正面的彰顯。中國古典美育側重于人生和倫理問題,強調通過審美活動和藝術活動來實現人格的養成,而這種人格是合于道的人格。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是以儒家為中心而形成的,而儒家進行人格教育的重要手段是詩教和樂教,詩教和樂教的目標則是讓人合于禮。因此《樂記》中才說:“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4]很顯然,儒家的美育,是要用飽含社會倫理規范的藝術作品,去感染浸潤人,使人能夠發乎情而又止乎禮。這是一種將倫理規范內化為個體內在情感需要的過程,也事實上是以理化情、以理節情的過程。在這樣的美育傳統中,我們雖然看到大量的身體意象,比如《禮記》中對于身體儀態和身體行為的討論,但這種身體僅僅是作為手段呈現的,即為了合于倫理規則而呈現的,其被動一目了然。身體感性在這種美育傳統中自然無法得到正面的重視,正如有學者總結的,“從整體與綿延的歷史來看,‘身體’意象由于受到以儒家為首的‘禮’與‘理’的壓制與溫情的弱化,它本身始終是處于虛無的被否定的地位的,是作為官方與正統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來存在的”。[5]
以追求個性完善和感性啟蒙為特點的中國現代美育觀,在吸收中西方美育觀念的人格教育、感性教育、藝術教育等創見的同時,也分享了它們對身體感性本身的忽視。這一情形在王國維的教育思想中便已出現,在《論教育之宗旨》中,王國維認為,“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為調和之發達。而精神之中又分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對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備真美善之三德,欲達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6]很明顯,王國維倡導的美育,包含在“精神”之下,美即感情之理想狀態,美育的目的是心靈的完善,而身體之發達只關涉到與精神教育相對的體育,因此他對感性的尊重并不徹底,而對身體感性之于審美的重要意義則更無討論。與之相似,蔡元培從審美的“無利害性”角度論述美育,認為美育使吾人“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7]。在蔡元培看來,美育可以去除個人私欲,從而使社會和諧。無獨有偶,朱光潛也認為現實的人心受利害關系的束縛,因而主張無功利的審美,以化解人的功利心。但是在蔡元培和朱光潛所倡導的那種有距離的靜觀審美中,感性被理性觀照的同時也被防范,形式化的同時也在抽離其本身的活態力量。而且,當個人的感性和個性遭遇理性與社會時,感性、個性要無條件地服從理性和社會。在他們的審美無功利學說背后,其實指向一種啟蒙理性的功利主義,這一指向當然有其時代的積極意義,但就美學和美育本身來說,它有存理性滅感性之嫌。
美育的歷史發展表明,審美的基本義是感覺、感性,而在中西方的美育史上,雖然都對身體感性做了強調,比如中國古代對人物形貌的品評;比如古希臘時期對健碩和富于比例的身體的推崇;比如以張競生為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對身體美的重視;在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研究中,已經揭示了人的生理節奏和審美節奏感的對應性,等等。但我們認為這依然是不系統和不充分的。這種不完全和不充分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身體感性的基礎性地位并未得到承認。受身心二元對立的影響,在中西方的主流美育觀中,美育事實上處于理性的管制之下。中西方要么為了倫理規范,要么為了糾正科技理性,要么為了順應啟蒙理性,都將感性視為被改造的對象,剝除感性中粗俗的、野蠻的、活潑的、原初的力量,以滿足道德理性的需要。正如沃爾夫岡·韋爾施所說,美育和美學“沒有發展認識和解放感覺的策略,而是發展了控制感覺、消滅感覺和嚴格管理感覺的策略”[8]。這種對感性自上而下、由心到身、由觀念到現實的控制,導致了對感性另一個方面的忽視,即對感性自身范圍的細致開拓。感性往往被限制在藝術感性、與人的心理相關的情感感性等方面,而感性的具身性維度或肉體性維度被忽視了,身體的主體性維度也未得到承認。
為此,身體美學旗幟鮮明地要求糾正上述兩種缺憾,解蔽身體感性。身體美學從誕生起,就拒絕唯理智論者將感覺或感受摒棄為理解的敵人,拒絕將事物的感性內容從理想化的形式中剝離出來,主張感性現實才是美學的開端,更重要的是堅持身體是這感性現實的重要維度。正如伊格爾頓所考察的:“美學是作為有關身體的話語而誕生的。……那個領域就是我們全部的感性生活——諸如下述之類:愛慕和厭惡,外部世界如何刺激身體的感官表層,令人過目不忘、刻骨銘心的現象,源于人類最平常的生物性活動對世界影響的各種情況。美學關注的是人類最粗俗的、最可觸知的方面。”[3]1
身體美學認為,既然美學是作為感性學而誕生的,就應該回歸它的原初定義去承認和思考感性及其肉體性。身體美學的預言者尼采很早就發出復仇式的呼喊:“我懇求你們,我的弟兄們,忠于大地吧,不要相信那些跟你們侈談超脫塵世的希望的人!他們是調制毒藥者,不管他們有意或無意。”[9]現實的生存是值得探究的,美的追尋應該從“大地”、從身體、從生存的現實出發,而不應該從虛幻的彼岸世界觀照。而在梅洛-龐蒂、福柯、舒斯特曼等身體美學的積極開拓者那里,我們同樣能夠看到他們對感性的肉體性維度的披示。福柯將自己的作品看作其生活和行動風格的注腳,而其現實生活則呈現出富于激情的感性力量,這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表現為對瘋癲、死亡、激情等的關注,在這種關注背后,潛藏著福柯對身體感性的某種癡迷。在梅洛-龐蒂眼中,美學應該注重人在具身參與世界的過程中產生的那種原初而直接的身體體驗,這種知覺現象學的直接性是基本的出發點,從此出發,才可以談論和理解藝術、理解審美。而舒斯特曼對感性的尊重在其為通俗藝術和大眾文化的辯護中已經展露無遺,在舒斯特曼看來,大眾文化盡管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卻反映出了人的情感的真實性和純正性,它是人的直接的、活潑的、樸素的、原初的感性的呈現,相比精英藝術,通俗文化所呈現出的感性里帶有感性肉體性的反叛色彩,比如,“由搖滾激起的那種更加精力充沛的和充滿肌肉運動感的反應,揭穿了傳統審美態度的無利害的、有距離的沉思的根本被動性”[10]。因此,基于身體美學這樣的觀念而生長起來的身體美育必然會強調身體感性的重要意義,或者更明確地說,身體美育主張解蔽長期壓制的身體感性,將美育理解為一種身體感性的教育。
二、身體感性教育的性質與對象
身體美育對身體感性教育的性質、對象、途徑和目的都做出了說明,展示出了理論的自覺。
就身體感性教育的基本特質來說,它是以身體為主體的具身實踐教育。這一判斷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涵。一方面,身體感性教育強調身體的主體性。在審美教育中,身體既是審美的主體,也可以是審美的客體;既是進行審美體驗的主體,也是接受審美教育的客體。以往的美育思想都多將身體看作惰性的客體,強調心靈對于這一客體的作用,身體美則主要是指形體美。而身體美學則強調,在美育活動中,身體首先是主體,據舒斯特曼強調,這一主體是整個身體美學研究課題的核心。它不再是充滿惰性的,而是“活生生的、敏銳的、動態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身體”[11]1。而身體感性教育活動應以這一活生生的、有目的有欲望的、體現出自身創造性和能動性的主體的參與為前提,作為客體的身體也應當在作為主體性的身體這一視角下去看待,也就是說,傳統美育中對于諸如形體美或儀態美的強調,只有在納入身體主體這一邏輯下才更完滿、更充分、也更有效。
另一方面,身體感性教育強調了身體的在世生存過程本身。因為具身實踐具有動態性和過程性,這讓身體感性教育跳出了傳統的二元對立思維。也就是說,美育既不是心靈對身體的靜態觀照或規約,不追求理性對感性的先驗牽引;同時,美育也不期望身體感性對理性的淹沒,不主張感性的泛濫或野蠻生長。相反,身體感性教育主張從感性本身出發,同時不拒絕理性的作用,在具身性的生存實踐過程中將感性和理性統一起來,感性和理性都內在于不斷完成的具身生存過程中。
進一步講,這種具身性的生存活動也是體現身體美育超越性的過程。實在地說,審美活動中的形而上超越性維度和以肉體感性為基礎的直接性維度應當是統一的,而以往的美育觀念并沒有充分關注后一維度,同時也就沒有充分重視站在后一維度向前一維度進行超越的連續性和必然性。這種忽略其實是強大的心育傳統使然,因此是作為生存實踐的身體美學所力圖糾偏和補充發揚的。在身體美育看來,感性并不是認識論意義上膚淺的、低級的認識,而是生存論意義上的人的豐富而具體的生存狀況。正如杜衛所發現的,感性意味著個體生存的具體性,意味著人的肉體性,意味著人的生命活力,也意味著以情感為核心的心理能力和體現于直觀形式中的觀念意識。[12]因此,在生存論意義上,身體感性就不僅僅是某種混亂的、惰性的、無序的、片段式的感性材料的堆積,它更具有向上超越的維度,蘊含了人的生命力和情感能動性的身體感性,在動態的具身生存過程中,會與理性活動結伴,逐漸走向整一的、立體的感性經驗。
如此說來,身體感性教育便不僅限于學校美育和藝術教育,而是擴大到整個生活領域中。以往的美育主張以心來牽引身的心育,而學校教育和藝術教育是這種定向性教育的最佳手段。與心育觀念不同,身體感性教育將美育看作從感性出發的生存實踐活動,而且這個生存過程本身就是感性的升華過程,也是人的完善過程。因此,可以說,只要有身體感性活動的地方,都可以是身體美育的領域。雖然藝術教育是感性活動的重要領地,但顯然感性活動并不限于此,事實上,人的整個生活領域都具有感性活動。在上述意義上,身體感性教育倡導的是在整個生活領域來完成感性完善,主張在生活實踐中,人人都可以成為生活的藝術家。
就身體美育的對象來說,整個身體感性都應成為對象,但具體說來,身體感性教育的主要對象包括三個方面,即身體感官知覺、身體習慣和身體欲望。
首先是身體感官知覺。發展身體感知能力,培養身體意識,這是體現身體主體性的最基本的表現。正如舒斯特曼所說,“身體美學盡管也關心形體的外在之美以及其他一些外在的身體表現和標準,但是,它所探討的主要是身體本身的內在感知與意識能力”[11]4。這種身體的感知能力和意識能力通常表現為在審美活動中體驗美和生成美時的特殊感受力,具體說就是身體感官的感受力和身體知覺能力。
身體感官的感受力不僅包括視覺、味覺、嗅覺、觸覺、聽覺等通常的感官能力,而且也包括身體的動覺,即一種位于肌肉和身體內部的感受器,它為我們的活動提供位置和信息。如果說身體感性教育活動是具身性參與世界的一種方式,那么,身體感官的敏銳性和豐富性對于身體在世界中的存在至關重要,因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美育作為一種感性教育,是以人們對對象的直接感知為基礎的,也是以人的感性不斷敏感和豐富為目的的。人的感官如果長期不去感知,就將變得遲鈍,就將逐漸退化”[13]。豐富敏銳的身體感官,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加精微的身體經驗,這有利于增進我們對于身體狀態和感受的意識,從而為我們把握自己的情緒狀態、“關心自己”提供更多的洞見。
身體感官的有機統一會形成身體知覺,但是,在身體美學看來,身體知覺不僅僅是像格式塔心理學所發掘的那樣,是一種把感覺材料加工組合為整體性經驗的能力,它更是我們覺知感性世界的第一道門。在生存論的意義上,身體的知覺經驗構成了我們看待真善美的基礎,那種原生的經驗恰恰也是美學所要探明的感性世界。正如梅洛-龐蒂所主張的:“知覺的經驗使我們重臨物、真、善為我們構建的時刻,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初生狀態的‘邏各斯’,它擺脫一切教條主義,教導我們什么是客觀性的真正條件,它提醒我們什么是認識和行動的任務。這并不是說要將人類知識減約為知覺,而是要親臨這一知識的誕生,使之同感性一樣感性,并重新獲得理性意識。”[14]很顯然,身體知覺并不僅僅在整體能動地認知世界方面起積極作用,在現象學意義上,它更是意義生成的基礎和理性認識的前提。
因此,對于感官和身體知覺的研究與陶冶,不僅是提升我們的身體審美注意力的重要手段,更是構成我們審美經驗的重要手段。因為身體感官和身體知覺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它因身體知覺的整體性和創造性而有可能形成美感,或者如杜威所看到的,將我們的感官聯合起來,就會形成一個完整的經驗,這樣的經驗具有美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說,身體知覺活動構成了我們審美活動的基礎,它對于身體感性教育意義重大。
其次,身體習慣也是身體感性教育的重要對象。身體習慣的獲得是在具身實踐過程中完成的,它既是個體具身生存經驗在身體上的積累,也是社會文化和倫理原則在身體上的呈現。按照布爾迪厄社會學的理解,習慣具有明顯的身體性,這個概念表示“一套深刻地內在化的,導致行為產生的主導傾向。它們指向一種實踐的而不是話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識的,身體化的同時是認識的,再生產的但又是創新的行為的理論”[15]。這個描述向我們指明了身體習慣的一些特點:第一,它是社會性實踐經驗的內化或身體性沉淀,表現出明顯的時間積累性。第二,身體習慣具有非反思性。這意味著,身體習慣不僅在獲得過程中可以是無意識地自然獲取,而且在身體實踐過程中,既成的身體習慣對我們生活實踐的指導也并不是有意識的,而是非反思的和無意識的,它在無形中影響了我們正在進行的身體行為和身體反應。然而第三,身體習慣并非不可改變,相反,它有極強的可塑性。可塑性的達成既可以是無意識的,也可以是有意識的。也就是說,身體習慣的改變可以在個體與世界的互動中自然地完成,也可以在個體有意識的、反思性的觀照下,有針對性地改變。
這樣的身體習慣,對身體美育具有重要的價值。威廉·詹姆斯說,身體習慣“簡化了為實現一個特定結果所需的運動,它使這些運動變得精確,并且減少了疲勞”[16]。身體習慣的非反思性使我們的行動更為自然和精確。舒斯特曼同意詹姆斯的觀點,同時進一步認為,對身體習慣的反思性觀察,可以改善我們的身體意識,從而促進自我認識和自我判斷,以更好地實現行動目標。更廣泛地說,身體美育旨在讓人更好地在世生存,讓行動更完善。身體習慣正具有這樣的功能,因為個體具身化地參與世界,將與世界互動交流的經驗內化于身體上,這種對于經驗的身體性保存并不是單調被動的,而是具有指導性和生產性,它對個體未來的生存行為具有導向和規范作用。因此,以身體習慣為抓手,完全可以進行身體感性的提高完善。
最后,身體美育將身體的欲望和需要也看作審美教育的一部分。身體美學并不認同康德所堅持的審美經驗的非功利性,相反,它在根本上認同尼采的主張,即應該將審美看作是某種生理學的美學。尼采不斷將我們在文化上的精微審美判斷追溯到更為原始的本能,在尼采看來,離開了我們最基本的自我保存的價值,去判定事物的美或者丑是沒有意義的。審美經驗誕生于我們的生存欲望,在身體與環境溝通時所出現的身體需要或身體欲望中,審美經驗出現了,并隨著這種身體欲望的解決而逐漸發展。
福柯繼承了尼采對身體欲望、情緒和情感的重視,在《瘋癲與文明》中,福柯揭示了帶有狄奧尼索斯精神的“瘋癲”是如何被現代理性文明幽閉起來的,在看似冷靜的歷史描述背后,潛藏了福柯對于沖動、瘋狂、欲望、情緒性的狀態、極限體驗等的辯護。在福柯看來,這種類似狄奧尼索斯精神的瘋癲,意味著某種未分裂的狀態,它是審美因子的母體。在這個意義上,福柯描畫的并不是瘋子,而是一種瘋癲狀態或者審美狀態,正如《瘋癲與文明》的評閱人康吉蘭所察覺到的,“該書寫的實際上完全不是精神病,而是一些藝術家和思想家們的生活、言論和作品所富有的哲學價值,而那些藝術家和思想家,習慣上都被認為是一些‘瘋子’”[17]。
進一步講,在身體美學思想視域中,由人的身體感官引發的情感、情緒、欲望等是需要尊重的,這種尊重是自我關懷的重要部分,也是培育完整的人所必然考慮的。也就是說,人們對自我的關心,不僅要著眼于心靈的完善,而且要考慮身體情感和身體欲望,甚至可以說,不關心身體情感和身體欲望,根本就無法實現真正的關心自己。也可以說,“在大多數情形下,大部分人認為如果他們行所行之事(自行其是),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對欲望、生活、本性、身體等等問題的真相有所了解”[18]156。身體感性教育主張關注人的情感、情緒及欲望,肯定而非拒絕它們,其目的就在于培養自由的人,實現完整的自我。
三、身體感性教育的途徑
我們認為,身體美學對身體感性教育途徑的討論,也應該在“具身實踐”這個界域中來進行。身體的具身實踐活動實際上是身體的在世生存活動,而這一充溢身體感性的具身實踐活動,可以有三個維度,即身體前反思地在世、個體的反思性在世和個體生存中的感性欲望。與此相對應,身體感性教育也可以有三種途徑來深化這三個維度。
(一)前反思的身體陶冶
身體美學認為,在身體的在世活動中,有一種前反省的、非課題化的維度。現象學家梅洛-龐蒂充分強調了這一維度。按梅洛-龐蒂的理解,我們被拋入世界的過程,就是身體向著世界和他人展開的生存運動過程。這種展開活動首先并不表現為理性主義的那種明確的主客體意識和課題化態度,而是首先表現為身體知覺對現象世界的整體性感知和綜合。這種身體知覺的綜合不是思維主體在形而上學的場域中對事物的概念化把握,而是身體憑借其身體圖式(bodyschema)的前邏輯統一性,對直接的物體和世界的意向性綜合。舉例來說,當我感知我正在其上打字的桌子時,這種知覺活動是十分投入的,因此我在實際上感知桌子的時候并沒有意識到我在感知桌子,而如果我一旦意識到我在感知桌子,那么我其實已經從這種身體知覺活動中抽離出來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將桌子分解為各種具體的屬性,以理性分析來構建我們在知覺活動中的桌子的對等物。因此,相比于理智的綜合,這種身體知覺的綜合是前意識的和前反思的,并且它沒有抹除世界的質感,相反,它充分尊重了現象世界的質感,以身體知覺的方式將世界的那種原初的、活生生的狀態呈現出來,表現出了對身體感性的充分尊重。
那么,如何來提高這種前反思維度的身體感性呢?我們認為,這首先要明確這種前反思身體實踐活動的基本特點。梅洛-龐蒂已經明確指出,這種具身實踐活動是身體與世界的一種相互成就,有機交互的身體意向性關系。這意味著身體的感知能力離不開世界,正是在身體與世界的有機關系中,才會出現感知、體驗和意義。因此,梅洛-龐蒂才說,身體感知“顯現的既非純粹意識也非純粹存在,而是如康德本人所洞見到的,是體驗。換句話說,它是一個有限主體和一種非透明存在的交流,主體就在這種交流中出現并仍然置身其中”[19]。此論和杜威相似,指明了審美感性經驗奠基于其中的生活經驗,是誕生于活的身體與世界的相互交流之中的,只不過,梅洛-龐蒂在這里充分披示了它的非反思性。
既然明了了這種前反省的身體感性奠基于身體與世界的原初有機關系,那么,積極構建一種具有良好生態性的身體與世界關系,就應該是進行此一維度身體感性教育的必然選擇。身體開始在世界中活動時,就必然會感知事物,而其中感性沖動定會先于理性判斷,身體的感性審美經驗會在無意識狀態下悄然進行,而身體的前反思的感知能力也會被所處世界不斷重新塑造。身體所處的外部世界不同,身體與世界的整體關聯就會發生變化,這必然會影響身體的感知能力和身體感性體驗。不健康的身體與世界關系會導致身體感官的鈍化、平庸化,身體感性也就會缺乏豐富性,相反,良好的身體與世界的關系則會促成身體感官更加敏感,或者銳化,身體感性也會更加細膩、微妙和豐富,由此獲得的審美經驗也會更加豐富。
那么,什么是良性的身體與世界的關系呢?我們認為,應當是古人所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的狀態,這并非倡導一種人對世界的消極被動狀態,而是一種人詩意地棲居于世界,人與世界相互成就并各成其是的狀態。這也就是一種人與物的自由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人與世界的關系也就是一種審美關系。曾繁仁對這種審美關系做過如下描述:“對象與主體構成‘此在與世界’共存并緊密相聯的機緣性關系,人在‘世界’之中生存,如果自然對象對于主體(人)是一種‘稱手’的關系,形成肯定性的情感評價,人處于一種自由的棲息狀態,是一種審美的生存,那么人與自然對象就是一種審美的關系。”[20]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狀態,然而卻是我們審美教育要構建的方向,那種前反省的身體感性的陶冶也應以此為標準和目標。
(二)反思性的身體訓練
理論反思活動是人的具身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身體感性教育的另一個維度便是課題化、反思性的維度。理查德·舒斯特曼對這一維度有重要的開掘。舒斯特曼當然承認梅洛-龐蒂所揭示的那個前反思的、未分化的身體知覺世界的重要性,也承認我們身體感官和身體行為的無意識維度。但是,那個前反省的、沉默的身體知覺世界對于我們身體感性的培養未必總是好的,尤其是當身體在一個不那么好的世界中存在時。因此,舒斯特曼才會說,“我們未經反思地獲得壞習慣如同獲得好習慣一樣易如反掌”[11]95。因此,舒斯特曼倡導一種更加明晰的、課題化的、反思的身體感性教育維度。這一維度是存在的,舒斯特曼強調說,“我們的身體有各種能被意識到的、明確的、體驗性的感知:它們包括清楚的感受、觀察、呈現于內心的視覺化以及其他一些對于我們身體及其部分、表層或內部的精神性的再現。它們的清晰或再現性的特征,將它們從梅洛-龐蒂所提倡的那種原初意識中明確區別開來”[11]81-82。而舒斯特曼對于這一反省維度的討論,對身體感性教育頗有啟發。
在反思性的維度上,身體美學提供了身體感性教育的具體路徑。即進行反思性的身體訓練,通過修正身體習慣,來改善身體意識,進而培養身體感性。反思性的身體感性教育,就是要有目的地糾正我們錯誤甚至有害的身體知覺、錯誤的身體自我使用,以便達成身體的改善,最終實現自我的改善。非常明顯,這種身體感性的培養,不能依賴于那種未經反思的身體自發性,因為那種自發性已經被污染了。正因為此,“未經反思的行動或習慣必須被帶入自覺的批判性反思(即使只是在有限的時間內),這樣它才能被掌握,能夠更加正確地工作。除了這些治療性的目的外,身體反思的訓練也增強我們體驗的豐富性、新穎性和愉悅感,而這些都是改善后的意識所能帶來的”[11]96。不僅如此,身體意識的改善,也會使我們的感官更敏銳、行動更為有效,從而更好地達成目標。比如,有意識地糾正我們的行走姿態和呼吸方式,有意識地訓練我們的身體感官知覺,都可以改變我們對環境的體驗和對自我的態度,這種對身體感受的留意,有效地增進我們對自我情感和意愿的理解。
最終,這種對反思層面的身體訓練和感性培養會在兩個層面上形成結晶。一方面是個人層面上,使人形成對科學規律的尊重意識,在遵循規律的前提下進行自我訓練,進而實現人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形成大量不同訓練方法,以改善我們的經驗和身體。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藝術教育,通過進行藝術感知以及反思性地調節我們感知藝術的身體態度,我們可以更加敏感而有效地使用我們的感官,進而提升我們的感性能力。當然,這個身體訓練的方法還可以列舉一長串:瑜伽、按摩、冥想、有氧運動、亞歷山大技法、費爾登克拉斯法、服飾形式,等等。而這兩個向度上的成果,會形成某種良性循環的基礎,可以進一步推動身體感性的反省維度的教育。
(三)身體欲望管理
如前所述,身體感性教育必然會關注與我們身體相關的情感、情緒和欲望。這些與身體相關的情感、情緒和欲望是在人的具身實踐活動中綻露出來的,它們誕生于我們現實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對于這種身體情感和身體欲望的管理,也是關心自己的必然要求。那么,以何種方式來管理這種形而下的日常身體欲望呢?或者說,以何種方式來關心我們的肉體呢?對此,美學上大致存在兩種方式:規訓技術和自我技術。
現代性的美學觀中有一種取向,認為美存在于一個廣袤無垠的烏托邦空間中,它遠離了趣味索然的物質現實,審美領域要防止經驗世界的污染,因此要與經驗世界相分離,而隔離的方式就是規訓技術。與身體相關的欲望和非理性自然處于經驗世界,也自然是被規訓技術隔離或排擠的對象。規訓技術將身體欲望看作危險的他者,然后用一系列外在的話語、知識、權力規范來持續地對身體欲望進行拆解和重組,以使其符合于某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道德法則,在這種黯淡的視閾中,身體欲望是被動的、絕望的和危險的。
與現代性美學的上述取向相反,身體美學利用自我技術來管理身體欲望。自我技術“使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狀態”[18]54。由此可見,福柯所指認的自我技術并不否定身體欲望,相反,它直面身體欲望,直面快感和欲望的肉體性,通過對欲望和肉體快感的管理和塑造,達到一種個人生活的完善狀態。福柯將自我技藝也稱作“生存藝術”,它主要面向的是像飲食、養生、性愛、友誼這樣的日常生活實踐。在這樣的日常生活實踐中,人對自身的塑造,對欲望的管理并沒有拋棄理性的因素,相反,它非常倚重反思的能力來形成一種與自我的新型關系,這種關系讓人擺脫快感和欲望的驅使,超越內心激情的束縛,保持理性上的平靜,實現某種對自我的充分享用。自我技術的基本目標就是實現人對自我的操控,進而達成自我的轉變和完善,也就是說,讓自己成為自己的主宰。
如果說規訓技術塑造的是一種標準化的、馴順的身體主體,那么自我技術則會形成一種風格化或藝術化的自我。自我技術當然要求對自我的嚴格控制,但“這一主體被塑造為自己的主宰所包含的節制要求并不具有人人都應該俯首聽命的一種普遍的法律的形式,而是針對那些想讓自己的生存具有盡可能美的和完善的形式的人來說,它是一種行為風格的原則”[21]。事實上,在日常生存實踐中,個體憑借自主運用其理性能力來直面自身的身體感性或身體欲望,避免墮入某種普遍理性規則之中,從而實現某種藝術化的生存,這一道路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而這也是身體感性教育所遵循的。
四、結語
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發展是人類社會追求的偉大目標,相應地,它也構成審美教育的終極目標。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一個重要向度就是身體的解放,或者說是感性的解放。可以這樣說,身體不自由,感官不自由,就談不上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或者說感性的自由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題中應有之義。應身體美學所啟發的身體感性教育,其最終目的便是促成人的身體解放和感性解放。我們已然看到,為實現這一目的,身體美育將身體感性從“心育”傳統中解放出來,然后通過身體與世界的生態性關系來陶冶身體感性,以身體訓練和身體欲望管理來提高身體感性,希望在一種具身實踐過程中,完成身體感性的解放和提高,最終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進一步講,身體美育所倡導的身體感性解放最終落腳在個體的自由完善上。個體在社會中,其個體感性要么會受到道德的管制以服從某種普遍的現實原則和道德原則,要么受到理智的排斥而抽空了感性的豐富性和個別性。針對此,身體美育在身體感性的基礎上發展一種美德倫理學,一種新的自我關系,這是一種倡導個人風格化和藝術化的生存倫理。在這樣的生存倫理中,個體的行為習慣、情感欲望、感官感受等均得到尊重,并以它們為現實土壤,生長出一種藝術化的人生,也即一種自由人生。
可以說,相比于美育史上對身體意象和身體感性的零星討論,身體美學所倡導的身體感性教育已經相當系統化了。身體美學對身體感性教育的地位、性質、對象、途徑、目標等均有明確的說明。這種系統性最集中地表現在身體美學對身體感性教育性質的說明上。身體美學認為身體感性教育應該發揚一種具身的實踐性,感性的解放應當在具身實踐過程中實現。只有在這一界域內,才能夠充分理解身體美學對身體感性的凸顯。身體美育這一系統性的觀念,盡管有拔高身體之嫌,但對“心育”傳統而言,不失為一種有益的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