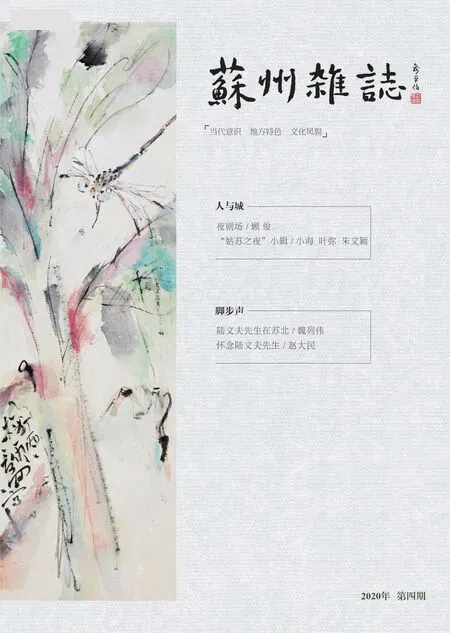懷念陸文夫先生
趙大民
那一日,與蘇州的朋友通電話,就又說(shuō)起陸文夫先生來(lái)。轉(zhuǎn)眼間,先生已經(jīng)去世15年了。我們都懷念著他,我也不由得又回想起見(jiàn)先生的情景來(lái)。
1986年,我還是一個(gè)十五六歲的孩子,張良街也只是去過(guò)一兩次,魯山城連邊兒也沒(méi)有沾過(guò),出門(mén)見(jiàn)山,回頭還是山,就一直長(zhǎng)在那個(gè)叫石圪尖的山窩里。
八月間暑假里,我接到了去蘇州參加由全國(guó)中學(xué)生作文與文學(xué)講習(xí)所、《語(yǔ)文報(bào)》等單位舉辦的全國(guó)中學(xué)生文學(xué)筆會(huì)的通知。
得了信,娘比我還要高興,趕了好幾夜,給我做了一對(duì)新布鞋和一條新褲子。但娘也和我一樣發(fā)愁,不知道怎么乘火車(chē)去蘇州。娘領(lǐng)著我走遍了一個(gè)莊子,最終從一個(gè)當(dāng)過(guò)兵的叔叔那里問(wèn)出個(gè)門(mén)道來(lái)。娘說(shuō):“記好了沒(méi)有?別忘了。到地方了,跟娘寫(xiě)個(gè)信,要好好跟老師們學(xué)習(xí)。”
第一天給我們講課的是詩(shī)人朱紅和散文家范培松老師。朱老師儒雅,似乎要比范老師年長(zhǎng)些,而范老師當(dāng)時(shí)在蘇州大學(xué)當(dāng)老師,年輕帥氣,已是很有名的散文家和文藝?yán)碚摷摇K麄兊恼n講得認(rèn)真,同學(xué)們聽(tīng)得也專(zhuān)心。
那天傍晚下課的時(shí)候,主持的老師給大家說(shuō),明天中國(guó)作協(xié)副主席陸文夫先生要來(lái)。他還說(shuō)先生剛從美國(guó)參加第48屆國(guó)際文學(xué)筆會(huì)回來(lái),還沒(méi)有好好休息,就答應(yīng)給我們講一課。
那個(gè)時(shí)候,我讀的書(shū)很少,買(mǎi)不來(lái)書(shū),也沒(méi)有錢(qián)買(mǎi),不少的文學(xué)作品都是從收音機(jī)的“小說(shuō)連播”中收聽(tīng)。陸文夫先生的《圍墻》《井》就是聽(tīng)來(lái)的。除了這兩部聽(tīng)來(lái)的小說(shuō),別的再也沒(méi)有讀過(guò)。
第二天上午,同學(xué)們還沒(méi)有到齊,先生就走進(jìn)來(lái)了。他向我們揮手打著招呼,一直都是微笑著。他那一身行頭,在我這個(gè)山里孩子看來(lái)都很寒酸,淺灰色的上衣和褲子都打著褶,光著腳,沒(méi)穿襪子,就穿著一雙灰色的塑料涼鞋。先生中等的個(gè)兒,瘦削,那裝扮愈發(fā)顯得人黑瘦,我就想起家鄉(xiāng)種地的叔伯來(lái)。
陪我們聽(tīng)課的還有車(chē)前子、陶文瑜、李希文、孫駿毅等青年詩(shī)人和作家,他們不時(shí)做著筆記,比我們還要專(zhuān)注。他們都是很有才華的老師,比如車(chē)前子老師的詩(shī)和散文皆好,是有“江南才子”名號(hào)的,他們說(shuō)這是一個(gè)難得的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
先生講了一個(gè)上午,天氣熱,沒(méi)有空調(diào),那時(shí),空調(diào)應(yīng)該還是個(gè)稀罕物。整個(gè)大廳里,兩個(gè)吊扇在呼呼地吹,還是悶。主持的老師不得不宣布休息一下,我們就沖下樓去玩耍一通,而陸先生卻還坐在那里,和車(chē)前子等交流著。
先生沒(méi)有講多高深的理論,他就是跟我們這群孩子談心交流,父親是嚴(yán)厲的,而他卻是和藹可親的。他講得最多的還是做人和讀書(shū)的事,無(wú)論是大人或孩子,無(wú)論寫(xiě)不寫(xiě)作,當(dāng)不當(dāng)作家詩(shī)人,都要多讀書(shū),做好人。他也講了世界文學(xué)的走向,講了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
先生說(shuō):“我相信在你們中間,將來(lái)會(huì)出現(xiàn)優(yōu)秀的作家詩(shī)人,更會(huì)出現(xiàn)最優(yōu)秀的人。”先生的課,通俗易懂,滿是熱情與溫暖,在我們的心上開(kāi)了一扇窗,種下了一份愛(ài)。
中午,我的指導(dǎo)老師沈融先生喊我過(guò)去和他們一塊兒吃飯,我成了唯一和陸文夫先生坐在一起的孩子。他笑著問(wèn)我是哪里人,見(jiàn)我不敢說(shuō)話的樣子,就說(shuō):“別拘謹(jǐn),就跟在家里一樣。”他還說(shuō):“飯吃飽,跟家里一樣。”沈老師介紹了我失去父親的家庭困境,他說(shuō):“你愛(ài)讀書(shū)學(xué)習(xí),就是有未來(lái)。別害怕,你看老師們多關(guān)心你,都把你請(qǐng)到蘇州來(lái)了。”
吃罷飯,和同學(xué)們一起送先生走,他還是那樣微笑著,向我們揮著手,走遠(yuǎn)了,又回過(guò)頭,揮了幾下。
以后的日子里,我想方設(shè)法去聽(tīng)去買(mǎi)去借有關(guān)先生的書(shū),從他的《獻(xiàn)身》《小巷深處》《小販?zhǔn)兰摇贰睹朗臣摇贰毒罚恢弊x到他的《人之窩》……我如饑似渴地讀先生的書(shū),也更了解先生創(chuàng)作的嚴(yán)謹(jǐn)與認(rèn)真,為人的樸實(shí)與端正。茅盾先生曾為先生的作品寫(xiě)了長(zhǎng)達(dá)14000字的評(píng)論,說(shuō),“他力求每一個(gè)短篇不踩著人家的腳印走,也不踩著自己上一篇的腳印走,他努力要求在主題上,在表現(xiàn)方法上,出奇制勝。”先生自己說(shuō),他創(chuàng)作一篇1萬(wàn)字的短篇小說(shuō),往往要寫(xiě)5萬(wàn)字的草稿,要修改四五稿,才能定稿。先生在蘇州生活了40多年,他用最自然的文字,最平實(shí)的心態(tài),寫(xiě)著蘇州的故事,寫(xiě)著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樂(lè)。他把自己沉到了那些最底層百姓的冷暖日子中去,始終如一。人送他“陸蘇州”的美譽(yù),是不為過(guò)的。
我們那一屆參加筆會(huì)的同學(xué)中,真的如先生所愿,出了“江南才女”作家朱文穎老師,出了文化學(xué)者李臻怡博士,還有學(xué)生時(shí)代已經(jīng)寫(xiě)出了好作品的洛陽(yáng)偃師籍的詩(shī)人朱海軍老師……而我依然沒(méi)有走出那個(gè)叫石圪尖的村子,我知道那些同學(xué)都是優(yōu)秀的人才,但不優(yōu)秀的我,卻一直沒(méi)有忘記先生的話,讀書(shū)學(xué)習(xí),做一個(gè)心懷愛(ài)、感恩愛(ài)的人,是我一輩子的追求。
2005年7月9日,先生在蘇州病逝。那個(gè)時(shí)候,我還在地里收著麥子,我沒(méi)有停下鐮刀,我想著先生,我的頭幾乎低到了土地里去,就流了許多的淚。
懷念陸文夫先生。我知道,他不會(huì)怪我當(dāng)了農(nóng)民。真的不會(hu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