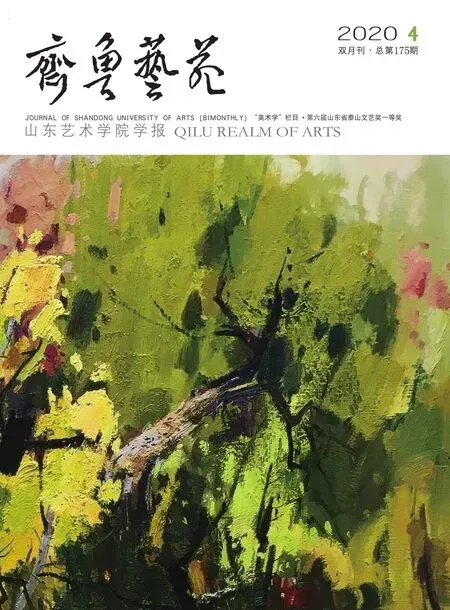生態批評視閾下的舞蹈作品解讀與闡發
范文昊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生態批評”(Ecocriticism),又稱“文學與環境研究”,是西方興起的一種批評潮流。其直接起因是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導致一系列的環境危機。特別是20世紀已降,現代工業技術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空氣污染、全球變暖、大氣層稀薄、水源污染、噪音污染等負面影響接踵而至,撼動著人類生存發展的根基。地球自然生態和人類精神生態呈現出重重危機,引發了西方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思和自省,20世紀70年代伊始,歷史、哲學、法律、社會學和宗教等諸多人文學科的研究,普遍呈現出“綠色化”的態勢,[1]加速促進了生態批評的興起。
一、生態批評的定義與應用
生態批評始于20世紀70年代,威廉·魯克爾特在《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的實驗》中,首次提出了“生態批評”這一概念。提倡將文學與生態學緊密結合,強調批評家應該具有生態視野。[2]而后“生態批評”作為文學術語,被賦予了諸多定義。主要倡導者之一的格羅特菲爾蒂認為,生態批評運用一種以地球為中心(earth-centered)的方法研究文學。哈佛學者比艾爾則將生態批評定義為:“在支持環境主義實踐的精神下進行的關于文學與環境關系的研究。”[3]較之于格羅特菲爾蒂的說法,比艾爾的定義雖過于寬泛,但包容性更強,且更具學理性。他認為,生態批評應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是一種以“環境問題為焦點”向多種方向擴展的學科。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向,將生態系統中的事物,置于相互影響的關聯中,形成了包含對思想變革的提倡,對人與環境關系現實的關注以及對倫理立場的堅持的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的共有特征。
生態批評在國內的實踐與應用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當時國內的部分學者呼吁將生態批評引入國門,應用于中國文本的研究,以便為文學研究打開一個新的視角。“生態批評”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最早出現于2001年。王寧教授在其著作《新文學史》中,首次將ecocriticism翻譯為“生態批評”。此后,“生態批評”一詞及其所代表的含義逐漸進入國內學者的視野,并產生了一定數量的研究成果。如劉蓓《生態批評研究考評》一文集中梳理了生態批評的興起與發展、原則與策略及理論建設的思路與思考;韋清琦《打開中美生態批評的對話窗口》一文主要闡述了生態批評的源起、生態批評的含義等相關問題;劉蓓翻譯的美國生態批評重要倡導者之一勞倫斯·布依爾的《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危機與文學想象》一書,則系統介紹了西方生態批評的產生背景、發展階段、主要流派與方法論。此外,亦有許多學者嘗試著將生態批評的理論用于具體的文本解讀與分析,并促成了一系列以生態批評為視角,或借用生態批評相關理論對文學、電影、美術等藝術作品進行研究與批評的成果。如孫霄《宗教典故與生態書寫——以梭羅〈瓦爾登湖〉為討論中心》、李小林《生態批評視野下的瓷板畫〈森林之歌〉研究》、余忠淑《生態批評視野下阿來作品對人與自然的生態觀照》;馬煥然《生態批評視域下〈侏羅紀公園〉系列電影》、張嘉如《論“動物倡導”文藝批評視野中的電影<可可西里>》等。這些成果都為生態批評理論在中國的應用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二、環境危機與生態意識
工業文明已降,環境問題已從單一的地方性問題,上升為全球性問題。環境危機在世界范圍的頻繁爆發,引發了全人類對生存環境的審慎思考。大量生態批評家在力圖揭示環境危機的同時,深入挖掘問題產生的根源。在這個進程中,生態意識作為有效扼制環境危機的一種自覺意識,其重要性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顯著。提升全人類生態意識,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觀念,不啻為應對環境危機最為有效的一條路徑。
在文學藝術作品中,敏銳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也注意到這一問題,以最真實的情感,喚起內心的藝術沖動,并將生態意識融入作品之中,以求引發人類對環境危機的警醒與生態意識的關注。例如,梭羅《瓦爾登湖》、華茲·華斯《汀登寺》、蕾切兒·卡森《寂靜的春天》和弗蘭克·赫伯特《沙丘》等自然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內容各有不同,但都包含一個普遍的傾向:揭露環境危機,宣揚生態意識。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認為,只有回到像瓦爾登湖這樣純粹的自然環境,才能享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真正的生活”。蕾切兒·卡森在《寂靜的春天》中,以寓言的方式描繪了一個美麗村莊的突變,并從陸地到海洋,從海洋到天空,全方位地揭示了化學農藥的危害。在影視作品中,揭露環境危機的作品比比皆是。災難片《后天》表現了環境惡化,世界進入冰河期,人類即將滅亡的末日結局;《2012》則根據瑪雅文明的寓言,描述了世界滅亡末日審判的到來;《海云臺》《雪國列車》《漢江怪物》則表現了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所帶來的嚴重的生態危機與生存危機。
在舞蹈作品中,對環境危機的描寫與生態意識的頌揚鮮明且深刻。作品《霾》中,編導立足霧霾這一空氣污染現象,展現了空氣污染所導致的環境危機正鯨吞人類的生存空間。舞蹈緊緊圍繞“霾”這一核心,充分調動一切因素來凸顯主題,使得每一處細小的設計,都蘊含著深刻的寓意。作品伊始,舞臺中僅有的幾處定點光,發出微微光亮,猶如濃烈的霧霾遮擋了絕大部分的光線,人類處于不見天日的環境中。演員渾身上下布滿的灰色粉塵,則代表了霧霾對人類切身的影響。舞臺中一顆凋零的樹木,體現了霧霾對于植物的侵蝕以及生態環境的破壞。音樂中急促的喘息聲,強化了霧霾對僅存的新鮮空氣的蠶食,窒息感撲面而來,加之演員雙手捂住口鼻等動作的渲染,“霾之下”“命何存”的畫面直擊人心。在舞劇作品《朱鹮》中,有關生態惡化引發環境危機的描寫同樣觸目驚心。在作品后半部分,人類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致使生態環境惡化,使得朱鹮的生存空間逐漸狹窄,往日藍天白云的自然環境和安逸寧靜的棲息狀態,更不復存在。舞臺中,凋敝的樹木作為舞臺布景給觀眾產生了先入為主的印象,而昏暗的燈光又進一步加劇了環境惡化的危機感,人類在面對惡化的環境時,所表現出的無奈與悲涼,使得作品的主題更加深刻。
而對環保題材舞蹈作品而言,揭示環境危機絕非最終目的,而旨在引發人們生態意識的提升以及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在《霾》的后半部分,人們一方面在霧霾的環境中努力生存;另一方面,則積極著手對自然環境進行保護。作品尾聲處出現的那一盆綠植,體現了人類僅存的生命希望,而在眾人的齊心呵護下,這一盆小小的綠植,最終使凋零的樹木恢復生機,環境也恢復到了往日的情況。而這盆綠植無疑是人類生態意識的縮影,也恰恰是這僅有的生態意識,才能逆轉環境危機帶來的滅頂之災。在舞劇《朱鹮》中,當僅存的一根朱鹮羽毛在眾人手中傳遞時,他們所表現出的渴望神情,亦是一種生態意識的體現。朱鹮羽毛對人類而言,不僅是朱鹮的象征,更是往日青山綠水的象征。而最終,人類及時地意識到了環境危機以及生態意識的重要性,才使得瀕臨滅絕的朱鹮,獲得了難能可貴的生機。而在舞劇《稻禾》中,生態意識作為核心,更是貫穿作品始終。在《泥土》章節中,女舞者雙臂環抱,彎腰踏地,開啟了稻禾的生命輪回。通過腳踏泥土,獲得了情感上的共鳴,展示了人通過大地汲取力量的過程。而在《花粉》部分中,舞蹈演員身著各種顏色的服裝,配合舒展的動作與流暢的舞步,營造了花粉在空氣中自由飄散的景象,都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生態意識與循環往復的宇宙觀念。
三、地方依附與鄉土情結
地方依附作為人類普遍情感需求,在社會中出現已久。但作為生態批評的一種理論,最早出自生態批評家勞倫斯·布伊爾的《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危機與文學想象》。布依爾認為:“地方依附是人與地方的情感連帶歸屬和認同。在日常生活里,個人和社區之間,由于個人的經驗,記憶和意向,形成了對社區這個地方的深刻附著。”[4](P77)而由地方依附引發了另一種普遍的情感趨向即是鄉土情結。不過,地方依附與鄉土情結相比,其范圍仍要大的多。鄉土情結通常是對故鄉的一種情愫,不論時過境遷,歲月波折,其如同一根紐帶牽絆著每一個在外的游子。而地方依附所“依附”的范圍,則不限于家鄉,任何有著特殊記憶的環境,都能成為地方依附的對象。而在藝術作品中,藝術家獨特的地方依附情感與鄉土情結,成為了重要的創作沖動以及作品鮮明的符號象征。例如,賈平凹熱衷于在小說中對家鄉陜西進行描寫,必定是地方依附情感發揮了作用;莫言小說中對其老家高密的描寫,張煒小說中對于膠州的描寫,都可被歸結為地方依附情感產生的鄉土情結在發生作用。而導演賈樟柯的電影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山西作為故事發生背景,也恰恰源于其對家鄉山西獨特的地方依附情感。
在舞蹈創作方面,也不乏地方依附情感與鄉土情結對藝術家產生的深刻影響。例如,當代著名舞蹈編導張繼剛的早期作品,熱衷以其家鄉山西當地的風土人情作為素材,展示了山西人粗獷豪放的性格特征。如舞蹈《獻給俺爹俺娘》《好大的風》《黃土黃》,舞蹈詩《西出陽關》,舞劇《一把酸棗》以及被譽為“黃河三部曲的”《黃河一方土》《黃河兒女情》《黃河水長流》。這些作品,無一不深深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無論是作品主題與環境,人物形象與生活狀態,都是編導張繼剛家鄉山西風土人情的一個縮影。而張繼剛本人也在采訪中透露,正是出于對家鄉的眷戀,才使得其萌生了創作表現山西風土文化的一系列作品,而這種眷戀,亦是我們提到的地方依附所帶來的一種鄉土情結。
而被譽為中國原生態舞蹈第一人的楊麗萍,其作品中也體現出了強烈的地方依附情感。她出生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受到了地域文化的深刻影響,不論是生活習慣、價值觀念亦或是藝術傾向,都體現了獨特的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的痕跡。今日,我們觀察楊麗萍的穿著打扮,仍可發現她的服飾多為民族風的樣式。可見,這種地域文化對她的影響,業已深入骨髓。而在楊麗萍的作品中,這種地方依附的情感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如她的代表作《雀之靈》表現了孔雀靈動自如的狀態,孔雀恰恰是云南當地文化的一種鮮明代表;而在舞蹈詩《云南印象》中,楊麗萍更是通過詩化和意化的藝術手法,原汁原味地展現了鮮明的民族元素,并大膽啟用山寨里從未經受專業訓練的村民作為演員,力求舞蹈原生態的表達。而在被譽為《云南印象》姊妹篇的《云南的響聲》中,她更是從響聲著手,通過小河流水、大河漲潮、電閃雷鳴和蟲鳴鳥語等多方面,表現了云南獨特的響聲,體現了云南人獨特的生活習慣與自然觀念。再觀察楊麗萍其他作品,諸如《孔雀》《月光》《孔雀之冬》《兩棵樹》,我們也不難看出,地方依附情感所形成的鄉土情結,催動她的藝術創作,并促成她具有地域特性的藝術風格的形成。
而遠在海峽對岸的現代舞藝術家林懷民,同樣將其獨特的地方依附情感體現在了作品中。只不過,與張繼剛和楊麗萍不同,林懷民的地方依附顯然不局限于家鄉臺灣,更包含對大陸深深的想念。這種情感構成了林懷民作品中重要的思鄉情懷。在作品《薪傳》中,林懷民講述了臺灣先民從唐山來臺,開荒拓土延續生命的偉大情懷,體現了臺灣先民們對于海峽對岸的深深眷戀。而在《我的鄉愁,我的歌》中,林懷民更是將這種鄉愁釋放到了極致。而在林懷民的新作《稻禾》中,則體現了林懷民對于“池上稻田”獨特的地方依附情感。林懷民曾說:“我在嘉義新港故鄉渡過童年。短短的街道之外,就是嘉南平原。天氣好的時候,會看到稻禾翻動的盡頭聳立著新高山。玉山,日據時代叫新高山。我也看到農友終年忙累。烈日下布秧,除草,踩水車。收割后,稻谷鋪滿厝前埕仔,在太陽下曬干。因為熟悉,稻米很容易挑動我。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5]在創作稻禾之時,林懷民就會帶領演員去池上體驗割稻,而池上對林懷民無疑就是一個情感依附的對象。
四、土地倫理與動物倡導
“在生態主義者看來,以人類為主宰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并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掌控人類的思想與行為”。[6]美國史學家林恩·懷特將人類中心主義的特征概括為:“人類將自己視為地球上所有物質的主宰,認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動物、植物和礦物——甚至連地球本身都是專門為人類創造的。”以此同時,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在生態思想發展史中更是由來已久。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曾指出:“在人類對自然進行統治時,不能像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那樣,因為人類并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相反,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無疑,恩格斯這種強調人的自身和自然界在存在上的一致性的理論就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駁。基于此,奧爾多·利奧波德則提出了與之相對的土地倫理思想。“主張人類應由‘人類中心主義’向‘自然中心主義’的轉變,即‘自我意識’‘生態意識’的轉變。認為人類已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員,與自然世界中的其他成員生死與共。這種“轉變”要求人們平等地接近、體驗并熱愛、保護自然”。[7]
在舞蹈劇場《桃花源隨想》中,就體現著對土地倫理的宣揚與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編導取材于陶淵明《桃花源記》描繪的生活圖景,設置了《漁》《樵》《耕》《讀》四個篇章,并以現代人作為“闖入者”,向漁夫、樵夫、耕夫問道解惑,從而揭示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存狀態。在第一篇章《漁》中,“現代人”試圖捕獲水中的魚,但每當魚鉤沉入水中,魚兒便四處散去。“現代人”疑惑不解向漁夫請教,并引出了漁夫的內心獨白:“釣魚只求垂釣內心,而非捕獲生靈”。而在第二篇章《樵》中,“現代人”對樵夫撿柴不砍柴的行為表示費解,故擅自對樹木進行了砍伐,樵夫對其嚴厲制止,并引出了樵夫的內心獨白:“樹枝掉落,乃上天予我,謂之可取;樹枝強行折下,謂之不可取”。以上的兩種傾向,均體現出了一種保護環境的生態意識,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模式。而對“現代人”急功近利、投機取巧的性格的批判,也暗喻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在上文提到的舞劇《稻禾》中,也包含了同樣的土地倫理的思想。該作品以舞蹈的形式講述了稻米從初秧、結穗、收割、焚田,到春水重新灌滿天地的生命周期,并以稻禾的生命周期作為紅線貫穿始終,通過《泥土》《風》《水》《花粉I》《花粉II》《日光》《谷實》《火》《水》八個各自獨立卻又密切聯系的章節,體現了自然周而復始的狀態,以及人類與土地的依存關系。而在第七章《火》中,則講述了是稻田收割后,農民們引火焚田,將稻茬和稻桿燒掉,為下一季水稻種植做好準備。“烈火焚田的影像鋪天蓋地,男舞者持棍械斗,劈打舞臺,象征人類對地球的無情破壞”。[8]
而建立在土地倫理思想基礎上的動物倡導理論,則更加深入地討論了動物在自然界的位置。該理論包含三部分:“一是解構那些對非人類動物那種化約式的及不尊重的呈現。二是評估作者在何種程度上把非人類動物當作有內在價值的生命體來看,就是不僅把他們當作有能力去經驗周遭的主體,也把動物當作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個獨一無二的物種。三是評論作品中人和動物之間的關系,譬如動作和消費者的關系”。[9]
動物保護題材作品《羚羊的外套中》就體現了鮮明的動物倡導理論。羚羊和睦的生活狀態被人類槍聲打破,隨著羚羊一只只倒下,皮毛被貪婪的人類剝下,成為了一件件沾滿鮮血與銅臭的商品。而這種漠視動物生命的行為,無疑是人類中心主義在作祟。同時,這又牽涉到了另一個問題,即是空間正義的問題。空間正義作為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理論,具體表現為,有權有勢的階層可利用優勢條件占據良好的地理位置,而下層階級只能生存在污染嚴重、交通不便的環境。而對于生活在自然環境的動物而言,人類對其獵殺的同時,也侵犯了它們專屬的空間,并通過暴力手段,對它們進行殖民化的管理。通觀我們人類文明發展史,無不伴隨著暴力與血腥,人類作為站在食物鏈頂端的物種,深諳叢林法則,并通過自認為正義的方式開疆拓土,侵占大量動物世世代代居住的空間,并將其占為己有,對動物進行奴役壓榨,又何嘗不是一種空間上的殖民。
結語
隨著環境危機的日益加劇,生態,不啻為一個世界范圍內的關鍵詞,得到了充分的聚焦。而生態批評作為一種話語,也隨著生態問題的備受關注而水漲船高。其適用范圍與理論深度,也隨著生態批評家的探索,得到了不斷深化。文學藝術,作為反映世界的一面鏡子,其呈現出的藝術世界,構筑在現實世界的客觀基礎之上,并注入了藝術創作者的假設與猜想,在某種程度上,藝術對現實世界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預測與先導作用。因此,以生態批評的視角,對文學藝術進行研究,不僅僅聚焦在顯而易見的環境與生態相關問題,更可借助相關理論,對常規性問題進行新的研究與新的闡發,獲得新的成果;亦或是,對現有的研究結果,提供一份堅實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