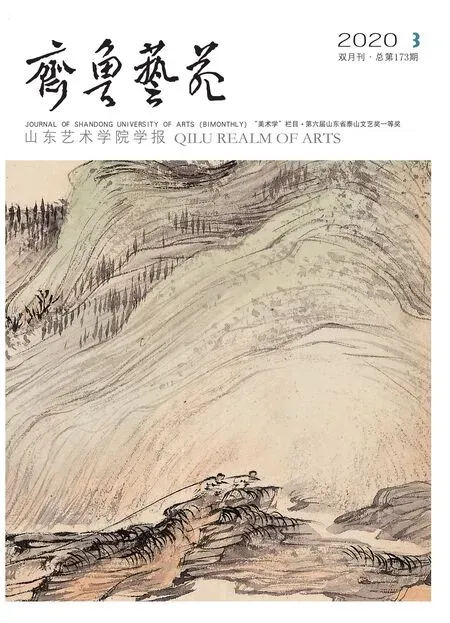崇新、交融、體悟
——關于美國鋼琴教學的思考
金 宇
(山東藝術學院音樂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音樂作為古希臘哲學思想中“七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有將近17個世紀的發展歷史。縱觀人類文明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音樂作為一種特殊的媒介和載體始終有著自己獨特的存在方式。我們廣義概念中的“古典音樂”起源于歐洲,后在19世紀末20世紀開始繁榮于歐洲以外的地區,例如美洲新大陸。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以其強大的國力為后盾,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最為優秀的音樂家,所謂“歐洲的古典音樂”在美國便形成了快速的推廣和繁榮。各個領域最為頂級的音樂大師亦紛紛赴美演出任教,于是這片新大陸便擁有了最為前沿的音樂會演出市場,陣容最為強大的音樂教育資源,最負盛名的交響樂團,以及最令人神往的音樂殿堂。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起,越來越多的音樂學子選擇赴美留學深造,以至成為當下的一種潮流和趨勢。多元化的文化沖擊和碰撞固然會給我們的思維模式帶來極大的啟發,畢竟我們所學的古典音樂屬于“舶來品”,但是對于海外學習宏觀上的思考,甚至是對于西方文化傳統和文化理念上的根本性分析和認知可能會給留學生們帶來更為深遠的影響。
美國巨大的文化包容性為音樂文化的傳播和繁榮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赴美學習于筆者來說最大的收獲在于對音樂宏觀層面的認知和理解,最大的幸事莫過于“頑守”BSO(波士頓交響樂團)和指揮家尼爾森足足聽了五年的現場。對于這樣的頂級樂團,前期的聆聽都是膜拜式的,因為耳朵里并沒有“儲存”太多這樣好的聲音。樂季中大多數的時間里,樂團每星期二、四、五演出三場,其中周四上午的開放排練對我來說也是一頓必不可少的加餐,毫不夸張的說我基本沒有錯過任何一場演出。有時候聽頂級指揮家一星期內的三場演出的不同處理也是一種極大的樂趣。當然一段時間之后我發現,頂級樂團也并不是每場演出和每套曲目都能處于最佳的演奏狀態,對于其中一次“車禍現場”至今印象非常深刻。在《圖畫展覽會》第六段《兩個猶太人》加弱音器的小號片段中,演奏員吹了兩拍發現自己拿錯了樂器,于是用了將近一小節的時間尋找C調小號,找到后又吹了兩拍發現調性依舊不對,最終無奈選擇了放棄,于是這一經典片段在木管聲部的和聲背景下持續了十個小節,直到下一片段弦樂組的出現才緩解了尷尬。非常不可思議的是這樣的重大低級失誤也會出現在這樣的頂級樂團的音樂會中,雖然很難想象指揮當時的表情,但是觀眾似乎選擇了最大限度的包容和理解,畢竟人非圣賢,有些失誤在所難免。也許這就是音樂最大的魅力,不像競技體育中恒定的輸或贏,音樂的世界里永遠充滿了未知。
在美國的音樂學習過程中會很意外的見到一些傳奇的音樂家和大師,我曾有幸見到了阿根廷傳奇鋼琴大師瑪爾塔·阿格里奇女士。對于她的膜拜大概是所有鋼琴演奏者共同的認知和習慣。兩年前我有幸一睹這位“女神”的圣容,還很榮幸的坐在她的身邊整整一個下午。對于自己為她演奏的作品沒有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但是她最為細微的言談舉止給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杯意式濃縮咖啡和一小碟堅果過后,她開始了自己欣賞音樂的模式,在音樂面前她像小孩子一樣天真和忘我,這也使我深刻感悟到音樂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后來她想試下那臺鋼琴的成色,毫不夸張的說她信手拈來的演奏瞬間改變了鋼琴的音色,整個下午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把同樣的一臺琴彈出那樣的聲音。
對于美式鋼琴教學的理念和思維方式,最為直觀的是美國對于新音樂的推崇。老師們甚至認為20世紀初的音樂也已經是100年前的“老音樂”,我們更需要去學習和欣賞當代作曲家的新音樂并從中找到一些新鮮奇特的內容。我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的時候,除了考試規定曲目外很少聽到大家會主動學習演奏當代作品,但是在美國——尤其是一些非亞裔的老師和學生群體中間,當代音樂甚至可能成為他們學習的主要內容。我們對于新音樂某種程度上的排斥其實是出于對其不夠了解,在系統研究分析了20世紀音樂的作曲理論和技法,并且對不同作曲家的不同風格的作品進行了分析和學習之后,我發現自己慢慢開始學會接受和欣賞這類音樂,甚至對于某些作品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喜愛,當然這樣的喜愛也會為自己的演奏帶來幫助。舉個最為簡單的例子,當我仔細研究過Pierre Boulez(皮埃爾·布列茲)的《第二鋼琴奏鳴曲》《notation》《Structures》和Tristan Murail(特里斯坦·米哈伊)的《Territoires de l’oubli》等作品以后,再去學習一些浪漫派甚至更早期的作品,就會發現識譜變得異常的容易。所以我認為對于20世紀音樂的學習和演奏是非常必要也是大有益處的。
用最為簡單通俗的語言概括,美國的鋼琴老師(這里指非亞裔的老師)更強調音樂的創造性,國內的老師可能更強調技術的完整性。這個話題很容易引起誤會,這里所說的強調音樂或者技術并不代表只看重某個方面,因為這兩個方面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兩種理念都有自己的側重點和優勢,對于鋼琴學習都非常的重要。在美國老師的班上,我們經常會看到貌似技術不是很完美,但是受到老師青睞的外國學生,因為相對于技術的缺失和不完美,老師們更多關注的是學生對于音樂特征、形象和風格的思考和理解,可能很多時候這種思考是不恰當的,但是老師們都會豪不吝嗇的對此大加贊賞。他們不大可能會陪著學生去“逐字逐句”的練習技術和細節,只會給出方向性的建議,然而這樣的教學理念帶來的后果可能是基本功的不扎實和技術的不完善。我們常常會聽到一些國外老師對于中國鋼琴演奏者的評論:“技術完美但是沒有打動我”“彈得很快但是不好聽”“彈得很好但是很無聊等”。類似的評論從側面反映了老師們之間審美的差異和側重點的不同,而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絕不是來自于鋼琴老師,而是來自于兩國整體文化的差異和對于教學理念認知的差異。我在美國大、中、小學都有任教經歷,通過長期的觀察和交流我發現,老師們無論是對于新音樂的推崇還是對于學生一些看似荒誕奇怪的想法,絕大多數都是持鼓勵和肯定的態度,這其實是一種對于未知新鮮事物的接納和無限的包容,而這樣的現象來自于美國教育尤其是對于學前教育理念的延伸。
下文將以幾位頂級世界鋼琴大師與教育家的例子來闡述美國鋼琴教學的特點。
羅素·謝爾曼(Russell Sherman)是美國傳奇鋼琴大師,也是鋼琴教育界的泰斗,今年88歲的他依舊活躍在舞臺上并有著出神入化的音樂表演。他的學生更有例如哈莫林、陳宏寬、安寧等當今活躍在國際舞臺的鋼琴大師們。卞和京(Wha-Kyung Byun)女士是美國著名的鋼琴教育家,也是謝爾曼大師的夫人。作為世界級的鋼琴教育家她培養出了例如白惠善(Haesun Paik)和黎卓宇(George Li)等鋼琴家,后者更是在2015年舉行的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大賽上斬獲大獎,成為當今聞名遐邇的新生代主流鋼琴家。我有幸的在2013年美國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拜入卞和京女士的門下,從而有了這一段非凡的鋼琴學習之路。
卞京和女士在我赴美的第一節專業課上徹底改變了我對于做人和從藝的認知。當年的我剛剛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自以為拿了些小獎便多少有些“桀驁不馴”,然而這正是卞和京女士教學中最大的忌諱。我當時用了五天的時間準備了肖邦《F小調敘事曲》和拉赫瑪尼諾夫《bE小調練習曲》,原本想炫耀自己演奏技巧和背譜能力,卻被老師無情的趕出了琴房。在被趕出去之前,我從老師口中得知了以下幾點:其一,我完全不懂得音樂和聲音的基本概念;其二,我的學習和演奏態度完全是低級的炫耀而忽略了音樂本身;其三,她無法對像我這樣一無所知的學生進行教學。我當時的無知觸犯了老師對于藝術認知的價值觀,但我卻絲毫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我心里她也許是夸大其詞,而且我并沒有覺得事實如她所說的那么不堪。我加倍努力,以每天十小時的練琴量來準備相同的作品,然而在第二個星期的專業課上發生的事情卻變得更加糟糕:課上老師指出我并沒有好好練琴,而我以具體的練琴時間段和時長予以佐證,同時也試圖要辯解她的判斷并非完全準確。她并沒有多說什么,而是非常嚴肅地告訴我學年剛開始,一切都還沒有塵埃落定,在這個時候換老師也不失為一個良機,說完之后她便起身離開,把我留在了琴房。我似乎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做了認真的反思,最終在苦苦哀求之下老師還是接受了我的道歉。這兩節課卞和京女士教給我的是做人和做音樂的態度,這是遠遠超越鋼琴和樂曲本身之上的也是最為根本的原則性問題。自此之后,我本著謙虛治學的精神去探討音樂的本質,并把這樣的精神貫穿到我今后的音樂學習和教學之中。
而對于上文中老師指出我沒有練琴的問題,后來我也有了深刻的體會。她所指的練琴并不只是時間的堆砌,而是對于音樂和自我的無限挑剔。她最反感的無疑是簡單的重復和機械般的轟鳴。在她的理念中,音樂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探索,我們永遠都不能滿足于當前的演奏,好的練琴模式下不應該有完全重復的兩次演奏,反之則是低級且無趣的機械運動。宏觀來說,卞和京女士的學生大多都具有無可挑剔的演奏技巧,這也似乎成為想拜入她門下學習的先決條件。但她本人并不喜歡甚至是抵觸所謂的炫技演奏,她最看重的是對于音樂的感知、樂句的劃分和聲音的控制。還記得和她學習的后期我得到了她極其罕見的表揚,這得益于她對我耳朵敏感程度和鑒賞能力具有本質性提高的認可。
卞和京女士擅長各個時期曲目的教學,然而最為拿手的莫過于對古典和浪漫時期音樂的品味和把控。作為她的學生,我們最害怕的其實是在她面前演奏古典時期尤其是海頓、莫扎特以及貝多芬的奏鳴曲,任何一個瑕疵都可能會招致她無情的批評和指責。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甚至整個美國地區,卞和京女士極端嚴厲的教學方式早已成為了眾所周知的秘密。她常常把“no(不對)”和“terrible(極其可怕的)”掛在嘴邊,并會著重強調幾乎每一個“phrase(句子)”。在這種充滿壓抑的教學氣氛中,一個小時的專業課常常會伴隨著學生的嚎啕大哭而結束。然而我通過對于上課錄音的回顧和分析后發現,她只是把錯誤毫不留情的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并施以嚴厲的指正,其實她從來不會夸大任何錯誤。這樣的教學模式和方法需要我們具有極其強大的抗壓能力和冷靜的思考能力。我本人從中受益匪淺,正是通過和她的學習才讓我在今后的演奏中總能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這一點至關重要。
相對于卞和京女士獨樹一幟的極端“打壓式”教學,謝爾曼大師則是非常和藹可親。還記得我曾經在大師的家中為他演奏《貝多芬D大調奏鳴曲》(作品10之3),演奏完畢后聽到了大師的肯定和鼓勵我感到了無比的詫異和欣喜,要知道一星期前,這首作品在卞和京女士的課上曾經被她狠狠的堅決否定過。大師并沒有對我的演奏逐句修正,只是宏觀地講解了貝多芬音樂的特質和對于聲音的理解。《D大調奏鳴曲》的第二樂章是一個悲情的慢板樂章,大師對這個樂章的演奏最為滿意,他認為我已經抓住了音樂的精髓,需要的是內心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表達。在問到我還在學習什么作品的時候,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了李斯特《B小調奏鳴曲》,而大師的回答則讓我記憶猶新:他表示這個作品他有一點了解,也正在學習。要知道謝爾曼大師是演奏李斯特《B小調奏鳴曲》的權威,而且我也欣賞過他不同版本的錄音和演出視頻,每一個版本都是精彩絕倫并各具特色。大師極其謙虛的治學態度以及對于藝術和音樂的虔誠深深感動了我,也讓我感受到了他作為藝術家的人格魅力。他在課堂中話語不多,語速很慢,置身其中感覺時間在某些瞬間發生了凍結,空間也開始凝固,他寥寥幾句話便可勾勒出復雜的音樂真諦,深入到聽者的內心最深處,用神乎其神來形容毫不為過。
當我在美國任教后,算是對美國教育和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暨回頭細想兩位大師之間的教學風格的差異本質上是亞洲和西方教學思維的碰撞和融合。卞和京女士早年在美國接受教育,但其嚴苛、細致,從點到面,從樂句、觸鍵、聲音、音樂結構到對音樂形象特點的宏觀性思維等模式更像是我們亞洲人的教育模式和縮影;而謝爾曼大師屬于純粹的美國學派,再加以其深厚的哲學和文學修養,他的教學風格常常讓人捉摸不透,更多的是以拋磚引玉的方式,從宏觀出發,啟發學生思考的方向和方式,再“含糊”地引導學生自行進行細化處理和思考,這樣的思維多少有些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境界。
文化只有差異沒有優劣,音樂本就是文化的一種體現方式。不同的文化歷史和氛圍相交融會為音樂學習者提供無限的資源和空間,在這里我們可以更好地體會音樂的美和魅力。對于文化包容性的思考和延伸會讓我們的演奏更加富有內涵,也會讓我們的音樂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