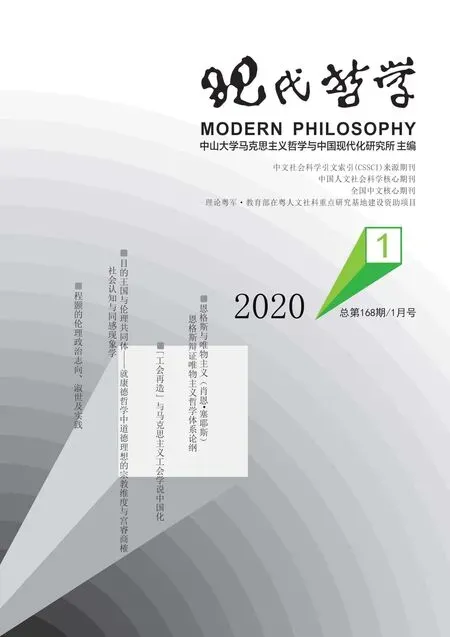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域下毛澤東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思想探析
——讀《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思考
徐 田 付東東
在我國,少數民族以中西部邊疆地區為主要聚居區,其貧困人口占全國貧困總人口的比例相對較高,這既不利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團結、和諧、穩定與發展,更有悖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宗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1)《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會議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1月1日。事實證明,有效提高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水平,加大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與振興的扶持力度,是中國共產黨人謀求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發展目標的本質要求。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就對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問題作出戰略性思考。1955年秋季至年底,毛澤東為了推進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運動,引導億萬農民群眾“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親自對這些材料進行文字修改以及題目擬定,并以“本書編者”的名義分別作了按語(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36—440頁。。該書關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業合作化以及鄉村治理的典型材料與鮮活案例,充分展現了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的基本思路。毛澤東的這些思想與實踐對新時代構建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一、發揮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主動性,奠定鄉村社會改革治理群眾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明確提出:“幫助各少數民族,讓各少數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是整個國家的利益。”(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369頁。由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具有獨特的鄉土文化以及民族經濟狀況,其鄉村社會改革治理更具有復雜性和必要性。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鄉村治理過程中,注重引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集體化發展道路。不斷發揮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主動性,為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奠定群眾基礎。
(一)從國家發展戰略層面推動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社會改革治理進程
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社會改革與治理是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鑒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發展的特殊情況,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將“慎重穩進”(4)參見《深切的關懷 偉大的跨越——黨中央關心西藏發展紀實》,《人民日報》2011年7月17日。工作方針,貫徹到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社會改革與治理的進程中。在毛澤東看來,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是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毛澤東明確提出:“幫助各少數民族,讓各少數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是整個國家的利益。”(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369頁。在他看來,少數民族的發展繁榮穩定關乎國家發展戰略的實現,對推動社會主義建設意義重大。與此同時,毛澤東批評部分干部存在的“大民族主義”錯誤傾向,并進一步指出“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6)《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5頁。。他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鄉村改革與治理離不開各族人民的團結與互助,同時需要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主體性作用的發揮,“只有先進民族的幫助,并不能徹底解放少數民族,因為不進行社會改革,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所受的壓迫就還不可能最后獲得完全的徹底的解放,社會不可能向前發展,過渡到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55頁。。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再次重申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在社會主義鄉村改革與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贊揚少數民族農牧群眾積極投身農牧業生產的主動性行為
毛澤東高度關注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踴躍創辦、發展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積極投身邊疆地區農牧業生產的主動性行為。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加入了“本書編者按語”,贊許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掀起農牧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有效措施,明晰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參與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運動及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的主體性作用。例如,在《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個畜牧業生產合作社,使牲畜大為發展起來》一文中,他充分肯定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少數民族干部和農牧民群眾貫徹黨中央“組織起來,發展牧畜業生產”方針,創造性建立牧業生產合作社,迅速提升農牧民生活水平,并使牧業生產合作社顯示出優越性的正確做法,稱贊說“這一篇寫得很好,可供一切畜牧業合作社參考”(8)《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9頁。。此外,在編輯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疏附縣色滿區關于鄉、村干部在建立農牧業合作社過程中所起到重要作用的材料時,毛澤東對維吾爾族鄉、村干部以及農牧民群眾如何放手建立與發展農牧業合作社的“五點有效措施”(9)“五點有效措施”指:“(一)通過總結過去的工作,使鄉、村干部明確建社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二)把辦社的政策方針和具體辦法,交代清楚;(三)幫助黨支部加強了集體領導;(四)加強巡回檢查,及時交流經驗,糾正缺點,具體幫助薄弱的環節;(五)正確對待鄉村干部在建社當中的錯誤和缺點”等內容。參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97—1299頁。表示贊許。
(三)肯定少數民族農牧群眾農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的有效做法
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農牧群眾在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進程中不斷釋放主體性活力,創造性地投身于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事業。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會主義高潮》中對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的有效做法與創新舉措給予肯定。例如,針對部分人提出的在少數民族邊疆地區不能實行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的錯誤觀點,毛澤東進行了有力反駁。他通過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少數民族農牧群眾的有效做法,堅定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的信心,強調“我們已經看到蒙族,回族,維吾爾族,苗族,侗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經辦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幾個族的人民聯合辦的合作社,并且成績很好”(10)《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第1293頁。。毛澤東肯定了維吾爾族干部和農牧民群眾走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道路以及進行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這種肯定奠定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的群眾基礎,彰顯了他注重釋放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主體性活力、進行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的重要理念。
《中國農村的會主義高潮》蘊含著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思想:既注重外部環境對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幫扶作用,更激發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的主體性活力;既照顧到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的現實特殊性,不以漢族地區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為模板“生搬硬套”,更關注到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的所想所盼,摒棄“大漢族主義”錯誤傾向,肯定贊許少數民族干部群眾的創新性做法,使少數民邊疆地區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工作實現“扶助性”與“主體性”的有機融合。
二、發展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業生產合作社,提升鄉村改革治理的組織化成效
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農牧合作化以及鄉村改革治理的組織化成效的提升,與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壯大密不可分。毛澤東結合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及鄉村改革治理的實際狀況,主張通過農牧業生產合作社,不斷提升農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的組織化成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編輯的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與鄉村改革治理的典型個案,充分體現了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對提升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改革治理的重要作用。
(一)通過農牧業合作社組織勞動力要素,促進生產力水平提升。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歷史與現實因素的雙重疊加作用下,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與其它地區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農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成效低于全國水準,迫切需要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力要素的投入、生產分配機制的調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究竟怎樣才適合,要好好研究一下。”(11)《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頁。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他明確了以農牧業合作社組織勞動力要素投入、改革農業生產管理體制及農業生產分配機制的重要原則。
第一,以農牧業合作社為載體,有效組織勞動生產要素,促進農牧業生產技術的革新與集約化經營。通過建立農牧業生產的經營管理方法、勞動分配規則與品種改良技術等,促進農牧業生產過程中勞動力、勞動工具以及其他勞動要素有機結合,“用細致科學的管理方法,代替過去粗放的靠天吃飯的經營方法”(12)《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256頁。,調動農牧區社員群眾從事農牧業生產的積極性,“在不同程度上顯示了合作社的優越性”(13)《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第1311頁。,進而為農牧業生產技術革新與集約化經營奠定組織基礎,不斷釋放農牧業合作社以及農牧群眾的生產新潛力。
第二,通過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建立有效的農牧業生產與分配機制,發展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生產關系,為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力水平提升創造條件。在農牧業生產管理體制上,該書以青海省循化縣農牧業合作社建立為分析材料,肯定他們“做好依靠貧農的工作的同時,還必須加強團結中農”(14)《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第1284頁。的做法,不斷建立貧農與中農齊心團結搞好生產的有效機制。在農牧業產品分配機制上,該書以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創建為典型材料,贊揚他們合理解決農牧社員“入股”與“分紅”的問題,兼顧勞動力與畜力的分配原則,以勞動力“分紅”為主,適當地照顧牲畜收入,進而“既照顧到社的生產,又照顧到社員的便利”(15)《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262頁。。該書收錄的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的材料,以內蒙古自治區、青海省以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為范例,展現農牧業合作社對組織勞動力要素投入及生產力水平提升的積極意義。
(二)鼓勵多民族群眾共同建立聯合生產合作社,實現“組織起來”目標
中國各民族在交往交融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品格與民族習慣。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進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進程中,高度重視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干部群眾打破民族之間的界限與壁壘,探索多民族聯合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創新性做法。
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將“民族雜居地方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6)《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第1350—1351頁。單獨作為一個類別進行歸納,對貴州省荔波縣民族雜居地區以及青海省亹源縣回族自治區的多民族聯合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進行深入分析。與此同時,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一文中,毛澤東以“本書編者按”的名義對幾個族的人民聯合辦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表示贊許。1955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決議》,以黨中央文件的形式對“在多民族雜居的地方,可以組織單一民族的合作社,或者是民族聯合的合作社”(1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20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9-420頁。進行政策性闡釋。毛澤東之所以肯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多個民族聯合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其戰略目標是通過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將各民族農牧民群眾“組織起來”,構筑起團結、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進而實現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繁榮與穩定。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編入《亹源縣回漢兩族農民組織的團結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文,其中回族與漢族農牧民群眾聯合建立“團結社”的做法得到肯定。通過建立“團結社”,回族與漢族社員之間互相照顧,加深了回族與漢族之間的友誼,迅速提高了農作物產量。與此同時,由回、漢兩族社員群眾共同組成的團結社管理委員會,在生產、生活中協調回、漢兩族社員群眾的關系,進而提升農牧業生產力水平。“團結社”的建立,使回、漢兩族社員群眾樹立了“只有互相團結才能得到各民族共同幸福生活的信心”(18)《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第1271頁。。
(三)引導各民族群眾發揮專長從事多種經營,增進民族團結協作意識
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的組織化成效,不僅需要農牧業生產合作社提供有效載體,而且需要各民族農牧群眾發揮民族專長與比較優勢,在增進民族團結協作意識的基礎上促進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繁榮穩定。
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以貴州省荔波縣布依族、水族和漢族農民群眾發揮民族專長與比較優勢,建立民族農民聯合社從事多種經營為分析素材,肯定他們的創新性做法。在引導各民族群眾發揮專長從事多種經營過程中,由于布依族、水族與漢族農民群眾在農業生產、日常生活和鄉土風俗上存在差異性,對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的生產體制和經營方式產生了一些困惑。針對這一特殊情況,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依靠各民族干部,運用多種靈活的宣傳方式,作好各族農民的思想發動工作”(19)同上,第1229頁。,充分做好布依族、水族和漢族之間的協商,解決好各族農民生產資料入社及鄉村改革治理生產經營利益分配問題。與此同時,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黨支部根據布依族、水族和漢族農民的生活特點與風俗習慣,采取靈活方式調整安排合作社的農業生產環節,使各族群眾發揮專長從事多種經營,實現布依族、水族和漢族農民之間的合理分業分工。毛澤東強調,多民族聯合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需要發揮各民族群眾的比較優勢與勞動專長發展多種形式經營,增進民族團結協作意識。
在毛澤東看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以農牧業生產合作社或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為組織形式,進一步發揮各民族群眾的比較優勢,不斷促進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勞動力要素投入和農牧業生產分配體制機制改革,對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乃至整個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和諧、繁榮與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
三、強化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干部隊伍和基層黨支部建設,夯實鄉村改革治理人才組織基礎
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開展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需要各民族干部群眾的同心、同力、同德、同向,需要強化基層黨支部建設并發揮其領導核心作用。“依靠當地少數民族的干部去做工作”(2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第665頁。是毛澤東推進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工作的重要原則之一。
(一)培養“眼睛向下看”為群眾解難題的少數民族干部
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干部是帶領農牧群眾走上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道路及進行社會主義鄉村改革與治理的“領頭羊”和“主心骨”。毛澤東十分重視對少數民族干部的選拔與培養,面對新中國成立后百業待興的現實狀況,他明確要求地方黨委對轄區內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干部進行選拔、培訓和任用,明確提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21)《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0頁。。可見,毛澤東認為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干部,尤其是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基層干部,對解決好民族問題意義重大。
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注重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干部發揮示范帶動作用,推進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以及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工作向前發展。該書關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相關材料表明,培養“眼睛向下看”為群眾解難題的少數民族干部,是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以及鄉村改革與治理的必要性條件。《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一文明確要求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疏附縣的干部,在領導各民族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和社會主義鄉村改革與治理過程中,不斷學習黨中央的方針政策,牢固樹立“眼睛向下看”(22)《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第1295頁。的工作意識。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疏附縣干部遵循“眼睛向下看”的工作方法,深入縣域轄區內鄉村的田間地頭,領導發動各民族人民群眾,走“組織起來”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在“本書編者按”中對疏附縣色滿區“為了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23)同上,第1293頁。進行選拔、培養與使用的做法表示贊許。
(二)任用具有良好政治覺悟與領導能力的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基層干部
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基層干部在推進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治理工作中起著“紐帶”作用,不僅需要“眼睛向下看”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態度,更需要具備良好的政治覺悟與高超的領導能力。《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對選拔任用具有良好政治覺悟與高超領導能力的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基層干部的要求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少數民族基層干部需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切實維護好民族平等與團結。該書介紹了青海省亹源縣回族自治區建立“團結社”過程中,回族干部采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有效措施處理回、漢農牧民糾紛的案例,維護好社內回、漢兩族人民群眾的團結,使“回、漢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成為一種力量”(24)同上,第1273頁。。此外,貴州省荔波縣板考鄉民族雜居區在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過程中,布依族干部與水族干部、漢族干部“鬧意見”,后來經過合作社黨支部的教育引導,使他們明白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構建起“有事都能彼此商量,互相尊重,共同領導社的生產”(25)《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第1133頁。的和諧關系。第二,少數民族基層干部需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方法做好各民族農牧民群眾的工作,使黨的路線、方針與政策“家喻戶曉”,維護好、協調好各民族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貴州省荔波縣板考鄉民族雜居區的布依族、水族等少數民族干部“采取大會報告、組織群眾討論、田間寨壩擺談和家庭訪問等多種多樣的方式……激發起群眾的建社熱情”(26)同上,第1130頁。。第三,少數民族基層干部需要以身示范做好團結協調工作,促進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生產發展。該書在介紹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伽師縣的區鄉干部做法時,提到區鄉干部在領導社會主義農牧業互助合作運動以及鄉村改革治理工作中,注重“加強貧農和中農的團結工作”(27)同上,第1307頁。,進而有效地發展了本轄區內的農牧業生產,提高了農牧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
(三)以農牧業合作社黨組織為引領,突出基層黨組織的核心作用
基層黨組織是黨中央農業農村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是推動農牧業合作化與鄉村改革治理的領導核心和“橋頭堡”。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進行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以及鄉村改革與治理,離不開基層黨組織這個戰斗堡壘,離不開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的發揮。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著重展示了包括內蒙古自治區、貴州省、青海省、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在內的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的生動案例,而這些地區都在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過程中成立了基層黨支部。《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試辦三個畜牧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等文章,充分展現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基層黨組織在領導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以及鄉村改革與治理工作過程中,積極、穩妥、有效處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改革治理事務的經驗與做法。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烏魯木齊縣與烏恰縣在建立農牧業生產合作社過程中“試辦了建黨工作”(28)同上,第1309頁。,并發揮基層黨組織“集體領導”的核心性作用,進而凝聚起少數民族農牧民群眾參與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及鄉村改革與治理的建設熱情,進一步形成黨組織統一領導與群眾主動參與相結合的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新機制,為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堅強的組織保障。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明確了新時代農業農村發展的根本方向。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需要基層治理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撐。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與振興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意義重大。在新的歷史時期,回顧梳理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思想,對新時代構建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具有啟迪意義。《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鄉村治理的思想,既展現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干部群眾投身社會主義農牧業合作化以及社會主義鄉村改革治理工作的高度熱情,更描繪了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主義鄉村改革與治理的發展愿景。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鄉村治理思想包括三個方面:發揮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群眾主動性,奠定鄉村社會改革治理群眾基礎;發展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農牧業生產合作社,提升鄉村改革治理的組織化成效;強化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干部隊伍和基層黨支部建設,夯實鄉村改革治理人才組織基礎。這些思想與實踐對新時代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戰略的借鑒意義在于:一是要激發少數民族人民群眾參與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為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釋放主體性要素活力;二是實現少數民族人民群眾的組織化與合作化,增強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三是加強少數民族鄉村干部隊伍與基層黨組織建設,為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提供人才支撐與組織保障,不斷開創新時代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和基層社會治理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