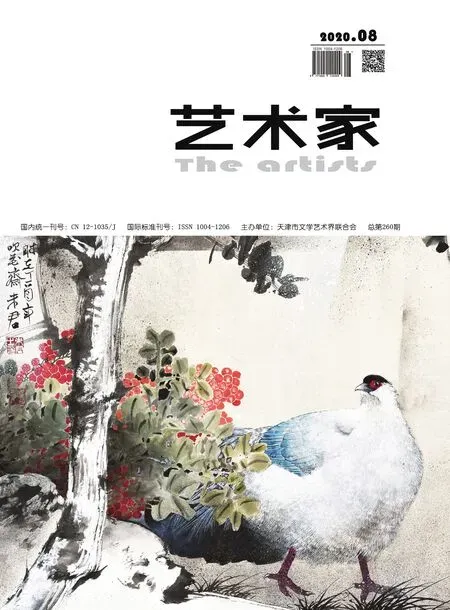我的藝術觀自述
——時代特性與藝術的關系
□劉 悅 魯迅美術學院
每個階段的社會都具有時代特性。而我們這一代生活在高度發達的信息時代,全球互聯無論在經濟還是信息方面早已不再是新鮮事,還有即將來臨的5G時代,在這樣的環境下筆者不禁思考,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時代特殊的烙印又是什么呢?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特殊的時代影響著我們兩代人。高速發展的社會進程不斷把我們帶往一個又一個未知的語境中。從小學到高中,緊張嚴肅的標語是幾代人成長經歷中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些信條一樣的標語,既是時代發展的訴求,同時也蘊藏著某種不可言喻的集體價值取向,其間蘊藏著深刻哲理卻也伴隨著諸多問題。集體與個體、規則與自由、誠實與虛偽、真實與假象,或許會成為時代的特殊組合與矛盾體。
筆者是所謂的“九零”后,受外來文化沖擊最大的一代人。很多時候,就像筆者第一批創作作品中所表達出的糾結、矛盾一樣,筆者常通過年輕人的視角來觀察自身的屬性。畢竟耳濡目染來自長輩的諄諄教導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與社會所帶來的新鮮事物之間形成了強烈沖擊,這也使筆者的觀察變得更加尖銳。每當想特立獨行時就會受到身邊人的勸阻甚至打壓,而最終“天天向上”等標語還是成了筆者真正的文化標桿。有時候筆者會覺得自己像被編寫好程序的機器人。有時人們會問:“你的創作源泉是什么?靈感來源于哪里?”筆者很少具體回答,因為在筆者看來,觀者對這個社會的態度或者看法會影響其對畫面的解讀。
在本科剛剛進入創作的這段時間里,筆者對“畫什么和怎么畫”也產生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迷茫與糾結。在那段時間的閱讀過程中,王朔的小說《看上去很美》給了筆者很大的啟發,他在其創作的巔峰時期敏銳地察覺到時代特質,并一針見血地指了出來。雖然筆者所處的時代與王朔不同,但是筆者所感受到的成長中的矛盾與困惑卻與他相似。于是,筆者借用了他的觀點。但與之不同的是,筆者更加關注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對物欲的渴望與期待。因此,筆者將兒童形象與奢侈品并置在一起,想通過這樣的組合方式對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展開探討。在繪畫語言的表現上,這兩種看似毫無聯系的圖像,在筆者看來更像兩個不同世界的代表符號,奢侈品象征著成人規則里公認的美好,但對于兒童而言,奢侈品像是強行闖入單純世界的侵略者。互不相干的兩種圖像相互抗拒又彼此共存,在產生強烈分歧的同時,又似乎在訴說著兩者之間隱蔽的聯系,可這一切不過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進入研究生學習階段,筆者期待在創作主題及手段上能有更多的探索。在那段時間里,筆者嘗試了不同的繪畫材料,同時《美麗新世界》和《娛樂至死》這兩本書所傳達出的社會問題也給了筆者啟發:當社會被劃分等級,人們被等級所支配、繁衍甚至發展時,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活在了幸福中。但這種每個人各司其職,心中充滿幸福感的烏托邦式的社會,又是如此令人心生恐懼。在最新一批作品里,筆者想訴說的就是人們當前扭曲的消費觀,許多人被大品牌、大流量影響,喪失了自身的主觀判斷,陷入了對潮流的盲目崇拜中。這雖是赫胥黎對未來世界所展開的一種想象,但反觀現在我們的生活,難道在某些方面不是一種反向攝影嗎?
同樣,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對20世紀后半葉美國文化發生的重大變化展開了探究與哀悼:電視改變了公共話語權的內容和意義,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容。回到當前,智能手機的廣泛普及,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使人們陷入瑣碎信息的不斷轟炸中,許多標準被模糊化,我們無法準確地評判事物的錯與對;信息的快速更新提高了社會效率,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信息過剩等嚴肅而不可抗拒的問題,這也是筆者在畫面中希望呈現出的糾結與矛盾之一。
在新階段的繪畫探索中,筆者放棄了相對傳統的繪畫媒介,選擇了高透明度的菲林片,這與無時無刻不在向外傾泄個人信息的時代特征形成了某種弱呼應。底層圖層,筆者不斷地使圖像進行拼貼與重疊,展現流行與經典元素之間的強烈沖擊力。與此同時,筆者又希望畫面能夠強調文字書寫的重要性,呈現或調侃或戲謔的感覺。而在最頂端的圖層,筆者運用了流行及大IP元素。
反觀自己的思考過程,筆者希望能不斷地挖掘更深處的隱蔽的心理活動,以便在接下來的創作中,可以更好地結合美學及美術史的理論啟發自己,直面當下的困惑與難題。在藝術道路上的成長是漫長且艱難的,希望筆者有足夠的勇氣與定力來面對未來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