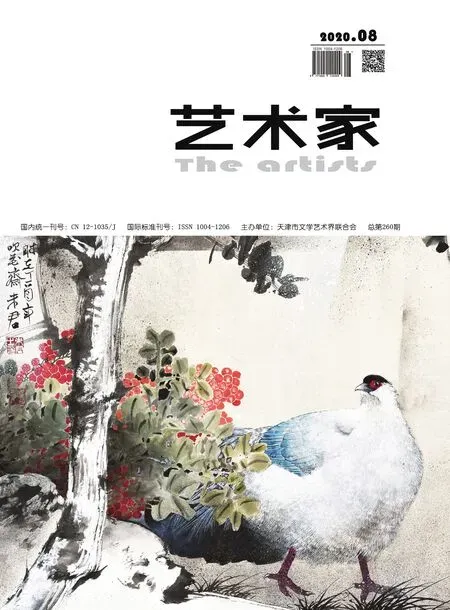從筆與墨角度探究《山靜居論畫》的藝術(shù)價值
□劉靜芝 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
在中國畫中,筆墨的變化和轉(zhuǎn)換可以最大限度地將畫作的表現(xiàn)功能發(fā)揮出來,筆墨于中國畫而言具有靈魂作用,這主要是因為畫者可以將自身的情感及寫意訴諸筆端,通過筆墨表現(xiàn)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在筆墨交匯中擺脫物質(zhì)層面,實現(xiàn)文化精神的傳達。
一、中國畫中筆墨價值及表現(xiàn)功能
(一)筆墨價值
中國畫充滿濃郁的東方文化特色,其抽象的表現(xiàn)形式和“筆墨”聯(lián)系甚密。筆墨也被稱為中國畫之魂,甚至出現(xiàn)了“有筆有墨謂之畫”的說法,換言之,離開了筆墨,畫便不能稱之為中國畫,至少不算是好的中國畫[1]。受認知及知識結(jié)構(gòu)的影響,畫家所用的工具及材料也會不斷地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在中國畫的發(fā)展長河中,筆與墨的性能得以高度發(fā)揮,并最終植根于中國文化的土壤,形成了完善的筆墨語言系統(tǒng),并使中國畫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獨特的風(fēng)景。而寫意畫的出現(xiàn)使筆墨擺脫了單純的形式技巧,成為觀者體味畫家情感、了解畫家人品學(xué)識的主要途徑之一,其藝術(shù)價值得到了深化。
(二)表現(xiàn)功能
中國畫中的筆墨可以理解為墨與線的勾勒,畫家更是靠筆墨表情達意,寄托情思。畫家通過對筆墨技法的運用與把握,體現(xiàn)了筆墨表現(xiàn)功能、毛筆的不同質(zhì)量、墨分五色的暈染。正如黃賓虹的“五筆七墨”之說:“‘五筆七墨’中,五筆:一曰平,二曰圓,三曰留,四曰重,五曰變;七墨:濃墨法,淡墨法,破墨法,潑墨法,積(有時用‘漬’)墨法,焦墨法,宿墨法。”這一理論與實踐的提出,將中國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使畫家在筆墨運用上自如灑脫,即使在形式結(jié)構(gòu)上存在瑕疵也會獲得欣賞者的承認和贊賞[2]。筆法不同,畫作所傳達的情感也不同。筆墨在畫作中是有生命力的,有其自身的氣質(zhì),畫作所表現(xiàn)的氣質(zhì)就是所謂“傳神達意”。正如板橋所言:“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于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
總而言之,筆墨的表現(xiàn)與審美功能之間有相當(dāng)緊密的聯(lián)系,如果形式美,元素與內(nèi)容美之間脫節(jié),那么單純的筆墨技法就沒有了存在意義。筆墨的使用是為了更加準確傳神地表現(xiàn)所畫之物,只有這樣,畫作中所傳達的沉厚凝重、剛健勁遒、生辣稚拙、沉著剛健、秀潤華滋、細膩超逸等才能被欣賞者準確捕捉。此外,畫作筆墨的使用是畫家主觀情感的具象體現(xiàn),畫家只有利用筆墨將主觀情感融入其中,才能讓觀者產(chǎn)生強烈的情感共鳴,實現(xiàn)畫家與欣賞者的情感交流。
二、《山靜居論畫》之論“筆”
(一)畫無定法
在中國畫發(fā)展的過程中,部分畫家通過對畫作技法進行分析形成了筆法定式,即在表現(xiàn)某一物時“應(yīng)該”怎樣用筆。而在方薰的《山靜居論畫》中,畫家直言“畫豈有定法哉”,他認為筆法的運用不存在定式,不同的畫者有不同的喜好,即使描繪同一場景同一物也筆法各異,而同一畫者在不同時期或描繪不同題材時運用的筆法也是有所不同的。方薰在文中以李成、范寬、郭熙及李唐畫柳為例,說明了每位畫家在筆法運用上均有差異,畫無定法。
(二)筆有虛實
方薰在書中對古人用筆的玄妙之處做了解釋,他認為畫法存在于虛實之間,虛實之法使筆法充滿生機,充分掌握虛實之間的度是古人用筆絕佳之處。在中國畫筆法中,虛實是一大特色,也是對畫者提出的要求,虛實的變化讓筆法更為靈動自然,在物像繪畫中極為重要,是畫作充滿生機的關(guān)鍵。
(三)筆有頓挫
除虛實外,中國畫筆法對于畫者提出的另一大要求便是頓挫,《山靜居論畫》更是認為“運筆瀟灑,法在挑剔頓挫”。畫論中,方薰以友人家的古人存稿為例,雖畫作看起來如未完之作,但是其中筆法頓挫自然,畫作依然充滿生機與靈氣,這就更加說明了筆法頓挫在中國畫中的重要作用[3]。
三、《山靜居論畫》之論“墨”
(一)墨分五色
《山靜居論畫》中有關(guān)“墨”的論法較多,其中主要的論述為墨的使用不能拖泥帶水,需潔凈干脆,而墨法的使用也與人的心性品格有關(guān),唯有沉心靜氣之人方可實現(xiàn)落墨的沉靜。之后方薰又提出了墨之五色,認為墨存在焦、濃、重、淡、清五種顏色,這既說明了中國畫墨法的獨特之處,也對畫者提出了要求:在用墨時應(yīng)區(qū)分墨色,五色俱全,否則就會使畫作呆滯無神[4]。
(二)用墨之法
在《山靜居論畫》中,方薰對用墨之法做了分析和總結(jié),他認為“濃不可癡鈍,淡不可模糊,濕不可溷濁,燥不可澀滯”,即畫者在用墨時,若用濃墨則不能呆滯癡鈍,缺乏靈性與活潑;若使用淡墨則不可使得墨色含糊不清;對水分較多的墨的使用也要避免渾濁;畫干處時也要保證用筆的連貫,不能有干澀停滯之感[5]。除此之外,畫家還要做到虛實俱到,如此才能真正踐行用墨之法。
(三)用墨之材
這一點較容易理解,方薰在《山靜居論畫》中就表明,畫者除需對用墨的濃淡進行掌控以充分表達畫意之外,還要對文房筆墨紙硯進行孜孜不倦的試驗與追求,唯有如此,才能最大化地發(fā)揮墨的功能和作用,為欣賞者帶來美的視覺體驗。
結(jié) 語
明清繪畫理論在畫學(xué)著述領(lǐng)域中占據(jù)著獨特地位,與其他時期作品相比,這一時期理論更多地將重點放在了形式和基礎(chǔ)技法上,方薰的《山靜居論畫》便是其中較為經(jīng)典的著作,其中對于筆墨的論述更是謂之經(jīng)典,在歷史長河中沉淀出了屬于自己的歷史重量,對后來者啟示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