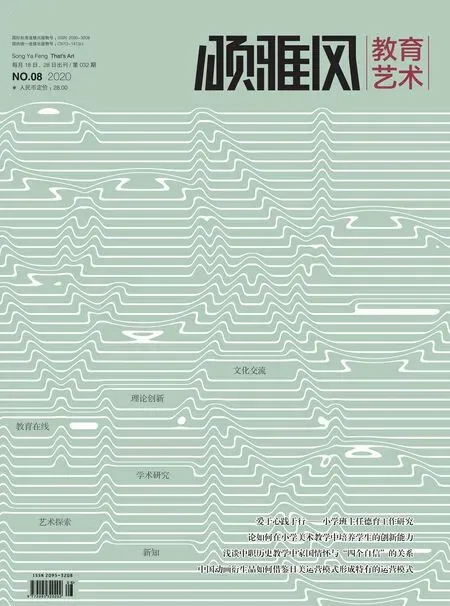淺談漢代書論的特點(diǎn)
◎閆淑霞
兩漢時(shí)期,中國(guó)書法發(fā)展迅速,尤其是東漢,書法突破實(shí)用性,出現(xiàn)了純粹以書法成名的書法家,并且漸趨形成流派,書法也成為一個(gè)獨(dú)立的藝術(shù)門類。隨著書法藝術(shù)的成熟和興盛,專門研究書法的理論著作應(yīng)運(yùn)而生。縱觀漢代書法理論著作,可歸納為以下特點(diǎn):
一、漢代書論伴隨時(shí)代發(fā)展
漢字是構(gòu)成書法的物質(zhì)載體。漢字最早成為規(guī)范系統(tǒng)的書體是秦統(tǒng)一“六國(guó)”后推行的小篆,到了漢代,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壯大,漢字書寫成為人們社會(huì)生活中的重要內(nèi)容,篆書實(shí)用與書寫的內(nèi)部矛盾越來越明顯,從而促成漢字的形態(tài)向易學(xué)、易寫的方向不斷變化,在書寫上也從注重實(shí)用性向兼顧藝術(shù)性發(fā)展。東漢時(shí)期,漢字書寫以實(shí)用為主的價(jià)值已被以藝術(shù)為主的價(jià)值取代,人們已刻意于漢字的點(diǎn)畫筆勢(shì)、用筆結(jié)體及法度,中國(guó)書法的篆、隸、八分、章草、草書、真書已大體齊備,并且隸書中楷書的因素明顯增加且呈現(xiàn)快速發(fā)展趨勢(shì)。天長(zhǎng)日久的書法實(shí)踐,使得人們對(duì)書法產(chǎn)生更多的理解與感悟,積淀成對(duì)書法的理論認(rèn)知,最終形成系統(tǒng)的漢代書學(xué)理論。
二、漢代書論形式內(nèi)容兼?zhèn)?/h2>
漢代書論形式多樣,內(nèi)容豐富,既有單一的論斷,也有整體表述,有些論述甚至已頗具系統(tǒng)性。如崔瑗《草書勢(shì)》,闡述了草書的起源和社會(huì)因素,提煉出草書的特點(diǎn),不但肯定了草書的社會(huì)價(jià)值,更是拔高了草書的審美價(jià)值,確立了草書從非自覺轉(zhuǎn)化為自覺的藝術(shù)地位。蔡邕的《篆勢(shì)》對(duì)篆書進(jìn)行了全面總結(jié),《筆賦》闡明對(duì)書法總體的把握與認(rèn)知,《筆論》《九勢(shì)》更是詳細(xì)總結(jié)了書法的創(chuàng)作要領(lǐng)、運(yùn)筆規(guī)則。漢代書論家從不同側(cè)面、不同角度,或整體、或局部,歸結(jié)書法要領(lǐng),提煉運(yùn)筆規(guī)則,論述筆勢(shì)特征,研判書者風(fēng)格,解讀書法整體,共同構(gòu)建起漢代相對(duì)完整的書法理論體系。
三、漢代書論蘊(yùn)涵審美意識(shí)
漢代人崇尚自然,追求形象美,這種社會(huì)風(fēng)尚影響到人們對(duì)書法藝術(shù)的審美意識(shí),人們更加主動(dòng)地欣賞、追求和研究書法之美,漢代書論也不再局限于對(duì)文字空間結(jié)構(gòu)的闡釋,還轉(zhuǎn)向?qū)徝雷杂X的關(guān)注。如崔瑗《草書勢(shì)》:“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guī)。……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蔡邕《篆勢(shì)》:“頹若黍稷之垂穎,蘊(yùn)若蟲蛇之棼缊。揚(yáng)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協(xié)翼,勢(shì)似凌云。”崔瑗、蔡邕的論述都采取審美想象中的類比思維,通過對(duì)現(xiàn)實(shí)事物的描述,形象地說明書法之美在于其“動(dòng)勢(shì)”,使點(diǎn)畫符號(hào)空間化,從而轉(zhuǎn)化為栩栩如生的審美意象,不僅點(diǎn)明了書法的內(nèi)在美,也完成了書法向外在審美的進(jìn)步。
四、漢代書論充滿生命意象
漢代書論中把書法看作是生命的律動(dòng),這是中國(guó)書法從實(shí)用性目的轉(zhuǎn)換為審美性目的的重要標(biāo)志。漢代書論重視書法藝術(shù)的內(nèi)在支撐,更看重外在的表現(xiàn)形式,認(rèn)為書法家就是要通過外在形式,將書法所蘊(yùn)涵的生命氣息傳達(dá)出來。崔瑗的《草書勢(shì)》“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將草書書寫的遲速頓挫描述為鳥在即將飛行前伸展脖子、踮起腳尖的停留,和狡猾的兔子在受到驚嚇時(shí)將要飛奔卻還未開拔的樣子,恰到好處地描繪出了草書創(chuàng)作中的寓靜于動(dòng)、引而未發(fā)的情形,蘊(yùn)含著強(qiáng)烈的生命意味。
五、漢代書論肯定書家稟性
西漢文學(xué)家楊雄提出:“書,心畫也。”認(rèn)為書法藝術(shù)作品是書家思想意識(shí)、品行操守的直接反映。漢代書論充分肯定書家個(gè)人能力,勸誡人們要正視自己,不能不切實(shí)際盲目攀比、好高騖遠(yuǎn)。趙壹《非草書》中說:“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可強(qiáng)為哉?”就是說一個(gè)人的性情,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是非常重要的,無法效仿與復(fù)制。世人眾多,稟性各異,書法的表現(xiàn)是基于人的稟性才學(xué),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特點(diǎn),不能扭曲本性而學(xué)某家某體,否則終歸是徒勞無益。
六、漢代書論重視創(chuàng)作情感
書法是情感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但情感本身不能構(gòu)成書法藝術(shù),只能融入書法藝術(shù),通過書法藝術(shù)得到彰顯和升華。因此,漢代的書論非常強(qiáng)調(diào)情感在書法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蔡邕所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蔡邕強(qiáng)調(diào)的是書法家在創(chuàng)作前所構(gòu)建起來的一個(gè)良好心境,認(rèn)為書法創(chuàng)作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主體的精神活動(dòng),要達(dá)到好的效果,起決定因素的是創(chuàng)作主體的內(nèi)心世界,而那些所謂的精良工具只能是輔助。
誠(chéng)然,漢代書論是中國(guó)書法理論的源頭,受歷史時(shí)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偏狹和不成熟,但其為書法理論體系的發(fā)展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在中國(guó)書法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