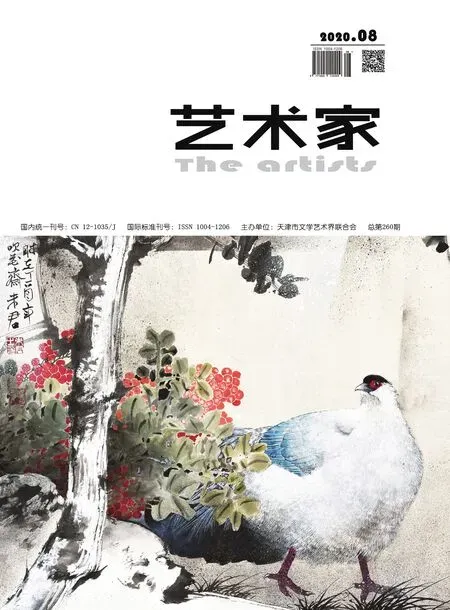追求精神文化層面的符號化消費行為的表現
□閆 策 王雨彤 趙 藝 河北師范大學
符號消費行為是一種具體的而非抽象的現象,它是消費者選擇商品、購買商品、使用商品的一系列的過程,并以此來實現商品的符號價值。消費者通過商品符號所承載的情感功能、交流功能、美學功能、指代功能等,將商品的符號價值轉移到交流客體上,同時將自身的主體價值進一步賦予商品。
一、品牌理念的共鳴
一般來說,人們更愿意購買的是那些宣傳做得很到位的商品,因為人們會不自覺地認為那樣的商品質量會更有保障。然而,在形形色色的“高宣傳”商品中,總會有更出眾的那個,它不一定是贏在了商品質量上,而是贏在了品牌理念上。
例如,宜家就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家具是有溫度的”“家具就像你的孩子一樣,不要隨意丟棄他們”。在宜家的臺燈廣告里,仍然擁有實用價值的臺燈被主人拿起,它像即將被丟棄的嬰兒一樣可憐地蜷縮在主人的懷里,隨著主人的步伐,一步步離開這個暖黃色的房間。大門被打開,巨大的風聲呼嘯而至,門外的世界一片陰冷沉郁,臺燈隨即被主人丟棄在垃圾桶旁,它仰望著主人遠去的背影,在寒風中竟然瑟瑟發抖起來,與昔日的溫存格格不入。寒雨中,它與樓上的新臺燈幾次對望,直到主人入睡,熄了燈,臺燈才絕望地低下頭,任雨水沖刷。
這樣的廣告比單純地介紹產品的性能擁有更加不同凡響的效果。把臺燈擬人化,賦予其人的情感,讓人心生憐憫。所以大多數人在挑選家具的時候,會先考慮宜家,因為和其他冷冰冰的器物相比,宜家的家具被賦予了溫度,給人舒適的感覺。
除此之外,廣告的形式也非常重要。例如,宜家的臺燈采用劇情片的方式,有思想、有深度,將品牌理念融入其中,采用了消費者喜聞樂見的形式,從靈魂深處打動消費者,開展精神攻勢,而不是一味地用字幕和旁白來吹噓自己的商品。
所以說,在保障質量的前提下,品牌理念大于產品本身。消費者從商品中汲取了除使用價值之外的價值,而收獲了符號價值。
二、地位象征的標志
在形形色色的商品中,同類同質的商品有很多不同的廠家,而這些商品的價值卻是千差萬別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不同品牌的產品展示給消費者的是不同的地位象征。
1899年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指出:在社會的一些“有閑階級”看來,消費已不僅是為了獲取產品的功能效用,更重要的是為了滿足其自尊心、得到榮譽和他人的尊敬,他將此稱為炫耀性消費。
當然,無論虛榮心怎樣作祟,最根本的還是由自己的經濟基礎決定,這種炫耀式消費行為大多出現在新富階層。而品牌消費讓新富階層有了更多“品牌情結”,其實質上就是對具有高象征價值的知名品牌的一種追逐行為。他們以“示差”為目的,將自己與他人分隔開來,以展示自己的個性,這不僅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重象征而輕實用,還將符號價值完全凌駕于使用價值之上,只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身份高貴或金錢充裕的人確實有資本來購買奢侈品、限量版和特質商品來凸顯自己的身份地位,但這些都是外在的,不應一味地追求,因為它只是一種膚淺的標志,一些人不應該為了所謂的面子而進行超前消費。
三、精神境界的追求
(一)審美需求
除商品的實用性之外,消費者們更傾向于購買那些外觀包裝好看的商品,這是他們對美的追求。消費的過程也是審美的過程,因為審美主體的差異性,也體現出人們的個性和品位的不同。
(二)情懷展現
拋去功利性的炫耀,有些人非常注重商品所富有的文化意蘊、藝術風尚和道德責任等,這是一種不僅僅局限于實用性和追求地位象征的一種高級的消費行為。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收獲了感官的快適和精神的滿足,這是一種升華,是對精神境界的追求。
我們沒有理由拒絕符號消費,也無法抵擋符號價值的魅力。但是過度的符號消費行為及觀念不利于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如非符號不消費這種觀念——這是很多先富起來的人群的基本心理特征,他們太看重商品所帶來的身份地位的象征性,這種觀念很不利于我們建立文明的社會風尚。因此,我們應該遵從自己的內心,少一分浮華,多一分體驗,遠離拜物、拜符號的陷阱,真正追求精神的慰藉,追求高雅而神圣的符號消費,讓消費做到真正的“物超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