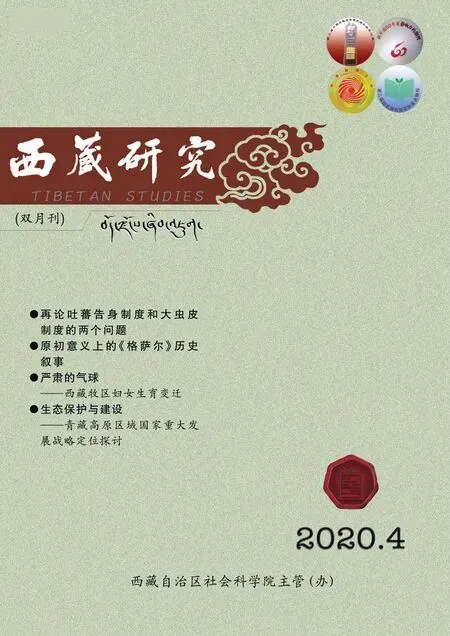珞巴族傳統體育的文化特征、變遷與傳承策略研究
洛桑澤仁
(西藏大學教育學院,西藏 拉薩 850000)
珞巴族是我國22個較少人口少數民族之一,珞巴族人口為3489人,約占西藏總人口的0.14%,主要生活在門隅以東、雅魯藏布江大拐彎以南山南市的隆子縣,林芝市的米林縣、朗縣、察隅縣和墨脫縣等地[1]14。這些地區交通閉塞,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直到解放前夕珞巴族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的家長奴隸制階段,過著以狩獵為主、刀耕火種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后珞巴族獲得了新生,1965年經國務院批準,正式確定珞巴族為單一民族[2]。珞巴族有自己的語言沒有文字,使用藏文,靠代代相傳的口頭傳說,延續著以狩獵生活為主、有別于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1]12。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特色鮮明,珞巴族傳統體育是在長期的狩獵、采集、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是珞巴族文化的符號和標志,與其他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共同譜寫了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健身娛樂的和諧樂章,對凝聚族群情感與民族文化認同起到了積極作用。對此,本文擬在對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特征分析的基礎上,探討珞巴族傳統體育的變遷與傳承研究的策略。
一、珞巴族傳統體育的文化特征
過去珞巴族以采集和狩獵為主,輔之以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方式,孕育了古樸、拙野的珞巴族民俗文化[3],并由此逐漸形成了與珞巴族民俗文化相一致的傳統體育。珞巴族傳統體育是世代相傳的文化表現形式,以活態的方式存在于珞巴人生活之中,是在特定地域環境、狩獵文化習俗與民族文化背景下產生,隨著珞巴族社會的文明進步逐步發展起來的,是西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蘊含多維度文化特征。
(一)地域文化特征
自然條件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基礎,特定的地域環境是一個民族繁衍生息的空間條件,珞巴族自古生活在喜馬拉雅山、雅魯藏布江流域極致、獨特的自然地域環境中,因此,將珞巴族傳統體育置于廣闊的自然環境中來審視有著重要意義。自然條件不僅直接制約著珞巴族的生產生活,甚至還間接作用于珞巴族的宗教起源和文明演進。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形成了珞巴人力量性、耐力性體魄,為在深山密林中狩獵攀藤索、溜索、跳澗、斷木桿、追逐等奠定了體質基礎。攀藤索、溜索、跳澗、斷木桿等是獲取狩獵生活資料必須具備的技能[4]601。為更好地適應自然環境,獲取更多的生活資料,一些與狩獵相關的跳竹竿、跳索、刀術、博嘎爾舞(刀舞)、投扎槍、摔跤、攀高、觸高、斷木桿、射箭等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的傳統體育項目,成為珞巴人休閑娛樂中不可或缺的內容[4]429。鏗鏘有力、優美的肢體動作,粗獷奔放和磅礴氣勢的刀舞;瀟灑自然、動感節律的跳竹竿;敏捷進退、吶喊聲宏亮的投扎槍,都顯示出珞巴族傳統體育有別于其他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地域文化特征。尤其是刀舞的地域文化特征最為顯著,刀舞與博嘎爾部的婚禮習俗有關,當新娘抵達新郎家時,“從木樓里奔出一大群年輕的和年長的男子漢,把所有送親者包括新娘在內,毫不留情地阻擋在大門之外”,抽出鋒利的珞巴刀,對著送親者揮舞起來,顯示威風和殺氣,而送親的珞巴男子漢也抽出長刀與他們對舞相搏,雙方還發出“哦! 哦! 哦!”的呼叫聲,兵器發出沉重而響亮的碰擊聲,無數雙赤裸的腳左邊跳、右邊跳、往前跳、往后跳,越跳越快,越跳越激烈,好似部落或氏族間的械斗、仇殺,實際上這是珞巴習俗婚禮開始時吉祥歡喜的刀舞歡迎慶賀儀式。當天婚禮眾人聚在一起一邊大塊吃烤肉、大碗喝燒灑,一邊跳刀舞、舉石頭、比跳高、射箭狂歡[5]60。表現出珞巴族人民剛強、豪放的民族性格和對力量、勇敢的崇尚[1]12。
(二)狩獵文化特征
直至20世紀50年代末,居住在深山密林的珞巴族仍過著狩獵、采集,“刀耕火種”的生活,使用刻木結繩來記事,珞巴族男子的裝束有著顯著的狩獵特征,日常生活中他們頭戴熊皮帽,身著短褲,身挎弓箭,肩挎“阿嘎”(毒箭筒),腰插砍刀[1]12。20世紀50—70年代,珞巴人的謀生手段以狩獵為主,他們打獵后拿獵物皮毛下山換取糧食[1]12,因而珞巴族的傳統體育射箭、跳索、溜索、跳竿、刀術、投扎槍等與狩獵相關[4]601。以射箭為例,珞巴族男子大多擅長射箭,射箭技能的高低決定著狩獵收獲的多少。珞巴族的先民在遠古時期,狩獵方法是圍捕,后來受甩石扔棒的啟示,創造了弓箭。時至今日,在米林縣南伊珞巴民族鄉才召村不少珞巴人家仍能看到古老的珞巴弓箭,弓是以強韌的竹子制成,并在弓背上貼有木塊,以防止弓背開裂,弓弦用植物纖維糅制而成,堅韌無比,箭頭為可重復利用的鐵制箭頭,箭靶大多以樹葉、竹竿、樹干等當之,或在一塊木板的中央用木炭畫近似箭靶的圓圈。人們在狩獵、生產勞作之余,以村為單位聚集在田野、廣場用手工制作的弓箭開展射箭比賽。比賽時,參賽者輪流張弓舉射,每人在規定時間內射3支或5支箭,以射中箭靶內圈多者為勝。參與者盡情宣泄自己的情感,精神上獲得快樂,既提高了狩獵技能,又滿足了當時原生態下珞巴人的娛樂生活,促進了身心健康。雖然具有狩獵文化特征的珞巴族傳統體育離現代競技體育的模式有些遙遠,但生活在現代語境下以狩獵內容的珞巴族傳統體育日漸式微。
(三)宗教文化特征
每一種文化的傳播都需要以特定的氛圍和載體為基礎,而宗教在這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與宗教有著密切的聯系,依賴于宗教信仰這個平臺得到延續與發展。“刀耕火種”時期人們對自然環境的認識能力有限,對千變萬化的自然力無法完全認識,因此,他們認為在這千變萬化的自然力背后有一種支配的力量——神靈的庇護。珞巴人多信巫教,認為“萬物有靈”,靈魂不死,每每出獵之前和獵獲之后,外出交換物質,或天災、復仇、失竊等,都要舉行祭祀儀式[5]45。珞巴族居于高山峽谷林區,對險峻的高山十分崇拜,每當出征出獵或外出交換時,均要殺牲祭祀山神,祈求神靈的庇護來消災化吉、驅邪懲惡[5]56。珞巴人每逢年節、春播和秋收要進行3次祭祀活動,祭祀完畢人們聚集在一起跳博嘎爾舞、刀舞、跳竹竿、投扎槍,為敬畏和崇拜的鬼神送上快樂和祈求,保佑山寨平安、谷物豐收,這是珞巴族傳統體育產生的根源。如珞巴族的宗教習俗舞紐布舞(刀舞),當人們出門行獵、遠行,或者得了某種疾病,主人把巫師(紐布)請到家里跳鬼。跳鬼時巫師披一塊紅色氆氌,手持大刀(或是削尖的竹竿和木棒),站在大約1.5米的曬籮里,腳不離籮,巫師用腳巧妙地蹬著籮底,手握長刀不停地轉動,同時人也自身旋轉,并舉刀、提刀、橫刀、砍刀,在刀光中剛開始比較慢,后來利用慣性越轉越快,進入一種如醉如癡的迷狂狀態[6]48。巫師(紐布)很重視平日對刀術的訓練,以及在竹籮內轉動的技巧和過硬的功夫,珞巴族傳統體育的刀術和刀舞基本上延續了巫師(紐布)的動作,并再現了珞巴人激烈的狩獵場面,具有原始古樸,豪邁奔放,氣勢威猛的特點[7]。珞巴人還把射箭用于占卜,“為預測生育是否順利,新郎新娘拿起弓弩箭簇,先由新郎向交叉立在院子的八根剛砍下的竹竿射箭,新郎射完后新娘接著射,直至射中竹竿為止。如果射出的箭聲音清脆,意味著新娘生孩子會順利,聲音沉悶則有難產的危險。”[6]46珞巴族的“達羌姆”歌舞射箭,以祭祀神靈為目的,是宗教習俗與傳統體育相結合的活動。首先,男女青年圍著燃燒的桑煙轉3圈,以祭祀神靈,邊轉圈邊唱敬神之歌;其后,男青年分成兩隊,一隊代表男方,另一隊代表女方,在離兩隊前方約幾十米處放置箭靶,兩隊人開始射箭。射箭開始時,由男射手歌唱一首祭祀神靈的歌。射箭有明確的要求,誰射中靶子,就在該隊的前面插一根竹子,竹子數量多者勝。
(四)民族文化交融特征
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中的許多項目屬于群體性活動,具有強烈的表演性、欣賞性和參與性。珞巴族傳統體育與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珞巴族與門巴族生活在同一區域,有的傳統體育項目與門巴族類似,他們都受到藏族傳統文化的影響,其抱石、摔跤、賽馬等體育活動與藏族傳統體育活動有著相似的內容和規則。珞巴族流行的響箭就是受藏族文化影響的典型,比如米林縣南伊珞巴民族鄉才召村的響箭場地、器材與藏族相同,每逢節日,或游客到才召村,年輕人就會聚集在一起進行響箭比賽。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身穿節日服裝,備好各種佳肴和青稞美酒,來到比賽現場觀看,他們還組成歌舞隊,為箭手們歌舞助興,加油助威,賽場上的選手不時以回唱呼應。伴隨著古樸歡快、扣人心弦的民歌與選手們射中靶心的歡呼聲此起彼伏,現場氣氛熱烈,既有藏族文化的內涵,又體現出珞巴族的民俗特點。目前米林縣在珞巴族中大力推廣藏族傳統體育項目響箭活動,取得了顯著成效。才召村幾乎每家都備有傳統響箭的弓和“畢秀”(響箭箭頭)。空閑時,人們聚集到村里的響箭場地進行練習和比賽。在2019年西藏自治區第六屆西藏戶外運動大會——林芝響箭比賽上,米林縣的珞巴族阿巴達尼隊用他們手工制作的傳統弓、“畢秀”參加比賽,并獲團體賽第一名[8]。米林縣珞巴族自治區級響箭非遺制作傳承人巴魯在研究藏族傳統體育響箭器械的基礎上,制作的“畢秀”深受珞巴人和游客的喜愛。
二、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變遷
珞巴族傳統體育活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珞巴族人民在與自然作斗爭中,根據狩獵、宗教祭祀、節日娛樂與健身需求,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表現形式。隨著西藏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珞巴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變遷,珞巴族傳統體育面臨著弱化甚至逐漸消失的困境。
(一)受眾群體少的變遷
人口少會導致傳統體育項目的受眾群體少,項目的影響力也有限。珞巴族人口為3489人,傳統體育項目僅有十余項,大多以狩獵生活有關。在這3489人中,除去不能參與的老人、小孩和不喜愛傳統體育項目的年輕人,能夠真正參與傳統體育項目的人數相當有限,因此,諸如跳竹竿、舉重石、攀高、觸高、投扎槍、斷木桿等因無人參與而自然消亡。項目的參與人群、受眾人群少,項目也就很難做大做強,在西藏乃至全國的影響力也就非常有限,也很難享受到文化體育部門的特別扶持,區外學術界對藏族傳統體育項目進行了全方位研究,但因為珞巴族傳統體育項目受眾群體少,認為其研究價值不高。這些主客觀因素不僅制約了項目的傳承與發展,也影響了珞巴族傳統體育在更大范圍內的傳播與實踐。
(二)生存環境的變遷
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國家扶貧政策和封山禁獵的實施,自治區政府為從根本上解決珞巴族的貧困問題,在環境較好的地區修建了寬敞明亮的房屋,將珞巴族群眾從喜馬拉雅山深山老林中搬遷了出來,長期居住在深山中的珞巴族群眾過上了定居的生活。隨著環境的變遷和現代生活方式的轉型,珞巴族結束了祖祖輩輩以狩獵謀生的生活方式,失去了與自然環境相適應的狩獵文化特性,“昔日的崇尚狩獵英雄的觀念不復存在,昔日的狩獵英雄成了孤獨的放牧者。”[9]關于生存環境的變遷,還可從珞巴族服飾的變異得到佐證。2006年11月,在米林縣南伊溝30戶才召珞巴民族新村入住剪彩儀式上,珞巴族村長身穿傳統的獸皮衣,外面披上一件西裝,其他村民大多穿著迷彩服或夾克,不難看出珞巴族服飾的變異也是很多現實的問題[10]28。隨著生存環境的變遷,脫貧攻堅的深入,扶貧易地搬遷的實施,珞巴族逐漸從狩獵生活向城鎮生活的轉變,尤其是青年人向往城市生活,到條件優越的城鎮工作、定居,使傳統體育失去了所依附的自然環境,尤其是缺少了所依附的“人”這一主體,與狩獵相關的射箭、投擲、攀高、投扎槍、斷木桿、觸高、跳竹竿、溜索等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人們的娛樂方式由鄉村集體化的自娛自樂轉向通過電視網絡居家觀賞現代體育競賽,這是由于生存環境變遷,珞巴族傳統體育保護傳承面臨的問題之一。
(三)傳播媒介的變遷
現代社會媒介是人類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與必要手段,傳媒的快速性、生動性已成為一種優勢。新興傳媒技術的變革不僅負載了傳統的精神交往、社會監督等功能,還負載了娛樂、時尚、消費、生活等更多的功能,而且對傳統文化帶來一定的沖擊。隨著廣播電視、網絡、融媒體、微博、微信等新媒體迅速在青藏高原發展,使地處祖國西南邊陲深山峽谷的珞巴族群眾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廣播電視、網絡、智能手機的普及,改變了村民們早已熟習并樂在其中的生活方式與習俗,尤其是年輕人通過網絡、微博、微信學習現代知識,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了急劇變化,再因珞巴族傳統體育僅在很少的族群中傳播,難以運用快捷的傳播媒介展現其文化內涵,使珞巴族傳統體育在現代傳媒的博弈中陷入了傳承的困境。
三、珞巴族傳統體育傳承研究的策略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現代文化與傳媒的興起,珞巴族群眾的生產生活方式、娛樂方式有了質的飛躍,人們的生活滿意度提高了,但具有原生態的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發展卻面臨挑戰。因此,學術界應擔當起對關注珞巴族傳統體育的變遷與傳承研究的責任,對傳承民族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共建精神家園具有重要意義。
(一)注重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挖掘研究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11]這一精神對珞巴族傳統體育的傳承研究具有指導意義。近幾年來有相關學者對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進行了研究,通過查閱中國知網、中國藏學網、中國西藏新聞網、中國民族宗教網等網站,以及相關報刊等資料,研究珞巴族的文獻共計有100多篇,研究珞巴族傳統體育的論文為7篇,從文獻分析得知,我國學術界對珞巴族的研究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珞巴族的歷史、社會形態、族群的生活習俗、族群聚居地的地理與氣候環境、宗教節日與民俗、民間文學、當代社會發展、非遺保護、族源、民族關系等方面進行了規模性和系統性研究[12]。涉及珞巴族傳統體育的研究主要有:1994年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關東升主編的《中國民族文化大觀(藏門珞族卷)》是最早涉及有關珞巴族傳統體育內容,認為珞巴族傳統體育有競技類和游戲活動兩種形式,是為了訓練技能、智能和體能的娛樂活動[4]601。西藏民族學院王國興在《珞巴族的射箭活動》一文中認為,珞巴族的射箭是與珞巴族長期生活在深山密林的狩獵生活分不開的,弓箭是珞巴男子的必備工具,從小不斷的練習形成了高超的射箭技能,狩獵休閑之余射箭比賽又成為珞巴族的競技娛樂活動[13]。西藏民族學院馬寧在《珞巴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一文中認為珞巴族傳統體育項目主要有射箭、跳竿、攀高、摔跤、舉重石、投扎槍等,提出要加強對包括民族傳統體育在內的珞巴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14]。西藏民族學院陳立明在《門巴族、珞巴族的歷史發展與當代社會變遷》中認為,隨著西藏現代化的加速推進,“珞渝”地區交通條件的改善和對外聯系的擴大,包括傳統體育在內的珞巴族傳統文化面臨弱化、消失的境地[15]。西藏大學丁玲輝發表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2期的《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略論》中認為,珞巴族傳統體育以節慶為載體,滿足珞巴族群眾的娛樂與精神需求,通過節慶習俗開展傳統體育活動,對展現珞巴族的民風民俗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劉愛軍、李祥妹在《西藏自治區人口較少民族發展問題研究》中認為,從鄉村文化發展看,西藏人口較少民族聚居的102個行政村有自己的語言、戲劇、體育等傳統文化,但這些傳統文化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搶救和管理[16]。西藏大學丁玲輝在《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及其生存現狀考察——以西藏米林縣才召珞巴村射箭習俗變異為例》(《西藏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中認為,射箭是珞巴族傳統體育中最具代表性的項目之一,隨著城鎮化和封山禁獵代表珞巴族狩獵文化的射箭競技失去了應有的地位。綜上,雖然有關學者對珞巴族傳統體育做了一些探討,但整體性、系統性、理論性、保護傳承探討研究不足,也未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藏學界研究關注不足。對此,學者們有待在前人對珞巴族傳統體育研究基礎上,對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進行系統挖掘研究,增強研究的科學性、系統性、前瞻性,制定切實有效的傳承對策,從而促進珞巴族傳統體育健康發展。
(二)注重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機制的研究
《西藏自治區“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指出:“西藏文化體育業應加強文化、體育和旅游等管理部門之間的合作,加強傳統體育項目體驗產品開發和供給,吸引大眾參與。”[17]因此,對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機制的研究,一是要積極探索“大文化”管理體制,搭建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層級保護網絡,將保護責任落實在邊境縣和基層鄉村,實現鄉村文化事業與珞巴族傳統體育發展的聯動效應,實現保護與發展的良性循環。二是圍繞生計方式特殊的珞巴族聚居鄉村,建立珞巴族傳統體育生態文化保護區,從政府層面引導體育文化資源向珞巴族聚居邊境地區傾斜,廣泛開展群眾性傳統體育文化活動。三是政府部門要設立面向珞巴族聚居社區的傳統體育發展基金,用于資助傳統體育傳承人、研究組織及傳播和演出單位申請使用,基金還可用于傳承瀕危體育項目搶救和研究、建立傳統體育文化活動站、創建傳統體育文化傳承中心,以及傳統體育項目體驗產品的開發等。
(三)注重珞巴族傳統體育融入鄉村文化的研究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挖掘鄉村多種文化功能和價值,統籌謀劃農村文化建設,著力推進鄉村文化振興。”西藏鄉村振興不僅是經濟的發展,還在于民族文化的傳承與鄉村文化的振興。珞巴族傳統體育根植于鄉村文化沃土,是鄉村文化的重要資源,在珞巴族傳統體育研究中,如何將這一資源融入“珞渝”地區鄉風文明建設,擬從以下兩方面著手。第一,將傳統體育作為促進鄉村鄉風文明、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工作來開展,要充分調動珞巴族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參與性,努力實現傳統體育在文化引領、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文化傳承中的作用。第二,要根據“珞渝”地區自然環境,有計劃、有組織開展傳統體育活動,滿足地處邊境地區珞巴族群眾的體育文化娛樂需求,推進村與村之間,族群之間,共居、共學、共事、共樂,增進珞巴族群眾的身心健康與獲得感、幸福感,使鄉村煥發出鄉風文明新氣象。
(四)注重珞巴族傳統體育與鄉村旅游融合的研究
國家確立把西藏建設成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對西藏旅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西藏自治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深度開發文化體驗、休閑度假、特種旅游等轉型旅游產品,鑄造旅游文化品牌。”西藏各地市積極探索、打造“旅游+體育”新模式,為西藏旅游發展注入新活力。近幾年來,民族傳統體育與鄉村旅游融合,已成為西藏鄉村旅游發展方向之一。林芝市米林縣南伊珞巴民族鄉依托南伊溝景區,在傳統體育與旅游融合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人們將過去用于狩獵的熊皮帽、刀、弓箭、響箭等提供給游客體驗,在村廣場為游客表演珞巴族刀舞、刀術,深受游客的歡迎。因此,對珞巴族傳統體育與鄉村旅游融合的研究,既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又能促進珞巴族傳統體育的發展與推廣。筆者認為要扶持發展溜索、攀索等探險體驗場地;打造響箭、射箭、跳竹竿等旅游休閑娛樂項目;鼓勵農牧民開發以響箭為主的傳統體育器材;建設以響箭、刀舞等為主的民族文化風情展示區,打造西藏鄉村旅游品牌。游客可參與當地的生活、勞作、傳統體育娛樂的體驗,在別開生面的活動中切身感受珞巴族的民俗風情。
(五)注重珞巴族傳統體育以人為主體的研究
珞巴族傳統體育是在長期的狩獵與生產勞動實踐中創造的以人為主體的文化,與珞巴族所處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相關。雖然珞巴族與生活在這一區域的藏族文化、自然環境相融合,但又凸顯出珞巴族文化的主體性。由于珞巴族與藏族相比人口基數少,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的民族學工作者在“珞渝”地區從珞巴族文化的主體性出發,開展了對珞巴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研究卻處于弱勢,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以珞巴族群眾為主體的傳統體育文化娛樂活動的話語權。如果在不具備普及現代競技體育的邊境地區追求“更高、更快、更強”,與地處高山密林環境的珞巴族群眾的主體性不相符。因此,在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研究中,要突出以珞巴族為主的主體性研究,提升珞巴族群眾使用民族文化資源的主體性,保障人們享有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權益,通過人的廣泛參與講好珞巴族故事,體現“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這一宗旨,實現傳統體育的文化價值與人文精神的統一。
(六)注重珞巴族傳統體育的傳播研究
在信息化時代,傳統文化的傳播離不開大眾傳媒,傳播的便捷性拓展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傳媒在傳承民族化中由過去學校、家庭等來完成的傳承任務,更多的被大眾傳媒的傳播所替代。隨著通信網絡在西藏的超前發展,即使深居大山密林深處的珞巴族群眾也能用手機看電子書、看電視直播,觀賞現代體育比賽成為時尚。但是,人們認為民族傳統體育只屬于民間藝人掌握的技能,與傳媒的傳播無多大關聯,對現代傳媒在傳播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重要性的認識不足。事實上,傳媒起著傳承文化、傳播信息的作用。因此,在對珞巴族傳統體育的傳播研究中,要充分利用各種媒介資源,例如廣播、報紙、網絡、電視等,對珞巴族傳統體育進行宣傳推介、推廣,使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通過現代傳媒的傳播可以有效提高社會公眾對珞巴族傳統體育的認知,成為弘揚民族文化的載體;有效推動珞巴族傳統體育與現代傳媒相關產業的社會關注和文化體驗;有效實現珞巴族傳統體育與現代傳媒深度融合下構建具有喜瑪拉雅文化元素、高原特色、民族風格的體育文化品牌,促進珞巴族傳統體育與現代傳媒融合互動和可持續發展;打造珞巴族傳統體育與現代傳媒互動發展的弓箭、畢秀、珞巴刀的制作與展示,形成與現代傳媒互動融合的傳播衍生產品,并具有較強知名度和較大開發價值的品牌,推動珞巴族傳統體育與現代傳媒互動融合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通過現代傳媒的傳播既能講明白為何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依然適用于當下,從更寬廣的視野關注珞巴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
四、結語
中華文化由56個民族共同締造,珞巴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為中國的文化發展與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珞巴族傳統文化正在經歷變異和復興,伴隨這一過程的文化融合和觀念更新,要促使珞巴人關注自身傳統文化的自覺[10]28,是當下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珞巴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要以“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為指導,根據西藏邊境地區的功能、定位,國家實施的“興邊富民”“建設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全民健身”“新農村建設”和“脫貧致富”等結合起來,增強研究的科學性、系統性、前瞻性,制定切實有效的傳承策略,促進珞巴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服務珞巴村寨民族文化的繁榮,實踐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文化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