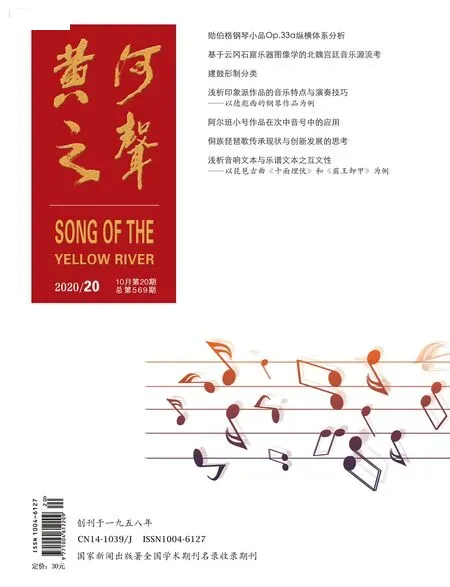建鼓形制分類
◎ 馬淼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
建鼓,最晚出現(xiàn)于殷商時期,因產(chǎn)生年代久遠,材質(zhì)不易長久保存,因此出土文物極少,至今所了解到的建鼓形制多參考現(xiàn)有漢畫像石圖像、歷史文獻資料、館藏仿制品,此文整合上述資源中的建鼓形制歸納整理為以下九式。
第一式 一楹穿鼓、下置底座
山東章丘女郎山樂舞俑中的大小建鼓①,是目前所見最早出現(xiàn)的建鼓樣式,該俑為戰(zhàn)國中期所葬,其中大小有別的兩件建鼓,為扁圓形鼓體,圓形支柱插于圓柱座上。兩擊鼓俑站立,一人一鼓,雙手各執(zhí)一鼓槌擊鼓,真實、直接地再現(xiàn)了漢代樂舞儀式中演奏建鼓的情形。大建鼓的鼓身頂部有圓錐狀結(jié)構(gòu)。這類結(jié)構(gòu),在“攢尖式”屋頂上也有出現(xiàn),稱為“寶頂”。此式建鼓除去鼓身,與現(xiàn)今天安門廣場升旗臺的升降柱無異。
此式建鼓整體為木質(zhì),一楹穿鼓,下置底座。或簡單的幾何形底座或復(fù)雜的動物、獸形底座,如羊座、象座、犬座等。除此式建鼓的底座外,在其他形制較為復(fù)雜的建鼓中,還有人面雙獸身座,虎座、象座、蟠蛇座、龍紋座等。建鼓底座又稱“跗”,孫穎達疏:“建,立也。立鼓擊之與戰(zhàn)也。”陳旸《樂書》曰》:‘儀禮·大射》:‘建鼓在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為一楹而四稜也,貫鼓於端,猶四植之桓圭也。”建鼓因鼓跗和鼓楹,得以在中華大地上巍然聳立了上千年,從未辜負“建鼓”這一稱謂。
第二式 頂“天”立地之鼓
天壇神樂署中的建鼓是目前所見建鼓實物中最為華麗的,頭頂金色寶蓋,寶蓋四邊拼接兩層長條布簾,蓋鼓身四分之一,華蓋四角飾及鼓身兩側(cè)均以彩色羽葆裝飾,粗碩的木樁貫穿鼓身,鼓楹頂部為四片扇葉狀寶頂,寶頂上立一神鳥,底座有四楞,四只虎獸趴附其上。底座有四楞,四只虎獸趴附其上。其形制為王正明先生以清代《皇朝禮器圖式》《律呂正義續(xù)編》為參考,請教專家學(xué)者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多次改進、實驗完成的建鼓仿制品,為明清時期兩朝祭祀、朝賀、宴享等宮廷儀式中所用建鼓樣式,主要用于演奏“中和韶樂”。漢畫像石建鼓圖像中呈現(xiàn)出的此式建鼓圖,因受各地風(fēng)俗習(xí)情及墓石刻畫者審美風(fēng)格等因素的影響,外觀有所不同,但結(jié)構(gòu)均為鼓身、鼓楹、鼓座附帶有羽葆華蓋等裝飾。此外,在神樂署建鼓頂部立著的神鳥也同樣值得納入此類形制的研究中。如東漢晚期的山東沂南北寨村樂舞百戲畫像石,樂隊中央植一建鼓,楹頂設(shè)有兩層華蓋,每層上均有繁盛的羽葆裝飾,頂部華蓋上也立一鳥,這種“蓋上立鳥”的現(xiàn)象,與古代屋檐上置放鳥、猴子、獸類的形制相似。
第三式 鈴鐺系鼓,金鼓齊鳴
東漢時期,山東滕州大巖頭建鼓雜技畫像石中的建鼓②,鼓身刻畫的極小,反襯出整個建鼓的體積之大,雙虎鼓座,楹頂蘑菇傘狀華蓋,上有兩猴嬉戲,華蓋兩側(cè)各掛兩條經(jīng)幡,經(jīng)幡系于兩個串連三角形物體的尾部。這類華蓋與幡條的結(jié)合在一起的結(jié)構(gòu),稱為幡蓋,在敦煌畫像中常有出現(xiàn)。直至今日,在四川、甘肅、云南等地,仍有一串串方形、三角形、條形的幡旗,被掛在門首、族幢、樹枝上,作為僧俗信眾溝通天神、宗祖的媒介,是福運昌盛的象征。王桂榛在《樂》一文中,通過考察古文“玄”字體的演變、“玄”與“樂”以及“建鼓”三者的關(guān)系,判定“幺”為掛于建鼓兩側(cè)的“鈴”,即懸鈴,筆者對文中核心觀點“樂即懸鈴建鼓”在此處不予發(fā)表看法,但漢畫像石中刻畫的建鼓形象中卻有懸鈴之建鼓,多為兩個懸鈴相接的串鈴,頭尾接幡條或羽葆成鈴綏,在此將這式建鼓稱為“鈴綏建鼓”。此式建鼓無實物出土,以山東鄒城金斗山出土的建鼓畫像石中的羽葆中段的懸鈴刻畫最為清晰,并非粗略的三角形代替,而是輪廓清晰的鈴鐺形。鈴鐺系于羽葆端掛華蓋之下,可想象其隨風(fēng)飄揚便叮叮作響,清脆悅耳。
第四式 青銅座建鼓
青銅鼓座曾侯乙編鐘的建鼓,是第一座考古出土的建鼓實物。現(xiàn)藏于湖北省博物館,是戰(zhàn)國早期(公元前年)入葬,鼓身部分為木腔皮鼓,長木柱貫穿鼓身,插于青銅底座上,青銅制作的底座由30條龍構(gòu)成,由8對主龍軀干及攀附其身、首、尾的數(shù)十條小龍組成,大大小小的龍均仰首擺尾③,這是最早出也是造型最為繁復(fù)的青銅制底座,將古代龍的雕飾發(fā)揮到了極致。可見對建鼓制作材料的講究,雖經(jīng)在歲月摧殘下,柱子、羽葆、華蓋都不復(fù)存在,目前所見為考古學(xué)家的復(fù)制品,但可以想見它曾經(jīng)一定有一副華麗的羽葆、一頂尊貴的華蓋,和一幢粗碩的鼓楹。這一類型的建鼓,底座為青銅鑄成,且均造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
第五式 應(yīng)朔搭配、“技”“樂”兼?zhèn)?/h2>
河南省出土的漢畫像石中,建鼓底座上兩側(cè)、鼓身周圍常伴有圓形圖案,學(xué)術(shù)界對此類圓形圖案的討論激烈,主要形成了“樂器說”、“蹴鞠說”兩大觀點④。
河南漢郁平大尹馮君墓出土的建鼓⑤畫像石中,建鼓鼓身下端兩側(cè)各有一圓形物體,兩名鼓吏側(cè)身弓步邁向建鼓方向,雙手各持一鼓槌,左邊鼓吏的右手鼓槌正在擊打圓形物體,右邊鼓吏左手鼓槌形似正在靠近圓形物體準備擊打。建鼓旁(側(cè))或有小鼓,搭配大鼓擊奏。根據(jù)圖中鼓吏的敲擊方式可以判斷,掛在建鼓兩側(cè)的兩圓形物體應(yīng)為應(yīng)鼓、朔鼓類小鼓。在先秦的雅樂樂隊中,應(yīng)鼓、朔鼓為單獨的兩個小鼓,先擊朔鼓、次擊應(yīng)鼓,再擊大鼓,圖中建鼓鼓身或底座的小鼓,與大鼓配合敲擊,不僅綜合三鼓于一便利演奏,還可根據(jù)不同的演奏曲目內(nèi)容豐富演奏的音響效果,展示鼓吏的高超擊鼓技巧。宋代陳旸《樂書》:“建鼓,魏晉以后復(fù)商置而值之......旁又挾鼙應(yīng)二小鼓而左右,然詩言應(yīng)田懸鼓,則周制應(yīng)田在懸之側(cè),不在建鼓旁也。”⑥宋代陳旸以為,這樣將建鼓旁掛小鼓的設(shè)計,是魏晉以后流行建鼓的制法。然而,“蹴鞠說”也并非皆無道理,從鼓吏動作、建鼓使用場合分析,建鼓所掛圓形物體有些確為鞠。作為樂舞百戲中的“固定樂器”,建鼓與雜技結(jié)合的例子也數(shù)不勝數(shù)。
第六式 建鼓掛銅鑼
西漢河南南陽方城東關(guān)漢墓出土的畫像石⑦,圖中建鼓形制復(fù)雜,華蓋下方橫置一木桿,兩頭各用三根繩固定一圓狀物,使其不會在外力作用下,輕易地左右搖擺,鼓身下端兩側(cè)各掛一三角形物體,三角形下方,有一正方形木框,底部似與底座兩稜重合,木框頂部橫木固定于鼓楹三分之一處,鼓楹樹木框正中間,木框上亦掛兩圓形物體。從圖像看似鑼。至今鑼與鼓的結(jié)合,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儀式活動中仍能見到。
第七式 鼓車、鼓騎
山東臨沂沂南北寨村出土的建鼓畫像石⑧,建鼓立于車上,楹頂上有豐富的羽葆,建鼓頂部為建鼓幢,幢竿頂部為方形平臺式,兩側(cè)垂掛流蘇裝飾,一人倒立于頂上,幢下雙層布簾華蓋,鼓身右側(cè)下端垂掛一小鼓,左側(cè)因樂人頭部遮擋未能判斷是否有懸鼓與其對稱。鼓旁一名鼓吏跽坐在鼓車內(nèi),雙手各持鼓槌正在敲擊。鼓車前段樹一幢竿,頂部亦為方盤狀,與建鼓幢對應(yīng),藝人兩者往返跳躍,展示了當時幢竿藝術(shù)的最高技巧。車前三匹駿馬,仰頭長嘯作奔馳狀,可以說明該圖所刻畫的是正在行駛中的建鼓戲車,用于樂舞百戲場面。《晉書·石季龍載記下》:“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建鼓常用于古代戰(zhàn)爭中,常于錞于配合,在戰(zhàn)爭中統(tǒng)一陣腳,方便將領(lǐng)發(fā)布號令,碩大的建鼓在戰(zhàn)場上不利于搬運挪動,所以要將其樹于“交通工具上”。后為更為便利的,將建鼓用于戰(zhàn)場,除馬車外,還有將其直接立于大象、駱駝、馬背上的“坐騎建鼓”。
第八式 大鼗亦建鼓
雷鼗、路鼗、靈鼗等大鼓在室內(nèi)擊奏或放置不用時,底部插入木(框)座,而室外擊奏式,左手執(zhí)鼓楹,右手持鼓槌擊奏。《周禮·春官·小師》鄭玄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⑨顯然,小而靈活是鼗鼓的一大特征。雷鼗除鼓兩側(cè)安“耳槌”可搖晃擊奏外,其他形制與建鼓無異。曾有學(xué)者以為,建鼓是鼗鼓發(fā)展而來,因先秦時期重視祭祀禮儀,故每個樂器應(yīng)嚴格擺放在固定位置,不差絲毫,故將鼓立于鼓座。筆者認為此類建鼓為多面鼗鼓與建鼓形制的結(jié)合,從大的方向看,符合建鼓一楹穿鼓下置底座而立的形制,應(yīng)亦屬建鼓。演奏上,形制較鼗鼓,體積大而不利于靈活快速擺動“耳槌”,鼓腔大導(dǎo)致聲音也與鼗鼓不同,音色應(yīng)更加渾厚,鼓聲傳得更遠;性質(zhì)上,這類建鼓與一般的建鼓相比,各司其職,分工明確,應(yīng)用場合不同。“建鼓”結(jié)合“雷鼓”“靈鼓”“路鼓”的發(fā)展形態(tài),同時繼承“祀天、祀地、祀鬼神”的祭祀作用于己身。這式建鼓形制特別,在中原地區(qū)少有見到。
第九式 “人形”建鼓
除上述八式建鼓形制外,還有一類最為特殊的建鼓——“人形”建鼓,見唐代敦煌石窟156窟壁畫《宋國河內(nèi)郡夫人宋氏出行圖》⑩中建鼓與上述建鼓形制相差甚遠,為一人身背建鼓,后又一人手持鼓槌擊鼓,兩人勻速步行前進。此式建鼓,以人體代替樹立的鼓柱,雙腳代替鼓座,背于背后身體中間位置,另有一人為鼓手,兩人移動擊鼓。至今,甘肅省河西地區(qū)的民俗社族儀式中仍有此式建鼓被使用。
結(jié) 語
中國的打擊樂器鼓和信仰、儀式聯(lián)系最為密切的就是建鼓,至今在北京天壇祭天,地壇祭地,國子監(jiān)祭孔,天地君親師。中華和鐘建鼓放在天安門城樓頂,一個鼓的放置位置決定了它的地位。在現(xiàn)代儀式中依然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從古至今從未中斷。橫向比較一下我們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群落都有不同式樣的鼓,但是沒有一個鼓,它的外在裝飾像建鼓這樣發(fā)展到如此華麗繁復(fù)的程度。集中了中國所有最高級的動物圖騰,龍頭、鳳、虎、龍身。甲骨文字的“中”,一豎中間穿一“口”字,上下像經(jīng)幡和飄帶,中間的“口”可解釋為中心一定范圍的區(qū)域。宋代蘇軾《教戰(zhàn)守》:“鐘鼓旌旗”,《周禮·春官·司常》:“凡軍事,建旌旗”,這片中心區(qū)域正是古代將士們手舉旗幟血拼下來守衛(wèi)住的國家。另一方面,甲骨文“中”的上半部分像極了一楹穿鼓,上附羽葆的建鼓,所以說,建鼓的羽葆一步步演變?yōu)閲业臉酥尽獓欤@一說法,并非空穴來風(fēng)。這件與古代中國最高儀式密不可分的尊貴樂器,其所包涵的文化意義值得我們深究。
注釋:
①②③⑤⑦⑧ 王子初.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M].大象出版社,1996.
④ 顧興立.漢畫像石中的建鼓研究[D].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2012.
⑥ [宋]陳旸.樂書(四庫全書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⑨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周禮·春官[M].中華書局,1980:797.
⑩ 鄭汝中,董玉祥.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甘肅卷[M].大象出版社, 1998: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