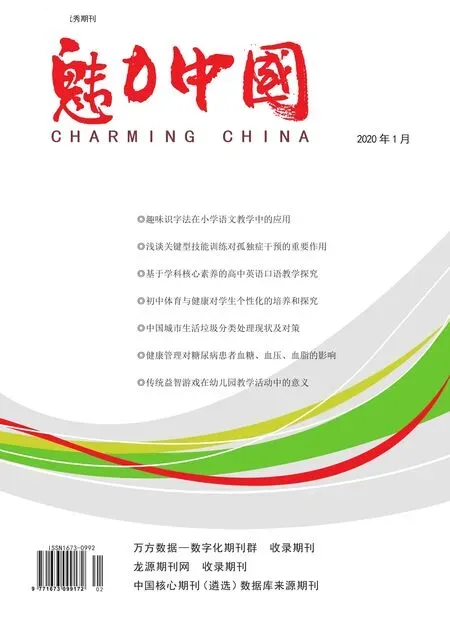稗官野史對史官正史的反哺
——小說與史學研究的互動
謝源庭
(貴州師范大學求是學院,貴州 貴陽 550014)
想象共同體的維系,依賴文本構成集體記憶作紐帶。史家和小說家同源于先秦時的“官學”,其群體所創作的史書和小說是中華文明歷史演進的兩套文明記錄系統。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稗官是“王者欲知閭巷風俗”而設立的小官。小說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一句,這里的小說并非文學上的小說,指瑣屑之言。稗官野史用來泛指記載軼聞瑣事,正史所不載的文學作品。
西周文化呈“學在官府”狀態,春秋晚期隨著鐵犁牛耕推廣,井田制瓦解,奴隸貴族們的“禮崩樂壞”。私學興起,大量的士活躍在歷史舞臺,出現“百家爭鳴”盛況。西漢劉韻編寫《七略》將此階段學術分類為“九流十家”,清人章學誠提出“劉歆所謂某家流,其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為某家學,則官守失傳,而各思之所至,自為流別也。”[1]在社會轉型的這個過程中,士階層的活躍使知識下溢到布衣之間,出現如蘇素、陳平等布衣之士。經歷秦朝的焚書坑儒,漢朝的罷黜百家,封建時期“小說家者流”進入非官方的民間成“為數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會思考的人們創造出”[2]的“小傳統”,具有敘事和教化功能,抒情上多表私情,內容寫廟堂百官,陽春白雪,也寫民間閭里,下里巴人,以個體創作為主。史家留在官方的廟堂,依附政權,成為“由多數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們創造出”[3]的“大傳統”將“屬詞比事,以月紀年,作生人之耳目者”作目的,內容多聚焦于宏觀維度,記錄國計民生大事。本文討論作為“小傳統”的小說和作為“大傳統”的史學,在歷史事實、歷史敘述、歷史詮釋之間的互動。
歷史有兩種定義:“一種是人類過去的活動,一種是人類活動的記載”[4]。中國古代史家有“秉筆直書”以使“亂臣賊子懼”的傳統,卻還有“隔代修史”“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缺陷,加上史書典籍保留傳世時,天災人禍等因素使文本亡佚,后人依據史料進行史實建構,就難免失真偏誤。小說與史書是記錄時代痕跡的兩套書寫系統,陳寅恪在探究唐人志怪與歷史真相關系時說:考證史事須“將官史及私著等量齊觀"。中唐李復言所著《續立怪錄》中“辛公平上仙”是傳世唐代志怪筆記中最隱秘一篇,與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柳宋元的《河間傳》形成證據場,影射了唐憲宗被弒秘聞,說明安史之亂后李唐皇權不穩的史實。漫長的古代,小說作為“小傳統”不經意間留下歷史的痕跡,補充“大傳統”正史的未記錄,為后人再認識我們的先民和腳下這片土地,提供更多材料。
歷史在歷史考據學層面上有“客觀的真實”后,材料的取舍,范圍的選擇影響著歷史敘述。“所有的敘事性的歷史作品幾乎都是依賴某種特定的歷史觀點編寫的,這樣它才能構成一個一貫的整體和一幅完整的圖畫。”[5]中國從公元前841年(周朝共和元年)起就有了每一年都能查出的記錄,一部《二十五史》浩如煙海,尚有二百九十四卷的《資治通鑒》存世,仍不能書盡史實。歷史流傳下來的僅是一個模糊的外形,只能根據史料與事理,無限的去不斷敘述。
小說源自說書。古時說書人社會地位不高,迎合大眾喜聞創作,加之未受良好教育,所講難免偏離史事導致以訛傳訛,內容敘事上這種非善即惡,快意恩仇的臉譜化敘事,裹挾著人們的價值判斷,且由脫胎其中的小說延續,干擾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以三國為背景,呂思勉在《三國史話》中說“現在舉世都說魏武帝是奸臣,這話不知從何而來?固然,這是受演義的影響。”[6]“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的說書郎,在“皇權不下縣”的鄉野,占據歷史敘事選擇主動權,反作用“大傳統”對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分析,展現了“大傳統”和“小傳統”的互動
文本背后的作者,將所認識的事實,用樹狀的語法,通過線性文字,書寫在不同材質的記錄工具上,形成文本得以感知。在解釋學看來,“文本不是外在于理解者的客觀對象,而是與理解者相互吸引的對話者,理解一個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種對對話中理解自己”[7]在這個“書寫-感知-理解”的環節中,歷史作品基礎是客觀事實,“小說的基礎卻是事實加上或是減去一個未知數”[8]這個未知數就是小說的虛構特權。
自封建社會肇始,文明深層邏輯就有“以吏為師”的思想烙印,兩千多年來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正統史學,長期把視野聚焦于社會上層,如梁啟超言“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9]放大歷史鏡鑒作用。近代救亡圖存的時代主旋律回響社會各界,1940年張蔭麟《中國史綱》自序中“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10]。同是1940年代,錢鍾書《圍城》序里講“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11]史書與小說在不同方向敘事。小說過去被視為“小道”,不能與詩文同上大雅之堂,長期處于“小傳統”,是文明記錄系統“執拗的低音”,但為歷史解釋拓寬視角。
思想通過語言具象化,獲得可被感知的物質形式,柯林武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小說作品同歷史作品一樣,依靠語言才得以鞏固和存在,所以呈現了類似的語藝模式,正如海登.懷特“歷史若文學”語。今日小說已成文學的中心文體,以塑造典型人物為核心任務。作家光輝來自寫作“對所處時代的剖析”“塑造的人物愈是豐滿復雜,并且鮮明獨有。”[12]史學,文學都是關于人的學問,作為“小傳統”的小說與“大傳統”的史學呈現了密切聯系,互相作用,文本形式類似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