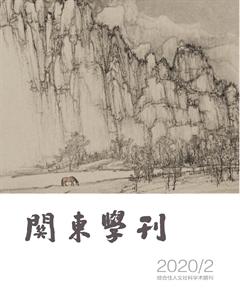論木心的愛情觀
楊大忠
[摘要]木心理想中的愛情,是唯美的,正因為過于唯美,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又是不存在的。木心將自己一生都交付給了藝術,這是造成他孑然一身的重要原因。木心對這個世界的濫情是失望的,認為這個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愛情;但對世俗愛情,木心卻又有著冷僻但精準的看法。木心的愛情觀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但主張愛情上的等量齊觀,反對強力蹂躪,主張男女在愛情中的平等,顯然又有著一定的價值意義。
[關鍵詞]愛情觀;唯美;濫情;探索
[作者簡介]楊大忠(1974-),男,歷史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中美木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杭州311121),桐鄉(xiāng)市高級中學教師發(fā)展中心正高級教師(桐鄉(xiāng)314500)。
木心的一生充滿傳奇性:他獨自前往西方的求學經歷,“文革”期間遭受迫害的自我浪漫,學貫中西的素養(yǎng)使之在當今文壇的獨樹一幟等等,無不令人嘖嘖稱奇,傾心贊嘆;而他一生的情感經歷,則更是引人注目。按照常理,像他這樣玉樹臨風的翩翩君子,身邊應當不會缺少女性伴侶,可他直至終老卻仍舊孑然一身,不能不令人感慨喟嘆。他留下的作品,幾乎沒有記載他情感經歷的蛛絲馬跡,而他自己對此也諱莫如深,從沒有對外界明確透露過自己的所愛所思所戀,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遐想了。那么,木心究竟如何看待愛情?他理想中的愛情模式是怎樣的?究竟什么因素使他終身沒有涉足婚姻?等等問題,都涉及到木心的愛情觀。從他留下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探索出木心對愛情的看法。
一、愛情已死,濫情大行其道,極少有人欣賞真正的愛情
應當說,對現(xiàn)實世界中的男女感情,木心是持悲觀態(tài)度的,他認為“愛情是一門失傳的學問”。在木心看來,自從溫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逝去后,真正的愛情就在這個世界消失了。愛德華八世為了愛情寧愿放棄王位,完美詮釋了“愛美人不愛江山”的內涵,這段感情可謂驚天動地、可歌可泣。
在愛德華八世和辛普森夫婦先后離世后,木心高度贊美了溫莎公爵夫婦之間的愛情:
愛德華八世與華利絲·辛普森,本世紀最后一對著名情侶,終于成為往事,各國的新-聞紙為公爵夫人的永逝,翩躚志哀了幾天,狀如藝術家的回顧展,華利絲年輕時候的照片,使新聞紙美麗了幾天。
看罷溫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愛情回顧展,猶居塵世的男男k'-k"都不免想起自己,自己的癡情,自己的薄情。
這分明是最通俗的無情濫情的一百年,所以驀然追溯溫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粼粼往事,古典的幽香使現(xiàn)代眾生大感迷惑,宛如時光倒流,流得彼此眩然黯然,有人抑制不住驚嘆,難道愛情真是,真是可能的嗎。
“無情濫情”的時間竟然已經長達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唯有溫莎公爵和公爵夫人之間的愛情獨居“古典的幽香”。這種真正的愛情似乎顯得很不正常,甚至可以說是畸形,因為現(xiàn)實中,“無情濫情”大行其道,使真正的愛情反而顯得另類了。公爵夫婦之間始終如一的愛情與庸俗毫不沾邊,純潔之至。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驚嘆甚至懷疑:“難道愛情真是,真是可能的嗎?”
正因為見慣了現(xiàn)實生活中的“無情濫情”,人們才懷疑愛情存在的可能性。純潔的愛情竟然成了生活中不可想象的奢侈物,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唏噓。
與世俗情感的“無”“濫”相比,木心對溫莎公爵夫婦之間的愛情是高度贊美的,同時也映照出他對現(xiàn)實中“無情濫情”現(xiàn)狀的嘲諷與鄙視。就木心個人來看,他終身未婚,原因當然非常復雜,但現(xiàn)實中的“無情濫情”或許也是他恐懼婚姻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溫莎公爵送給辛普森夫人的珠寶象征、見證了兩人之間的愛情,但是,這些珠寶最終竟然成了拍賣品。對此,木心感到無法接受:“愛情需要鑒定?瑞士的珠寶鑒定專家將鑒定溫莎公爵與溫莎公爵夫人的愛情,無價的,有價了。”將愛情明碼標價,這不正是現(xiàn)實中的“無情濫情”的具體表現(xiàn)嗎?!沒有被拍賣的時候,這些珠寶是“傳奇性的圣物”,因為它們象征著愛情的永恒;拍賣之后,佩戴在世俗之人身上,這些珠寶就成了“商品性的俗物”。
拍賣后的珠寶必將“零落殆盡”,溫莎公爵夫婦的愛情在世間連見證物都沒有了,難怪木心如此憤慨。木心的憤慨也引起有些學者的共鳴:“溫莎公爵和溫莎公爵夫人的愛情是浪漫的,太過浪漫了,有不實在的虛幻,這虛幻歸結到墓園來,只叫人感慨,因那身后的信物就將在蘇士比拍賣了,再恢弘的愛情也得拿這樣的方式決出含金量,這是世界的悲哀還是情人的悲哀。”“溫莎公爵夫婦的愛情見證物被拍賣,曠世的愛情被世俗取代。”世界的悲哀,情人的悲哀,兩者兼而有之吧。
鑒于公爵夫婦的身份和他們愛情的傳奇性,這些珠寶當然拍出了很高的價格,這些高價的珠寶將會佩戴在一些大亨巨富的身上,成為競相炫耀的資本。他們似乎分享了公爵夫婦的愛情,但在木心看來,擁有這些原本不應該屬于他們的珠寶,是對神圣愛情的褻瀆,與神圣愛情絲毫不沾邊。或許,人世間真正的愛情,也將永遠消失。
毋庸諱言,木心對愛情的要求太高了,高得令人無法企及。人世間像溫莎公爵夫婦之間的愛情,從古至今又有幾位?以溫莎公爵夫婦的愛情標準來要求世俗大眾,未免強人所難。木心似乎排斥了世俗生活中的其他愛情模式:相濡以沫的患難真情、青梅竹馬的日久生情、志同道合的深入之情,都被木心排除在了“愛情”的定義之外。在情感上,木心是個完美主義者,在他眼里,似乎只有像溫莎公爵夫婦之間轟轟烈烈且持久一生的感情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愛情”;木心又是個對愛情極其挑剔的人,既然將溫莎公爵夫婦之間的愛情視為真正的愛情,對其他情感視若無物,讀者自然不難理解木心孤獨一生的原因了。追求完美的人往往是生活中的孤獨者,對愛情所定的高不可及的標準,注定了木心一生的愛情生活只能存在于他的主觀理想世界中。
二、愛情的基礎是一見鐘情。外在形象在愛情中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木心眼里,愛情的先決條件必須是一見鐘情,“唯有一見鐘情,慌張失措的愛,才攝人醉人,才幸樂得時刻情愿以死赴之,以死明之……”但是,木心的觀點有時候也是矛盾的。在《芳芳No.4》中,“我”開始對鐘情“我”的芳芳并沒有產生情愫,毫無一見鐘情的感覺;可是,當芳芳下放到農村勞動春節(jié)后重回上海,“我”看到了另外一個脫胎換骨的芳芳,也不禁使“我”浮想聯(lián)翩:
……膚色微黑泛紅,三分粗氣正好沖去了她的纖弱,舉止也沒有原來的僵澀,尤其是身段,有了鄉(xiāng)土味的婀娜。我這樣想:長時的勞作,反使骨肉亭勻,回家,充足的睡眠、營養(yǎng),促成了遲熟的青春,本是生得嬌好的眉目,幾乎是顧盼曄然,帶動整個臉……無疑是位很有風韻的人物。我們形成了另一種融洽氣氛,似乎都老練得多。她言談流暢,與她娟秀流利的字跡比較相稱了。
之前的羞怯、纖弱、清癯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健康、陽光、成熟、老練。于是,“我”不無遺憾地想:“如果當年初次見面,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言下之意再明白不過了。
可見,木心強調一見鐘情,其實也不盡然,因為人是會變化的,俗語“女大十八變”有時的確有深刻的道理;但強調兩情相悅中的“一見鐘情”,對于愛情的確立直至成熟的確有著重要意義。
“一見鐘情”的基礎,自然是外在形貌與氣質,首先體現(xiàn)為“臉”是否精致:
愛情,是性為基點,化作出種種非性的幻想和神話——歸結還是性。都說性征是性器,其實第一性器是臉。真不好意思,人類每天頂著性走來走去。第一性器是“臉”!說得多么直白。臉,是外在特征最主要的體現(xiàn)。木心強調了外在特征在愛情中的重要性:
在愛情上,以為憑一顆心就可以無往而不利,那完全錯!形象的吸引力,慘酷得使人要搶天呼地而只得默默無言。由德行,由哀訴,總之由非愛情的一切來使人給予憐憫、尊敬,進而將憐憫尊敬擠壓為愛,這樣的酒醉不了自己醉不了人,這樣的酒酸而發(fā)苦,只能推開。也會落入推又推不開喝又喝不下的困境。因此,不是指有目共睹,不是指稀世之珍,而說,我愛的必是個有魅力的人。丑得可愛便是關,情侶無非是別具慧眼的一對。甚至,還覺得“別人看不見,只有我看得見”,驕傲而穩(wěn)定,還有什么更幸福。
這段話起碼包含了木心對愛情的多種看法:
第一,愛情不是單相思,不是單方面真心付出就一定能夠獲得愛情;愛情可以是一方追求另一方,但必須得到對方的回應。以為憑借熱情就可以獲得愛情,有時的確是癡人說夢。
第二,男女相戀,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外在形象。如果對對方的外在形象不滿意,但感動于對方的德行與哀訴而接受對方,在木心看來,這樣的接受不是愛情。如果把這種接受也叫做“愛情”的話,這樣的“愛情”就是“酸而發(fā)苦”的酒,毫無意義與價值。接受者一旦接過這杯“酒”,即看不上對方的外在形象但感動于對方的德行或哀訴而接受了對方,將來就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想離開對方,對方不同意;想由衷接受對方,但實在對對方產生不了興趣,只能違心地屈從自己。木心的意思非常明顯:對方的外在形象一旦吸引不了你,無論他(或她)對你的追求作出多大努力,也不能夠答應他(或她),否則,是自討苦吃。
第三,愛情沒有確定的標準。彼此相愛的人,也絕非一定是“有目共睹”“稀世之珍”的佳人才子。只要雙方能夠產生愛的感覺,即發(fā)現(xiàn)對方的魅力,情人眼里出西施,那么,哪怕在外人看來對方很普通(尤其是外在形象上),甚至可以說對方是“丑”的,只要在自己看來對方是“丑得可愛”的,這樣的情感也是愛情——愛情中最注重的,是自我感覺,而非大眾眼中的“帥”和“靚”。一句話,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木心一再強調愛情中的“一見鐘情”,排斥了以“一見鐘情”為基礎的感情在木心看來不是愛情,對于接受者來說是一杯“酸而發(fā)苦”“推又推不開喝又喝不下”的苦酒,這很好地詮釋了木心“一見而不鐘,天天見也不會鐘”的內涵。但木心有時也豁達地認為人是會改變的,“一見鐘情”的對象也絕非人們通常認為的帥氣男人和靚麗女人,它是“情人眼里的西施”。“一見鐘情”是愛情的基礎,對于愛情的確立而言相當重要。
三、扭曲的時代只能產生畸形的情感。這不是愛情
在木心看來,愛情只能在正常年代或正常歲月里產生,扭曲畸形的特定年代,不會產生真正的愛情。這里所說的“正常年代”,是指在這樣的年代里,男女雙方在社會地位或家庭地位上是平等的,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屬物,不會遭到屈辱與不對等的對待。只有在這樣的年代,男女雙方在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在世界觀與價值觀上往往能夠找到共同點,從而能夠在愛情上等量齊觀;反之,在男性采用暴力或強權來欺侮、壓迫甚或蹂躪女性的年代,由于雙方地位的不對等,即使有情人之間兩情相悅,也會因為時代的特定因素而勞燕分飛,造成許多人間悲劇。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真正的愛情往往會因為中途夭折而令人扼腕。這種思想就具體體現(xiàn)于《芳芳No.4》中。
芳芳對“我”鐘情,“我”當然是知道的,但“我”對芳芳卻始終不能產生感覺;直至芳芳響應國家號召下鄉(xiāng)安徽,經過勞動的洗禮,原先纖弱的芳芳變得“顧盼嘩然”,“有了鄉(xiāng)土味的婀娜”,“我”才對她變得注意起來,并且不無遺憾地想:“如果當年初次見面,就是這樣一個人……”,情愿對芳芳“鐘情”起來。
接下來就收到芳芳的來信,信中芳芳主動向“我”表達了愿意和我共度平安夜的想法,并且語氣非常決絕:
……即使不算我愛你已久,但奉獻給你,是早已自許的,怕信遲到,所以定后天(二十四日),也正好是平安夜,我來,圣誕節(jié)也不回去。就這樣,不是見面再談,見面也不必談了,我愛你,我是你的,后天,晚六點正,我想我不必按門鈴。
投懷送抱的堅決在使“我”欣喜萬分的同時,甚至覺得有點傷自尊。芳芳準時到來,木心用含蓄雋永的筆調將“我”和芳芳之間的兩性關系寫得如此唯美:
亞當、夏娃最初的愛是發(fā)生于黑暗中的嗎,一切如火如荼的愛都得依靠黑暗嗎,當燈火乍熄,她倏然成了自己信上所寫的那個人,她是愛我的,她是我的,輕呼她的名,她應著,多喚了幾聲,她示意停止,渴于和她說些涌動在心里的話;然而她渴于睡……
木心絕非思想頑固守舊的老夫子,他沒有將愛情與性分離開來,相反,他充分認識到了愛情與性的緊密聯(lián)系:
性只有在愛情前提下,是高貴的,刻骨銘心的,鉆心透骨的。愛情沒有性欲,是貧乏的,有了性,才能魂飛魄散,光華燦爛。不足了藝術達不到的極地。一個人如果在一生中經歷了藝術的極峰,思想的極峰,愛情的極峰,性欲的極峰,真是不虛此生。所以,木心沒有掩飾芳芳和“我”之間的性的體驗,而是將性的體驗寫得唯美絕倫。但激情過后,芳芳的表現(xiàn)卻是令人無法理解:
我迅速下床,端整早點,又怕她寂寞,近去吻她,被推開了。
一點點透過窗簾的薄明的光也使她羞怯么,我又偎攏——她站起來:
“回去了。”
這時我才正視她冷漠的臉,焦慮立即當胸攫住我:
“不要回去!”
“回去。”
“……什么時候再來?”
她搖搖頭。
“為什么?”
“沒什么。”
“我對不起你?”
“好了好了。”
也不要我送她,徑自開門,關門,下樓。
“冷漠”“搖頭”不耐煩,推開“我”的吻,之前的似火熱情蕩然無存,實在令人無法接受,也無法理解。這到底怎么回事?:
是個謎,按人情之常,之種種常,我猜不透,一直痛苦,擱置著,猜不下去。
因為猜不下去才痛苦……再痛苦也猜不下去——是這樣,漸漸模糊。
該怎么理解芳芳的舉動?
筆者曾在《(芳芳No.4>思想解析》文中聯(lián)系特定的時代背景與事情的前后邏輯關系合理推斷過芳芳的舉動:芳芳在農村遭到過侮辱。在“我”這個自視甚高的人眼里芳芳都是一個令人動心的女孩,她在農村,也絕對會成為一些心存不良動機的人覬覦的目標。我們不知道她遭到了什么樣的侮辱,但她主動找“我”獻身,顯然是為了彌補自己的一大遺憾:從沒有得到過心愛的人的愛撫,甚至都沒有甜言蜜語,她不甘心。與心愛的人共度良宵后主動離開,是因為在她看來,失身后的自己是不配與心愛的人在一起的。這應當是對芳芳蹊蹺做法的較為客觀的解釋。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年份與年代,怎么可能會出現(xiàn)芳芳對待愛情與戀人的匪夷所思的舉動;鬼蜮橫行的時代,強力劫取了女性的貞操,并且一并帶走了女性原本應有的矜持與羞恥心。之后,“我”的愛情(也許沒有愛情)自然與芳芳沒有了任何聯(lián)系,芳芳最后竟然由一個大城市的女孩成為了遠在哈爾濱的供銷社的一個小社員的妻子,由一個矜持內秀的少女變成了一個粗喉嚨大嗓門的庸俗不堪的老女人。木心在作品中沒有交代芳芳具體經歷了什么,這與木心在文革期間遭受非人待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更與木心對文革的經歷始終諱莫如深相吻合。在木心看來,愛情應當植根于健康正常的土壤,應當?shù)玫疥柟馀c甘露的普照與滋潤;人性扭曲的時代與愛情是絕緣的,這樣的時代最多只能產生短暫的兩性愉悅,但這種愉悅充滿了屈辱與不甘;之后就是人性的沉淪與自甘墮落,直至變得庸俗卑下。一句話:扭曲的時代里沒有愛情,只有欲望。
由火辣,到激情,再到冷漠,芳芳的舉動中蘊含著難以啟齒的隱痛,她是時代的犧牲者,莫名其妙的時代必然產生匪夷所思的情感怪胎,在沉重的濁世里,所謂愛情,輕得像一片羽毛似的,凌空飄舞。
四、愛情屬于年輕人。歷經風霜后終將返璞歸真
在木心看來,愛情是屬于年輕人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纏綿悱側的愛情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趨于平淡。“愛情再好,是終要厭倦的。”人到中年,生活的閱歷日漸豐富,少年時的稚氣與青年時的激情將會淡化為沉郁開朗的成熟穩(wěn)重,愛情中的激情也會隨之淡化直至歸于寧靜。老年階段,木心欣賞的是繁華褪盡的質樸真實,愛情已經被世俗的生活掩埋殆盡,留下的,是天然的豁達與看穿世事的恬淡,真正是“夕陽無限好”啊!
小說《完美的女友》正體現(xiàn)了上述思想。
在某次筵席上,來自西歐的華裔物理化學專家“我”偶遇中學同班的女同學,如今已成為女雕塑家。青春時期,共同的詩人之夢將“我”和她聯(lián)系在了一起,她曾不遺余力地幫助“我”,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夠成為一位詩人。但是,種種不可預知的因素卻使我倆人生殊途,之后二十年中的“戰(zhàn)爭、婚姻、職業(yè)和生活的滄桑”摧毀了“我”的詩人夢,“我”最終沒有成為詩人,而是成為了一個似乎與詩人背道而馳的從事物理化學研究的高級知識分子。
曾經,成為詩人,是多少具有浪漫情懷與小資情調的少男少女渴求的事,但生活往往是殘酷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是必須面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浪漫情懷在現(xiàn)實面前往往妥協(xié)得煙消云散。嚴峻的生活教育了“我”,使“我”明白詩歌不能當飯吃,詩人引起膜拜的時代已經結束。人到中年洞明世事,“我”不僅不再推崇詩歌,而且對詩歌產生了本能的反感與排斥:
我已久不近詩,偶或觸及,像聞到使人窒息的酒糟的濃香,還是石油的氣味好受些。
中年的“我”,浪漫情懷消失了,而女雕塑家卻依舊執(zhí)著于少年時期的夢。為了這個夢,為了擺脫與詩人之夢完全背離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糾纏,可能也因為丈夫的不夠浪漫與詩人氣質毫不沾邊,她毅然與丈夫離了婚,在人生的空白期再次遇見了“我”。
此時的“我”還在做著詩人之夢嗎?她不清楚。為了一探究竟,她借口想在“我”下榻的旅社午睡,作了精心的設計:
……每當我夜晚歸來,房屋總有新鮮感;或是名貴的花,或是書桌上多了幾件小擺設,抽屜里有巧克力,本來滿著的餅干箱,又換了品種,大盆的水果,是清朝宮廷格式,吃不了,只聞香味……
名貴的花、精巧的小擺設、巧克力、多樣的餅干和宮廷格式的水果,不都是青少年時期浪漫情懷的體現(xiàn)與寫照嗎?每一個過來人,對此應當有共鳴吧。可是,女雕塑家的浪漫布置還不止此,她真的想通過創(chuàng)造各種在她看來似乎可以獲取靈感的布置來觸發(fā)“我”對文學與詩歌曾經的熱愛:
某晚,我惴惴啟門,先看見壁上的歌德像,然后是窗畔艷紅的大理菊,一盆非洲常青藤吊了起來,綠葉繞過臺燈,垂及古銀鏤花的橢圓鏡框,中有普希金的相片。書架上原是幾本笨重的工具書和零落的數(shù)據(jù)資料,此時卻嚴嚴正正地站著大排世界名著……
不僅如此,枕畔竟然還有一件絲質的襯衫:“我見過別人穿這種式樣的襯衫,例如拜倫、羅密歐等。”這件襯衫完全是手工縫制。“哪有時間睡午覺,這針針線線的活兒,多費神。”女雕塑家的意圖昭然若揭了:她到“我”這兒根本不是睡午覺的,而是力圖喚醒“我”對文學與詩歌的熱情啊!
但作為一個中年人,“我”已經失去了浪漫情懷與文學夢想,并且“我”也非常認同如今的生活方式:在研究的領域拓展開掘,一切圍繞自己的事業(yè),而不是圍繞咖啡、巧克力以及濃得化不開的牛奶等小資情調。人到中年,蘊藉沉淀的應當是責任、事業(yè)與擔當,青春的激情早已經漸行漸遠,逐漸湮滅了。木心認為,這就是中年階段應當具有的樣子,愛情,那應當成為過去式了。正因為兩個人的思想觀念迥異,對生活的態(tài)度也產生了裂縫與分歧:
與女雕塑家重逢后,飲得不多,談得更少。彼此忙于工作。生活瑣事,毫無興趣啰嗦,我的本行,她是不問的,她的雕塑事業(yè),我有一點好奇心,就評論起古今的雕塑家來,真奇怪,她推崇的幾位,我漠然,我贊賞的幾位,她已近乎反感,我學會哈哈大笑,她學會悶悶不樂,話題急轉為“你再來一杯咖啡,還是紅茶”。時或同看電影,也曾于散場后漫步夜的街頭,對那電影的導演、演員的藝術,所見略同,互為補充;不期然涉及劇中人的善惡、賢愚、岔路漸顯,甚而爭論,分手時各自作出一副不介意的樣子。有一次看了《梅麗公主》,我自來同情皮恰林,她認為他是全然不良的,我為之辯解了一陣,她說:“那,多半因為你是一個男人。”
同為中年人,成熟穩(wěn)重的“我”看待問題比較理性而客觀,擁有浪漫情懷的她看待問題則比較感性而膚淺。
世界觀、價值觀與各自看待問題的差異,最終使女雕塑家對“我”徹底失望了,她退回到了她的世界里,最終也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既然都是明悉世事看穿世態(tài)的中年人了,我們應該明白,浪漫情懷是不應當在中年人的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在招待大家的宴請上,女雕塑家顯然通過“我”的朋友的言行意識到遠離浪漫和青春情懷的人絕非“我”一人,而應當是人到中年這個階段的共性。她的思想世界與同齡人格格不入絕非針對“我”這個個例而言,而是針對中年人這個群體了。于是,她只能泯滅自己一廂情愿但無濟于事的試圖改造“我”的想法,遠離“我”了。
她的最終結局是復婚,“有了兒子和女兒,很可愛的。事業(yè)順利,雕塑件數(shù)倒并不太多”。經過與“我”的重逢、對“我”浪漫情懷重塑的失敗以及看到“我”及朋友們的老成持重,她也真正意識到浪漫情懷已經逐漸偏離中年階段了,中年階段應當是什么樣子,她清楚了。她的復婚,意味著她思想的成熟,“事業(yè)順利,雕塑件數(shù)倒并不太多”意味著她已經將重心轉移到了家庭中并且很有中年時期的成就感,浪漫情懷也逐漸遠離這個曾無比執(zhí)著于此的人。
木心認為,中年階段就應當以事業(yè)為重,上有老下有小,都要靠中年人的肩膀擔起來。浪漫、激情與沖動已經與這個人生階段背道而馳。試圖將中年階段重新拉回做著文學之夢的少年與青年時期,只能是幻想與徒勞。每個人生階段都應當有其特有的特征,花前月下的愛情與中年時期是不應當沾邊的。
中年階段隨風而逝,老年階段呢?還有浪漫的愛情可言嗎?
從她最后的一封信看,我覺得,她和京城中滿街走的老婦人行將看不分明,我很喜歡很敬重那里的出沒于胡同口、菜場上的歸真返璞的老太太,即使她們爭斤論兩,也笑口大開,既埋怨別人的不公平,又責怪自己太小氣。
木心將老年階段看作是人生的“返璞歸真”階段。這個階段與浪漫激情的青年階段以及成熟穩(wěn)重的中年階段又大不一樣:世事完全洞穿,榮辱完全看淡,人生進入了大開大合隨性自然的坦途,再也沒有了心機、羞澀、陰謀、算計、爾虞我詐、你爭我奪……留下的,只是聽天安命、寵辱不驚、指天罵地、痛快淋漓……木心對老年階段的自然本性是持贊同態(tài)度的,對那位女雕塑家“和京城滿街走的老婦人行將看不分明”更是感到欣慰。
頤養(yǎng)天年、含飴弄孫、恬淡自適、待人寬容,盡情享受人生黃昏階段的嘉年華,這是老年階段正常而又精彩的生活。木心終生單身,但他對老年階段的看法卻很有意味。在《兩個小人在打架》中,木心寫下了這樣的話:
退休生涯,南江北漠,野鶴飛在閑云里。我已不止一次發(fā)覺自己的臉上凝固著微笑,這是傻相,該糾正為恬然木然的樣子,才與我的年齡身份相符,我試著做,做到了,而不知不覺,那傻氣的微笑又布滿了嘴角眼梢——也不能說虛偽,看一切,我都是抱著寬容的心態(tài)……
試想一下,在人生的這個階段,如果還有什么“愛情”產生,這還是木心心中的老年階段嗎?顯然,木心是排斥老年階段再生“愛情”的,他說過:“老者殘者的‘愛,,那是‘德,是‘習慣”,而非“愛情”;“青春肉體不再,愛情就不知還是什么。”木心曾論述過愛情與青春的關系:
愛情與青春
是“一”,是同義詞
青春遠而遠
愛情
不過是個沒有輪廓的剪影
為什么青春才是愛情
不懂嗎
那你一輩子
也算不上情人
枯萎的花
哪里來的
芳香 艷色 蜜晶
青春與愛情是“同義詞”,兩者是等同關系;中年與老年,屬于愛情之花凋謝、枯萎的階段,尤其老年階段,更是與“愛情”徹底絕緣了。
所以,在《完美的女友》最后,木心以特寫鏡頭的方式再現(xiàn)了一個后天命之年的老年人幸福的生活方式:
中國的京城,除了風沙襲人的春天,夏、秋、冬,都是極可愛的。尤其是十月金秋,藍天、黃瓦、紅楓,一個白發(fā)的老婦人,腰挺挺地騎著自行車,背后的車架上大捆的菠菜、胡蔥,幸福而顫抖……
“您老好啊,上我家來玩哪!”
在木心眼里,家長里短、鍋碗瓢盆、買菜做飯、老友過訪,都是老年人的樂事;當然,老年人快樂的一大前提就是身體要健康,這從老婦人騎自行車“腰挺挺”的狀態(tài)可以看出。青年時期的愛情,在不知不覺中早已隨風消散,淡出了老人的意識。經過多年的沉淀,愛情早已成為生活中相濡以沫的親情,少年夫妻老來伴,人生最后階段的情感是多么珍貴啊!就那位年老的女雕塑家來說,木心也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
但愿我能有這樣喜樂的一天,作為她家的賓客。如果她住的不是洋樓,而是古風的“四合院”,那就真是一個完美的夢。
希望以老友的身份拜訪女雕塑家,“我”和她都不會再有詩歌之夢,不,是這個夢現(xiàn)在想起來是多么甜蜜又多么可笑;而且希望她住的是古風的“四合院”而不是洋樓。這反映出木心的思想還是非常傳統(tǒng)的。作為思想傳統(tǒng)的中國老人,木心希望在生活方式上老年人也要契合傳統(tǒng)的安排與設計。
筆者非常自信,如果要問木心先生如何看待楊振寧與翁帆的“爺孫戀”,木心先生當然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但在他的內心,一定是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的,甚至對此鄙夷不屑。木心曾說過:“青年想戀愛,中年想旅游,老年想長壽,不是浪漫主義是什么。”青年人的浪漫主義是戀愛,戀愛與中年和老年是絕緣的。木心在《文學回憶錄》第四十講還說過:“老了還寫愛情,拿不出手。來美九年,敬愛情而遠之。”皆可謂木心認為老年人戀愛很荒唐的明證。
五、對木心本人愛情故事的探索
以我等世俗之人的眼光來看,木心這一生是比較悲苦的(當然,老先生不一定就如此認為)。他才華橫溢,卻孑然一身,無兒無女。在他的一生中遇到過愛情嗎?他到底愛什么樣的人?為什么他終生不娶,難道是愛情上受到過傷害?木心曾言:“光是愛情,有多少東西?”似乎對愛情不屑一顧;又曾調侃自己的愛情是“柳暗花明,卻無一村”,似乎自己曾有過愛情但有始無終。李頡先生認為:“木心所愛的,大都是虛無縹緲的佳人,或者說在文字世界里呈現(xiàn)出來的英雄或美人。”言下之意,木心所愛的人要么“虛無縹緲”,要么只能存在于文學世界中。一句話,木心所愛的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難覓蹤影。
木心本人是否曾有過愛情,這從《此岸的克里斯多夫》中可以一窺究竟。
1948年,木心準備離開臺灣前往大陸,同在臺灣的好友席德進“黯然而泫然”,情緒低落而傷心。兩人離別前的談話,似乎可以推斷出木心心靈世界的某些側面。
木心:“你以后,以后你的一生,將充滿痛苦。”
席德進:“我也不是不知道……但,你說,就沒有人會愛我?”
木心:“有的。很難有人像你愛他(筆者注:當指翁祖亮)那樣的愛你。”
席德進:“你呢?你的命運?”
木心:“我沒有命運。”
席德進:“奇怪,你不談自己,杭州認識,臺南重逢,這次再見,你從來就只談藝術?除了你的姓名,我還什么都不知道。”
木心:“我這個自己還不像自己,何必談它。”
這段對話其實預示了兩個人的命運:木心在席德進面前,所談的只是藝術,至于他的理想、追求當然也包括愛情,席德進與木心相處了那么長時間,竟然也全然無知。木心對此的解釋是:“我這個自己還不像自己,何必談它。”“自己還不像自己”有點過于深奧,以愚意揣之,大概意思是:所過的生活絕非自己想要的生活,尤其提升藝術的環(huán)境更是一塌糊涂。木心對自己生活的環(huán)境尤其藝術環(huán)境的要求是苛刻的,他是純粹地愛藝術、追求藝術,為此不惜以一種近乎自虐的方式來宣泄對現(xiàn)實的不滿。將自己的一生完全付諸藝術,從藝術中獲得心理的慰藉,以此來接近藝術上的理想國。由此,犧牲愛情就是獻身藝術的重要條件之一。愛情誠可貴,藝術價更高,將愛情也排除在外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木心與愛情絕緣,還有另外三層因素:
第一,從生理器官的隱顯系統(tǒng)被撤除看愛情的荒誕性。木心說:“能說‘偉大的性欲‘高貴的交媾嗎,不能。那么‘愛情自始至終是‘性的形而上形而下,愛情的繁華景觀,無非是‘性的變格、變態(tài)、變調、變奏。把生理器官的隱顯系統(tǒng)撤除凈盡,再狂熱纏綿的大情人也呆若木雞了。”雖然木心從來不排斥愛情與“性”的緊密聯(lián)系,他曾經說過:“性只有在愛情前提下,是高貴的,刻骨銘心的,鉆心透骨的。愛情沒有性欲,是貧乏的,有了性,才能魂飛魄散,光華燦爛。”認為“性”能給人帶來愉悅的巔峰,這是高貴的愛情的基礎;但是,性的愉悅是通過生理器官的接觸來完成的,一旦從生理學的角度看待生理器官,剖析其結構,生理器官和人體其他器官一樣,并沒有什么神秘與高貴。可見以性的愉悅為基礎的愛情是多么荒誕,那不過是普通器官的接觸而已。鑒于此,木心鄙薄十八、十九世紀把愛情當作事業(yè)奉為神圣的人,認為他們“半生半世一生一世就此貢獻上去——在文學中所見太多,便令人暗暗開始鄙薄”。高聲宣布:“決不再以愛情為事業(yè)。”不能不說,木心對愛情的看法是存在偏見的。以性欲為基礎的愛情,銷魂蝕骨,是不能從生理學的角度來冷冰冰地剖析的,那是科學與醫(yī)學的范疇;對于在身心與情感上水乳交融的愛情雙方來說,“性”是應當排除“器官活動”的說法,因為這必須考慮“人”的因素了。愛情的美好就在于她的神秘和愉悅,拆穿性器官的結構來解析愛情,就會將愛情置于一覽無余的境地。神秘感、朦朧感一旦消失,愛情就不復存在了。木心的看法無疑是有缺陷的。
第二,對婚姻的恐懼。木心的《同車人的啜泣》說的是婚后的男人因為妻子與婆婆、小姑之間沒完沒了的爭斗而疲憊不堪,最后竟然在公交車的椅背上不顧體面地大聲啜泣起來,內心的悲苦可想而知。可怕的是,這種爭斗還是在新婚不久,真不知道今后還會發(fā)生什么樣的無法調和的事。對此,木心幸運地評價道:“我似乎很滿足于心里這一份悠閑和明達,畢竟閱人多矣,況且我自己是沒有家庭的,比上帝還簡單。”單身的人是“悠閑和明達”的,免去了婚后的痛苦與不幸。
第三,木心與婚姻絕緣,極有可能源于少年時期的一次“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朦朧經歷。
木心十五六歲時,曾鐘情于一位軍官的夫人:“女的恰好是頎長白皙,瑩潤如玉,目大而藏神,眉淡而人鬢,全城人都不住地驚嘆她的柔嫩,我知道歷史上有過美子被眾人看死的事,真恨這么多的人不罷不休地談論她,她要被談死的……軍官夫人天性和悅,色笑如花,隱隱看出我對她的崇敬,在談話中時常優(yōu)惠我。軍官才智過人,他明白我的癡情,悄然一瞥,如諷嘲似垂憐,偶爾對我有親昵的表示,我決然回避——知道自己的愛是絕望的,甘心不求聞達,也無福獲得酬償。愛在心里,死在心里。”
后來,軍官夫人在一次渡水中,船被風浪打翻了,淹斃在船底下。木心產生了一種徹骨的疼痛:“……也曾在一部希臘影片《偽金幣》的畫家的情人的臉上看見那軍官夫人的臉,貌稍有所合,而神大有所離,軍官夫人更靈秀,清醇,她是一見令人溽暑頓消的冰肌玉骨清無汗者——為何有這樣的死?”
那么,木心的這段敘述是真實的嗎?毫無疑問是真實的,因為木心說:“此非傳記,我不寫出那軍官一家三人的姓名。這不是小說,我免去了許多本也值得編纂的情節(jié)。更未可說是我的自白,我殯殮了當年更凄苦更焦灼的不可告人的隱衷——可惜,也真可惜。”
木心之后的人生,雖然也有過不為我們所知的羅曼蒂克史,但從木心所有作品來看,他似乎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從沒有再遇到過像軍官夫人那樣的優(yōu)秀女性了。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木心對自己的愛情對象是相當挑剔的,但少年時期“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先人之見,似乎始終束縛了木心的愛情抉擇。李頡先生認為木心所愛的大都是虛無縹緲的佳人或者說在文字世界里呈現(xiàn)出來的英雄或美人的確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忽視了木心將愛情對象僅僅局限于文學作品中“佳人”“美人”的深層原因:既然像軍官夫人那樣的女性在現(xiàn)實生活中再難尋覓,就只能與文學與藝術中的佳人相伴了。
木心理想中的愛情,是唯美的,正因為過于唯美,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又是不存在的。木心看淡愛情,他以“我的愛情觀”為題明言:“愛情,人性的無數(shù)可能中的一種小可能。”既然人性概念中有無數(shù)種可能,愛情只是其中的“一種小可能”,可見木心看透了愛情,對愛情很厭倦:“愛情再好,是終要厭倦的。再找?人生的麻煩就是這樣。”木心將自己一生都交付給了藝術,這是造成他孑然一身的重要原因。木心對這個世界的濫情是失望的,認為這個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愛情;但對世俗愛情,木心卻又有著冷僻但精準的看法。當然,木心的愛情觀有著一定的局限性,如認為中年與老年階段不應當有浪漫情懷,但是,木心主張愛情上的等量齊觀,反對強力蹂躪,主張男女在愛情中的平等,顯然又有著一定的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