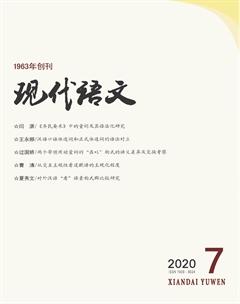認知語言學視角下漢語網絡流行語研究
李佳欣



摘? 要:認知語言學各種理論的出現,為解讀漢語網絡流行語提供了新的視角。以“‘X精格式”“涼涼”“上班996,下班ICU”“我太南了”等網絡流行語為例,從認知語言學的原型范疇理論、隱喻轉喻和概念整合理論、象似性理論、關聯原則等方面,探討網絡流行語的語義形成、認知心理和構成機制,從而對漢語詞匯的語義演變有一個更為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網絡流行語;認知解讀;隱喻轉喻;概念整合
周海中曾指出,“網絡語言是一門介于網絡技術和語言科學之間而偏重于語言科學的交叉學科”[1](P62)。孫潔等認為,流行性是網絡流行語和普通網絡語言最重要的區別特征,很多網絡流行語的研究,只強調網絡流行語的“網絡化”特征,而忽視或者弱化了其“流行性”的重要特征[2](P102)。關于網絡流行語,學者們的界定也不一致。陳建偉指出,“網絡流行語是網絡上流行的一種語言形式,是網民們約定俗稱的表達方式。”[3](P10)陳一民認為,“網絡流行語指伴隨現實社會新聞事件的發生,在網絡幾近同步產生、迅速流行風靡于網絡內外、短時間內生命力極其強大但并不長久的熱門詞語,又叫網絡雷語、網絡熱詞語。”[4](P16)韓玉花認為,“網絡流行語是指以互聯網為載體而廣泛傳播的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鮮活語言形式。”[5](P3)現在的網絡流行語并不只是詞匯,還包括短語和句子,如“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問”“你有freestyle嗎”等,因此,我們將網絡流行語定義為:反映特定時期社會熱點事件或現象,在網絡上流行并延伸至現實生活的一種語言現象。因為流行具有動態的特征,所以網絡流行語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從出現、演變到消亡的過程。同時,某個網絡流行語的意義也不是穩定不變的,在傳播過程中會因為使用群體、具體語境的情況而產生不同的解讀。
王寅指出,“認知語言學是一門新興的、跨領域的學科,它堅持體驗哲學觀,從身體經驗和認知出發,圍繞概念結構和意義研究,探索語言事實背后的認知方式,并通過知識結構等對語言作出統一解釋。”[6](P2)本文擬從認知語言學的原型范疇理論、隱喻轉喻和概念整合理論、象似性理論、關聯原則等方面對漢語網絡流行語進行分析。
一、原型范疇理論與原型轉移
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物體和現象,人類要認識它們,就有必要在認知上對它們進行分類。像動物、植物、桌子、椅子等,我們不難對它們進行分類,也不難給予它們分類的名稱。不過,對有的現象進行精確分類就不是那么容易,如冷水、溫水,我們很難把握它們之間的明確分界線。因此,對這類現象的分類可以視作是一種心理過程,這種分類的心理過程就稱之為“范疇化”,即在我們的認知中某種現象屬于哪種類別。范疇是圍繞著原型形成的,原型從心理上來說是一個認知參照點,從表征上來說就是一個范疇中最典型的成員,具有認知顯著性。同時,范疇是按照家族相似性原則組織起來的,因此,范疇的邊界是模糊的。一個范疇內的成員之間的一致性來自家族相似性,而非具備某一或某些全部范疇成員所共有的屬性。原型轉移則是指范疇的核心成員被其他成員所替代這種現象。
漢語“X精”格式中的“精”,就經歷了原型轉移的過程。在魏晉時期,“精”是“妖精、妖怪”的意思,后來也指怪異、反常的事物或現象。圍繞這一語義中心,漢語中出現了很多這樣的用法,如《西游記》中的白骨精、蜘蛛精、琵琶精,《聊齋志異》中的狐貍精、蛇精、鼠精等。這些作品中的精怪都可以幻化為人形,不僅具有自身物的特質,還體現出社會人的特點。“精”在某種程度上便被賦予了反常的或不被大眾接受、喜愛的人的意義,這種意義在后世中得到固化,網絡上也出現了“檸檬精、戲精、杠精”這樣的說法。在傳統視野中,這樣的詞義演變被認定為是詞義泛化、比喻等;從認知語言學理論來看,則可以用原型范疇與原型轉移來解釋這種詞匯意義的變化。
我們不妨將“精”看作一個范疇,范疇原型符號則借用Ungerer中的符號><來表示[7](P27),如“>蜘蛛精<”等。接著把“精”的范疇成員匯集在一起,更確切地說,這些成員都是它的下位范疇。就傳統意義上來看,它的中心成員為那些不是人類卻具備人類的一些核心特征的生物,如蜘蛛精、鼠精、白骨精等。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網絡的傳播,又出現了一些新興的流行語,如檸檬精、戲精、杠精等。這些詞語雖然都屬于“X精”格式,但是在語義上卻有所區別。比如,蜘蛛精、鼠精、白骨精、蛇精等,是指那些不是人類、但能幻化為人的生物,它們可以像人一樣說話、行動、思想等,并常常給人帶來災禍;狐貍精是指妖媚迷人、給人帶來災禍的女子;害人精是指給人帶來麻煩的人;豬精是指又丑又胖的人;戲精是指表演、演戲很厲害的人;檸檬精是指嫉妒別人的人;杠精是指喜歡抬杠、故意唱反調的人。
如前所述,這些范疇成員應通過家族相似性組織在一起,那么,在“精”這一范疇中,它們是怎樣組織在一起的,又是經歷了怎樣的原型轉移過程呢?下面,我們就結合圖示的方式,對這一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我們構建了傳統意義上的“精”的原型范疇示意圖,具體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在表示“妖精、妖怪”義時,最接近“精”的原型范疇是>蜘蛛精<、>鼠精<這類怪異或反常的事物,我們在圖中用粗線圈起。隨著>
狐貍精<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文學作品和日常用語中,它的隱喻意義“專指魅惑人的女人”得到廣泛使用,這就使得“精”產生了專門隱喻某類人的用法,正如圖中>狐貍精<的圓圈所示。這種表“人”的用法在后世逐漸得到加強,并固化下來,于是>蜘蛛精<、>鼠精<等核心成員遂被其他成員所替代。這一原型轉移過程具體如圖2所示:
從圖2可以看出,>狐貍精<逐漸取代>蜘蛛精<等成為原型的下位范疇,>蜘蛛精<等范疇成員逐漸邊緣化。在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下,又催生出一大批新的網絡用語,如>杠精<、>檸檬精<等,這些流行語的出現使范疇原型出現新的競爭。此時,>檸檬精<這樣的用法便成為新的原型,>狐貍精<又被推向范疇邊緣。這一原型轉移過程具體如圖3所示:
從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在“X精”格式中,“精”的概念原型從>蜘蛛精<、>鼠精<向>杠精<、>檸檬精<發生了轉移,原先的“妖精、妖怪”意義先是被隱喻為“給人帶來災禍的人”,再逐步向專指“人”的意義過渡,最后>蜘蛛精<、>鼠精<被推向了范疇邊緣,>杠精<、>檸檬精<遂成為新的范疇原型。面對這個原型的概念內容所發生的演變,尤其是從>蜘蛛精<、>鼠精<到>杠精<、>檸檬精<的變化,語言使用者所受到的干擾卻很小,理解起來也沒有太多障礙。這是為什么呢?這主要是因為“精”的重要屬性(如“怪異、反常的事物”“某些情況下令人難以接受的事物或現象”),都從傳統的范疇原型轉移到新興的范疇原型上了。也就是說,盡管“精”的原型發生了轉移,但它的某些概念結構仍保持不變。
二、隱喻、轉喻和概念整合
隱喻和轉喻是認知語言學的重要理論,也是我們對世界進行概念化的重要認知工具。大致來說,隱喻表示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相似性關系,轉喻則表示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鄰近關系。我們可以借助源域對目標概念進行概念化。心理學家發現,人類的情感體驗和生理體驗之間具備某種關聯,當人們在描述憤怒、悲哀或快樂時,總是把體溫升高、脈搏頻率變化、心悸或出汗、流淚等生理癥狀包括進去,生理癥狀被看作是情感體驗的結果。萊考夫、約翰遜由此假設了一個普遍轉喻,即某種情感的生理結果可以代表這種情感[8](P32)。
這里以網絡流行語“涼涼”為例,對這一問題展開分析。《涼涼》最先是一首歌的名稱,原本是張碧晨和楊宗緯為電視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所演唱的片尾曲。后來在網絡直播間里,游戲主播在玩游戲時,游戲中的人物如果死掉了就會說“涼了”,觀眾們也會在直播間說“一首涼涼送給主播”。于是,一些網迷就用“一首涼涼送給某某”“涼了”“涼涼”等表示“死了、沒救了”。這種用法經過微博、貼吧等媒介的廣泛傳播,逐漸被更多人所熟知,并在網絡迅速走紅。
我們發現,“涼涼”這個詞語的網絡用法有兩個認知心理來源:一個是來源于身體經驗,即人死后體溫會下降變涼,就此而言,用“涼”來轉喻死亡,是由原因——結果這一基本關系對應起來的轉喻;另一個是來源于心理感受,因為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傷絕望的事情,所以“涼”又能用來隱喻悲傷絕望的心理感受,由這一生理轉喻所引發的基本隱喻就是“悲傷絕望是涼”。在漢語中,有許多這樣的隱喻實例。例如:
(1)蔣家妻兒飛離溪口后,父子二人甚感凄涼。(李松林《晚年蔣經國》)
(2)當此之際,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涼氣氛中,蔣介石與宋子文兩人作了徹夜的長談。(陳廷一《宋氏家族全傳》)
(3)我帶著如此冰涼的思想走到了街尾27號。(胡玥、李憲輝《女記者與大毒梟劉招華面對面》)
(4)當時,宋慶齡曾想回國,但一想到她的家庭與蔣介石的關系時,心頓時涼了。(陳廷一《宋氏家族全傳》)
當人們在網絡中使用“涼涼”或者“涼了”一詞時,我們很難說是單純激活了“身體涼代表死亡”這一轉喻,還是單純激活了“悲傷絕望是涼”這一隱喻。人們更傾向于將這兩種認知心理整合在一起,因此,“涼涼”在語境中就不僅可以表示悲傷絕望,也可以表示 “沒救了、完蛋了”等意思。例如:
(5)王思聰欠了銀行一個多億,他老爸縮水600多億,他倆是不是都要涼了?(新浪微博,2019-11-07)
(6)考完試我就知道自己涼涼了。(新浪微博,2019-03-04)
網絡流行語“上班996,下班ICU”則是一個典型的概念整合的例子。概念整合就是將兩個輸入心理空間(input mental space)通過跨空間的部分映射匹配起來,將兩個輸入空間有選擇地投射到第三個空間,即一個可以得到動態解釋的整合空間(blended space)。
“上班996”中的“996”代表每天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一周工作6天。這是一個形式——概念轉喻。而“下班ICU”則是用地點“ICU”轉喻身體健康受損、生病住院。讀者在看到“上班996,下班ICU”這一表達時,就構建了兩個心理空間。第一個心理空間可以稱為“工作空間”,這一心理空間包括員工超長時間工作等信息,同時激活的是過度勞累會使人健康受損這一信息;第二個心理空間可以稱為“治療空間”,這一空間包括醫生搶救重癥病人等信息。根據概念整合理論,這兩個心理空間即工作空間和治療空間被稱為輸入空間。在認知處理時,它們被并置整合成一個新的“整合空間”,這個空間包括了從兩個輸入空間映射的信息。“上班996,下班ICU”這一網絡流行語的概念整合過程如圖4所示:
如圖4所示,輸入空間以跨空間映射的方式相互聯系。對“上班996,下班ICU”這個轉喻來說,這個跨空間映射的基礎是原因——結果關系,即過度工作會導致身體健康受損甚至危及生命。兩個空間在此基礎上經歷了壓縮,壓縮的重要結果是,來自兩個源頭的概念復雜性大大降低。也就是說,這個新出現的整合空間具有認知上的經濟性。至于“上班996,下班ICU”這一事件中重要的行為參與者員工,則從輸入空間1中工作行為的施事轉變為整合空間中的需要被搶救的受事。
三、象似性
象似性最初是一個哲學話題,認知語言學將它用來解釋語言的認知基礎問題。王寅在《論語言符號象似性》一文中把語言符號的象似性定義為:“語言符號在音、形或結構上與其所指之間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現象。”[9](P4)也就是說,象似性包括音近象似,如杯具—悲劇;形近象似,如囧、槑;結構象似。結構象似可以解決語言成分排列的問題,它包括順序象似、數量象似和距離象似。順序象似是指語言成分的排列順序要與事件的自然時間順序相符;數量象似是指語言單位的數量與所對應的概念的信息量和認知復雜程度成正比;距離象似是指短語或句子中關系近的成分應該靠近放在一起。
網絡流行語“我太南了”來自日常生活用語“我太難了”,表示一個人步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或者遇到困難不知如何應對的情況。從“我太難了”演化到“我太南了”,是來自于網絡上的一段對話:
(7)北極熊:你怎么不來找我玩?
企鵝:我太南了!(搜狐網,2019-09-08)
這實際上相當于修辭學中的諧音修辭格。在漢語中,很多歇后語、諺語、謎語都是借用諧音的方式而形成的,如:“打破砂鍋紋(問)到底”“外甥打燈籠——照舊(舅)” “孔夫子搬家——凈是書(輸)”等。從認知語言學理論來看,諧音現象其實就是音近象似。“我太南了”的用法得以廣泛流傳,還得益于有人把麻將中的“南”拿來當表情包。由于“南”和“難”是同聲詞,于是人們用麻將中的“南”來諧音“難”,從而產生了詼諧調侃的效果,這同樣是因為這兩個字之間存在著音近象似的關系。無論“南”的意義是來源于方位詞“南北”的“南”,還是麻將中“南風”的“南”,它都可以使讀者迅速從“南”的字形聯想到“nán”的讀音,繼而關聯到同樣讀音的“難”,并用“難”的詞義來解讀“南”,從而完成認知解讀過程。
由“我太南了”又引發出更多的類似用法,如“南上加南”“左右為南”“南的找不著北”等,這些用法配上麻將的表情包,效果更加直觀形象。需要指出的是,來源于南北方向中的“南的找不著北”等,與來源于麻將中的“南上加南”“左右為南”等并不完全一樣。“南的找不著北”除了音近象似以外,還經歷了概念整合的過程,它是將“困境空間”與“方向空間”進行概念整合后形成的新的整合空間。
網絡流行語在形近象似方面也有著廣泛的表現。除了上文提到的“囧”“槑”之外,流行語“是個狼人”“9012”也是通過形近象似原則構建的。我們先來看“是個狼人”。這個流行語是由“是個狠人”演變而來的,它的意思是“比狠人再狠‘一點”。因此,最開始使用時,“是個狼人”并不是運用隱喻機制,從源域“狼”的兇猛殘忍特征映射到目標域“人”,而是運用形近象似原則,由字形“狼”喚起讀者對相近字形“狠”的聯想,從而激活“狠”的詞義,再由“丶”的字形激活“一點”的意義,從而完成對“比狠人再狠‘一點”意義的構建。
網絡流行語“9012”的意思是“都這個年頭了,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它是把我們現在所處的年份“2019”進行了倒裝,用來夸張時間的久遠。我們借助倒裝后的“9012”聯想到當前的2019;同時,按照公元紀年法,隨著時間推移是會有9012年的,不過那將是幾千年之后的事情了。因此,“9012”又會使人聯想到時間的久遠。這里除了形近象似,還運用了概念整合的方法。將9012年所代表的久遠的未來和當前2019年的時間整合在一起,在新的整合空間中,“9012”就不再指未來的年份,而是使當前的年份“2019”被賦予了“從過去到現在經歷了很長的時間”的意義。例如:
(8)為啥都9012年了,大家還在瘋狂用18年前的表情包?(《字媒體》微信公眾號,2019-12-07)
(9)都9012年了,還不讓我穿破洞牛仔褲呢?(搜狐網,2019-11-28)
(10)都9012年了,怎么還有那么多的封建迷信的人啊!(閩南網,2019-02-23)
(11)現在都已經9012年了,怎么還有那么多人瞧不起女孩子中性的打扮啊。(閩南網,2019-02-23)
四、關聯原則
關聯原則最初由Sperber、Wilson所提出,后來被Fauconnier、Turner認為是概念整合的一條重要的控制原則。關聯原則認為,人類的認知傾向于與最大程度的關聯性相吻合,“聽話人憑借認知語境中邏輯信息、百科信息和詞語信息作出語境假設,找到對方話語與語境假設的最佳關聯,通過推理推斷出語境暗含,最終取得語境效果,達到交際成功”[10](P39)。
關聯與認知環境關系十分密切。認知環境是對說話人來說清晰的、可快速辨認的所有假設情況的總和,說話人能夠在所處的環境中感知到或通過調動自己的經驗、記憶、邏輯思維等去推斷出這些假設,其中也包括對會話中出現的新事實的感知和新的假設的推理。關聯原則強調,當交際一方做出推論行為時,他不只是要把新的信息告訴另一方,還把他傳遞信息的意圖告訴了另一方,并且這一點是更為重要的。交際主體在認知環境和假設的影響下,根據處理信息的效率來理解對話,以達到最快最佳關聯。因此,關聯原則必須滿足由Sperber、Wilson提出的兩個條件:“一個假設達到如下程度時被認為與個體相關:當此假設被優先處理時獲得了巨大的積極認知效果;獲得這些積極認知效果所需的努力是小的。”[10](P332)認知經濟性和認知效率原則也經常被運用于轉喻的分析中。例如:
(12)You see the whole medical staff, doctors and nurse and all,are working to rule.
(13)You see the whole hospital is on strike.[7](P337)
例(13)使用了以地點指代人員的轉喻,用“the whole hospital(整個醫院)”代表“the whole medical staff,doctors and nurse and all(全體醫護人員,醫生護士和所有人)”,讀者就不必對醫院的各種人員一一進行認知處理,而是通過“整個醫院”這樣的表達直接構建出“全體醫院員工”的意義,用最小的認知努力獲得最大的認知效果。因此,例(13)比例(12)顯然具有更高的認知處理效率。
上文提到的“涼涼”“上班996,下班ICU”“南的找不著北”“9012”等,在網絡交際中能夠很快且較少障礙地為人們所接受并得到廣泛流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過概念整合,人們在即時語境處理時可以快速地獲得最佳關聯。再以網絡流行語“母單花”為例,“母單花”是“從出生起那天就單身并且每個月還得還花唄的女孩”的轉喻,其中的“花”還以隱喻的方式提示了這個詞所代表的“女性”的意義。如果每次在交際中都用“從出生起那天就單身并且每個月還得還花唄的女孩”,會給認知處理帶來負擔,因為詞語或者句子的長度越長,信息量越大,認知處理所花費的時間就越長,而說話人在表達時總是盡可能地追求花費更少的努力來傳達更多的信息,聽話人也希望付出更少的認知努力而取得更大的認知效果。因此,在關聯原則的作用下,“母單花”這個轉喻會使聽話人(讀者)快速捕捉到“母胎、單身、還花唄”以及女性這四個信息,從而構建出完整的語義。當然“母單花”的使用也不能脫離具體的語境,否則會造成交際雙方的交際障礙或誤解。
語言是社會發展變遷的鏡子,詞匯是語言中對社會變化反應最靈敏的部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網絡時代的到來,一大批新興的網絡流行語出現在網絡交際里,并延伸至人們的日常生活交際中。這些網絡流行語新奇、生動、簡潔,富有幽默詼諧的特征,它們的產生、衍變及廣泛傳播與人們的認知心理密不可分,認知語言學為我們解讀這些網絡流行語提供了新的角度。本文運用認知語言學的一些經典理論,對網絡流行語的產生機制、語義演變和解讀進行了淺顯的分析,其結果還有待于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周海中.一門嶄新的語言學科——網絡語言學[J].科學, 2000,(9).
[2]孫潔,樊啟迪,巢乃鵬.網絡流行語的概念辨析與傳播過程[J].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
[3]陳建偉.網絡流行語研究[D].南寧: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4]陳一民.語言學層面的網絡流行語解讀[J].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
[5]韓玉花.網絡流行語的社會鏡像[J].新聞愛好者, 2010,(3).
[6]王寅.認知語言學探索[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7][德]弗里德里希·溫格瑞爾,漢斯-尤格·施密特.認知語言學導論(第二版)[M].彭利貞,許國萍,趙微譯.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8][美]喬治·萊考夫,馬克·約翰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何文忠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9]王寅.論語言符號象似性[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9,(5).
[10]Sperber,D. &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2nd) [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