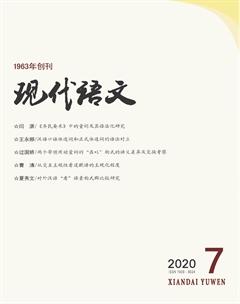國外第三語言習得語言遷移研究評述
段然
摘? 要:語言遷移是國外三語習得研究領域的重點內容,目前的成果集中在遷移來源的探索、影響因素的確定等,已挖掘的因素有:語言類型相似性、“二語地位”、語言水平、近現性等。句法層面的遷移研究也十分突出,相繼提出“累積強化模式”“ 語言類型優選模型”等理論。對國外三語習得中語言遷移研究的成果進行梳理和評述,不僅可以加深對遷移本質的理解,更能推動國內漢語作為第三語言習得研究的發展。
關鍵詞:三語習得;語言遷移;句法遷移
一、第三語言習得研究概述
第三語言習得(以下簡稱“三語習得”)一直被學界歸為第二語言習得的分支。Gass(1996:318)認為,第二語言習得包括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語言的習得,并且這之間沒有區別。隨著二語習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語言多樣性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區分二語習得和三語習得的必要性,開始呼吁將三語習得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三語習得涉及了多種語言之間、多種因素之間的互動和影響,因而更加復雜。Fouser(2001:150)以“L3”來表示三語習得,De Angelis(2007:10)以“第三語言或多語(third or additional language)”來泛指第三語言、第四語言乃至第n種語言。Herdina & Jessner(2000:84-98)將三語習得的特點歸納為:非線性發展;學習者的個體差異;維持性、可逆性、穩定性;相互依存性;質變性。在實際層面上,三語習得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是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越來越多的多語者和多語習得迫使我們站在更廣闊的研究視角去探尋語言習得更深層次的問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三語習得得到真正關注,在歐洲和北美迅速發展,多是與心理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及多語教育領域相結合。目前三語習得的研究已經歷了三十余年的發展,研究的重點逐漸集中在多語之間的語言遷移、元語言意識發展、基于轉換生成語法的三語習得研究等;涉及的語種則包括英語、法語等印歐語系及日語、韓語等非印歐語系30多種語言。
語言遷移研究是第三語言習得研究中最集中、最重要的部分。學習者在習得L3時,所有的舊知識都是可以利用的,這就與二語習得截然不同。大腦獲得了選擇權,學習者不像在二語習得中那樣只有一種語言可以利用;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從復雜的內部系統中選擇遷移來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實上,也只有在多語系統中研究遷移才能真正理解其本質內涵。遷移的選擇性和復雜性也只有在多個遷移源的情況下才得以展現(Dewaele,2001;Rothman,2010)。本文對國外三語習得語言遷移研究的理論發展進行梳理,旨在深入認識和理解該領域取得的新成果及存在的不足,從而為漢語作為第三語言的習得研究和教學實踐提供參考。
二、三語習得的語言遷移研究
(一)遷移來源
從邏輯上看,三語習得的遷移發生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1.沒有遷移;2.主要來自L1;3.主要來自L2;4.在某一階段、某一部分來自L1或L2;5.在習得的全部過程同時來自兩種語言的遷移。目前對遷移來源的研究仍未達成共識,主要集中在對3、4、5的假設和驗證上,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確認。Williams & Hammarberg(1998,2001)通過對學習者三語詞匯產出中的語碼轉換的個案追蹤研究,證實了L2對L3習得有更大影響,并認為學習者為L1和L2分配了不同的角色——L1主要為工具性語言(instrumental language),幫助目的語交際過程順利進行,L2則是外在的遷移來源(external supplier language),為交際產出提供語言材料。Cenoz(2001,2003)通過對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多語社群的一系列調查,認為英語為L3的學習者同時受到母語巴斯克語和二語西班牙語的影響,盡管從語言類型相似性上看,L2和L3距離更近。雖然已有不少研究認為母語表現出更大的遷移影響,但并沒有證據表明母語影響始終是最強的。
(二)遷移的影響因素
目前已挖掘的影響遷移因素有:語言類型相似性(Cenoz,2001;De Angelis,2007;Ringbom,2001),“二語地位”(Dewaele,1998;De Angelis & Selinker,2001;Ecke,2001;Llama等,2009),語言水平(Hammarberg,2001;Tremblay,2004;Dewaele,2001;Navés等,2005),近現性(Dewaele,1998;M?hle,1989)等,上述因素都對三語習得中的語言遷移產生了一定影響。
語言類型相似性(typological similarity)、語言類型(typology)、語言相近性(linguistic proximity)、對語言距離的感知(perception of language distance)等術語,本質上都是聚焦于語言距離以及語言之間的異同。與二語遷移研究范式相同的是,三語習得遷移研究也經歷了這一階段——通過語言異同的對比來預測可遷移性。三語習得研究者認為,學習者會從與目的語距離更近的語言中遷移更多的語言知識(Cenoz,2001;Ringbom,2001;De Angelis,2005;Foote,2009)。De Angelis(2005)通過意大利語學習者對功能詞使用的調查,發現遷移來源取決于其與目的語的類型距離。Foote(2009)則設計了三組被試習得完成體和未完成體語義的對比實驗。三組被試分別為:L1英語、L2羅曼語、L3羅曼語;L1羅曼語、L2英語、L3羅曼語;L1英語、L2羅曼語。數據顯示,兩組三語習得者的表現都比二語習得組好。Foote由此認為,已習得的羅曼語促進了L3羅曼語的習得,語言類型距離是促進三語習得中正遷移的決定性因素。Bardel & Lindqvist(2007)、De Angelis(2007)的研究都證實了羅曼語L2對羅曼語L3的遷移。Rothman(2011,2015)提出的“語言類型優選模型”、Westergaard等(2016)提出的“語言臨近模型”,均認為語言類型上的相似性決定遷移來源。
實際上,以往的相關研究對于這種相似性的定義均比較模糊。De Angelis(2007:22-33)、Falk & Bardel(2010)、Puig-Mayenco等(2018)都對此展開過討論。綜合來看,語言類型相似性應當考慮4種內涵:1.譜系歸屬。它是從全部語言層面考慮語言的發生學關系和整體聯系,并不指向具體的語言特征相似。由此,即使法語和意大利語同屬羅曼語,但卻有不同的空賓語參數;而漢語和西班牙語距離甚遠,卻都允許空主語。2.地緣上的遠近關系。橋本萬太郎(1985)認為,地緣上接近的語言會因語言接觸而相互影響。如阿爾巴尼亞語、羅馬尼亞語和保加利亞語分屬不同語系,但因地理位置相近而表現出某些共同的特點——通過在名詞后添加后綴來標記限定性。3.具體的語言特征。如是否允許空主語、修飾語和中心語的語序等。4.心理類型距離(psychotypology),即學習者對語言之間距離的感知。盡管在多數情況下,客觀上的語言類型距離與心理類型距離重合,但Kellerman(1983)、Hammarberg(2009)都認為,心理類型距離才是更準確、更重要的說法。有些情況下,心理類型距離與真正的類型距離并不相同:一方面,客觀類型相近時,學習者并不一定感知得到;另一方面,即使客觀類型距離遠,學習者也可能感知到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征的相似。尤其是當L1、L2、L3的客觀類型距離均沒有明顯差別時,心理類型距離就成為十分重要的變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將心理類型距離視為語言類型距離因素的一部分,測試手段也比較單一,主要是依靠調查問卷或有聲思維等方式獲取受試者的主觀報告。
“二語地位”(L2 status)是Hammarberg(1998,2001)在Meisel(1983)的“外語影響”(foreign language effect)基礎上提出的,他將這種因素定義為“學習者對‘外語化的追求”,這種追求主要通過抑制L1、依靠L2的策略來實現。De Angelis(2007:28-30)進一步指出,學習者將L2和L3共同儲存在“外語聚合(association of foreignness)”中,在“正確性感知(perception of correctness)”的影響下,學習者直覺上認定在三語產出中使用母語是錯誤的;而二語和三語同為外語,從二語中遷移被認為是更“外語化”、更正確的選擇。在三語習得發展初期,Hammarberg(1998,2001)、Cenoz(2001)、De Angelis & Selinker(2001)、Jaensch(2012)等人,都針對這一因素開展實證研究,并證實了學習者的確存在這種傾向。在最近的研究中,學者們發展了之前的理論,根據這一因素提出“二語地位因素假設(the L2 status factor hypothesis)”,認為L2會影響L3習得的整個過程;并結合認知語言學理論尋求解釋,認為L2與L3在認知上有更多相似性(De Angelis,2007;Bardel & Falk,2007;Bardel & Sánchez,2017)。Bardel & Falk(2007)將這種認知上的相似性歸因為L2和L3與母語儲存在不同的記憶系統中。母語主要依靠程序性記憶,而非母語主要依靠陳述性記憶,這使得非母語建立起認知關聯,進而學習者傾向于從非母語遷移,L1的遷移則受到L2的阻斷。目前針對“二語地位”的研究還缺乏嚴謹性,如L3與L2正好語言距離較近時,就很難分辨清楚究竟是哪種因素在影響遷移;“二語地位”與語言距離共同作用時,影響力大小也是有一定爭議的。Cenoz(2001)認為,語言距離始終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而Llama(2009)卻認為,二者在語言的不同層面表現出不同的影響力。根據De Angelis(2007:28)的觀點,“二語地位”是當三種語言屬于同一語系或語族,語言類型距離都相對較近,很難僅根據語言距離預測遷移時,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因素。
語言水平,包括二語水平和三語水平,它共有兩大假設:第一種假設是,當L2水平達到一定的閾限值后,會對L3習得產生遷移影響,水平越高影響越大。Tremblay(2004)證實學習者的L2水平未達到某一閾限時,L2的影響微乎其微。Hammarberg(2001)和Jaensch(2009)的研究都表明,這種遷移影響既包括正遷移也包括負遷移。Ringbom(1987)提出語言水平將影響遷移類型,意義遷移一般發生在L2水平較高時。第二種假設是,語言遷移一般發生在L3習得的較早階段,即L3水平越低,越容易受到L1和L2的影響;隨著L3水平的提升,學習者逐漸掌握利用L3、學習L3的技巧,此時便會擺脫對L1和L2的依賴。Navés等(2005)對不同年級的英語三語學習者的調查發現,年級低的學習者比年級高的學習者出現更多的借用和詞匯發明。
近現性(recency)因素主要探討哪種語言對目的語習得影響更大。研究者普遍認為,最近使用的語言更易激活。一些研究者認為,近現性不僅指向語言使用的順序,還包括習得的順序。Shanon(1991)就報告了一種“最近語言影響(last language effect)”,他發現,學習者無論水平高低,都表現出對最近學習或接觸的語言的依賴。Dewaele(1998)的研究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將母語為丹麥語、L2為法語和L2為英語、L3為法語的兩組學習者進行對比,結果發現,第一組受母語影響,第二組主要受英語影響。同時,也有不少研究證實,即使是長久不用或很久之前學過的語言也會對目的語的習得產生影響。M?hle(1989)以德語是L1、英語是L2、L3是法語或拉丁語為研究對象,作者指出,盡管法語已經很久不用,但在他們學習西班牙語時也表現出法語的影響。
總的來看,在三語習得的遷移研究中,已證實的影響因素很多,但實際習得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過程。目前研究對每種因素的影響力仍舊不甚清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L3習得其實是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Puig-Mayenco等(2018:34)在系統分析了2004—2017年三語習得的主要研究后認為,盡管語言類型相似性因素表現出極大的影響(涵蓋了60.5%的研究),但是沒有某種因素能夠單獨解釋全部研究數據。
三、三語習得中的句法遷移研究
近二十年,結合普遍語法理論的語言習得研究專家越來越關注三語習得,因此,三語習得的句法遷移研究也繼承了二語習得的研究范式,以轉換生成語法為理論源泉。根據“完全遷移,完全可及”假設,L1和L2的語法都將遷移到L3的初始狀態中。Leung(2002,2003,2005a,2005b,2006,2007)對此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在L3習得中驗證了這一假設。目前三語習得句法遷移的大部分研究都接受這一觀點(García Mayo & Rothman,2012:16),進而探索當L1與L2參數值不同時,L3初始狀態將采用哪種參數設定,什么因素決定了這種選擇性。目前的假設共有以下幾種:
(一)L1起決定作用
Hermas(2010)將L1為阿拉伯語、L2為法語、L3為英語的學習者作為研究對象,同時設置了英語母語者和法語母語者作為對照組,通過動詞移位的調查發現,L3學習者的表現與L1英語者、L1法語者的表現都不相同,由此得出結論,L1阿拉伯語在L3習得遷移中起決定作用。Jin(2009)調查了漢語為L1、英語為L2、挪威語為L3的學習者習得賓語的情況,結果發現,盡管英語和挪威語的語言距離更近,但母語仍是學習者遷移的最主要源泉,二語的影響微乎其微。Na Ranong & Leung(2009)也對賓語習得中的語言遷移情況進行了探討,其研究對象是L1為泰語、L2為英語、L3為漢語的初級學習者,通過對照實驗,作者發現,母語在漢語二語習得、三語習得中都發揮重要作用。Rothman(2015:229)認為,對這一現象只有兩種解釋:一是母語阻斷了L2的遷移;二是根據Bley-Vroman(2009)的“根本差異假說”,外語習得類似普通問題的解決系統,只有母語知識發揮作用。但是目前三語習得研究的絕大部分數據都證實了L2對L3的影響,因此,大多數學者都反對這一觀點。
(二)“二語地位”因素主導下的二語遷移
Bardel & Falk(2007)以否定詞的位置為考察焦點,驗證句法層面是否也存在L2地位的顯著影響。通過L1和L2不同的瑞典語或丹麥語L3學習者的對比,作者認為,L2會阻斷L1的遷移,從而使L2的形式句法更易遷移到L3中,因此,L2地位是超越類型學因素的影響力更強的變量。Falk & Bardel(2011)隨后進行了一個更為嚴格的驗證,他們采用句法遷移研究常用的經典對照實驗,保持L3不變,將L1和L2互換,形成兩組受試,結果發現,以德語為L3的學習者都會從L2中遷移,盡管英語與德語距離更近。Rothman & Cabrelli Amaro(2010)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這一觀點。
(三)累積強化模式
Flynn、Foley & Vinnitskaya(2004)真正開啟了對多語句法遷移的研究。他們關注的是已習得的語言在L3習得中的作用——究竟是L1起主導作用,還是所有已學語言都會發生作用。其研究對象的L1為卡薩克語、L2為俄語、L3為英語。卡薩克語和日語都是中心語在后的左分支語言,而英語、西班牙語、俄語則是中心語在前的右分支語言。研究內容是限制性關系從句的習得表現。結果發現,L1和L2都在三語習得中發揮作用,而且都是正遷移。Flynn等由此進一步提出了積累性強化模型(Cumulative Enhancement Model,簡稱“CEM”),認為母語在跨語言影響中并不占據主導作用,已習得的所有語言都將會對后續語言的習得產生可選擇性的影響,學習者會從已習得的語言中選擇與目的語相似的某一特性進行遷移,L1或L2對目的語習得的影響只有中性和正遷移兩種可能。這一模式實際上是對語言類型相似性的重新演繹,擯棄了將類型相似性視為一個整體的觀點,認為學習者出于認知上的經濟、省力原則,不對L1和L2嚴格區分,而僅僅關注所有語言的特性與目的語的匹配程度。CEM的提出,引發了很多的驗證和反駁。對這一模式的反駁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大量的實際語料表明,遷移并非總是正向的;第二,CEM實際上是對類型相似的因素的驗證,但在這一研究中,L2同時是與L3類型相近的語言,這就無法排除“二語地位”的影響。
(四)語言類型優選模型
語言類型優選模型(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簡稱“TPM”)是Rothman(2010,2011,2013,2015)在CEM的基礎上提出的。他同樣認為,多語習得中的語言遷移是可選擇性的,這種選擇基于對語言類型相近性的感知,也即“心理類型相似性”,無論是L1還是L2,只要類型上的句法特性與目的語相似,就會被遷移。Rothman(2010,2011)以語序為切入點,發現三語學習者總是從與L3類型相近的語言中遷移,無論它是L1還是L2。TPM提出了遷移的經濟性選擇,是對CEM的進一步發展,但也并未完全排除L2 status因素的影響,仍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如當L3與L1、L2都不相似或相似程度對等時,遷移如何發生;學習者內部系統如何評估這種相似性。Rothman(2011)對此進行了進一步解釋:多種語言系統在大腦中互動、競爭,學習者在TPM模式下的遷移選擇,是在普遍的語言經濟原則和認知處理因素基礎上,對有限的認知資源最優化的處理。這種對類型相似性的評估是一種無意識的“最佳猜測(best guess)”。
Westergaard等(2017)對TPM提出了質疑,認為目前大部分支持TPM的研究本身所涉及的語言組合都有明顯的相似性,如L1、L2同為羅曼語的英語習得研究,從而降低了TPM的解釋力;另一方面,作者還反對Rothman(2013:235-236)對某一語言整體語法完全遷移的觀點,認為完全遷移可能會加重學習者的認知負擔。進而,作者在TPM基礎上提出了語言臨近模型(The Linguistic Proximity Model,簡稱“LPM”),認為無論習得順序和語言距離為何,相似的語言特征將激發遷移,這種相似性是特定的、具體的語言特征,如是否允許空賓語,并進一步通過實驗調查英語作為L3的挪威語、俄語雙語者對動詞短語副詞①和助動詞語序的習得,從而證實了LPM。
Slabakova(2017)在CEM、TPM基礎上提出了手術刀模型(The Scalpel Model,簡稱“SM”),認為已習得的L1和L2語法共同構成語法遷移待選項,學習者會根據L3的特征從中提取匹配的參數進行遷移。手術刀模型與CEM、TPM一樣,也認為L1和L2都沒有表現出更強的遷移影響;同時對CEM的某些觀點予以反駁,認為負遷移也會發生。目前手術刀模型還僅停留在理論探索階段,沒有進一步的實驗數據支持。
總的來看,整體的完全遷移還是部分的、具體特征的遷移是上述模型爭論的焦點。實際上,這一問題觸及的本質是,兩種已習得的語言是否能夠同時作為遷移源的備選項出現在三語習得的初始狀態中。Rothman(2013)指出,TPM是基于“完全遷移,完全可及觀”的理論,認為原則上L1和L2都能進入L3習得的初始狀態,但是為了避免習得冗余,降低認知成本,學習者內部的語言習得裝置會對結構相似性作出無意識的、整體的判斷,進而完全遷移類型距離更近的語言。如果一個語言系統的影響意味著對另一個系統的抑制,那么,這種抑制是否同樣需要耗費認知成本?語言習得裝置為何會完全舍棄可能有助于后期習得的正遷移?在初始階段,僅憑借對類型的感知就倉促遷移某一系統的全部語法,確實是不夠合理。這樣看來,Flynn等(2004)、Slabakova(2017)、Westergaard等(2016)的觀點更為合理。他們認為,遷移是對一個個具體特征的選擇性的遷移,學習者會根據L3的特征,從L1或L2中遷移有幫助的部分,兩種已習得的語言都能夠出現在三語習得的初始狀態中作為遷移備選。這樣的觀點也在詞匯遷移的研究中得以證實,如Ecke(2001)在研究心理詞匯系統時提出L3詞匯習得的“寄生性”策略,認為學習者將L3詞匯與L1和L2詞匯表達的共同特征作為檢索L3詞匯的線索,L3詞匯系統的建立是“寄生”在L1和L2詞匯系統上的。Clements(2017)通過研究母語為英語、西班牙語為二語、漢語為三語的學習者在習得空賓語和代詞時的遷移表現,認為盡管三種語言各不相同,學習者對遷移來源的選擇表現出“基于特征相似”的復雜遷移模式,遷移可能來源于母語或二語。
縱觀三語習得初始狀態的主要模型,可以看出轉換生成派研究者對三語習得的探索和努力,這無疑加深了我們對三語句法習得遷移情況的認識,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對語言相似性、差異性的界定和量化還沒有很清晰、統一的解釋。第二,多數研究對初始狀態的界定都處理為習得的初級階段,或者對初始狀態避而不談,在實際操作中,研究對象的L3水平有高有低。初級階段并非初始階段,這是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共識。完全的初始狀態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操作難度,那么,研究設計和研究方法就成為問題所在。第三,大部分三語習得研究一般都采取內省法和試驗誘導來獲取語料,難以克服主觀性及策略使用的干擾。其實應結合產出性和判斷性多種測試工具,來保證效度和信度。需要指出的是,可以參照二語習得語料庫建設經驗,建設三語習得語料庫,為今后研究的準確性奠定基礎。
四、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語言之間的遷移影響作為三語習得研究的重點內容,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橫向遷移研究較多,縱向追蹤研究有待發展。根據語言水平對遷移的影響研究來看,中介語發展的不同階段必定會呈現不同的遷移情況。第二,參照Jarvis & Pavlenko(2008:20)總結的遷移維度,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詞匯和句法遷移,對語音、語用、語篇等領域研究較少;同時,絕大部分研究關注的是L1、L2對L3的順向遷移,而忽略了L3的反向遷移。第三,研究所涉及的語種主要停留在印歐語系內部,涉及漢語的少之又少。
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來,三語習得研究被引入國內,在少數民族習得英語和漢語母語者習得第二外語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曾麗、李力(2010)在國外理論的基礎上,將三語習得的區別性特征概括為非線性發展、語言損耗與逆轉性、認知優勢、語際遷移的復雜性、社會環境因素復雜性、習得過程多樣性,由此呼吁學界將“三語習得”作為獨立領域開展研究。之后,蔡鳳珍、楊忠(2012),烏日罕(2012),李增垠(2016)等,相繼開展研究,探索少數民族學生學習L3(英語)的習得情況,集中在L1、L2對L3的遷移和元語言意識發展兩方面。此外,歐亞麗、劉承宇(2009),劉承宇、謝翠平(2008),呂新博、石運章(2017),陳鶴(2014)等,則聚焦漢語母語者習得第二外語(法語、日語、德語等)時,受到的跨語言影響和對元語言意識的促進作用。總的來看,國內三語習得歷經十余年發展,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漢語三語習得還鮮有研究,值得我們關注。隨著對外漢語教學的不斷發展,漢語作為第三語言習得研究勢必要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們在國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本土特色,必將會推動漢語教學和漢語三語習得研究邁向新的臺階。
參考文獻:
[1]蔡鳳珍,楊忠.L2(漢語)對新疆少數民族學生L3(英語)習得的影響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2,(2).
[2]陳鶴.中國德語學習者篇章寫作中的詞匯錯誤分析——一項基于語料庫和三語習得的研究[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3]李增垠.藏族學生在第三語言習得中元語言意識研究[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
[4]劉承宇,謝翠平.外語專業學生第二外語學習中的跨語言影響研究[J].外語教學,2008,(1).
[5]呂新博,石運章.三語學習對中國日、韓語專業學習者二語元語言意識影響的研究[J].語文學刊,2017,(6).
[6]歐亞麗,劉承宇.語言距離對英語作為第三語言學習的蒙古族學生語音遷移的影響[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09,(4).
[7]烏日罕.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對蒙古族學生第三語言英語句型習得影響的實證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8]曾麗,李力.對“三語習得”作為獨立研究領域的思考[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0,(2).
[9][日]橋本萬太郎.語言地理類型學[M].余志鴻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
[10]Bardel,C. & Falk,Y.The rol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the case of Germanic syntax[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07,(4).
[11]Bardel,C. & Lindqvist,C.The role of proficiency and psychotypology in lexical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A study of a multilingual learner of Italian L3[A].In? Chini,M.,Desideri,P.,Favilla,M.E. & Pallotti,G.(eds.).Atti del V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ll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Linguistica Applicata[C].Perugia:Guerra Editore,2007.
[12]Bardel,C. & Sánchez,L.The L2 status factor hypothesis revisited:The role of metalinguistic knowledge,working memory,attention and noticing in third language learning[A].In Angelovska,T. & Hahn,A.(eds.).L3 Syntactic Transfer:Models, new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C].Amsterdam,NL:John Benjamins,2017.
[13]Cenoz,J.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distance,L2 status and age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A].In Cenoz,J.,Hufeisen,B. & Jessner,U.(eds.).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C].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1.
[14]Cenoz,J.,Hufeisen,B. & Jessner,U.The Multilingual Lexicon[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3.
[15]Clements,M.Exploring the role of previously acquired languages in third language(L3)acquisition: a feature-based approach[D].Unpublished doctors thesis,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Southampton,UK,2017.
[16]De Angelis,G. & Selinker,L.Interlanguage transfer and competing linguistic systems in the multilingual mind[A].In Cenoz,J.,Hufeisen,B. & Jessner,U.(eds.).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C].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1.
[17]De Angelis,G.Interlanguage transfer of function words[J].Language Learning,2005,(3).
[18]De Angelis,G.Third or Additional Language Acquisi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7.
[19]Dewaele,J.Lexical Inventions:French interlanguage as L2 versus L3[J].Applied Linguistics,1998,(4).
[20]Dewaele,J.Activation or inhibition?The interaction of L1,L2 and L3 on the language mode continuum[A].In Cenoz,J.,Hufeisen,B. & Jessner,U.(eds.).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C].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1.
[33]Jaensch,C.Acquisition of L3 German:Do sone learners have it easier?[A].In Cabrelli Amaro,J.,Flynn,S. & Rothman,J.(eds.).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dulthood[C].Amsterdam,NL:John Benjamins,2012.
[34]Jin,F.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Norwegian Objects: Interlanguage Transfer or L1 Influence?[A].In Leung,Y-k.I.(ed.).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C].Bristol:Multilingual Matters,2009.
[35]Kellerman,E.Now you see it,now you dont[A].In Gass,S. & Selinker,L.(eds.).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C].Rowley Mass:Newbury House,1983.
[36]Leung,Y-k.I.L2 vs. L3 initial state:Evidence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French DPs by Vietnamese monolinguals and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s[A].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rilingualism[C].Ljouwert/Leeuwarden:Fryske Akademy,2002.
[37]Leung,Y-k.I.Failed features versus full transfer full ac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ird language:Evidence from tense and agreement[A].In Liceras,J.M.,Zobl,H. & Goodluck,H.(eds.).Proceedings of the 6th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ference (GASLA 2002):L2 Links[C].Sommerville,MA: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2003.
[38]Leung,Y-k.I.L2 vs. L3 initial st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French DPs by Vietnamese monolinguals and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s[J].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2005a,(8).
[39]Leung,Y-k.I.Second vs.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tense and agreement in French by Vietnamese monolinguals and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s[A].In Cohen,J.,MacAlister,K., Rolstad,K. & MacSwan,J.(eds.).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C].Sommerville,MA:Cascadilla Press,2005b.
[40]Leung,Y-k.I.Full transfer vs. partial transfer in L2 and L3 acquisition[A].In Slabakova,R.,Montrul,S. & Prévost,P.(eds).Inquiries in linguistic development[C].NL: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6.
[41]Leung,Y-k.I.L3 acquisition:why it is interesting to generative linguists[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07,(1).
[42]Llama,R.,Cardoso,W. & Collins,L.The roles of typology and L2 status in the acquisition of L3 phonology:The influence of previously learnt languages on L3 speech produ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09,(7).
[43]M?hle,D.Multilingual interac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production[A].In Dechert,H.W. & Raupach,M.(eds.).Interlingual Processes[C].Tü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89.
[44]Na Ranong,S. & Leung,Y-k.I.Null Objects in L1 Thai-L2 English-L3 Chinese:An Empiricist Take on a Theoretical Problem[C].In Leung,Y-k.I.(ed.).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C].Bristol:Multilingual Matters,2009.
[45]Navés,T.,Miralpeix,I. & Celaya,M.L.Who transfers more…and what?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relation to school grade and language dominance in EF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05,(2).
[46]Puig-Mayenco,E.,Jorge,G.A. & Rothman,J.A systematic review of transfer studies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18.
[47]Ringbom,H.The Role of the First Languag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87.
[48]Ringbom,H.Lexical Transfer in L3 Production[A].In Cenoz,J.,Hufeisen,B. & Jessner,U.(eds.).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C].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1.
[49]Rothman,J.On the typological economy of syntactic transfer:Word order and relative clause high/low attachment preference in L3 Brazilian Portugues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IRAL),2010,(48).
[50]Rothman,J. & Cabrelli Amaro,J.What Variables Condition Syntactic Transfer?A Look at the L3 Initial State[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10,(2).
[51]Rothman,J.L3 syntactic transfer selectivity and typological determinacy: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11,(1).
[52]Rothman,J.Cognitive economy,non-redundancy and typological primacy in L3 acquisition:Evidence from initial stages of L3 Romance[A].In Baauw, S.,Dirjkoningen,F.,Meroni,L. & Pinto,M.(eds.).Romanc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11[C].Amsterdam,NL:John Benjamins,2013.
[53]Rothman,J.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s for 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 (TPM) of third language(L3) transfer:Timing of acq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considered[J].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2015,(2).
[54]Shanon,B.Faulty language selection in polyglots[J].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1991,(4).
[55]Slabakova,R.The Scalpel Model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17,(6).
[56]Tremblay,M.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The role of L2 proficiency and L2 exposure[J].Cahiers Linguistiques dOttawa,2006,(34).
[57]Westergaard,M.,Mitrofanova,N.,Mykhaylyk,R.et al.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a third language:The Linguistic Proximity Mod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17,(6).
[58]Williams,S. & Hammarberg,B.Language switches in L3 Production:Implications for a Polygot Speaking Model[J].Applied Linguistics,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