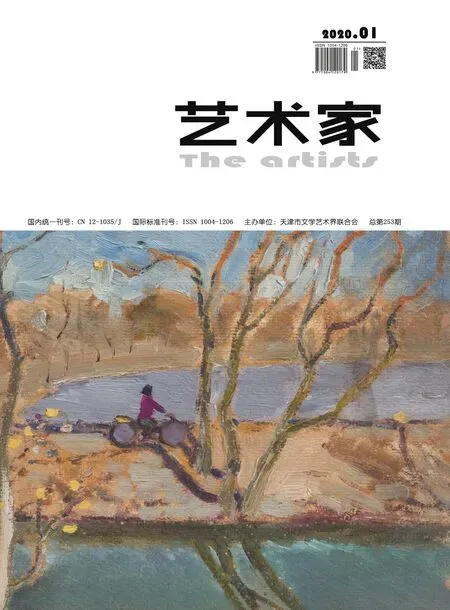淺析王承斌書畫作品的“寄托”品格
□龔文政 吉林大學藝術學院
王承斌所畫竹石,清逸瘦勁,人與竹合二為一,將自身理念寄托在蕭蕭清竹之中。竹,在中國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有比德的稱謂,儼然成了德行化的符號。尤其是宋代蘇東坡曾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將竹的自然形態人格化。中國畫畫蘭竹其多自謂,利用華人心理的暗示來揭示自身深層次的“人格”標準。中國畫足矣安撫心靈、凈化心態、陶冶情操,王承斌能夠從泯滅本土文化的迷霧中,堅定民族精神,為藝術創造做出自身最大的努力。
民國時期東北奉天地區(今遼寧省)最有影響力的三大書畫家——王承斌、王光烈、張之漢,以及他們的弟子門生,構成了民國時期奉天地區一個特殊的文化群體,支撐著中國書畫傳統,延續著美術的社會功能,孕育了新時代中國畫的新面貌。他們在藝術方面肩負的歷史使命、弘揚的民族精神、表現出的民族氣節、為中國畫命運發展而堅持的立場、在美術思潮沖擊下產生的觀念、經歷的亂世坎坷境遇和人生悲劇,確有共性共通的一面;然而他們三位又是有官職和社會地位,且個性強烈的人物,他們對革命風雨、社會變革、民族存亡、國家大事的理解方式不盡相同,各自的學養、興趣、喜好、品格、認知、情趣、理解方式、表達方式以及生存理念均迥然不同。其中,王承斌的修養和學問尤顯精醇厚重,且更具有隱逸名士之風范。
據《興城縣志》所載:“王承斌善書畫,晚年客居大連,以書畫自娛,長于水墨竹石,頗具水平。”“寄情”是中國畫最重要的一個傳統,多是由“移”景或“移”社會旨趣入畫。如寫名山大川來寓情于景,或寫花卉枝葉來托己之態,再或以特定題材加以表現,所謂題材的模擬自然和觀念的倫理化。這需要作畫者不受回避觀念的影響,直抒胸臆。他筆下的山川景物,實際上是在寫自身情愫,通過物象來傳達自身的理解。這種理解不是簡單描繪畫家對大自然的生氣或者生機的看法,而是力求再現這種神韻,技巧和法度在此已消融于筆墨之中。狀物的技巧和神采均已淡化,作畫者從自身生命的方向來轉化自然的生機,通過筆墨盡情抒發、揮灑。王承斌在奉天地區的畫家中,其自身特點得以凸顯。首先,他在自身畫面的構成上將“寫心”提到了最高位置,這與宋元文人畫家有著共同的旨趣。王承斌畫蘭石、山水、竹木,不再局限于題材的選取和歸納梳理,而在于其主動把情感灌注到蘭石、山水、竹木等特有題材上,心靈如何才能更進一步地貼近這些竹木、山水、感悟,生發的過程便是自身藝術加工的經歷,理解、體察山水、竹石的生命規律和恒常的面貌,再由這諸多外在生命符號承載畫家的自身情愫,使蘭竹、山石人格化,畫家也由此“物化”為蘭竹、山石。關于這一點,王承斌的探索要比同時期人走得更遠。因為他的繪畫有書法功力的支撐,畫家不僅是寫物、寫心得“再現物象”和“再造物象”的二元論,更多的是要有對用筆、用墨的恒常規律的研判,這一點必須下足功夫來讀書思考。王承斌的書畫不是文人士大夫的“清玩”,也不是市場上的“畫家畫”。在專家評判的視野里,王承斌似乎不足掛齒,但恰恰是在受到各種質疑聲中顯得他的作品格外茁壯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與20世紀市民階層的興起有著密切聯系,從京津唐向北擴張,在市井、在鄉村均以張貼書畫為尚。什么是市民階層所喜好的,并為廣大消費群體所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的藝術?梅蘭竹菊題材的書畫銷路盛行,這已不是“清玩”“遣興”所能表達清楚的了,某一種形態的繪畫大行其道也是基于社會功利價值的勃興。換言之,中國畫價值的沉浮變革,顯示了這一時期中國民族精神的趨向。
我們長期以來把視野放在畫壇名家上面,忽略了本質的評價標準,畫家的畫作、畫家的著述,而不應是畫家的社會活動和職務。甚至有些評論家仍在以社會形態的優劣來評判某一時期藝術的長短,這種傾向很有可能導致文化虛無主義盛行。人類精神層面的發展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過程,需要特定時期特定的創造性藝術家和藝術作品,以及這些藝術作品之間的交流互動和恒常不變的特征。在20世紀之前,中國畫從形式到內容上與外界交流較少,吸收的多是本民族其他藝術形式。這種封閉雖然阻滯了藝術作品的交流互動,但也保證了東方藝術血脈的純正,確保能夠產生出富有區域特征的藝術。現在人的眼界雖然開闊,但往往難以設身處地地看待文化發展和藝術發展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