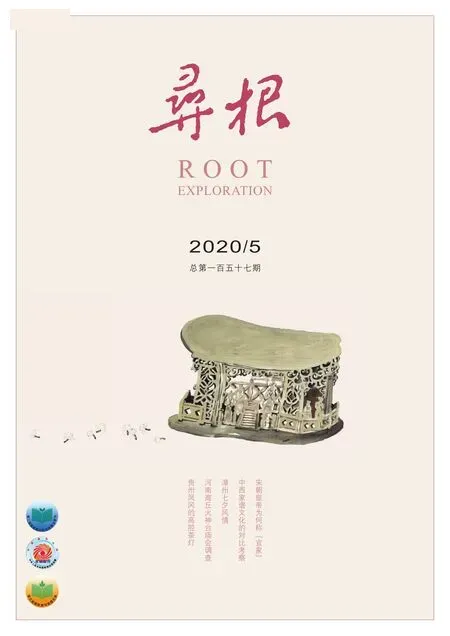孔子化行中都與汶上圣澤書院
□武振偉
汶上縣距曲阜50余公里,春秋時期為魯國的中都邑,戰國時為齊國的平陸邑。金泰和八年(1208年),始將縣名定為汶上,延續至今。汶上因孔子曾任中都宰而聞名,公元前501年,孔子任中都宰,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今汶上境內尚存孔廟、孔子講堂、孔子溝、中都故邑碑、平陸祠等遺跡。
孔子為中都宰事跡
據歷代志書記載,中都故城位于今汶上縣境內。萬歷《汶上縣志·古跡》記載:“故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乾隆《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三十·兗州府》:“中都故城,在汶上縣西。春秋時魯邑,夫子為中都宰,即此……”《元和郡縣圖志》:“中都故城在今中都縣西三十九里。”據考證,魯中都城遺址,在今汶上縣城西南25里的次丘鎮湖口村附近。
孔子為中都宰,在《春秋》及《左傳》等文獻中均無記載。最先見于《禮記·檀弓上》:“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家語》《兗州府志》《汶上縣志》等史籍文獻也有明確記載。《史記·孔子世家》:“(魯)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其后,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錢穆分析說:“魯國既經陽虎之亂,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機緣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魯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遂翩然而出。”
孔子為中都宰的事跡以《孔子家語》的記載最為翔實。世人一直將《孔子家語》視為偽書,但其也有價值,不能簡單判定其內容全部為偽。《孔子家語·相魯》記載:“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涂,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按其記載,孔子在任中都宰時制定了養生送死的禮節:不同年齡的人享有不同的食物,強弱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任務,男女行路各走一邊,撿到行人的遺失物品不能據為己有,制作器物不能人為地雕畫;安葬死者時用四寸厚的棺、五寸厚的槨,依丘陵為墳,不聚土成墳,墓地不種植樹木。實行一年,各諸侯國都紛紛仿效學習。《墨子·節葬下》曾記載了當時厚葬的社會風氣:“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諸侯死者,虛車府。”厚葬之風的盛行,對于發展生產、培養民風具有很大的負面作用。孔子宰中都在當時和后世對魯國尤其汶上縣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乃至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的發展演變,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兗州知府金一鳳為《續修汶上縣志》寫的《序》中寫道:“今汶上者,古中都也。去圣人之世雖遠,而流風善政,無不班班可考。”
可以說,中都是孔子從政生涯的起點。孔子宰中都的從政實踐,在儒學發展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非常獨特的作用。《淮南子·泰族訓》記載:“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孔子后來任魯司寇的做法和成就,也被認為是他治理中都做法和政績的繼續和光大。戰國時代的孟子曾到中都。西漢司馬遷也曾為“觀孔子之遺風”,來汶上實地考察。
最著名的是“汶上三孔”,即孔廟、圣澤書院、思圣堂。思圣堂建在縣署內,始建于北宋元三年(1088年),由縣令周師中創建,目的在于“求孔子之意而行其政”,“以己之心思圣人之心,以己之政行圣人之政”。其后,雖多經改朝換代,思圣堂卻不斷得到修繕,成為汶上舊縣署鎮衙之寶。
孔堂和釣魚臺,相傳為孔子宰中都時遺跡。萬歷《汶上縣志·古跡》記載:“孔堂,俗名講書堂,相傳孔子宰中都時,政暇,與弟子談經于此。舊址在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移建城中,為圣澤書院”;“釣魚臺,即在孔堂舊址。相傳為孔子釣處。”乾隆《兗州府志·卷九·闕里志》也將“中都城”“汶上舊講堂”列入至圣遺跡。據《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等文獻,大致可推斷孔子為政中都時,是其名聲提升的重要時期,也是一個收徒的高峰期。
元代大學士李謙的《圣澤書院記略》載:“城野之南,湖水之側,有講堂故基存焉,乃吾夫子與群弟子講道之所,后人欽慕圣澤,不忘云耳,其興廢不能悉考,所可知者,魏孝昌丙午條石,記興建之由。”可知,講堂可追溯的歷史至遲在北魏孝明帝孝昌丙午(526年)時,記講堂重修之由,那么講堂的始建年代至遲也為北朝。李謙《圣澤書院記略》:“天寶壬辰舊刻吳生所畫宣圣、兗公小像,額則徐浩所題,其上復有顏魯公書、程浩所撰《夫子廟堂記》。元四年(1089年),南陽周師中作宰是邑,重加修建,王堯年為之記……二百年來,薦罹擾,毀于灰燼,鞠為瓦礫。”可知,天寶十一載(752年)修建了夫子廟;元四年,知縣周師中重修夫子廟。可以說,歷代對于孔子的遺跡重視不衰。康熙《續修汶上縣志》記載,到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衍圣公建修講書堂。
圣澤書院的創建
萬歷《汶上縣志·學校》記載:“圣澤書院,舊為講堂,在城西南二十五里開河之東。昔孔子宰中都,政治之暇,與群弟子講習地也。俗名講堂,旁有釣魚臺,相傳孔子釣魚于此。興廢莫考。魏孝昌丙午有斷碑存焉。唐吳生有畫宣圣、兗公小像,徐浩題其額,又有顏魯公所書、程浩《夫子廟堂記》。宋元四年,南陽周師中宰是邑,重修葺之。歲久灰燼,鞠為瓦礫。元至元間,馬櫟庵,東平教授也,得地十二畝,構堂藏書,以授生徒,而都水少監馬之貞則建大成殿三楹,中肅圣容,旁列十哲,堂室、門廡、庖庫、池井,無不具備。”對于講堂的歷史,圣澤書院的記載也是依據李謙的《圣澤書院記略》而來,內容基本相同。對于圣澤書院的創建時間,此處記載比較籠統,而李謙的《圣澤書院記略》則記載較為清楚:“故東平教授櫟庵先生馬公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得地一十二畝,藏書千余卷,構亭講誦,其后都水少監馬之貞復建大成殿四楹,中肖圣容,旁列十哲像”。記文雖略有不同,但從中可知,圣澤書院創建于至元三十年,經馬櫟庵和馬之貞相繼修建完成。此時的圣澤書院,屬于初創期,雖規模粗備,但講學、藏書、祭祀功能齊全。
北宋汶上知縣周師中在縣志有傳,據萬歷《汶上縣志·宦跡志》記載:“周師中,南陽人,哲宗時知汶上縣,為政寬猛適宜,鋤奸惡,撫良善,百姓安之。嘗取中行之義刻準字池于堂,又移建圣澤書院,以育生徒,置思圣堂以自勵云。”周師中,嘉靖《山東通志·名宦》、萬歷《兗州府志·歲貢》均作“周中師”,按李謙的《圣澤書院記略》記載,應為“周師中”。按縣志記載,周師中有“移建圣澤書院”之功,但具體移建于何處,因王堯年所撰記文沒有流傳,其事跡已不可考。據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明《楚潭周御圣澤書院碑》記載:“至金石之刻,則有若吳生之所畫,徐浩所題,顏魯公之書,程浩、王堯年之所撰,悉臚列于左右。”唐、宋碑刻尚存,圣澤書院之歷史班班可考。如按周師中傳記載,則圣澤書院的創建當在北宋元四年。
圣澤書院遷建城中考
明嘉靖年間,圣澤書院遷建于城中。萬歷《汶上縣志·學校》記載:“皇明嘉靖初,撫臺陳公鳳梧求遺址,縣令吳公瀛請建于城內西南隅,中為正殿三楹,前為拜殿,又前為門,繚以周垣。繼修之者,則趙公可懷、張公惟誠(改為復古書院,郡人于慎行為記)及尚公瓚,殿宇一新,而門易以坊焉(仍題圣澤書院,郡司理周公御為記)。”這一段簡短的記載蘊含的歷史信息考證如下。
嘉靖初年,山東興建了許多書院,這跟時任山東巡撫的陳鳳梧有直接關系。嘉靖《山東通志·職官》記載:“陳鳳梧,文鳴,泰和人,丙辰進士,嘉靖元年以副都御史巡撫,至右都御史。”萬歷《汶上縣志》言“撫臺陳公鳳梧求遺址”,可以作注腳的是道光《沂水縣志·書院》記載,明嘉靖年間巡撫山東的官員要求,“一各所屬公署、山川、亭檄、寺觀、碑刻,凡有關系山東地方名賢古跡等項,俱要匯寫成集,依限上報”。可以確定,道光《沂水縣志》所言山東巡撫即陳鳳梧之后任袁宗儒。查《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世宗即位不久,“升河南按察使陳鳳梧為山東左布政使”,不久升任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巡撫山東期間,對先賢遺跡高度關注,不僅要求各地將先賢遺跡整理上報,而且將先賢的祭祀也進行了整頓,使對先賢祭祀正規化。在陳鳳梧及其后任的直接要求下,汶上圣澤書院遷建城中。知縣吳瀛將書院建于城中西南隅,當在嘉靖初年。萬歷《兗州府志·學校》記載:“國朝嘉靖二年(1523年),知縣吳瀛移建城中。”這在萬歷年間重修圣澤書院時周御所撰圣澤書院碑中有所記載:“世宗初,巡撫都御史陳公鳳梧始下檄,移建今縣治太仆寺之南際,舊制益拓,編役司守,嚴事有容,衿紳之士斌斌焉,居無害祀,省入廟,專為講肄之所。”此次遷建,將祭祀的功能并入文廟,而書院成為講學肄業的專門場所。
吳瀛創建書院后,知縣趙可懷、張惟誠對書院進行了修繕。《邑侯趙可懷德政記》:“趙公可懷,四川巴縣人,嘉靖乙丑(1565年)進士,以司馬中丞出鎮于楚。”“趙公當嘉靖末而為宰,春秋盛而敏,宣慈而肅,在政四年。”據此可知,趙可懷重修圣澤書院當在嘉靖末隆慶初。萬歷《兗州府志·學校》記載:“隆慶元年(1567年),知縣趙可懷重修。萬歷元年(1573年),知縣張惟誠改為復古書院。”
張惟誠,隆慶壬申(隆慶六年,1572年)調任汶上知縣,其到任不久即將圣澤書院改名為復古書院,還創建了汶陽書院。郭朝賓《邑侯張惟誠愛養坊記略碑》:“萬歷二年(1574年)春正月,天下有司各述所職,以會于闕下。詔舉廉能異等,得二十五人,吾邑張侯與焉……侯復蒞縣。”可知,張惟誠兩次任汶上知縣。據萬歷《汶上縣志·學校》記載:“汶陽書院,在預備倉右。創自永清張公,堂軒爽塏,號舍曲回,建坊構橋,引流種樹,諸士伊吾其中,而政治之暇,亦時臨辨義也。郡人于慎行為記。蓋數年而廢。邑令彭公健吾因改為察院云。”可惜的是,于慎行所撰復古書院和汶陽書院記文在縣志和府志中均未收錄,對于書院的具體情形已不可考,而從張惟誠建立汶陽書院后的行動看,汶陽書院在一段時間內成為汶上縣的主要書院,圣澤書院雖然改名為復古書院,但已不復盛況。
此后不久,即遭遇明代數次毀書院之風波,圣澤書院雖未被毀,但卻陷入荒廢狀態。周御記文中提到:“又五十余年,而書院之禁下矣,坐是荒蕪不治,螢飛蟲走,垣若毀,殿宇若撤,殘碑斷碣,□□于澹煙荒照之中,識者有魯壁金絲之感。”按“五十余年”記載,當指萬歷年間張居正輔政時期的禁毀書院事件。萬歷七年(1579年),首輔張居正輔政,“詔毀天下書院”,“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后毀應天等府書院六十四處。”(《明通鑒》卷六十七)圣澤書院雖荒廢,但地基尚在。
至萬歷年間,知縣尚瓚將書院修葺一新,重改為圣澤書院。關于尚瓚重修時間,萬歷《汶上縣志·學校》沒有記載,宣統《山東通志·學校》則明確記載:“(萬歷)十二年,知縣尚瓚重修,改名圣澤。”但周御《圣澤書院碑》記載:“表章先圣之遺跡,修復累朝之曠典,尚侯之功,皆其功也。考厥成功,為今萬歷二十八年。”明確記載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是重修年歲,當以周文為準。尚瓚,“銳精治理,留心圣跡”,據周御《圣澤書院碑》記載,尚瓚對汶上的縉紳之士說:“汶為古中都,先師筮仕之地,講堂則顏閔游夏辨志之區……假令講釣之跡遂荒,則圣澤之謂何?”命縣儒學教諭董光為督工,率領諸生掌管錢財,“榛穢誅之,洼平之,磽陋廓之,拉舊易新,撥篆丹,檐楹斐尾,周垣鄰菌,外設戟門,中置黼座,至金石之刻……悉臚列于左右。庖庫井池,咸亦粗備焉。而圣像儼然南面矣,令率父老子弟行釋菜禮告成”。重修圣澤書院,雖然是重視先賢遺跡,不使其毀滅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更有現實的目的,意在“自今以往,吏于其土者,洵夙夜惟先師之政;生于其鄉者,亦夙夜惟先師之學。有能圉生民、登咸往哲、無愧門墻而有當祀典者,請即俎豆于先師之旁,倘亦修之之意乎”?不僅激勵為官者,也激勵為學者,如有業績即可陪祀于先師之旁。
明末崇禎年間,圣澤書院正式納入由曲阜衍圣公府系列的孔子祭祀體系,由衍圣公保舉奉祀官,書院山長也改稱太常寺博士,成為朝廷命官。民國《續修曲阜縣志·政教志·書院》記載:“明崇禎間,衍圣公題準以第三子襲授太常寺博士,專主圣澤書院祭祀。”此項規定,直至民國年間。民國23年,圣澤書院奉祀官為孔祥瑜。乾隆《兗州府志·闕里志》記載:“太常寺博士。圣澤書院即孔子宰中都地也,明設太常寺博士一員,以主祀事。例以衍圣公三子承襲。崇禎間,五經博士孔允鈺以違例罷職。”清軍入關后,定鼎北京,迅速祭出了尊孔的大旗。清順治元年(1644年),孔允鈺被命為暫主圣澤書院祭祀官。乾隆《曲阜縣志·職官二》記載:“太常寺博士,正七品,奉圣澤書院祀。”康熙《續修汶上縣志·人物》記載:“孔衍鈺……國初補太常博士,主圣澤書院,受事之后,整廟貌,肅明。”之后歷任奉祀官都經過了朝廷任命。圣澤書院也成為曲阜縣外專門祭祀孔子的書院之一。
清代圣澤書院考
清代圣澤書院史事資料缺乏,《闕里文獻考·林廟二之三》記載:“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六十八代衍圣公為世子時又重修。”六十八代衍圣公即孔傳鐸。
因自康熙之后汶上縣未再修志,宣統年間所修縣志未刊行,只存手稿本。據1996年出版的《汶上縣志》記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知縣龔聰勸捐一千二百金修繕書院。浙江中丞劉玉坡(汶上人)慨捐千金,以六百歸兗郡考棚,以四百歸圣澤書院。孔衍鈺勸募衍圣公捐助京錢一千串。后相繼捐款者多人。圣澤書院增建了學舍,并建東西考棚等。圣澤書院原址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因外擴湖堤,沒于水。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令各省書院均改為學堂。汶上圣澤書院遂于光緒三十年改為官立高等小學堂(后相繼改稱縣立第一小學、書院小學等)。圣澤書院以學田租銀為主要經費來源。道光元年,有學田2864畝,多為南旺湖田。光緒十九年,知縣劉鑒復查出南旺湖公田5900畝,丈入圣澤書院3900畝。”
據乾隆《新泰縣志·選舉下》記載:“(元)單肇,東平路圣澤書院山長。”乾隆《曲阜縣志·學校貢舉》記載:“(金元時)孔思范,圣澤書院山長。”
與其他衍圣公府管理的書院不同,圣澤書院并沒有成為徒有書院之名的孔子專廟。道光《重修平度州志》記載,有一個平度人曾任圣澤書院主講。戴金鼎,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列傳五》記載:“金鼎,字調梅……嘉慶癸酉舉鄉試第一……在汶上六載,從游者多,汶上令并延主圣澤書院講席。”道光《重修平度州志·藝文上》收錄的《戴公心泉先生傳》也記載:“乃以道光丙戌(1826年)大挑,選汶上縣訓導,訓迪有方,從游者日眾,邑宰遂延主圣澤書院。”
孔子講堂遺跡距縣城二十五里,在明嘉靖年間移建書院于城中后,少人問津,遺跡逐漸荒廢。民國5年汶上人馬煥奎《講堂釣魚臺留地保護記碑》記載:“明嘉靖間,移建城內,此地遂鞠為茂草矣。然圣澤之名猶存也。至我光緒三十年,書院易為學堂,而名亡矣。夫圣道上下與天地同流,豈同君子小人澤約五世而斬者?今圣澤之名雖亡,而堂臺故址之實,尚幸嘖嘖于耕夫牧豎之口。”在知縣的主持下,眾人決心保護先賢遺跡,具文上報,并得財政廳清理官產局批復:“除故址面積外,各留陳地六畝,以重圣跡而資保護,飭縣清查定界,繪圖貼說,報上存案,永禁侵漁,并飭立碑記事。”
因先賢遺跡而興建書院,又因遷建書院而致使遺跡荒廢湮沒,令人惋惜。民國初年雖有保護,但兩處遺跡在1978年土地平整時被鏟平,幸運的是,先賢遺跡又得到了恢復。千載之下,先賢遺跡的真偽,難以考究,但應發揮先賢遺跡的感召作用,為當今的文化建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