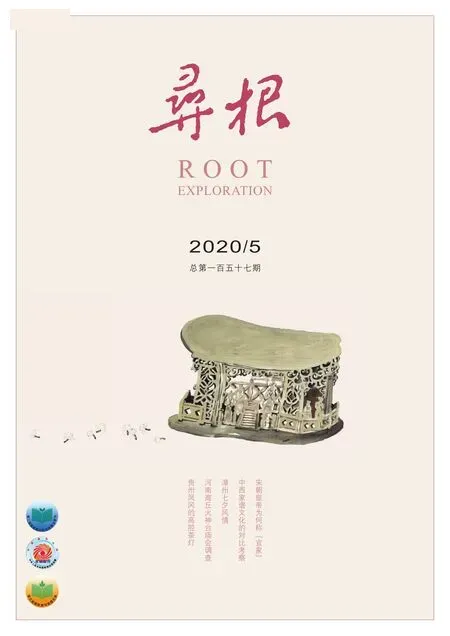貴州鳳岡的高腔茶燈
□解洪興 王湘栗
貴州農村廣為流傳的花燈俗稱“茶燈”,鳳岡高腔茶燈在貴州北部地區以濃郁的地域特色著稱。遵義地區花燈受巴蜀文化影響較大,表演形式也多淵源自川劇,其中鳳岡縣茶燈藝術以高腔與打擊樂配合而獨樹一幟。筆者在對鳳岡高腔茶燈傳承人、群眾的實地調查與訪談中注意到,鳳岡高腔茶燈在沙壩村最為典型,方言色彩濃烈,民歌趣味濃厚,情感表現質樸。
鳳岡高腔茶燈的藝術特點
雖然當地鄉民堅信茶燈是從唐朝流傳至今,“唐二”“幺妹”還被說成是李世民和他的妹妹,但茶燈應是隨著明朝衛所移民來到貴州的,春節至元宵各地農村花燈是明代以來黔北地方志中“唱采茶歌”風俗的存留。就鳳岡高腔茶燈的群眾藝術創作氛圍而言,他們有著相對獨特的文化環境條件。茶燈是鄉民在農耕休憩時,在田間地頭娛樂,手持手巾和紙扇邊唱邊舞,逐漸形成的表演藝術。鳳岡高腔茶燈的曲調悠揚,在周邊山地縈繞的沙壩村極易形成彼此應和的場面。勞作中的鄉民為了舒緩枯燥與勞累往往伴以對歌,群山激蕩出悠長而美妙的回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勤勞的耕作者往往是矯健的善歌者,他們在勞動中飆起高腔,于“吼唱”中形成了音質旋律獨特的“高腔”。鳳岡高腔茶燈源自勞動生活,筆者曾問起具體形成年代,鄉民往往報以純樸的笑聲,完全一副既無從考起又何必自尋煩惱的神情。
地處黔北的鳳岡高腔茶燈,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吸收了川劇高腔中的“幫腔”。“幫腔”即由一人領唱眾人幫腔,有力地烘托表演氛圍。鳳岡高腔茶燈的幫腔還有自己的特點,不僅所有參演人員都可以幫腔,高潮之處觀眾往往也會幫腔,正是群眾性的幫腔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了鳳岡高腔茶燈相對廣泛的傳承。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當地很多村民并沒有系統地學習過鳳岡高腔茶燈,但因身處高腔茶燈的傳播環境中,也潛移默化地掌握了鳳岡高腔茶燈的很多唱法。
鳳岡高腔茶燈是采用鳳岡當地方言演唱的曲牌體音樂,唱腔變化多端,有“九板十三腔”之說。王德塤認為,“板”指戲曲板式,“腔”指有特性的唱腔。但“九板十三腔”只是當地通行的說法而已,“九”“十三”并非實數,鳳岡高腔茶燈一句話里不同的字均有不同的旋律和唱腔,從現有的板式和唱腔來看,早已超過了“九”“十三”之數。
鳳岡高腔茶燈運用的樂器組合也是當地特有的“鳳岡吹打”。“鳳岡吹打”兼有嗩吶主奏鑼鼓協奏與只打鑼鼓的兩種陣容。鳳岡高腔茶燈吸收了“鳳岡吹打”,卻并未采用“鳳岡吹打”擅長的嗩吶,其形式屬于高亢激越的鑼鼓隊。鳳岡高腔茶燈鑼鼓隊配樂節奏以唐二、幺妹的動作為主導,鑼鼓的起止、緊慢、高低必須忠實地追隨演員步法。鳳岡高腔茶燈的鑼鼓由馬鑼、銅鑼、鈸、鼓組成,馬鑼是鑼鼓隊的指揮,鑼鼓的起頭、間奏、收尾都要唯馬鑼的馬首是瞻。鑼和鈸則是主要樂器,常常相互呼應。鑼聲必須渾厚,擊后要馬上用手按住鑼面,不讓尾音發出。除連擊外,鑼聲要求響亮,但又要有戛然而止的控制力度。鈸手雙手要緊扣鈸中凸起部分,擊打時亦不能發出尾音。鼓則主要填充鑼鈸間空白,以控制節奏,整個表演呈現出立體感。
鳳岡高腔茶燈表演流程基本是生產生活的生動反映,主要流程為:開財門—送吉利—采茶—倒茶—販茶—推燈—上香—表根生—掃殿。每個環節都敘述了不同的故事,表達著當地人最質樸的生活祈望。這里謹以《上香》的唱詞為例: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鑼鼓仙師請放下,上香娘子到寶府。
一炷真香插燭臺,香煙緲緲下凡來。二炷明香插爐邊,香煙緲緲透腳青。三炷寶香歸天去,又有三條入海中。還有三條無去處,元宵會上受香煙。
還有閑香有插處,天地君親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南海岸上觀世音。還有閑香有插處,三元三品三觀神。還有閑香有插處,孔子先師受香煙。
還有閑香有插處,五谷先師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文武二魁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七曲文章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求財四官受香煙。
還有閑香有插處,求財四門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子童地君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東邊灶王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燈頭上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東邊青帝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南方赤帝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西方北帝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北方黑帝受香煙。
還有閑香有插處,中央皇帝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長生土地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蓋天古佛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官授插在大門前。還有閑香有插處,門神二將受香煙。還有閑香有插處,滴水郎君受香煙。
還有閑香有插處,元宵會上帶五瘟。上香娘子解滿愿,上香娘子要回程。
在《上香》唱詞中,將各路神仙幾乎都拜了一遍,祈求官運、財運、健康、豐收、升學等,生活中最樸實的愿望幾乎無一遺漏。鳳岡高腔茶燈傳承中,雖然許多內容和環節被改變,甚至有的已經消失,但上香等傳統儀式依然存留至今,應該與其生活訴求的表達密切相關。
鳳岡高腔茶燈的表演場所與當地流行的儺堂戲、陽戲完全一致,會在主人家的堂屋進行表演。學者王義先生在對茶燈儀式解讀上堅持“與儺堂戲、陽戲里的祭祀儀式相同”的觀點。筆者雖然可以認定三者所信奉的神靈不同,但也不能不承認茶燈與儺堂戲、陽戲在儀式流程上有相似之處。尤其是鳳岡高腔茶燈儀式類唱詞可以發現與遵義陽戲、遵義儺堂戲相近的痕跡。陽戲遵循請神—酬神—祈神—送神的表演流程,儺堂戲主要儀式是“過關”“沖壽儺”和“還愿”,前所述及鳳岡高腔茶燈儀式《開財門》亦有請神、祈福等環節,從唱詞“……珍珠瑪瑙兩邊排,開路先鋒到堂來。信奉神來信奉神,手提大刀到東方。……你把財門緊些把,莫放邪神入家庭。魯班釘門三尺三,白天開起夜晚關。白天開起招財進,夜晚關起閉邪神。開路先鋒參拜你,安安穩坐把財門”不難發現鳳岡高腔茶燈與遵義陽戲、儺堂戲表演流程的相似之處。傳統民間愿事活動中,陽戲、茶燈、儺戲經常同臺演出,大多數傳統藝人均會延長幾個劇種腔調。鳳岡高腔茶燈天然伴有儺文化的元素應該與此不無關系。
鳳岡高腔茶燈的傳承變化
地方文化部門對高腔花燈頗為重視,遵義花燈劇團的文藝工作者曾深入農村搜集資料創作歌舞。在世的鳳岡高腔茶燈傳承人萬友國、唐治元、唐友江,最大的已有70多歲。據他們回憶,自記事以來,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的茶燈從未斷過。“文革”時期,茶燈一度銷聲匿跡,不過之后又在城鄉生活中悄然興起。到了21世紀初,后繼乏人,鳳岡高腔茶燈面臨失傳的困境。茶燈隊不得不開始削減出場演員,演出效果難以避免地受到了影響。為了適應現代生活和演出需要,茶燈表演中的一些儀式性流程也被取消。隨著現代群眾審美和娛樂傾向的變化,鳳岡高腔茶燈唱詞內容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傳統高腔茶燈表演多是由一座村寨籌辦一支茶燈團隊,當然也有某個龐大家族獨力組織一支茶燈團隊的。“燈頭”是茶燈團隊的核心,負責整個團隊的組織管理運營,事無巨細均由他來調配。一場演出一般需要20個人,燈頭必須逐一物色唐二(丑角)、幺妹(旦角)、茶頭大仙,再配以12個花園姊妹和4個打擊樂器伴奏。目前鳳岡高腔茶燈表演人才凋落,一支團隊很難湊夠20人,只好減少了提花燈的人數。雖然12個花園姊妹可以視演出規模調整,但人數必須為偶數,主角唐二、幺妹和茶頭大仙絕對不能缺少。
傳統茶燈是男扮女裝,一般選擇“弱男童崽”“姣童”表演。新中國成立后依然延續了這一傳統,據當地60歲以上的群眾回憶,他們在13~15歲時就開始參與茶燈表演了。改革開放以來,鳳岡外出務工人員非常多,年輕人的娛樂審美現代化,鳳岡高腔茶燈演員漸漸趨于固定,年齡集中在50~70歲,大部分來自原來同一個生產隊。“幺妹”這一角色按傳統均由男性扮演,筆者在實地調查中也發現,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過女性扮演“幺妹”,年齡在12~17歲。目前鳳岡青少年女性大量外出求學務工,留守城鄉的越來越少,基本不再參與茶燈表演了。
傳統茶燈“出燈”一般是在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夜晚,如今鳳岡高腔茶燈表演不再局限于過年期間,“出燈”儀式也不一定選在晚上,重大節日活動或當地有需求時,都可以進行表演。傳統鳳岡高腔茶燈在“玩燈”始末要舉行“開光”和“化燈”儀式。“燈頭”選定演職人員后,組織大家“扎燈”,燈籠共6式12盞,每式2盞,也有只扎3式6盞的,同樣每式2盞,但一般會另扎一座“排燈”。出燈前的“開光”儀式一般在春節或春節第二天舉行,“燈頭”請“先生”“祭燈”,焚香燒紙以祈佑平安。“開光”儀式后茶燈團隊必須每晚都玩燈,茶燈忌隨便觸摸,演出結束后,“燈頭”負責守護燈籠。“化燈”儀式一般在正月十五或十六舉行,“燈頭”請“先生”到場書寫文書后火化,以示茶燈表演季圓滿結束。茶燈團隊“化燈”時要表演全套采茶歌,是整季茶燈最隆重的表演活動。茶燈團隊的“開光”“化燈”儀式不能隨便舉行,具體時間都要提前安排。但是現在由于經費問題和表演時間不定,“開光”和“化燈”儀式已經消失了。
鳳岡高腔茶燈傳統唱詞內容主要涉及祈福、愛情、歷史故事、敘事、教育五個方面。祈福類作品有《遇壽仙主家》《十大財門》《十二頌》等,愛情故事類有《一更里來跳粉墻》《小妹搖扇》等,歷史故事類有《盤燈》《說香》《十畫》等,敘事類作品有《五月花》《陽雀三更》《十二月采茶調》等,教育類有《猜字歌》《五重門說字》《五更勸君》等。貴州各路花燈在唱詞上大同小異,“唱燈之戲,遠鄉為最,情歌艷曲,曲盡形容,小家婦女隨惡少奔走者時有之”,鳳岡自然是“遠鄉”,茶燈唱詞內容喜好描述男女之事。如《一更里來跳粉墻》里年輕男女大膽追求愛情的橋段,《小妹搖扇》中“小妹出臺把扇搖,看燈君子把妹瞧”也反映了在看燈時節的男女交往行為。
目前,鳳岡高腔茶燈的唱詞基本以傳統的“采茶”“賣茶”“倒茶”“謝茶”和“團茶”為主,表達五谷豐登、團團圓圓、財源廣進等愿望,有時也有教育類主題的表演,青年男女夜訴衷腸類的愛情故事已經較少表演。為了迎合現實生活,在外出表演時,茶燈隊為適應活動主題也會新編或改編唱詞。雖然豐富了鳳岡高腔茶燈的唱詞內容,但據傳承人反映,改編唱詞后的茶燈表演效果并沒有達到觀眾的預期,甚至還有人認為改編后的鳳岡高腔茶燈失去了原有的味道。
結 語
源于民間質樸生活的鳳岡高腔茶燈曾是當地看燈玩燈的傳統年俗,存留至今的文化面貌雖然距離傳統藝術特點有較大差別,但這一娛樂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依然活躍,仍是在用當地最熟悉的方言和熱烈愉悅的氛圍表達人們最純樸的生活愿望。鳳岡高腔茶燈已被列為遵義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深切感受到,傳承人的零落與唱詞文字記錄稀疏是目前最嚴峻的問題。鳳岡高腔茶燈研究雖然受限于資料,但其當下及將來的生存狀態調查仍有待繼續。如田野調查中涌現出的女性曾參與表演及其受到村民支持的材料打破了傳統文獻沒有女性表演者的認知。同時筆者亦不無遺憾地認識到,鳳岡高腔茶燈調查與研究目前過多依靠口述,時間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只好選擇沙壩村作為典型調查,調查數據及意義自然有限。田野調查應該更廣泛地應用于非遺保護研究工作中,不僅在調查范圍與規模上有待深入,調查方法上亦應多元化。